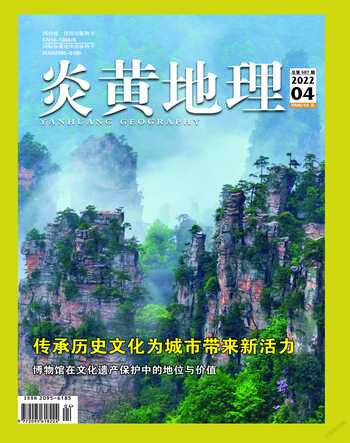民间传说“刘海戏金蟾”的由来
谢丽丽






“刘海戏金蟾”是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从宋元时期至清代,其图像中刘海其人、刘海形象以及刘海与蟾的组合均发生了演变。可以从中发现在明代中期出现了转折点,此类文物的类型、图像等都有了明显的扩展,“刘海戏金蟾”的寓意是财源兴旺、幸福美好,对宗教学、社会学,文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劉海戏金蟾”题材文物几例
“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形成很早,至迟在北宋时期。北宋李石所著《续博物志》中就有记载。词人柳永少年时作《巫山一段云》第三首“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相将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可以看出当时“刘海戏金蟾”已经非常流行。但宋代的关于刘海的可靠实物未见,无法了解宋代对刘海形象的塑造。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颜辉所绘《蛤蟆仙人图》(图1)可以说是目前确定的关于“刘海戏金蟾”的最早实物。
画中刘海为一中年形象,体态清瘦,衣着随意,赤脚、蓬头,面容沧桑。眼角朝下、眼珠上翻,大圆鼻头,嘴轻敛,少须,下巴微上翘。右肩负一硕大的白色三足蟾蜍,右手上扬,左手持一带枝的桃。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社会上层对刘海的认识反映在实物上有如下几个特点:刘海为一散仙形象,无拘无束,超凡脱俗。金蟾体型硕大,比自然生长的蟾蜍要大的多,且为白色,也已神话。刘海一手持有带半截枝叶的桃子。至于民间流传刘海是一种什么形象暂时没有可靠的实物依据。元代的刘海被元世祖封为“明悟弘道真君”,其在官方还是民间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因此统治阶级和民间对于刘海形象的塑造相对严肃保守,世俗化的程度不是很高,与普通人有很强的距离感。
到了明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刘海的形象更趋向于世俗化、多样化,更加生动起来。明代宫廷画家刘俊所绘《刘海戏蟾图》(图2),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刘海被塑造成一青年形象,宽袍大褂,立于万顷波涛之上,一副得道成仙的模样。头发蓬松,中分,面庞圆润,微笑,憨态可掬。双手捧白色三足蟾蜍,右肩挂一小葫芦。天水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铜“刘海戏金蟾”造像香熏(图3)。造像由刘海和金蟾两部分组成。刘海面相憨圆,面带微笑,两耳宽大,长发披肩,着有发箍。身着长衫,左下摆外飘,束腰打结。身背葫芦,跣足。双臂微曲,似握钱串,作耍钱状。左腿足下有圆形托板扣于金蟾背部圆孔中。金蟾体量巨大,三足粗壮有力,昂首上观,阔口隆鼻,暴突眼,浑身凸起酥瘤。腹中空,嘴角成两孔。身上无酥瘤处刻有小圆圈纹,嘴角刻须。高41.5厘米、重12公斤。
明代“刘海戏金蟾”题材的文物主要是绘画,“刘海戏金蟾”已经是画家笔下重要的人物故事之一;造像可细分为具有招财、驱邪等民俗功用的摆件和具有实用、观赏等功能的实用器两类;装饰品,一般体积较小,方便佩戴,质地有多种。
清代关于“刘海戏金蟾”题材的实物种类更加丰富,包括铜、木、玉石等各种质地。从目前可知的有明确年代的文物和艺术品来看,绝大多数来自民间,很难判断官方所造与民间工艺在造型组合及人物特征上有何明显不同。甘谷县博物馆藏有几件清代“刘海戏金蟾”造像(图4)。刘海为一孩童形象,笑容可掬,袒胸露腹,右足独立于金蟾之上。两手上举,执一串金钱,金钱之上连接一枝花叶。金蟾为座,可与刘海拆分。另有两件同样器物,不完整。天水市博物馆、青州博物馆等亦藏有同样造像。
刘海其人
关于刘海的原型,多数研究者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五代后梁时期的刘玄英。目前所知最早记载见于明代嘉靖时期的《陕西通志》、万历年间刊刻的《湖广总志》和《列仙全传》。《陕西通志》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马理等人编纂的地方志书。《湖广总志》是明代徐学谟等纂,万历十九年(1591)刊印,清代康熙和雍正年间都有新刻本。《列仙全传》传为王世贞编辑,李攀龙作序,汪云鹏书。《陕西通志》载:“刘海名哲,字元英,号海蟾子。相燕王刘守光,好黄老之学,后弃官。从正阳子(汉钟离)隐修于终南山成仙去。”《湖广总志》和《列仙全传》记载:“刘玄英,燕地广陵人,号海蟾子,初名操。后得道改称焉明……”从记载内容来看,《陕西通志》要概括简洁一些,应是总结其他文献的记载,而《列仙全传》记载内容较为详细,且明代版本留存至今。因此笔者认为后两本书记载可信度更高一些。至于刘元英之说,可能为清代康熙年间重刻时为了避讳玄烨之“玄”字,玄英改为元英。刘海则是后来的俗称。
组合特点
元代初期官方认同的组合是人物刘海、金蟾和带枝的桃子,没有出现金钱,以颜辉《蛤蟆仙人图》为证。应是延续了宋代以来官方风格;明代戏曲家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中载“海蟾子,哆口蓬发,一蟾玉色者戏踞其顶。手执一桃,连花叶,鲜活如生”,可以看出,至迟在李日华生活的正德、嘉靖时期,文人认可的依然是元初颜辉《蛤蟆仙人图》中的形象。由此推断,在明代中期以后刘海形象以及自合特点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文章所列举的明代标本其年代基本属于明代中晚期,与元代相比出现明显变化。刘海手中的桃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手拿颗圆珠,或是金钱。金钱形式有两手执一串钱,或是一只手拿一枚铜钱等方式,双手执一串钱的形象较为多见。拿一枚铜钱期意义可能偏重于戏金蟾,而拿一串钱的意义也许在于“散钱”,两种组合特点传达的信息是不太一样的。有的肩上挂一葫芦。清代以后组合基本固定,刘海、金钱和金蟾三者共存。
人物特点的演变
此类人物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宋至元早期,此时刘海的形象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是依据的历史事实,据相关资料记载,刘玄英弃官后修道时已经在五十多岁。到了明代时形象为青年,典型作品就是刘俊的刘海图。青年形象的创作来源于民间流传的刘海的爱情故事,因为浪漫的爱情故事在古代只会发生在青年身上,可以推测“刘海砍樵”的爱情故事也是在明代产生的,明代中刘海的形象出现的比较多,以少年和顽童居多,刘海的孩童形象可能是受到佛教中“善财童子”的启示,笔者亦认为此说法很有道理。佛教中的善财童子有很多珍奇财宝,但他视为粪土,潜心修行,终成菩萨。这与刘玄英经历相似,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也合情合理;清初文学家褚人获的《坚瓠集》中记“今画蓬头跣足嘻笑之人,持三足蟾升之,曰此刘海戏蟾图也,直以刘海为名,举世无知其名者。”此描述代表了清代初期人们对刘海形象的一种认知。典型代表便是康熙时期吴之璠作笔筒上的刘海形象(图5)。甘谷县博物馆藏“刘海戏金蟾”造像属清代中期(图5),刘海是一个孩童形象。刘海戏蟾泥人(图6)属清代晚期,刘海是一个青年形象。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刘海的多种形象共存。艺人们根据各种传说和自己的理解,充分发挥了创作能动性,对之后刘海戏金蟾这个题材的丰富多彩奠定了基础。
金蟾的形象及功能
金蟾是“刘海戏金蟾”题材的故事核心之一。表现在实物上,不同的文物或艺术品有其不同的形象和功能。由前文可知,最早的金蟾是元代颜辉《蛤蟆仙人图》中的一只硕大白色蟾蜍,角色是刘海的一只宠物,同时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体形上看显然不是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的。明代的几件文物中金蟾有了不同的功能,多为“刘海戏金蟾”造型的组成部分,体形小,没有突出表现,如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中的金蟾,被刘海捧在手中,小巧可爱。而天水市博物馆藏明代铜“刘海戏金蟾”造像香熏主体为蟾,刘海则为一种附属装饰,造型大胆,是一件美观又实用的文物精品;清代“刘海戏金蟾”造像中,金蟾模铸成一半,作为造像的座,并能拆分下来,大小没有按照比例来做,因此在文物本体中偏重于实用功能。总之,金蟾形象在不同的文物中有不同的表现,与创作者的初衷和文物的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海戏金蟾”的民俗文化寓意
关于文化寓意和民俗功用有学者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概括起来,早期多作为一种富贵、长寿、驱魔镇宅、济世等的象征,后来主要是作为一种招财的瑞兆。
“刘海戏金蟾”题材文物的发展了近千年,由早期的数量较小、种类单一到今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当今民间对于此一题材的创造是令人眼花缭乱,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色,也很难总结出一个发展规律。明代中期可以说是此类文物发展的转折点,不管是文物的类型、图像的组合、用途还是民间寓意都有了明显的扩展。经过了清代、民国的发展到现在,此类题材的艺术品或工艺品基本上集中反映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尤其体现了商业信仰风俗中招财进宝和财源广进的观念与愿望。与早期所要传达的不为利禄、散财济贫等价值理念完全不同了。对这一题材文物深入的认识,在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甘谷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