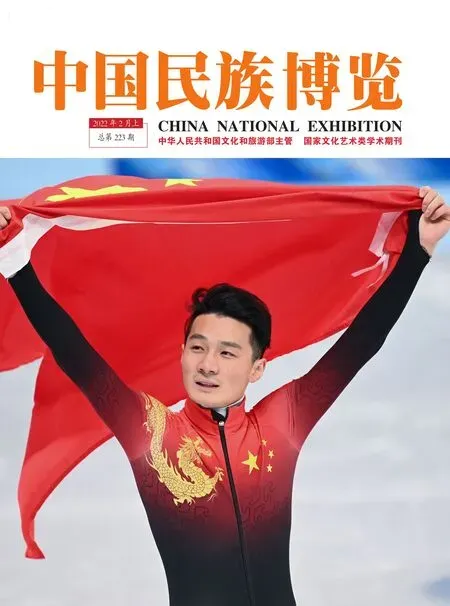试论青铜大立人像手势所象征的文化内涵
【摘要】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座大型商代晚期祭祀坑的发现以及蔚为大观的青铜雕像群的横空出世,不仅反映出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为我们探索古蜀国的社会文明形态、宗教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大立人像为研究对象,试论大立人像手势与《山海经》所载众巫“操蛇”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有祭祀先祖大禹的同时,兼顾“以祖配天”之意。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蛇;操蛇之神;夏禹;昆仑;以祖配天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3-202-03
【本文著录格式】唐敏 .试论青铜大立人像手势所象征的文化内涵[J].中国民族博览,2022,02(03):202-204.
一、大立人像为神、巫、王三者于一体的“群巫之长”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特别是以青铜大立人像等一批具有本地鲜明风格青铜器的横空出世,填补了古代中国青铜文化衍变序列的重要缺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二号坑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当中,有一件被誉为“东方巨人”的青铜大立人像。这件大立人像由人像和底座两部分构成,采用“分段嵌铸法”铸造而成。身体中空,通高2.62米,其中人像高1.72米,底座高0.9米,重达180公斤,是迄今发现的殷商时代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立人像头戴天目冠,身穿绘有龙纹的长袍,两手抱握置于胸前,竖立于高台之上,庄严肃穆。关于此青铜立人像的身份表征,赵殿增先生认为,立人像站于 高 台、身披 法衣、头 戴 华 冠 、神 兽 护 体 等 方面 的特征,显 示其 在 祭 祀活动 中居于 中心 地位。[1]如果再结合二号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情况来看,这些器物是被砸碎、火烧之后,再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扔进坑内。与铜立人像埋藏在一起的还有诸如青铜大神树、青铜太阳轮形器、青铜纵目面具等一批国之重器。这批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器不仅体量硕大,而且铸造工艺精湛,应当是古蜀国最高祭礼仪式中使用的重要道具。如果从铸造工艺、艺术造型及蕴藏的文化内涵等角度对立人像进行综合考察,无不呈现出古蜀人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及创造力,这尊人像应当是古蜀人原始宗教崇拜下的精神偶像。笔者认为此人物雕像应当为古蜀国重要祭祀活动中“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之象征,是名副其实的“群巫之长”。
二、“群巫之长”大立人像双手“操蛇”寓意“以祖配天”
立人像所站高台有座基、座腿、座台面三部分组成。座基成梯形,座腿为四个相连接的怪兽头;座台面为方形,四周纹样装饰以日晕纹为主。立人像所站立的高台整体成方形,很有可能与《周礼·大司乐》所载的“于泽中之方丘”应当有着某些内在联系。贾《梳》曰:“言泽中方丘者,……因下以事地,故于泽中。……不可以水中设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另根据《尔雅·释丘》载:“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此说可看作山有三重即有“昆仑”之意象。在古籍神话中,“昆仑”这个词往往与通天有关,而且其方位在西北。《淮南子·原道训》:“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高诱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2013年,三星堆遗址北面的青关山台地一号建筑基址被发掘。杜金鹏先生认为此建筑基址属于商代最高规格的建筑……该建筑是一座纵轴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做长方形的大型地面建筑。”[2]青关山台地宫殿朝向为西北方位,此方位正是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一带。现阶段的考古表明,整个遗址区内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两大区域,一个是南城墙附近的“三星堆”(三个人工夯土堆)与祭祀坑组成的祭祀区,另一个是北面月亮湾台地所属区域。而这一南一北两大区域正是清代嘉庆《汉州志》所描述的“伴月三星堆”。吴维羲先生根据两坑坑向、叠璧拟峰、碎璋之礼等诸多因素分析认为,两坑祭礼中有较大的祭山成分,并进一步指出两坑“瘗埋”所祭之山即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3] 陈显丹先生指出,掩埋大立人的二号坑,根据出土的堆积迭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大的青铜人像由腰部折断成两段,人像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4]综上所述,无论是祭祀坑的朝向还是大立人底座掩埋在坑内的方位都与经文中所描述的神山昆仑所在的西北方位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另依此理从整体造型来看此方台,与《周礼》所载的祭祀所用方丘吻合。虽《周礼》为后世所著,但夏、商、周三代之礼必有共通之处,可做参考。正如《论语·为政》所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前,笔者拙文中已明确提出方台由座基、座腿、座台面三层组合之造型寓意《尔雅》所载“昆仑丘。”[5]毕竟,此大立人像为古蜀国的“群巫之长”,立于神山“昆仑”,祭祀通天非他莫属。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方丘”,座基为方形,素面无纹饰,取象地;座台面虽为方形,但上面装饰有明显的日晕纹,古之制器者应当是为了区分座基的方形而刻意为之。日在天上,所以可取象天。中间的座腿为组合型的怪兽造型。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怪兽有向上扬起的兽角,身体象蛇形(小龙为蛇),而怪兽的头部明显是鸟形的艺术抽象化表达,眼睛硕大且修长,炯炯有神。复合形态的怪兽造型居于座基、座台面的中间,或许是为了寓意此怪兽可在天地间自由往返穿梭。根据其主体造型有鸟、蛇兼容的复合型特征,可暂且称此怪兽为“飞蛇”一类的精灵之物。被称为华夏第一奇书的《山海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神巫形象当中都有龙、蛇的身影,尤以《山海经·海外经》所载较为详细。
《海外经》记载的与龙、蛇有关的四方神——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為《海外经》所述的与龙、蛇相关的四方神实乃甲骨卜辞当中的四风之神,这就客观证明了《山海经》对事物的描述并非荒诞不经,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神话叙事手法。除了《海外经》所载四方神与龙、蛇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之外,在《山海经》其他篇章中所描述的大巫或人王也与龙、蛇产生了联系。例如《大荒北经》所载:“……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日夸父。” 《大荒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山海经》当中描述的“天下之中”的地域尤其详记岷江中、上游,这一地域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6] 笔者认为蒙先生的观点颇具说服力,《山海经》当属于南方文化系统。那么经文当中出现的人、神、巫与龙、蛇组合的奇异描述很有可能是对上古西南地区,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域祭祀活动中所呈现的神巫元素的隐晦表达。
晋代道士葛洪所著《抱朴子·杂应》:“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龙蹻,二日虎蹻,三日鹿卢蹻”。前文已述怪兽有蛇形身体,而传统文化中一般称“小龙为蛇”。综上所述,此“飞蛇”应当是巫觋祭祀通天的动物助手,即“蹻”。大立人所站立的方台中间部位取象“飞蛇”之造型,或许正是为了凸显此方台整体寓意神山昆仑有着独一无二的“登天之梯”的功能。大立人光脚站立于昆仑之巅,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便能更好地“天人感应”“人神互通”。
大立人像最吸引人之处应为那双巨大的双手。双手中空,一高一低呈抱握状放置于胸前。从肉眼不难发现,此巨手与整个人像的其他身体比例极不协调。这样的设计,或许是制器者为了凸显这双巨手在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三星堆出土器物所呈现的神圣、神奇、神秘之特征,笔者倾向于认为大立人像这双呈抱握状的巨大双手应该有着多方面的宗教文化内涵,如果单从立人像手里是握着某种祭祀法器的角度来考察;再结合与上古西南地区有着极大渊源的《山海经》的记载,大立人像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应为古蜀国当之无愧的“操蛇之神”。而蜀人的源头与成都平原西北方位的岷山一带有着紧密的联系,岷山一带的茂汶地区被视为夏朝先祖大禹的发源地。《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淮南子·汜论训》:“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史记·夏本纪》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
扬雄《蜀王本记》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王家祐先生指出:“盖羌族之宗教,亦即中国西部夏民族最古之宗教也……在祖国黄河折支河曲附近的昆仑神山所发源的黄帝轩辕氏文化,经过崇禹(夏部落)的扩播,形成了西南民族的原始文化。[7]
《礼记·祭法》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大禹治水有功,成为了上古各部族的祭祀对象。 结合“禹兴于西羌”这一史料线索,三星堆祭祀的先祖对象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在古蜀先民心目中有着极大功劳的来自西羌的大禹。 《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汶读若岷,即岷山。《元和郡县志》茂州:“汶山即岷山也。”由此可知,汶山(岷山)为古蜀人心目中的天彭阙,蜀地自古以来有魂归天门之说。,而“天门”所在的位置正好与大禹出西羌的地理位置相对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古蜀人“魂归天门”不仅有通天之寓意,同时还隐藏着对先祖大禹祭祀这一重要线索。其实,古文中的禹字也或多或少地透露着一些蛛丝马迹。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有对“禹”字的解读:“虫也。……象形,古文禹。”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与三星堆遗址有着较大联系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两者有许多共通的文化因素,例如在两地都有出土陶盉,而学界多认为两地出土的陶盉在考古文化序列分期当中有着明显的层次递进演变关系。除了陶盉以外,较为明显的夏文化元素的器物当属两地出土的青铜牌饰。何驽先生结合对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绿松石龙牌和铜牌饰分析研究认为,金文禹的形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虫;另一个是臂……当祭祀者手持或高举绿松石龙牌祭祀,龙牌就不仅仅是虫、蛇,而是禹的化身。[8]再进一步说,金文中的禹可以理解为人手持蛇之象形,而作为与夏部族有着很深文化渊源的古蜀国的“群巫之长”—大立人像,其双手“操蛇”这一动作姿势的深层内涵或许正是为了体现将先祖大禹拥入怀中进行祭祀。由于大禹治水的功劳与天齐高,在双手操蛇象征祭祀大禹的过程中便自然而然的与世间万物的主宰—“天”产生了某种联系,这就是古蜀人“魂归天门”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而双手持蛇祭祖的行为进而引申到祭天,其祭祀文化内涵同时也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转换,最终形成“敬天法祖”的古蜀国最高规格祭祀。萧兵先生认为,“操蛇还有控制自然力、保证蕃育力,包括土地和群团繁盛的作用,这等于掌握了国运或命脉……夏启的珥蛇……象征天与神授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象征交通天人的灵力,象征对自然力与社群的有效控制。”[9]
三、结语
众所周知,龙是作为夏文化部族的主要图腾崇拜之象征。从三星堆两坑出土的器物来看,夏文化因素表现得尤为明显。遗址内不仅有独立的青铜龙、蛇之类的器物(例如长有山羊胡须和羊角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体型硕大的、器身满是菱形纹图案的青铜蛇),还有一些巨型青铜器物上有明显的龙蛇一类的造型和图纹;例如高达3米95的青铜一号神树侧面有一青铜巨龙头朝下、尾朝上,刀状羽翼下垂,整个身子倒挂在树干上,仿佛从天而降;这条神龙可谓是青铜一号神树最重要的构件之一……青铜大立人所穿服饰上清晰可见龙衮图纹)。大立人像的两手一高一低呈抱握状这一动作,或许正是为了突出将灵蛇这一祭祀所用的重要法器拥入怀中。此时此刻,手握灵蛇这一姿势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龙、蛇象征,而是转换为大禹的化身,与此同时大立人像也完成了从人到巫再到神的升华和轉换,俨然已经成为了古蜀国名副其实的“群巫之长”“操蛇之神。”综上所述,我们不妨把此立人像双手操蛇的特定文化寓意释读为:“敬天法祖”“以祖配天。”
参考文献:
[1]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A].三星堆与巴蜀文化[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J]. 四川文物,2020(5).
[3]吴维羲.试论古蜀人的神性思想与中央意识[J]. 四川文物,2002(1).
[4]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J]. 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1989(S1).
[5]唐敏 ,李翊枭.三星堆之眼[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
[6]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7]王家祐.道教论稿[M]. 成都:巴蜀书社,1987.
[8]何驽. 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J]. 中原文化研究,2018(4).
[9]萧兵.《操蛇或饰蛇》:神性与权力的象征[J]. 民族艺术,2002(3).
作者简介:唐敏(1983-),男,四川金堂人大专(目前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在读),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古蜀文化、先秦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