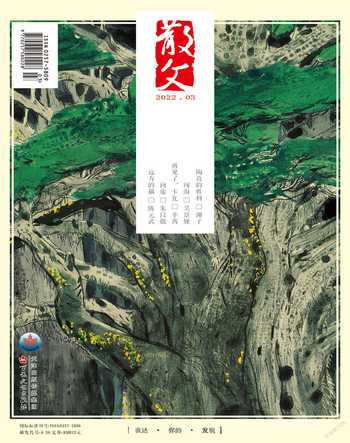祖先的树
彭家河
树有子孙吗?是谁?
老家瓦房周围有四棵巨大的柏树,是小时候村里安电时砍剩的。春节回家,发现每棵树都钉着县上统一制发的全省古树名木登记牌,有编号、科属、树龄、类别、保护等级、简介等信息,还有个二维码。我特地扫了一下码,原以为是一树一码记载了一棵树的前世今生,结果只看到对柏木的简介。这四棵树的编号前六位数字与我身份证号码上的一样,说明我与这几棵树的亲近关系已如铁板钉钉,这让我扫码后的失望有所缓解。从登记牌上看,这四棵树只有编号和数龄不同,仅凭这两点就想区分或者认清一棵树,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之前一直在猜测这些树生长的年辰,还用“树围测龄法”推断过,但从没得到过确认。登记牌标注这四棵树分别生长了五百年、两百年、两百年、一百年,是明朝正德、清朝道光和民國初年间栽植的。显然,这几棵前后相隔数百年的树站在一起,其间有漫长的时间空当需要人间烟火来填充。更何况,登记牌标注的树龄与我推断的极不一致,要还原当年栽树的场景,或者描绘每一棵树下曾经的红尘往事,绝非易事。如果树木有记录功能并能让人类提取,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发明,世间的许多未解之谜都会真相大白。只是人类尚未掌握如此技术,还没有能力解读一棵树。
我用卷尺在树干离地一点三米处测量这几棵树,树围分别是二点五四米、一点五六米、一点五二米、一点五米。“树围测龄法”是按树围每年增长二点五厘米至三厘米来计算的,一棵一百年的树一般就有三米粗。但我对这个算法持怀疑态度,对一棵树一年长粗三厘米也表示怀疑。这几个登记牌显然禁不起“树围测龄法”的检验。后来才知道,为了保护这几棵大柏树,村民们向上级层层申报,能给树编号领证都非常不易了,对树的具体年龄,谁也没有格外在意。我后来查找资料,发现一句:
古树年龄的估测,在国内没有统一的规范,随意性较强,不同的调查者,对同一棵古树年龄估测会相差几百年。
至此,我对寻求这几棵大树准确年龄的想法才彻底放弃。不但大柏树的年龄难以确定,对它们的高度也没有简单的办法进行测量。庞大的树冠舒展在空中,凝成一团翠绿的云覆盖在房顶上。如果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在自留地和房屋间根本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参照物。用无人机或许可以想想办法,我却没有这些设备。我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爬上屋后的山坪找到与树冠持平的位置看一下高度计,然后再到树根处看一下高度计,就可以算出树高。手机上是有这个APP的,我却没想起,只凭肉眼估计。这些树估计有十五层楼高,也不过五十米左右。想起时常使用的“参天大树”“树高千尺”这些词语,不禁心头一震,我们的思维与感受是多么粗糙甚至草率,或者说我们时常忘记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切换,一个是文学的语言体系,一个是科学的语言体系,而我们的生活因之而含混不明。
“立起的女人倒下的树”,农村人对长度单位没有精准要求,都是通过此物与彼物进行对比来描述。我家院坝前有棵杜仲,是我小时候父亲栽的,当年只有我的拇指粗,四十多年后,不过茶杯那么粗。再过个四十年,我估计也只有碗口那么粗,树高绝不会达到三米。由此,我再次断定,那四棵大柏树的年龄肯定比“树围测龄法”得出的树龄更大。这四棵树,我既不知道它们的年龄,也不能确定它们的高度。它们在我眼前生长了四十多年,我并没发现它们有多少变化。就连在身边和头上朝夕相处的树,我们对它都如此陌生,想想小学时背诵的“要上天入地下海,探寻宇宙的秘密”,的确是真正的任重道远。譬如说对面山腰老坟林灌木丛中年代久远的祖坟和柏树下坟台子上几个我还见过的爷爷奶奶的坟茔,长眠其中的祖先和长辈,虽然我身上有着和他们一样的骨血,可哪里能一眼分辨得出其中的细微同殊,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呢?除了知道他们就长眠在附近,我们其实已形同陌路。
从这四棵树的粗细来看,它们肯定不是兄弟,至少是祖孙或者隔得更远的辈分。村民们不会想到这几棵柏树有辈分的差距,不会想到,树围粗一点细一点,年份的差距可能就是几百年。村里有人胖有人瘦,但只要是同辈的,全都直呼小名,辈分高一辈的全叫“爸”,高两辈的全叫“爷”,即使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人,也全要按辈分来称呼。村民们没给这四棵树取名,估计是因为它们的树皮看上去都一样苍老斑驳,枝叶都一样伸展覆盖在半空,看上去如同一个辈分的族人。村民就都叫它们大柏树,有时为了表述准确一些,就说屋后那棵、路边那棵、坟台子下那棵或者碾子边砍掉的那棵。这些大柏树一站就是上百年,不走动半步,直至站成一处地标一处风景。每棵树在空中也相互谦让,你的枝叶伸过来了,我的枝叶就让个道,你枝上的雨水洒到我身下,我也同样礼尚往来,风霜雨雪、酷暑烈日一起担当。就这样,这四棵树彼此心领神会,护佑着树下的院落和人家,一代又一代,几百年就这么过来了,并且还会又一个几百年地继续下去。百年树木,恰是风华正茂。
村里的人都在这几棵大柏树下走过路乘过凉躲过雨抽过烟,当然也吵过嘴打过架撒过泼,但都没有更多需要细细分辨指认每一棵树的时候。唯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安电,要砍树变卖成钱买电杆电线时,三棵与这棵标注五百年的差不多粗细的柏树便从此只生长在为数不多的村民的记忆中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砍树的人差不多都去世了,连我们这些当年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也人到中年,我知道,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那几棵树倒下后是个什么样子了。当初是村民砍伐树木,后来是岁月砍伐村民。如今面对长满蔬菜的自留地,再提起那几棵当仁不让的柏树,还有几人能说清这些往事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呢?当年鸡鸣狗叫的村庄如今已不复人烟,又有谁来证实当年的村民曾经在这个世上是如此生动地存在过呢?村口宗族碑上刻写着一个个祖辈的名字,整个宗族繁衍生息的脉络一目了然,谁是谁家的香火,谁是谁家的根脉,都可以一望而知。但这一排高大雄健的柏树矗在跟前,哪一棵是哪一棵的母亲?哪一棵是哪一棵的兄弟或者子孙?这么简单的疑问,想不到百年过后竟然成为难解之谜。或许,这些问题只是没有人在意,但是,没人在意的问题,是否就真的没有意义?
多年没有回老家,由于疫情,又两年不能回家。终于在牛年春节前回村,见到陌生的男女老少,父母就一一给我介绍,他们是谁的孙子谁的媳妇,我还要回忆辨别好久,寻找他们与记忆中某个族人的相似之处。如同瓦屋后的竹木,我知道,他们就是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伙伴的长辈或者晚辈,但也没有捕捉到多少能够准确辨识的细节。
屋外的四棵大柏树繁茂的枝叶在空中连成一片,在遮风挡雨的同时也遮蔽阳光,树下一年四季干燥阴暗。我也曾担心,这么高大粗壮的柏树,每年有那么多的柏果成熟掉落,如果它们都发芽生长成树林,咋挤得下?但数百年来,树下几乎都没有灌木和小草生长,只有几丛父亲早年移栽的慈竹顾自生长,几十年来砍了又发,发了又砍,还是坚守着自己地盘,没有扩张也没有收缩。竹叶铺了一层又一层,柏果落了一次又一次,但这几棵柏树,一直没有看到它们繁衍生息,只看到它们各自沉默的生长或者生存。
这余下的四棵大柏树,或许是我不能确知的祖上栽植的。我找到我们宗族的族谱,上面也只简单地记载着一代代的传承关系,他们中的哪一位生于何年、卒于何年、经历过多少故事、曾经的音容笑貌一例全无记载。我知道,唯有这几棵柏树,它们见过族谱上的每一个人,听过他们每一个人说的话,也明白每一个人在村里经历过的事。可是,大柏树心中藏着的故事,又有谁能够读得明白呢?几百年风云变幻,几百年世事沧桑,大树都亲历过,都见证过,谁又能让大柏树给我们讲述出来呢?
那些祖辈中,我似乎还依稀记得几位堂祖的相貌,却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今年已九十七岁了,皮肤也如那些柏树,沟壑纵横,但她耳聪目明,逢人仍有说不完的话。我没有让奶奶去指认她栽种的树,她也无意说给我们听。如果那棵最小的柏树真是一百年的话,奶奶一定知道那棵树的故事,但奶奶说,那棵树她嫁进村来就差不多那么粗了。
这四棵大柏树到底是哪年哪一辈祖先栽下的,估计永远也无法查询到了。大树树皮剥落,根部蛀虫钻噬,早年由于人为损伤,一溜光滑的木质裸露在外,如同白森森的骨头,那些早年砍断枝丫的创口、铁丝捆绑过的深渠、深深浅浅的刀痕,都长成了疤瘤。纵然伤痕累累,它依旧巍然挺立,仿佛坚不可摧。我们都明白,它们一定是我们的祖上亲手栽下的,这些树仿佛就是植树人永远的管家,一直在代我们的祖上照看我们,我们才是这些树的子孙后代。村口的宗族记事碑上,村里同宗几代人的名字也就仅限于几个汉字,他们其余的一切我们毫无所知,只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不易分辨的血脉呼应祖先的遗传。前不见古人,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古人栽植的树,这是古人留下的信物。
数百年来,这些柏树几乎没有改变,而植树人的后代经过了一辈又一辈,百年沧桑,世事变迁,只有这些柏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寂静的夜晚,那些树梢的声音,或许就是树与树在复述祖先们的话语,是树与树在闲坐讲述某一位祖宗的故事。祖先们的肉身都回到了土地,而他们的灵魂或许都住在树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听见的,就是他们的话。即便我们疲惫得没有精力去细听,他们也会轻轻抚慰一个个回乡的孩子酣然入梦。
在乡下瓦屋里睡觉,床脚就压着土地,安稳踏实。一觉醒来,屋后的鸡鸭鹅早就闹开了。鸡鸭的叫声很熟悉,我们大人小孩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鹅的叫声让我特别意外,竟然是“关关”声!这是《诗经》就已记载下的声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到底是一种什么水鸟,众说纷纭。但我躺在床上听到屋后的鹅叫声,顿时体会到了《诗经》中的叫声。“关!关!关关!”《诗》始于《关雎》,在典籍中流传数千年的关雎之声,终于在此刻变得如此真切生动。想必,西周的那些古人,也是在这样的晨晨昏昏品味雎鸠关关以及其他。
春节后离开村子回城,车在山路上开了很久才爬上对面的山坡,在山顶上停车回望,父母的身影已经不见,那几棵柏树還挺直着身子一动不动,那团浓郁翠绿如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一直在瓦屋后目送。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