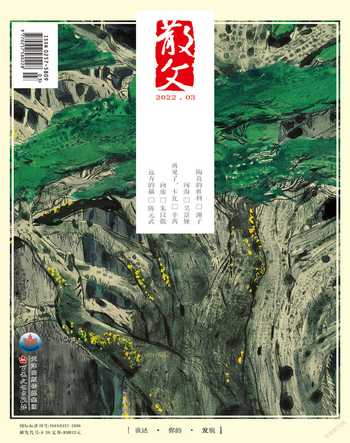命运符咒
茨平
在宋城某纸厂打工时,认识了一位湖南妹子,叫秦小蓉,在厂里做清洁工。
她应聘的本不是清洁工。填好应聘表,校验身份证毕业证时,人事胖脸姑娘把她的毕业证扔了回来:你这个是假的。她一下子慌了,很是夸张地说:怎么可能?初中毕业证怎么会有假的?又不是大学的,这是校长亲手发给我的。胖脸姑娘笑笑,说:那我考考你。她在纸上写下@b≌,说:你说这是什么?一下子把她难住了。她想起老家道士画的符,跟这很相像,便说:这是一道符。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围观的人们哄然大笑。
秦小蓉的毕业证是假的。她只读了小学四年级。毕业证是十七岁那年在东莞从假证贩子那儿花二百元买的。没办法,没有毕业证进不了工厂。假毕业证帮她敲开了很多工厂的大门。有次她跟我说,那么多地方都没事,怎么在这儿就露馅呢?我说,哦,哦。她说:王师傅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事没法讲,只能用“命运”两字来讲。她向我要了纸笔,认认真真地画上@b≌,问:你知道这是什么鬼字吗?我怕到别的地方又拿这鬼字来考我。我也是初中未毕业,这东西也不认得,只好摇了摇头。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她很不甘心,跟在胖脸姑娘身后不停地说:求领导高抬一下贵手哈,求领导高抬一下贵手哈。胖脸姑娘说:做清洁工不?厂里还少一个清洁工。她点了点头说行。后来她跟我说:其实扫地比进车间好,车间管得死死的,扫地自由一点,就是钱太少了。
一次我从她身边走过,掏烟时钱包掉了出来。她在后面喊:师傅,你钱包掉了。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她也是我老婆的好姐妹。有次老婆洗会议室的茶杯,不小心摔坏一只。管后勤的拉长脸骂。老婆差点哭了。秦小蓉走过去说:有你这样骂人的吗?要老天保佑你一辈子高高在上。老婆说她讲义气。她时常跑到我家蹭饭吃。星期天或夜间,时有几个工友来我家里打麻将。有角色,她坐在一旁做看客,没角色就顶角色,有时会看到散场,就在我家里睡。她说,王师傅你睡地铺哈,今晚我要跟姐姐谈恋爱。
她是湖南省耒阳县人。很小她就知道,长大了要有出息只能靠读书。可她父母不让。她上有哥哥下有弟弟,父母重男轻女。她记得很清楚,九月开学时,哥哥弟弟从父亲手中拿了学费走了。她走过去,看着自己的脚趾说:爸。父亲说:别念了,家里负担不起。她再喊一句:爸。母亲大吼一声:还不赶紧去打猪食草。她扭头抓起书包就往学校跑。母亲从后面追上来,揪住她往回拖,把马路拖出两条痕线,竹鞭子噼里啪啦抽过来。十七岁时她出来打工,母亲送她去镇上坐班车。在山路上走着走着,母亲突然停下来了。她回头,见母亲坐在那儿呜呜地哭。她说:我一下子心软了,从此原谅了她。
在外面,她有一位好姐姐叫宋艳,在绿皮火车上相识的。她们相对而坐,说起同是耒阳人,一下子亲热起来。假畢业证是宋艳帮她买的。初始,她和宋艳进了一家电子厂。那厂好大,打个来回要半个小时。走进车间时她惊呆了。车间犹如一个巨大的水族馆,灯光雪亮,一条一条流水线循序摆开。每条传送带前都坐着一列工装女孩。女孩都皮肤白,像鱼肚皮一样白,凑近了能看到脸上微细的浅蓝的血管。车间里很安静,一下子把她镇住了。她刚从山里出来,脸是黝黑的。她想,要是我能长那么白就好了。她的工作是往电路板上插二极管,每三秒钟要插上五个二极管。流水线上每个员工的工作量都精确到秒来计算。二极管很小,只有米粒那么大,两头的管脚细得不比头发丝粗。就这么小的东西,要在花花绿绿的电路板上精准地插到两个细小的孔里,真的很难。一个月后她仍然无法完成三秒钟插五个的任务,可想而知,她被电子厂扫地出门。她很沮丧。宋艳跟管事的吵了一架,也出来了。宋艳说:我怕你这傻丫头没人照顾,会被人坑了。
她喜欢城市,高高的楼房,夜晚灯火辉煌,宽阔平坦的街道,绿化树都经过打理修剪,很好看,不像山里的那样野蛮生长。可她还是很想家。想哥哥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了。想弟弟放牛砍柴会不会碰上吊脚蜂。她以前砍柴就碰过好多回,柴刀砍过去,吊脚蜂轰地一下飞出来,直叮人。天下雨了,她就想老家是不是也在下雨,就担心爸爸田里干活会不会淋雨。在山上砍毛竹就麻烦了,淋雨是少不了的,特别担心爸爸会跌倒,雨天路滑,山上更滑。她也上山砍过毛竹,跌倒过好多回。有一回跌得好惨,从山坡上滑下去,坐飞机一样。
后来她去了足浴城上班,那儿能多赚点钱,又不像工厂那样管得死死的。家里太需要钱了,哥哥要讨老婆,弟弟要上学,爸爸又不能赚钱。她本不想去,在那儿上班遭人看不起。可宋艳她们去了,天天在她面前数票子,今天三百明天四百。宋艳说:傻丫头别死心眼,趁着年轻赚到点钱来,将来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钱这东西诱惑力太大,她抵抗不住,加上姐妹们拉拉扯扯,就去了。在足浴城上班,她人长得好看,这就免不了要做那样的事。足浴城是个大染缸,什么红的白的,都能染成绿的。后来有个长得挺帅气的男人扔了一大沓钱给她,有五千元,她数钱的手都在抖动。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对金钱的渴望使得她也觉得要放开些。钱的确赚到一些,但那些钱都归了家里,帮哥哥娶上了老婆,家里建起了一栋两层的砖混房,外墙贴上瓷板,挺洋气。
后来,她结婚了,嫁在邻乡,媒人介绍的。她谈过两个外省男孩,一个湖北的,一个重庆的,家里强烈反对,特别是母亲,拿着绳子要去上吊。她理解父母,女儿嫁得太远了就等于卖掉了。她也没做更多的挣扎。
男人叫谭小青,个子不高,一只脚长一只脚短,不是残疾,人的脚都一个长一个短,他特别明显些而已,走路给人一拖一拖的感觉。人倒是粗壮,就是五官搭配不怎么匀称。过年回家去相亲时,她打心眼里不愿意,自己的锦绣身段就交给这么一个人?可母亲说她,挑什么挑,坏了名声的人,你还能再挑吗?在足浴城上班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了。在乡下,这是叫有破败,让人看不起。
谭小青好像不在意她在足浴城上班,定下亲后,还跟她到足浴城做保安。再后来她怀孕了,腆着大肚子回乡结婚,然后就在家里带孩子。日子似乎要这么平淡地过下去,虽不富裕,但也波澜不惊。
她身上的钱不多,孩子出生,开支大起来。谭小青没有外出赚钱,守在家里,山里种那几亩瘦田,只能赚到吃,没有钱用。谭小青不是勤快人,时常跑去村街上打麻将。看他一点也不为家里的经济担忧,秦小蓉忍不住就骂他没本事。开始,谭小青倒能逆来顺受,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挥拳相向。打她的第一拳是吃午饭时,谭小青外公第二天八十大寿,要准备钱去贺寿。两人为贺礼的事吵起来了。谭小青说他没钱,而她身上的钱也快归零了。平时的开支都是她拿钱出来。谭小青说:钱不就是花的吗?留着干吗?秦小蓉说真的没钱了,然后就拿存折和打开箱子给他看,再数落他没本事。谭小青确认她真没钱后就跳起脚来骂。秦小蓉回骂。谭小青揪住她头发一顿拳打脚踢。她与他对打,然而,女人终是打不过男人。她遍体鳞伤,哀吼几声跑了出去。
她跑回娘家,希望得到娘家人的抚慰,去讨伐那个没良心的东西。可娘家人并不支持她,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嘴打架的,做女人就该委屈点。言语间,或明或暗地说她,曾经在足浴城上过班,女人就该低眉顺眼。她心寒到了极致。娘家是待不下去了,就这么没皮没脸地回去了。
她没脸没皮地回去,无疑给谭小青壮了胆,娘家人没有来声讨他,他觉得占到理了。以后的日子,有恃无恐的男人变得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开口骂脏话,拳脚相向。她变得低眉顺眼,偶尔也会反抗,但遭到的是更凶狠的殴打。男女间的厮打,吃亏的永远是女人。每一次她都遍体鳞伤。挨了打她再不会回娘家了,那不是她疗伤的地方。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孩子会走路之后她又出去打工,进过很多工厂,也上街卖过烧烤。她去哪儿,男人就跟着她。谭小青似乎预感到这个女人想挣脱他,家庭暴力也是愈演愈烈。她会来到宋城,其实就是想挣脱。宋城名气小,她没来前还不知有这地方。她是瞎走来的。她想,这儿好,死男人打死也不会想到我跑到这里来了。可她失算了,她进厂五个月后,谭小青已站在厂门口。她与我老婆说说笑笑走出厂门,猛然见到他,脸色就变了。如果不是我老婆架住,她会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那个死男人是配不上秦小蓉。吃晚饭时,老婆跟我说。
以后常看见她神情憔悴,我知道,又挨男人打了。她是个向往快乐的女人,聊天时说到开心事会哈哈大笑,还会做各种怪动作逗我们开心。我心里有点难受,却没办法帮她。谭小青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她不愿意回去。但这没用,谭小青会追到公司来。那会儿生活区还没有院门。她躲他还有一个办法:来我家打麻将。她说,王师傅今晚有活动没?我知道她的意思,便会约两个朋友过来。有天晚上谭小青追到我家来了,一来就伸手想扫麻将。我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他的手受惊似的缩回去,良久才弱弱地说:我来接我老婆回去。我说这不是三缺一嘛,别扫兴好不好?次日秦小蓉直夸我:王师傅你太酷了,一下子把那鬼人镇住了。我不是狠人,但知道家里耍威风的男人外面多是懦夫。秦小蓉说:王师傅我问你句话,不可以打谎。我说你问吧。她说:你喜欢我吗?我说:当然喜欢呀。她说:那我们私奔吧。她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愣在那儿。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看你吓的。
我表面看起来憨厚,但内心还是有些野想法。十八岁曾有一次离家远行,跟余华写的那个少年一模一样。我有时怀疑他写的就是我。就是現在四十多岁了,夜深人静时依然会瞎想,想与一位红颜知己共骑一匹快马闯天涯。第二天,生活是怎样还是怎样。
三个月后,也就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秦小蓉没有来上班。我们都以为是让谭小青打伤了,你一言我一语骂谭小青不是人。晚八点,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谭小青的声音:秦小蓉在不在你那儿?我说没有哇。
秦小蓉跑了?她到底没有死心,要挣脱。我想,她是很难挣脱的,除非带上孩子。可一个弱女子,带上幼小的儿子就没办法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又怎么办?这是个死结。
我想起胖脸姑娘给她的考题:@b≌是什么。她的回答没有错:它就是一道符,命运符咒。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