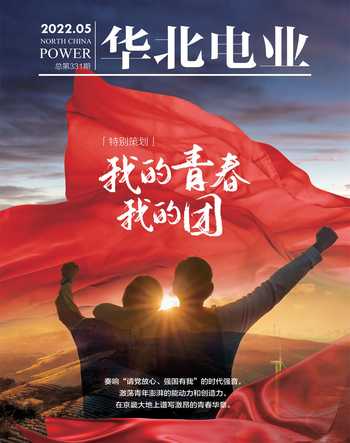春去夏犹清
刘明明

疫情反复出现,封控反复进行,对我来说是第三次,第一次在3月份,全市封控23天;第二次在4月份,路北区封控3天;这次部分疑似小区实行封控,又不幸“中奖”,断断续续从初春封到浅夏。
孩子们自3月19日第一次封控就一直在家上网课,家长们本还以为过完“哪都不去”的“五一”假期,终于可以“神兽归笼”顺利返校,可经过一早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开学季”,还没来得及吃上庆祝的午饭,就在3个小时后遭遇无理由“退货”:继续回家上网课,开学时间等通知。父母只能满脸无奈地把欢呼雀跃的孩子打包带回,继续一旁“陪读”。
幸好,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突然的“暂停键”,从第一次封城的诸多不适到现如今的迅速自觉被封控,情愿或不情愿,都要接受疫情带给我们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现在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工作,也不是梦想,而是带着赵丽蓉口音的“下楼做核酸”,之后就是准备一日三餐,为“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在各种物资群团购接龙,很多从前不爱吃的,现今能够吃出独特的美味;那些以前没吃过的,满足了对新口味的尝试探索,日子就在下楼核酸、一日三餐中消磨掉,单调重复却流逝如飞,眨眼又近一周。
人们活动的最大范围也不过就是楼下的绿化面积。院子里的花从三月至今已经开开落落好几批,从嫩黄一片的迎春,到沾衣欲湿的杏花,再一树雪白的海棠,此起彼伏,姹紫嫣红,因为封控,大部分人才有时间欣赏院子里美丽的花朵。有人在微信群里说物业将要铲除松树下那片悠悠淡淡紫的二月兰,于是大家发起保卫二月兰的讨论,一至认为此花虽不名贵,但花期长且素雅大方,实为园中一景,必须保留,并由此唤醒了业主意识,就园区的物业管理、宠物的粪便清理、基础设施的维修保养,甚至假山的风水方位进行建言献策,让我惊叹于高邻们的学识渊博、博古通今,为能住在卧虎藏龙的小区深感荣幸。感谢疫情封控让曾经“相见不相识”的邻里相互了解,日渐亲近。
和二月兰的常开不败相似,月季也始终在努力盛放,沿着小径已经形成一垛红肥绿瘦的花墙,遛弯的人们就着晨曦朝露或落日余晖纷纷拍照,有种网红打卡地的热闹。
院里的人看风景,院外的人也在好奇地看着封控区内的人们,正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时节,有人在杏树旁的回廊里挂了一架秋千,虽无佳人,却有儿童清亮的笑声,想来这是她们久未体验的无忧无虑,有父母陪伴,少课外负担,疫情带给了他们一段清澈欢乐的时光。
儿子的网课讲到了《桃花源记》,我重温了一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竟觉与封控的境遇相似:微信朋友圈里依旧热闹精彩,外面的世界仍在繁华喧嚣,而我们却如与世隔绝,不论有汉,无论魏晋,或尽享桃花源内的悠然自得,或在忍受如坐牢般的难挨焦虑,总之,出不去。
记得第一次封控,所有人都茫茫然,不知道封控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要怎样调适生活,虽有武汉封城的先例,但对于这座历经毁灭性大地震又拔地而起的英雄城市,因出现疫情全面封城却是第一次,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市民也是第一次经历,大家能做的就是在慢慢摸索中不断调整和适应,尽量放松心态,平息焦虑。
经过23天封控的第一次解封,小区门打开的那一刻,有的人马上奔赴心念已久的目的地,有的人却茫然四顾不知该去往哪里。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一些期盼已久的计划戛然而止再无重启,一些妄想逃避的事情突然悄无声息就此过去。有人说我的青春才几年,封控过了3年;有人说2022年的上半年,掐指一算总计上了50天的班。这要是放在“前疫情时代”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现今却是非个例的存在。网上因疫情引发的新闻包罗世间百态,有冲锋“疫”线的医务工作者,有无私奉献的社区志愿者,有健身明星大火,有贫困父亲寻子未果,还有更多平凡人的悲欢离合默默上演。但无论如何,绝大部分人仍要回到既定的生活轨迹,只在记忆中留下又一段不同寻常经历。
谁持妙笔绘初夏,岁月清和更胜春。
不知不觉树成荫,幼蝉鸣,而我依旧封控中。
我对荡秋千的邻家女娃说:“夏天来了。”
她仰起粉嫩的小脸问:“夏天有什么?”
“夏天?有荷花,有蜻蜓,有花裙子。”
“还有冰淇淋。”女童笑嘻嘻地补充。
夏天还有每个人心里更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