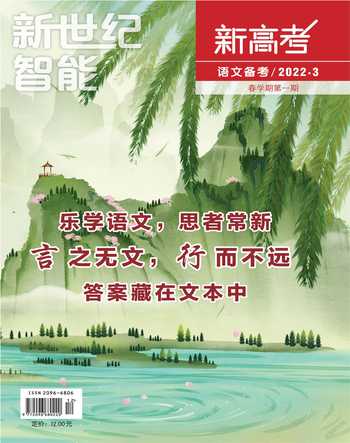歌旧曲,酿新醅
武健
《声律启蒙》有言:“歌旧曲,酿新醅。”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的文学或社会价值绝不限于当时,《玩偶之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以及中国产生摧枯拉朽的社会作用,直到现在,依然可以启发我们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思。学习《玩偶之家》要兼顾过去与当下的意义,既要唱好“旧曲”,也要酿好“新醅”。
三幕话剧《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也是现实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是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女权与人类
《玩偶之家》曾被比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部宣言书里,娜拉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以此作为对以男权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剧本结构紧凑,情节集中。全剧采用追溯的手法,通过债主的要挟,海尔茂收到揭发信,交代剧情发展的关键事件——娜拉伪造签名,然后集中刻画他们冲突和决裂的过程。
文艺理论谈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时,通常会说一部作品发表出版之后,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往往是读者所赋予的,而不一定是作家创作的原始动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的哈姆雷特可视为这种观点的夸张表达。《玩偶之家》问世以后,在欧洲甚至世界,掀起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思潮。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受易卜生影响创作的一系列话剧作品,也多把“妇女解放”根植于剧作中。1898年5月易卜生在挪威妇女权益保护会一个宴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不是妇女权益保护协会的会员。我在作品中无论写什么,都不会有意识地做某种宣传。与人们通常以为的不同,我主要是个诗人,而并非社会哲学家。谢谢你们的敬酒,但我不能接受自觉促进女权运动的荣誉。说实话,我甚至不清楚女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我看来,妇女的权利问题在总体上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我的任务一直是描写人类。”
这样看来,《玩偶之家》的女权主义思想,是当时社会的解读,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尊重社会历史赋予作品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易卜生创作的目的——描写人类,揭示与表现的是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女性。
即使从妇女权益上看,21世纪的世界包括中国,也没有完全解决性别差异问题。不论是台湾地区当代作家林奕含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还是韩国女作家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都揭示了男权意识的可怕惯性和女性生存上的困境。
对比与讨论
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虽然没有死板遵守“三一律”(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但考虑舞台的有限时空,还是把故事集中在圣诞节前后共三天的时间内,舞台场景都是在通到门厅,连着海尔茂书房的一间屋子里。易卜生采用了追溯的方式,把过去与现在、屋外与屋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拓展了戏剧表现的时间与空间。通过娜拉与林丹太太的对话,交代了借款的背景;与柯洛克斯泰的对话,补叙了伪造签名的前因后果;与安娜的对话,告诉观众娜拉自幼失去母亲的不幸;与好友阮克的对话,暗示了娜拉自小就常被父亲教训。通过林丹太太与柯洛克斯泰的对话,观众发现了两人过去还有一段苦涩恋情,这也给娜拉一家面临的“灾难”带来了一线转机……应该说,易卜生熟练地运用“追溯”方式,完美充分地展示了这部剧作需要的所有背景故事与明暗线索,让所有的问题矛盾在一间屋子里三天内完全展开,淋漓尽致。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人物的刻画中,充分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舞台形象。
第一幕中的娜拉,活泼开朗,看似陶醉于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中;第三幕中与海尔茂面对面谈话并毅然离家的娜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的对比,更能表现出娜拉的自我觉醒的意识,逐渐成熟的主见,以及与过去决裂的果断。海尔茂的舞台表现更体现出人物形象的多面性,表面上爱护妻子,随意的海誓山盟,但隐形的管控已经让娜拉不堪其扰。一派道貌岸然的大男子主义,却不顾过去的同窗情谊,因同学所谓不尊重自己而怀恨在心;已经知道多年交往的好友阮克大夫得了绝症即将辞世,却一点也不在意;发现因娜拉伪造签名可能会让自己前途大损,立马撕掉虚伪的面具,露出狰狞的面孔。看似柔弱孤单的林丹太太,面对好友娜拉的困境,冷静从容,机智聪明,最后既化解了娜拉的麻烦,也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海尔茂面前的阮克大夫和在娜拉面前完全两样,甚至在知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时,向娜拉表白了多年以来的爱慕之意。
娜拉的家庭,一个中等收入的资产阶级五口之家,即将因海尔茂的升职而步人更加幸福的生活,却因一个偶然,所有的美好被撕得粉碎。易卜生在戏剧故事的推进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而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与一般戏剧不同的是,《玩偶之家》中,舞台说明较少,整个剧作的写作中心多放在人物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上。而《玩偶之家》的人物对话多有讨论的情境,如娜拉与林丹太太的对话,讨论的主题有家庭的开支、人生的烦恼与得意之事、娜拉暗中承担的债务、娜拉与阮克的关系等话题,表现了同为女性,娜拉与林丹太太既有相似的人生体验、自觉的女性意识,又有不同的处境与况味。
娜拉原打算想请阮克帮忙,但阮克向娜拉表白内心之后,娜拉改变了主意,“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了”。看似家常般的聊天,却体现了娜拉在友情与爱情之间严格的尺度与分寸。第三幕结尾娜拉与海尔茂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下来“夫妻正正经经”地谈话,更是把剧作的讨论场景推向了一个高潮。娜拉最终明白自己在家中傀儡的地位,在丈夫心目中玩偶的角色,毅然与丈夫海尔茂决裂。海尔茂做最后挣扎,力图挽留娜拉。可娜拉说的“奇迹中的奇迹”让海尔茂疑惑不解,因为他从未真正了解他的“小松鼠”“小鸟儿”,更不了解坐在桌子对面的新的娜拉。这种隔阂不仅是情感态度上的,更是思想意识上的。
娜拉出走,代表了女性的觉醒,自我意识的回归,对自主独立社会家庭地位的追求。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呢?尽管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说,“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与丈夫讨论过后离家,剧作在大门关闭的声音中缓缓落幕。但这场讨论却把问题抛给了观众,抛给了一个时代。
世界与中国
《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反抗出走,反映了当时西方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提升的社会现实。娜拉虽然还困于家庭的琐碎之中,但她的好友林丹太太已经只身进城谋生。从戏剧中看,娜拉和海尔茂等人对林丹太太找工作的事也没表现出什么异样的态度。这也表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在外工作的认可。而娜拉虽身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没有工作,困难时也仅限于做些编织刺绣之类的零工。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丈夫讨要。
娜拉在家庭中的地位,亦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缺乏独立的精神意识,更谈不上社会的政治权利了。“玩偶”的概念,一定程度上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群体在家庭与社会的处境与地位。从林丹太太谋求工作,到娜拉离家出走,这正是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强大的过程。
娜拉为追求人格的独立,不甘做丈夫的玩偶,毅然深夜离家出走。她的出走是女权运动对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法律、家庭、婚娴制度的挑战,是觉醒的女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冲击。“过去我以为快活,其实不快活。”“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这一句句铿锵有力的台词,正是娜拉代表广大妇女发出的呐喊,更成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
从某种程度上说,《玩偶之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或许是在中国。
1918年《新青年》杂志发行“易卜生号”专刊,发表了罗家伦与胡适翻译的《玩偶之家》,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开始进人正处于新旧文化变革开寸期的中国后,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带动了中国现代话剧创作与演出的发展。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欧阳予倩的《泼妇》(1922)、郭沫若的《卓文君》(1924)、张闻天的《青春之梦》(1927)等话剧中的女主人公,多具有娜拉一般的反抗精神。《玩偶之家》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其中有两位名为“苹”的演员。1934年,万籁天导演《玩偶之家》,赵丹和蓝苹分饰海尔茂和娜拉。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惕。因躲避当局的追查,女主角蓝苹离开上海,最后去了延安。1935年,南京“磨风”剧社排演的《玩偶之家》女主角是一位名叫王苹的小学教师,王苹所在學校的校长以有违家庭伦理为由,开除了王苹。这一新闻引发了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舆论纷纷痛斥校长的保守与愚昧。离开南京的王苹后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代表作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闪闪的红星》《柳堡的故事》。
对易卜生剧作的翻译与研究也日渐丰富。潘家洵在《近代西洋问题剧本一一从易卜生到萧伯纳、麦利生》(《西洋文学1940年第1期》对易卜生剧作为代表的“问题剧本”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与阐释:
因为近代戏剧以人生为主要对象,所以政治法律、经济组织、婚姻恋爱、风俗道德、宗教信仰、个性环境、教育遗传,种种问题,无一不在讨论之列。于是产生了“问题剧本”一个新的名词;“问题剧本”亦称“讨论剧本”,亦称“有思想的剧本”,亦称“有目的的剧本”。总而言之,可以说是正经讨论当代问题的剧本。
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河南》1908年第2、3期)和《文化偏至论》(《河南》1908年第5期)两篇文章中肯定易卜生的社会批判精神。1923年,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演出了《玩偶之家》后,鲁迅应邀做了《娜拉出走怎样?》的演讲。包括刘大杰《易卜生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林语堂译《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在内的一系列研究专著的出版,代表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关于易卜生,关于社会批判,关于女性解放等问题的讨论,进入了更深人的阶段。现在看来,《玩偶之家》引发的社会大讨论,与那个“觉醒年代”的时代风貌,有着相当的关联性。
易卜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对当时的欧洲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当时的挪威与欧洲其他国家,还是20世纪初的中国,这些强有力的呐喊,对广大妇女争取自由、平等、人格的独立起了巨大鼓舞作用。娜拉的出走成了震惊男权社会、震醒昏睡的女性的社会现象。娜拉与海尔茂的决裂,揭示了资产阶级婚娴中的不平等,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
阅读《玩偶之家》,不能仅限于课文中从第三幕中节选的内容,要读整部剧作;也要进行跨媒介阅读,把电影与剧本参照着学习。而要理解《玩偶之家》对近现代中国的意义,我们可以对围绕易卜生产生的一系统研究文章进行梳理挑选,从而进行群文阅读,也可以通过对现代文学中戏剧发展初期的剧本进行研读,探索易卜生戏剧创作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