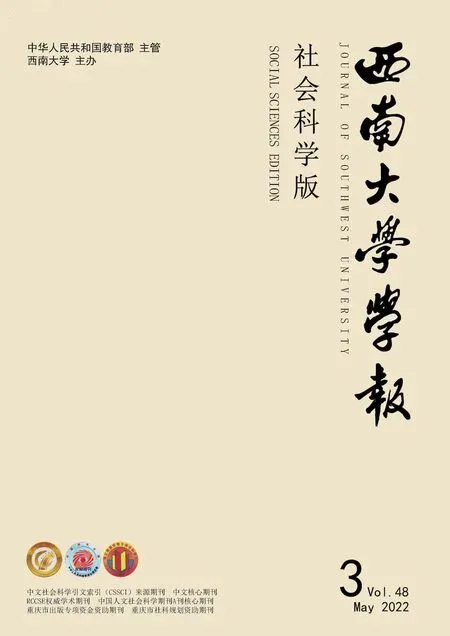文字改革语境下章草书体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启示
胡 长 春,刘 洪 健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400715)
一、问题的提出:以拼音化和汉字简化为主的文字改革研究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文化领域,作为承载国民教育基础和开启民智的语言文字,首当其冲成为一批有识之士强烈呼吁的改革对象。他们认为,中国汉字源于象形,笔画繁冗,艰涩难识,且在语言运用方面“言文不一致”,这相较于西欧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字而言,存在着先天不足和严重的滞后性,他们由此视汉字为“封建毒瘤”,斥其为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元凶。比如,鲁迅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陈独秀谓:“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他们纷纷主张把汉字作为文化改革的切入口,力求参照西方语言系统来施行“文字改革”,期冀改变落后、陈腐的国民生态。
在这场文字改革运动中,虽然拼音化是其中的主流声音,但在拼音化方案之外也有若干不同的改革方案。比如黎锦熙致力于汉字简化的研究和实践,他认为对简化字的整理,应“遵循‘自然’演变的法则,不强定系统,不臆造新体,管理部门的职责更多是‘审定’和‘承认’”,在推行过程中,建议“简体字和注音符号配合使用,还主张‘写简识繁’”[3]。这些关于汉字简化的探索和举措,有利于民众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坚持拼音文字始终是汉字改革的方向,也暴露出对汉字简化的认知局限。陆费逵主张文字简化,提倡以注音字母来辅助汉字的学习,先后发表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整理汉字的意见》等文章,一方面注重采用民间习用已久的俗体字,缘于其笔画简易,便于实用;另一方面力倡普及国语国音,以使“国语统一”“言文一致”。钱玄同堪称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旗手,呼吁汉字改革不遗余力,他前期受到激进思潮影响,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后期态度有所缓和,因为“短期内只是拼音文字的‘制造时代’,而非‘施行时代’,并认为这样的过渡期需要10年”[4],因此提倡汉字不可一时废弃,最好的方案是以简化形体作为过渡方式。
对于汉字改革的这段历史,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崔明海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而拼音文字方案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声调问题、字母形式问题、标准语问题、同音词问题一直争论未决,民众是否接受拼音化文字亦未可知,当时在中国推行拼音文字并不具备现实性;二是因为新中国建设需要尽早扫除大量的文盲。尽管繁体字也可以用来扫盲,用来学习文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者基于追求工具效率的考量,认为实行汉字简化改革在当前是‘迫切需要的’。”[5]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于目前的应用。”[6]综合而言,汉字不可一时废弃,而最好的方案则是以简化形体作为主要方式。那么,在实施简化的诸种方法里,除了列出已有的简体字以外,通过借鉴草法规律,省减部件,削繁为简,化多为少,无疑也是推行简化字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1955年《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及1966年《汉字简化方案》,都采用了行书、草书写法来简化汉字及其偏旁。
在现有关于汉字改革的研究成果中,以拼音化为主题的成果仍占主流。杨伟东指出,注音字母是民国时期推行“言文一致”的有力工具,为保证国语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力地“促进了识字教育的开展和教育的普及”[7],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湛晓白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国语注音的诉求,国语罗马字注音方案在钱玄同、黎锦熙的支持下进行了实验,并得到官方认可,然而因对其价值的认识不足和推广方法欠妥,最终处境尴尬,甚至赶不上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8]。童滢认为,20世纪初汉字改革主要方案有三种,一是废止汉字,二是保留汉字,三是持中立状态,归根结底是文字本体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结果[9]。高玉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认为简化有其合理性,但“长远来看,简化字是错误的,它本意是简便汉字,简化汉字,但实际上是增加了汉字的负担,使汉字变得更加混乱”[10]。
在关于文字改革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时世平的系列成果特别值得重视。他认为,语言文字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在既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同时,亦能真实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时期,随着救亡图存、启蒙等时代主题的出现,中国文学语言便成了社会关注且急需改革的主要对象[11]。然而,是径直废止汉字使用万国新语,还是在保留汉字的情况下实行简化呢?前者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和乌托邦心态的表现,故不可取;后者较为明智,需要我们充分认识作为表意文字的优点,“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12]。他举例说明,在清末民初汉语言文字面对西学的冲击而面临变局时,章太炎为保存汉文化,大力倡导保存汉字的汉民族文字观[13]。
迄今为止,研究文字改革的成果已有不少,主要内容多是围绕拼音化和汉字简化两大方案进行研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民国文字改革运动中兴盛一时的书法字体改革谈得很少。有鉴于此,本文拟钩沉20世纪初文字改革背景下章草书体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通过梳理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章草理论著作,着重从字形、释正等方面分析章草书体由盛转衰的原因所在,并以此剖析章草书体与文字改革的关系,为汉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二、20世纪初章草书体在民国的兴盛与《急就章》研究
章草在秦汉之际就已诞生,东汉时达到鼎盛之势,魏晋时期被纵横流媚、上下连绵的今草所取代。章草因其自身的程式化而导致的实用缺陷日益凸显,到隋唐时一蹶不振,乏人问津。黄伯思《东观余论》曰:“(章草)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14]在尊崇“复古”的元代,虽然出现了赵孟頫、邓文原、杨维桢等章草大家,掀起过章草学习的热潮,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章草并未真正得到复兴。明清时代,随着写意书风渐兴和碑学兴起,章草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虽有少数书家偶有涉及,但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则已成定局。
清末民初,西北简牍、写经墨迹相继出土,特别是对20世纪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流沙坠简》,在罗振玉、王国维的精心整理下,凭借成熟的印刷技术得到广泛传播,其中《屯戌丛残》等大量鲜活生动的简牍章草,弥补了自宋以来刻帖失真的缺陷,同时也引起了民国众多学人的强烈关注,付诸政治、文化、教育改革发展中,力图发挥其潜藏的经世效应。章太炎、钱玄同、卓定谋等学者皆致力于章草的搜集、考据和整理,甚至主张以章草来武装“文字革命”,一时之间,章草备受关注,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元代以来的章草史上颇为罕见,可用“兴盛”二字以概括。
(一)“文字改革”语境下“万国新语”与章草书体的较量
在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潮流中,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制的Esperanto(即万国新语,又称世界语)颇受时人瞩目,以简单、灵活、明确且易与其他国家、民族沟通的特点,让欲融入世界的中国看到了希望,在20世纪初被刘师培引入中国后,很快得到陈独秀、蔡元培、胡愈之等人的大力支持,在中国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与此同时,万国新语因断然主张废除汉字的过激之举,遭到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每个民族皆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即使使用了万国新语,只能使汉字所记载的文化,以及语言文字之独异性消失殆尽”[13]。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刘师培则以《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驳斥万国新语说。而之前提倡废除汉字的钱玄同,也因对万国新语“这种缺乏地域文化作为根基的表音文字究竟能够真正付诸国民的应用和普及心存犹疑”,从而转向“减省汉字笔画”的草书方案,称此为“实为至正当之办法”[15]47。
作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两种改革方案,万国新语与保留汉字的草书方案,在观念、方法及功用方面存在着较大分歧。“在文字改革方面则可以划分成为两大阵营:一个是钱玄同、胡适、赵元任等提出的通过‘草书楷化’或‘通字方案’来实现‘改良’的渐进的思路;另一个则是傅斯年等不经过此阶段而彻底拉丁化、世界语化的主张。”[15]46前者重在“改良”,后者重在“革命”,两者皆以汉字的繁复与难写的弊端作为改革目标。前者运用简省笔画、简省汉字部件等方法化解书写之繁琐,手段渐进温和,故能保留汉字形体。后者则认为西方文字“兼具音符、意符之简洁和精妙,……功用在于便利、实用,易为大众接受”[16],主张以拼音化的世界语、拉丁语取代传统的表意汉字,但这种方式彻底激进,因为一旦用拼音替代汉字,“就是废除以汉字为载体的居于主流的文言,同时也将废除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这在文言传统为尊的格局中根本不可能”[17]。
历史证明,顺应历史潮流、保存民族文化的改革方案倾向于前者,虽然“承认汉字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方向,也宁可主张以‘渐进’而不是‘突变’的方式来结束汉字在中国的命运”[15]46。草书楷化的方案不仅能够解决汉字书写的繁难之弊,易见实用功效,而且其渐进温和的改良做法亦可作为“汉字革命”以解当务之急,缓和万国新语与汉字书写繁冗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同时,只要汉字不废,不少爱好书法的“汉字革命派”也能为金石考据、碑帖临摹找到一个正当堂皇的理由。然而要兼容这些条件,就必须寻找一种既快捷实用又不失艺术审美和历史感的字体,那么章草无疑是众多字体中的佼佼者,其字体系统、整齐、规范,是东汉文人们对汉草整理优化后的一种成熟草书体。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评其“兼功并用,爱日省力”[18],唐孙过庭《书谱》称章草“务检而便”[19],这些评价都明确指出章草具有良好的社会实用性。
(二)民国章草书体的兴起与《急就章》研究
当然,在主张以简化为重要途径的文字改革中,亦存在其他的汉字方案,比如陆费逵于1909年发表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的《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就提出“近人创制的‘简字’与旧有文字在形体上差异过大,不如推行俗体字”[20]。1928年陈光尧倡导的手写俗体,“其中包括简易之古文、篆书、隶书、行草、章草、今草、别体、俗字等字体,凡笔画简于现行之楷字而使用简易无流弊者,即总称之曰简字”[21]。之后又有1932年于右任筹建的“标准草书社”,以易写、易识、准确、美丽为原则等。但综合而论,这些方案都无一例外地偏向于草书,尤其对章草的认同比例不小。
笔者现将民国学人涉及章草书体的评论例举如下:
沈曾植说:“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出……章草。”[22]
郑孝胥说:“子敬尝叹章草宏逸,余又恶草书纵笔有俗气,故欲以皇象、索靖为归耳。”[23]
章太炎说:“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文字宜分三品:题署碑版,则用小篆。雕刻册籍,则用今隶。至于仓卒应急,取备事情,则直作草书可也。然自张旭、怀素以来,恣意钩联,形淆已甚。当依《急就》正书,字各分区,无使联绵难断……。”[24]
钱玄同说:“从那时起,就时时留意章草法帖,颇想搜罗许多材料,写定其字体……但章草以《急就》为最早,章草的文字以《急就》为最多,又《急就》多举物名,故可供撷取的偏旁也最多。”[25]
陆丹林评价王秋湄说:“近年来他对于章草,颇见肆力,是由赵松雪宋仲温入手,进窥皇索的。他见得近人好写章草,以写时髦,然多不知章草原理,字形的组织,和笔画的演变……因又编了《章草例》一书。”[26]
卓定谋说:“窃以章草字字有区别,字字不牵连,定体有则,省变有源,草体而楷写,非如今草之信手挥洒,想象意造者比。”[27]绪论2
从上述可以看出,从民国初年到1930年代末,由于中国西北部出土了大量简牍残纸,相当多的书家学者对其中的汉简墨迹给予了高度关注,广为搜罗,精心整理这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和创作。从上举资料看,大约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等晚清遗老为代表。他们见到《流沙坠简》影印本后,大力借鉴其中的章草墨迹来改进陈旧的碑学观念及僵硬的创作面目。如李瑞清便感慨说:“世所传草书……则粗犷而狂怪。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28]沈曾植晚年书法更是得力于此,沙孟海评道:“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路,没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29]沈氏还建议身边的学生、朋友学习章草,并以简牍章草的标准来品评书法。这表明沉寂已久的章草在《流沙坠简》的整理推广下,以其高古、精细、简省的特点博得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青睐和肯定,并在他们的摇旗呐喊下,唱响了章草复兴的第一声。之后稍晚的章太炎、王世镗、林志钧、王秋湄等都深受他们的影响,纷纷加入章草队伍,还进一步转向对章草本体的研究,产生了不少考证章草源流、版本及技法的理论著作[30]。同时,他们分居南北重镇,且多为社会名流,对推动章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大有助益之功。尤其是卓定谋,他对章草资料的收集整理可谓不遗余力,他主持出版的《自青榭丛书》就汇集了《补定急就章偏旁歌》《宋仲温临急就章真迹》《章草考》等著作,搜集章草近3 000字,在“北平大学且专设讲座,资传习焉”[27]林序2,又将“市民千字课,试改成章草简体表”[31]106,使章草能在大众之中得到认知和普及。
在上述所持论点及所涉及的著作中,人们屡屡提到皇象和《急就》。《急就》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通用的童蒙识字课本,相传系西汉史游所编。此书最初称为《急就篇》,因几乎全是以章草书写就,故又有《急就章》的称谓。在今天流传的《急就章》版本中,以松江本最为常见,史载为吴国皇象所写,北宋叶梦得释正。全章原文共31章,计1 953字,章正对应,体态朴茂,字字珠玑,裘锡圭称其“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章草资料”[32]。历代章草大家如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等都曾反复临摹过,近现代的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高二适等书家也无不受其深刻影响,《急就章》一直被视为章草学习的典范教材。随着民国章草热潮的兴起,致力于《急就章》的研究成果频频出现,从1914年到1948年,李滨、王世镗、卓定谋、刘延涛、于右任等都发表了关于章草研究的论著,一致围绕《急就章》进行讨论和探究。可以说,要研究章草,皇象的《急就章》是始终绕不过去的经典之作。
三、由对《新定急就章》及民国章草文献的考察探析章草书体的实用问题
通过这些学人的积极关注和参与,古老的章草书体在民国得到了深入挖掘和整理,这使它的艺术性得到了不少学人的青睐,对认识章草书的实用性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章草这种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书体,在汉字改革的强烈呼声之下,能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本身的实用功能,而不会在文化大变动背景下陷入“政治性的封建与革命、陈腐与新生乃至中西古今等等对比中去”[33]7。因此,以实用章草为文字改革方案的热潮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
(一)民国章草书体的衰落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
章草热潮持续至1930年代末渐趋衰落,有关章草史论、技法研究及推广的著作急剧减少。1930年1月12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正式成立,以卓定谋、林志钧为骨干,其宗旨“意在将研究之结果,供为将来实行改革字体之准备”[31]105,其宗旨即是以促进章草发展为中心。然而,研究会到1937年停办,其最初的宗旨“通过推行章草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更是无从谈起”[34]55,这标志着昔日得到积极响应的章草运动,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终结,预示着在民国有复兴迹象的章草,在稍稍能够转化为社会实用功效的转型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很快便已日薄西山。
至于章草衰落的具体原因,不久即有书家学者进行分析。1936年,于右任《标准草书后序》指出:“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35]1947年,《草书月刊》第3期登载刘延涛《于先生临标准草书千字文后序》说:“而章草之倡导,历时不久,即风流云散,间有作者,或为好古,或为耽艺,不复留意于实用,而违提倡者之初旨矣。然其失败,亦可分为内外二因:内因者,章草本身之缺点,外因者,提倡方法之疏阔也。”[36]
在当下学界研究成果中,元国霞分析说:“由于这一推广既不契合民国阶段的文字衍变,又无良好的群众基础,章草书自身也带有一定的实用缺陷及规范简便的假象,加之推广者在面临‘西化’势力时势单力薄,又混淆了章草书的艺术功能与文化功能等,共同造就了失败的结果。”[37]759曹建等列举了四个原因,分别从主体、客体、本体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章草方案的倡导者多为具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对章草的实施持保留态度,同时也受到章草本体的限制,其自身存在的实用缺陷无法与时代相适应,故而难以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只能以失败告终[34]55。吉德昌认为“章草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不真正的适合日常的使用。因此,认为章草为最简便实用的书体的观点本身是存在问题的”[38]。
简而言之,或谓章草字数少,根本不够用;或称章草字形近古,识读难度大;或言与民国时代语境不相一致,章草难以推广。种种说法,皆有一定的合情合理之处,均可构成民国章草衰落的个中原因,特别是章草本身的实用缺陷,在以上众多的分析中均有提及,应视为章草文字改革失败的主要症结。然而,深入细致的阐述却并未展开,或只轻描淡写,寥寥数言;或有所论析,却语不中的。
学者型书家高二适撰写了《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对松江本《急就章》的草形演变及章正对应作了详尽的整理与考证。从时间上论,该书始撰于1954年,到1969年才得以完成,但其起草准备工作可以上溯到1930年代,如其自述云:“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计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八年。”[39]陈振濂也认为此书上续民国章草的专题研究,“足可以划出一个单独的草书研究系统”[33]137。因此,《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实可纳入民国章草理论研究范畴之内。
值得说明的是,是书在梳理《急就章》多字有草形舛误、章正难以对应及一形多字等缺陷的同时,自身在考证、释正等方面也有不少讹误,因此通过对此书的考察,以小见大,足以反映章草书体的发展依然问题重重。现笔者拟从《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急就章》的整理以及笔者对高二适此著的订正两个层次出发,分别就其与民国章草衰落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
(二)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急就章》的整理论章草书体的缺陷
高二适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言中说:“松江吴皇象休明之书为最古,此本经唐宋人之钩摹,迄明正统初始刻于石。其章草之讹误,与宋叶梦得释文之误,亦正复不少。余尝考之,石本章草之讹误,可卅余字,叶氏释正之误,及不合章法者,乃增至五十余字,宋克补本,章正均误者,计章草十余字,而释正之误,亦几于叶释之半数,统计有百十余字之多,而二本章正之脱误,与失注之字,尚不在内,此均亟待改正者也。”[40]自序4根据高氏对《急就章》的整理,为求简明扼要,可将上述揭示的章草问题归纳为石本章草和章草释正两个方面,此两者又分别由石本和宋补两部分组成。
《急就章》中不少章草字形与释正难以一一对应。如第一章“與”“展”、第二章“侯”“由”、第四章“赣”、第五章“”、第十九章“耒”、第廿八章“肎”,等等。高二适共考证《急就章》石本及宋补本中的草正讹误计有一百多个。究其原因,客观上,石刻历经数百年,字形易于磨损脱泐,笔画增减无常,致使后人“不识章书,妄为臆度”[40]8。更严重者,从局部至整个字形,漫漶不清,难以识别,甚至多字疏漏;主观上,《急就章》屡经唐宋人钩摹,临榻转写多,不无失实,讹误良多。加之彼时章草衰落,今草兴盛。虽有唐颜师古作《急就章》注本,惜“亦只惟其文,不惟其书”,“颜氏不但不存章法,而释正亦不全依当日章草由隶书省变之原体。致使后人之校录《急就》者,以隶草之笔法,不能与正书之笔画相同,遂多构别体俗书。或则易假字为本字以迻译之”[40]自序1。出于此,高二适不拘于《急就章》文本的考订注疏,而是着力从章草字形出发,辨析草法之省变,厘定对应之释文。在资料的搜集上,竭力搜罗《急就章》颜王注本、《玉海》、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之《急就》考异本以及《流沙坠简》等凡与章草关涉之什,对于与章草相应的释正,也“必求与章合”;总之,“吾书凡章草一字,必求合隶之变;凡释正一字,亦必求合于草之形体”[40]序5。所以,他不仅整理出了《急就章》大量的草形讹误,而且对不合草形的误正、别正也一一进行了考证纠改。如第二章“侯”、第五章“”、第廿八章“肎”。举凡此类生僻的释正,或源自战国文字,或出于金文大篆,或起于小篆。这说明,章草字形并非单一由汉隶省变而来,战国简牍、金文大篆、秦小篆也是章草发展的重要源头[41]。那么,要明晰章草释正及草法流变,倘若没有较深的文字学基础,是根本无法识别的。
根据梳理唐颜师古《急就篇注》,清孙(星衍)庄(世骥)《急就章考异》乃至民初李滨《玉烟堂帖本急就章草法考》、王国维《校松江本急就篇》以及王秋湄《章草例》等资料,可以发现,他们对《急就章》中文字的考定有所差异,甚至截然不同。这致使章草的释正往往难以统一,聚讼纷纭,模棱两可,久无定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章草文字笔画简省,且字形近古。不光对于初学文字者起到的简化效果有限,而且对具有一定文字学基础的学者来说,识读的难度也不小。再加之《急就章》年代久远,摹泐、释误、摹误时有发生,种种实用的缺陷,要让普通民众接受并进而运用,无疑难以成功。
(三)由订正《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看民国章草书体的局限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在证草和释正的推绎过程中,对一些章草字形的考证、释正也出现了一些讹误。比如《急就章》第一章章草“与”,叶(梦得)释正“與”,沈曾植认为“《急就》‘与’字两见,……省变所由不可识,为传刻舛误无疑”[42]。《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则以古文“”考定此字。仔细揣摩,高二适分析谨严,言之成理。但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进一步发掘整理,诸多从事汉草研究的学者认为,高二适考证“”作章草,在出土的章草书演进序列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不合乎章草书的发展规律,应作为是[43]。
再如第六章“定”字的章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仍然以《韩碑》《曹全碑》进行论证,谓“定”之章草应由此碑中的隶书演进而来。但实际上,“定”之章草的雏形在秦汉时期早已出现。囿于时代的发展和资料的限制,高氏无法见到1978年印行的《云梦睡虎地秦简》、2001年出版的《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以及《马王堆简帛文字编》等书中存在的草法“”字。所以,高二适的论证似乎合理合据,实则牵强附会。
(四)从梳理民国章草理论著作看章草书体应用的不足之处
不仅如此,检视民国期间出版的章草理论著作,同样可见其中的考订释正易陷入主观粗浅的分析模式。
1914年李滨的《玉烟堂帖本急就章草法考》一书,时人评价云:“纂述精详,为言章草之杰作,有功贡献,不愧先河。其论定、变、通、独、断、连、穿、逆、籍、移共十端,均有见地。惜所举太略,于各字体之综合分析,尚欠具足。”[46]2其中“所举太略”“尚欠具足”,主要原因便是受出土汉简残纸数量的制约,不能掌握到足够充分的章草字形等相关资料,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整理研究。
1930年印行的《章草考》也是如此。卓定谋在该书“绪论”中说:“而后之谈字学者,但数篆、隶、楷、草,孰知由篆而隶而章,由章而楷而今草?盖隶与楷之间尚有章草之阶级存焉。”[27]2此论既指出“篆—隶—章—楷—今草”的文字演进轨迹,又指出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同时特别强调章草是承隶启楷的重要书体,而且其“笔画又简单,又分明,易写易认”,这相较于笔画繁复的楷书和笔势钩连的今草来说,无疑要简化规整得多,理当作为文字改革领域优先考虑的字体对象。但是,卓氏因过于突出章草与楷书的关系而认为今草是在楷书之后形成的观点,无疑“与书体演变的真实情况不符,这正是民国时期一部分人对书体演变问题的误解”[38]22。
再如1944年王秋湄撰述的《章草例》一书,王氏因见“近人好写章草,以为时髦,然多不知章草原理、字形的组织和笔画的演变。非驴非马,徒乱耳目”[25],遂倾注大量心血编著此书,并在“急就本字释文校正表”中矫正章草释文计82字。但不少的校正仍然颇受后人诟病,“我们暂且不深究其‘校正’是否完全正确,但至少能反映出以《急就章》为代表的章草字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37]766。
王世镗历时七年编撰而成的《稿诀集字》,在对历代章草进行追本溯源的同时,在实际运用上却多处挪用了不少假借、通假的方法,如“将‘眉目’写成‘攗目’。其草法既不见今,又不见章,执之私撰,令人费解”[47]。于右任创建的“标准草书”,以“文字救国”为根本,竭尽全力搜集一切与草书相关的书家及范本,除章草外,另有狂草、今草等文字。但结果仍不尽如人意,此中原因就是“于右任从草书的理想出发或许只能做到诸部首组织结构方式、代表符号设计的准确性,制定周详细密的操作条例,却无法化解‘标草’书写的便捷与识读之间的矛盾”[48]。
综合以上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及民国章草理论著作的剖析,可见章草书体在释正、草形、推广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不足。从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对松江《急就章》草形和释正的整理,以及笔者对《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的讨论中,可以发现,笔画脱泐、字形讹化、一形多字以及对草正考证的误差,都会导致一些章草文字处于多元解读而难以定型的状态,从而构成了章草文字本身固有的实用缺陷,也与《章草例》所感慨“松江本本字及释文之摹泐显明乖舛”[46]144的论点颇为一致。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章草自身,尚有一批字没有发展到完善的定型,没有规范写法,行草混写,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等现象一直存在,这就给章草的具体使用和流行造成了基本障碍。”[49]
章草本是极具艺术审美意味的传统书体之一,张怀瓘《书断》曾评:“天资特秀,若鸿雁六翮,飘摇乎清风之上。”[50]刘熙载《艺概·书概》亦云:“(索靖)书如飘风忽采,鸷鸟乍飞,其为沉着痛快。”[51]但在民国时期,章草贵在简易的实用性远在艺术审美性之上,且被社会激进的有识之士牢牢抓住,将之施用于文字改革并被研究到极致,“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书法的文化中心地位已被打破,因而来自书法的审美、文化性质已在整个文化艺术系统中被否认,书法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均依赖于汉字的实用性支撑”[52]。放眼卓定谋、王秋湄、王世镗、于右任等人的章草理论著作,皆主要为实用的需要而大力普及章草知识,即使如后来的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亦可洞见其考定草正对应、探寻文字发展规律的实用成分。
然而,深具“历史感”的章草“经历了从战国到西汉的长时间孕育发展,民众的熟识度较高,而民国时期的正体字是楷书,强行地将章草书安置在楷书的底下,又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实用章草书实施起来必定是异常艰难的”[53]。这表明“实用”与“历史”二者于文字而言,应是血脉相通、合为一体的。文字的成熟和规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规律和时间连续性,可谓其“历史”;将当下通行的文字付诸生活场域,适以叙事、记言及名物,可谓其“实用”。二者自主发展,流变有序。倘欲对千余年前的《急就章》等章草字形进行考定厘清,使之得以规范与统一,进而成为现行世界通用的文字符号。但事实上,由于字体本身固有的实用缺陷和历史语境的彻底置换而无法最终完成。基于此,卓定谋力图在考定、推广章草文字方案时,尝试对字形晦滞、数量有限且有多字重复[54]的章草书实行“组合成字,更以简易字体,不背章草之原则者以补之,务使字数足用”[27]绪论2,但民国承袭清末,与盛行章草的汉魏相较,“历千年未有之奇变”,文化变迁,语境有别,方式变更,观念迥异。这就使得《急就章》中一些来源复杂、形体生僻的章草文字,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让人难以识读。这种“介入”的书体,表面上似乎符合实用的特点,是“渐进”“调和”中西文字的折中举措,但实际上已与民国时期推崇的“进化论”背道而驰,很难令章草承载起民国文字实用的神圣使命,也无法真正得到一些具有西化背景的有识之士的全力支持,故而与时代难以适应,只能在文字改革中昙花一现罢了。
四、章草对当代汉字文化的启示及意义
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字改革潮流中,存在着拼音化、简化汉字等几种主要的改革方案。而以万国新语为代表的拼音化方案,认为中国国力的衰弱,与繁难、复杂的汉字息息相关,从而主张参照西方的语言系统,废止汉字,改用拼音化文字。但这种观念举措,显然仅仅只是救亡图存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应激反应,并不符合文字改革的内在规律,也不是汉字改革的内在要求,因而违背了汉字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容易陷入偏激和冒进之中。同时,若是废除汉字,那么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这种改革最终会导致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背道而驰,结果自然是难以成功的。
保留汉字但简化笔画的简化字方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成为汉字改革的首要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提上议事日程。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经过反复研究修改,1956年得到国务院批准。在制定过程中,草书依然是简化字方案的重要来源。而章草以其“简、省、变”等固有的实用性特点,再次成为文字改革参考的对象之一。根据黄震云对张芝草书的分析统计,“其中,章草80字,与简化汉字相同或基本相同写法的有6字”[55]。在1984年出版的《简化字总表》的考察中,也有“报”“庆”“书”“头”“兴”等字是参考汉简或《急就章》等章草名帖的类似字形,继而实行草书楷化而来。这表明章草不会因为民国文字改革的失败而彻底衰落甚至被社会所抛弃。相反,它在当今步入数字化时代、人们追求多快好省的社会潮流中,能积极发挥其本身由繁趋简、省便精炼且力求规范的文字性特点,故而应予以肯定。
同时应该看到,章草的实用性质在当代得到了一定的利用,其作为艺术性的书体也不能忽视。通过对章草的深入挖掘、整理及推广,孕育了一批杰出的章草书家和学者。除了上述所涉及的数位代表书家外,另有罗复堪、余绍宋、马一浮、郑诵先、王蘧常、沙孟海等书坛巨擘。这一章草书家群体的崛起,对现当代的书法创作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若置之于章草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蔚为壮观,可谓是“继汉魏、元明之后的第三个高峰”[56]。这些章草书家,虽生长于晚清民国,但多数在创作、理论研究上的造诣却是在步入新中国之后才得以形成的。他们承袭清末遗风,亦受汉简残纸的影响,且能把章草的“实用性”转向于艺术审美中来,故能通晓篆隶,碑帖兼容,创造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如王蘧常章草主碑,熔篆隶、汉简、汉匋、汉帛于一炉,在晚年形成生拙朴茂、气息静穆的高古书风,被誉为“蘧草”。高二适草书贵帖,提倡“草本于章”,并杂糅章、今、狂于一体,遂在20世纪中期开创出真气弥满、风神凌厉的“狂草新体”。沙孟海草书以碑入帖,苍劲老辣,晚年钻研《急就章》尤深,故书作气象博古,“体势在章、今、隶、行间”[57]。这些书家学养深厚,精通文史,乐于授学,留下大量珍贵的有关章草的书论著作与书法创作,培植了不少艺文兼备的书家俊彦,对推动章草在当代的发展和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尤其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出土文献的进一步挖掘整理,越来越多的章草墨迹不断公布于世。如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先后出版了《敦煌汉简》《尹湾汉墓简牍》《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等多种简牍资料,其中包含大量的汉草墨迹,能够“生动地展示出不同时期章草字体的真实面貌,为研究章草书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58]。这必然会克服民国期间因囿于时代限制所带来的因资料不足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能为章草字形及释正研究提供更客观的学术依据和丰富的文献依据。因此,通过借鉴这些章草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指导当代草书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则能使人充分认识章草形成的演变路径,科学地把握文字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当下乃至未来的文字改革提供参考和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堪比一座储存丰厚、取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大力深入其中进行挖掘和整理,从而为社会发展和文字改革提供厚实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盲目崇洋,全盘否定传统,全面废止汉字,导致走上一条无根可立的拼音化路线。因此,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理性地认识汉字的长处,增强文化自信心,在保持与外来语言交流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对方的优点来充实完善汉字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这是20世纪文字改革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