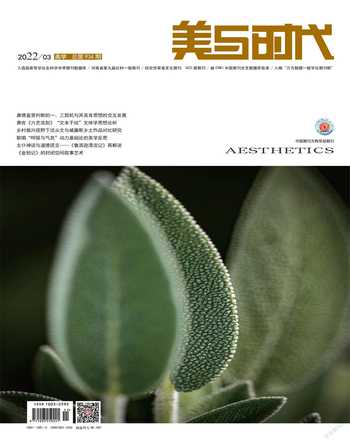民族审美与现代舞台

摘 要:建国以来,以民间传说、民族舞蹈二元构架为主体语汇的少数民族舞剧作为中国舞剧发展的重要类型不仅拓宽了中国舞剧的表现“疆域”,更在不同民族地域内引起了创作的“热潮”。广西作为壮、瑶、苗、侗、仫佬等多个民族聚居、杂居的地域,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推动了广西地域各艺术院团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并且在90年代以来中国舞剧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创作理念影响下,广西也催生着具有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传统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转型与探索。广西地域内这种既有传统又有时代探索特征的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发展历程突显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探索的“强区”形象,并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现代化、多元化发展进程。
关键词:少数民族舞剧;现代意识;民族审美;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重点学科和一流学科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建设经费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民间传说、民族舞蹈的二元架构之下,少数民族舞剧作为中国舞剧重要类型之一,“其特征在于主要用各少数民族舞蹈语言进行舞剧叙事,而最初又主要以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为表现内容”[1]。广西因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的先在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少数民族舞剧成为中国舞剧发展的重要类型之时,因其持续地开发、转化自身地域内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而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代表地域之一。新时期以來,在中国舞剧的少数民族舞剧、“交响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等发展趋势之下,广西各艺术院团以广西具有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传统为基础,进行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并以此为基础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创作探索。这种既有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传统与时代创新性的舞剧发展进程整体上建构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之路。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大型舞蹈诗《咕哩美》获得第八届中国文化部“文华奖”新剧目奖(1998)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获得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金奖(2000),大型壮族舞蹈诗剧《花山》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银奖(2016),及角逐2019年第十六届“文华奖”的大型民族舞剧《花界人间》(2018年创作)也显示着广西在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方面创作的价值与影响。
一、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重要地域
“舞剧创作与国家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休戚与共。”[2]少数民族舞剧作为中国舞剧的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初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舞剧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等时代发展趋势之下。贵州省歌舞团1960年演出的苗族舞剧《蔓萝花》(吴保安、肖联铭等编导,冀洲等作曲)因开创性地以苗族民间的代表性舞蹈语汇来表现民间传说的创作模式,其不仅“是新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最早成型的作品”[3],更被视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舞剧似乎并不过分”[4]60。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成熟与繁荣期,更是少数民族舞剧作为中国舞剧重要类型的本体建构与完善期。1979年四川傣族自治州文工团演出的傣族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刀国安、珠兰芳等编导,杨力、思聪等作曲)作为新时期的第一部少数民族舞剧揭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发展的序幕。藏族舞剧《卓瓦桑姆》(四川省成都市歌舞团,1980)、满族舞剧《珍珠湖》(辽宁省歌舞团,1981)、鄂伦春族舞剧《英雄的格斯尔可汗》(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歌舞团,1981)等不同地域内具有相应民族“首部”性质的少数民族舞剧借鉴、开拓或深化了苗族舞剧《蔓萝花》和傣族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改编民间传说作为剧性叙事主线、以地域内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为本体性舞蹈语言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类型。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由于受“交响编舞”“舞蹈诗剧”“舞蹈诗”及歌、舞、剧、声、光、电等现代舞台的综合演艺观念影响,少数民族舞剧在传承、深化80年代的民族性、民间性、地方性创作传统前提下,《春香传》(延边歌舞团,1991)、《阿诗玛》(云南省歌舞团,1992)、《土里巴人》(湖北宜昌市歌舞团,1994)、《云南印象》(云南印象歌舞团,2004)、《花儿》(宁夏歌舞团,2009)等也以“歌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等形式进行了与中国主流舞剧相统一的现代探索与发展之路,这整体上表现着少数民族舞剧多元化的艺术流变历程。
卢广瑞指出:“舞蹈语汇是构成舞蹈语言材料的总称,它包含了一切具有传情达意的舞蹈动作组合,以及舞蹈构图、舞蹈场面、舞蹈中的生活场景等。”[5]显然,从时间维度上看,1960年的苗族舞剧《蔓萝花》作为首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因其对民间传说故事原型的剧性主线把握和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合理编排、组合在中国舞剧发展史当中第一次呈现了少数民族舞剧主体语汇的本体性构成形态,即舞剧当中民族性、民间性及地方性的舞蹈场面、场景的生成及一种剧性的审美表现。可以说《蔓萝花》所构成的这种少数民族舞剧的主体语汇一方面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剧艺术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过程(也即“中国化”过程)当中“少数民族舞蹈都没有成为舞剧主体语汇:作为插入性的‘代表性’舞段,它们只是舞剧‘场景性’的缀饰”[4]136问题;另一方面也以改编民族民间传说的剧性主线和以地方性民族舞蹈的综合编排的演绎形式建构起了少数民族舞剧主体性的语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剧也是在《蔓萝花》的民族创作思维前提下,结合中国舞剧的“交响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等理念进行舞蹈、戏剧、音乐及声、光、电等演出舞台形式方面的诸多跨界与综合探索,以建构自身的时代发展与转型。
就少数民族舞剧的主体语汇而言,其作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舞剧类型,最初是以相应民族的民间传说的故事原型为整台舞剧演出的剧性主线,并强调对相应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舞蹈的综合编排,整台舞剧的舞蹈演绎与叙述也即是由这些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舞蹈节目所完成。少数民族舞剧这两点具有舞剧主体语汇性质的艺术本体建构了其与中国其他主流舞剧类型的本质性差异与艺术魅力。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交响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等理念的影响,少数民族舞剧在舞蹈、戏剧、音乐及舞台的声、光、电等综合表现方面都产生了诸多的改变与探索。这些改变与探索构成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舞剧(也可以说是中国舞剧整体)的新变化与发展。在这一过程当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少数民族舞剧与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舞剧的构成形态实现了“由既往的‘戏剧本体’向‘音乐本体’的转换”[4]211。简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少数民族舞剧大致是以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舞蹈节目编排来“言说”其民族的民间传说,以构成其整体的舞剧语汇,这种构成特征突显地是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舞蹈节目的重要性,其次才是民族的民间传说的价值;而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舞剧则是“按戏剧关系来‘结构’的舞蹈”[4]211,在这一过程当中舞蹈、音乐、意境、情境及舞台的声、光、电等综合表现技术都变得同等重要。这种具有“诗化色块”(于平语)特征的舞剧创作与演绎观催生了“舞蹈诗剧”和“舞蹈诗”等具有创作类型的少数民族舞剧的发展。
广西作为以壮族为主体,瑶、苗、侗、仫佬等多民族融合杂居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既产生了丰富的民间传说,也形成了代表各民族风情、审美和精神的师公舞、蚂舞、铜鼓舞、盘王舞、歌堂舞、芦笙舞、依饭舞、调套等少数民族舞蹈。据金涛在《中华舞蹈志:广西卷》一书中的考察,虽然由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广西现存的民族民间舞蹈(节目)也有300多个(种)[6]。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发展的大潮之下,广西歌舞团、广西彩调剧团、广西演艺集团、广西南宁市艺术剧院、广西北海市歌舞团等也以广西地域的民间传说为演绎主线和综合编排、衔接广西各少数民族代表性舞蹈的舞蹈语言的形式,创作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舞剧。可以说,无论是从民间传说的剧情演绎还是从少数民族舞蹈的主体性表现上看,广西作为以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为主体的地域,其多年来的舞剧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能够反映和表现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转型及发展的种种特征、形态。现有的史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末创作和演出的壮族舞剧《刘三姐》是广西最早的舞剧,这一经典的舞剧“曾五进中南海,四入怀仁堂,为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两年内演出500多场,演出规模、场次都创造了我国戏剧史上的记录”[7]245。由此说明,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渊源与影响。
纵观广西舞剧发展史,其整体的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主体发展与探索相统一。这不仅表現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创作演出了首部大型壮族舞剧《刘三组》(时间上比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舞剧《蔓萝花》略早),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柳江地区民族歌舞团1984年创作演出的苗族舞剧《灯花》(龙老太、於贤太编导,蓝寿生、朱诵邠作曲)、广西北海歌舞团1997年创作演出的大型舞蹈诗《咕哩美》(宋亚平、曾强、钟丽春编导)、广西南宁市艺术剧院1999年创作演出的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丁伟、冯双白编导,刘钢宝、刘可欣作曲)、广西歌舞剧院2001年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歌舞诗《漓江诗情》(张仁胜、温国鸣等编导,杜鸣、何超立等作曲)、广西彩调剧团2005年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剧《刘三姐》(新版)(江波、龙杰锋等编导,沈桂芳编曲)、南宁市艺术剧院2013年创作演出的大型壮族舞剧《百鸟衣》(章东新、李紫君等编导,孟可、丁纪作曲)、广西演艺集团2014年创作演出的大型壮族舞蹈诗剧《花山》(赵明、任卫新等编导,刘彤、赵程作曲)、南宁市艺术剧院2018年新改编演出大型民族舞剧《刘三姐》(冯双白、丁伟编导,李沧桑作曲)及广西演艺集团2018年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花界人间》(冯双白、佟睿睿编导,郭思达作曲)等大型的民族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作品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发展与探索的谱系,既整体反映与表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在“交响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发展趋势下广西少数民族舞剧一种完整的发展与流变特征,也以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场域”特征表征、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时代性和多元化的表现与审美维度,呈现出一种广西特有的创作经验与表现模式。
显然,自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从主体语汇还是内容及舞台表现方式上看,少数民族舞剧自身已实现了“从单一的依托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文化,发展为融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道具、舞美元素等到舞剧创作中”[8]的时代转型与发展。这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整体的现代化、多元化探索与发展之路。广西作为具有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的多民族聚居、杂居地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创作出了首部大型的壮族舞剧《刘三姐》,两年内500多场演出记录也足以表现出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所具有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在《刘三姐》的民间传说加民族舞蹈二元构架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语汇之下,广西一系列的少数民族舞剧及在鲜明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创作出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作品既完整、系统地呈现了广西具有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传统与时代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时代审美与探索方向。可以说,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重要和典型性的地域,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探索具有重要的地域特征与类型价值。
二、广西民族舞剧的民族审美与多元性探索
中国少数民族舞剧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创作与审美倾向,并相应地诞生了不同类型的演绎与探索形式,但作为中国舞剧重要的艺术类型,新时期以来(包括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其发展与探索形式显然也表现了明显的模式化特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发展特征,吴晓邦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舞蹈》一书中指出:“不少民族地区,在深入开掘与拓展舞蹈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填补了舞剧创作的空白,而且不断有各种不同艺术追求的舞蹈新作问世,形成了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争奇斗艳,携手并进的格局。”[9]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发展特征,其在民族的民间传说题材演绎和民间舞蹈综合编排、舞蹈诗剧和舞蹈诗的诗性表现,以及声、光、电的综合表现方面具有显著的类型特征。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探索的重要区域,新时期以来的发展与探索不仅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发展的整体性特征,更以一种广西地域的类型特征展现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发展的诸多现代性转型与探索思考。大体来看,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既遵循、演化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民间传说加民族传说的、民间的舞蹈相结合的主体模式,又以广西地域内的多民族文化为舞蹈的核心构成形态,进行舞蹈诗剧和舞蹈诗的创作与探索,进而逐渐建构起广西当代少数民族舞蹈的“文化”转向。
(一)民间传说与民族舞蹈结合的主体模式。广西地域内各民族都具有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在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潮流之下,广西地域内的各艺术院团亦是轻车熟路般地开展了以本土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结合的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我们看到,在广西获得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金奖的壮族舞蹈《妈勒访天边》当中,就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民间传说+民族舞蹈”这一模式而言,“民间传说”的整部舞剧的剧性主线即是由壮族民间传说《妈勒访天边》的原型故事改编而来,整部舞剧整体上也是在演绎传说当中壮族“妈勒”(即母子)远走天边为族人和人类寻找太阳的原型故事。而在“民族舞蹈”的本体性演绎方面,在具有的舞剧情节当中,《妈勒访天边》“有机融入了广西民族民间广泛流传的‘斗鸡舞’‘绣球舞’‘蜂鼓舞’‘板鞋舞’‘芦笙舞’‘铜鼓舞’‘抢花炮舞’等舞蹈”[7]230,整体上建构起《妈勒访天边》作为少数民族舞剧的主体语汇。很显然,“民间传说+民族舞蹈”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演绎的主体模式,其鲜明地被运用到《刘三姐》《灯花》《百鸟衣》《花界人间》等舞剧的创作当中。这一创作模式既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具有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优势,也表现着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舞剧重要地域的历史价值与形象。
(二)舞蹈诗剧和舞蹈诗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刘三姐》到新时期的《灯花》和《妈勒访天边》再到2018年的《花界人间》和《刘三姐》(新版),虽然“民间传说+民族舞蹈”的创作模式贯穿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全过程,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舞剧萌生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探索趋势,广西北海歌舞团和广西歌舞剧院在1997年和2001年也创作出了广西“首部”性质的大型舞蹈诗《咕哩美》(宋亚平、曾强、钟丽春编导)和大型民族歌舞诗《漓江诗情》(张仁胜、温国鸣等编导,杜鸣、何超立等作曲),整体上表现着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思考。“‘舞蹈诗剧’以淡化情节、弱化冲突为特征”[4]212,而“‘舞蹈诗’是舞剧创作单纯依赖‘交响编舞’而放弃情节、冲突、形象及个性的一个结果”[4]212,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破中国舞剧传统的“戏剧+舞蹈”的结构模式(本质上是以舞蹈为重),进而试图建构当代舞剧舞蹈、音乐(歌)、意境、情境及舞台的声、光、电等综合表现并重的结构,以还原、创造、表现舞剧艺术诗性、神性的特征。
《咕哩美》作为一部大型舞蹈诗,其以“歌舞诗”结构表现了北海地域的北部湾风情和海洋文化。在灯、网、帆三个篇章当中,分别以“渔灯谣”“月光光”“抢烟筒”“跳哈”“闯海”“颠船”“对花屐”“网娘”“升帆”“南珠赋”“扬帆”等歌舞节目进行诗性演绎,以表现北海文化的灯之“心”、网之“情”和帆之“意”。在这一过程当中,北海代表性的地域和民族舞蹈虽然还是本体性的表现形式,但其也得服从于《咕哩美》作为歌舞诗类作品诗性结构,即“以具象的、个体的、独立的、有意味的‘形式’来达到抽象的归结和‘内容’的表达”[10],以呈现、生发舞蹈、音乐(歌)、意境、情境及舞台的声、光、电等综合表现的诗性审美。在大型民族歌舞诗《漓江诗情》当中,张仁胜、温国鸣等编导更是“以民族歌舞、情景诗朗诵、音乐短剧、民族乐舞等综合舞台艺术为表现手段,立体演绎了广西漓江山水的自然魅力和民族风情”[7]201,表现着张仁胜作为中国实景演出大家的“实景”观念,呈现着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在舞蹈诗剧和舞蹈诗上的新探索与新思考。
(三)以“花山”为核心舞剧语汇的民族文化表达。新时期以来,在“民间传说+民族舞蹈”的创作观念影响下,虽然以“仙凡之恋”或“阴谋与爱情”为题材视角的民间传说一直是少数民族舞剧演绎的主要内容,但随着编导和演员的创作能力、表现能力及演绎能力的提升,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与演绎越来越表现出要超越“仙凡之恋”和“阴谋与爱情”题材的“樊笼”。换言之,即是希望以一种当代的文化视野重新审视民族的传说故事与舞蹈,这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文化”探索与追求。就广西而言,在其多民族杂居的区位优势之下,其不仅流传着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资源,同时也形成了具有象征性的民族文化。壮族作为广西人口最多的民族,“花山”(指花山岩画)文化既是壮族的起源文化,更是整个广西的文化核心。因而,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文化探索与思考意味越来越重的趋势之下,广西演艺集团在2014年也创作并演出了以“花山”为核心舞剧语汇的大型壮族舞蹈诗剧《花山》(赵明、任卫新等编导,刘彤、赵程作曲)。
作为一部以“复活花山悬崖千古岩画,演绎壮族先人生命密码”为目标的舞蹈诗剧,《花山》以代表壮族文化精神的铜鼓、绣球、蚂拐及壮锦四大元素建构着整部诗剧的太阳·铜鼓·男人(第一幕)、月亮·绣球·女人(第二幕)、繁星·青蛙·子孫后代(第三幕)及山水·壮锦和花山岩画(第四幕)的主要架构。并且以“红色”作为演员服装和造型(“红人”形象)、道具、舞台布景的色调(花山岩画的所有图案颜色都为红色),通过单人、双人及多人的铜鼓舞、蚂舞(青蛙舞)、绣球舞等舞蹈场景、情境演绎,既还原了远古时期壮族先人的生活、劳作、祭祀、爱情等场景,更以一种诗性和神性的剧场场域和感觉审美激起人们对壮族文化的想象与追忆。苏珊·朗格认为,舞蹈动作作为一种有情感特征的形象,“是通过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作用于我们全身的形象,是作为一个浸透着情感的形象而对我们起作用的”[11]。我们看到,《花山》在其创造的壮族文化情感空间和场域当中,它不仅使“舞蹈接近神性”[12],更让其表现出诗性的文化意味。
由以上分析而知,由于鲜明的民族区位优势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丰富的民间传说与民族舞蹈资源,在中国舞剧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趋势下,广西各艺术院团紧跟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大潮,以广西地域内不同民族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剧为题材和内容,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少数民族舞剧主体性语汇的剧目。并且,在中国舞剧的“交响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发展理念影响下,广西亦创作演出了具有广西不同民族特色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作品,这些不同类型、特征、风格的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创作与演绎,不仅逐渐建立起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经验和特色,更建构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强区”形象,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和中国舞剧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三、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探索的价值及意义
在广西地域内,由于受民族及其相应的舞蹈及地方性的舞台表现形式的综合影响,新时期以来的舞剧创作不仅基本上属于少数民族舞剧的范畴(舞蹈诗剧和舞蹈诗本质上是在广西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传统与架构基础上创作与创新而来),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发展潮流中都具有代表的类型价值与地域性探索意义。可以说,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舞剧或民族舞剧创作的重要和典型区域,无论是其鲜明的少数民族舞剧还是具有少数民族舞剧传统与特征的舞蹈诗剧及舞蹈诗等形式的创作与演绎都表现了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经验与模式。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发展与转型进程中,新时期以来广西系列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与演出既构成了广西地域内自身少数民族舞剧本体的探索与尝试历程,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发展的深度与本体性的流变特征。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发展的格局当中,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也具有显著的位置与影响。
(一)构建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探索的传统与“强区”形象
纪兰慰、邱久荣在《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当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思想感情了。”[13]广西亦是如此,由于广西一直是多民族聚居、杂居,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丰富的舞蹈文化与传统。因而,在少数民族舞剧成为中国舞剧创作与探索的重要类型的情况下,广西地域内的各艺术院团紧跟中国舞剧创作的发展大潮和国家及政府层面的文化和艺术要求,积极进行广西地域内的少数民族舞剧和民族舞剧创作。从60年代的《刘三姐》、80年代的《灯花》、90年代的《妈勒访天边》及新世纪的《百鸟衣》和《花界人间》,广西地域的各艺术院团不仅一直致力于以广西本土的民间传说和民族传统、民间舞蹈为主体性语汇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更以此传统与模式创作了大型舞蹈诗《咕哩美》《漓江诗情》及大型壮族舞蹈诗剧《花山》等作品,从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发展的整体性特征来看,广西地域内各艺术院团坚持少数民族舞剧主体语汇并不同探索新的舞剧表现的形式和可能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探索的传统与“强区”形象。
(二)呈现广西多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时代价值与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舞剧的“交响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及“诗化色块”发展理念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舞剧传统的“民间传说+民俗舞蹈”单一化创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让少数民族舞剧创作走上了舞蹈、音乐、意境、情境及舞台的声、光、电等综合表现技术并重的现代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舞剧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创作趋势,为不同地域内的艺术院团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将舞剧与地域内的戏剧、曲艺相结合探索的可能。于平指出:“广西历年来的‘舞蹈诗’创作也颇显业绩,北海的《咕哩美》、柳州的《侗》也都引人关注。”[14]在这种“舞蹈诗剧”“舞蹈诗”的创作理念影响下,广西地域内的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创作为了展现自身地域内的特色与差异,其一系列的舞剧创作既注重“民间传说+民俗舞蹈”这一传统的有地域优势的创作模式的新探索,也强调对广西地域内壮剧、桂剧、彩调、文场等艺术元素的特色介入或整合尝试,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将广西多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时代价值与影响的趋势。
(三)创造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广西经验与区域性思考
现代舞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与演绎十分注重现代舞台的声、光、电等技术的综合表现与运用。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舞剧的重要地域,其新时期以来的系列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一方面表现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和中国舞剧主流的舞蹈、戏剧、音乐及声、光、电技术的综合表现,更积极创造少数民族舞剧或民族舞剧创作的广西经验与区域性思考。我们看到,由于当前中国的实景演出技术最初始于广西籍导演梅帅元、张仁胜等人创作的《印象刘三姐》(桂林),虽然在此之后梅帅元或张仁胜在江苏、湖南、甘肃、云南等多个省市打造了具有地域风情的实景演出项目,但其作为一种现代的舞蹈演出表现形式也深刻地影响着广西地域内的舞台艺术诗性、神性的创造与思考。在这一具有广西特色的技术优势前提下,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实景”融合思考。实景技术的先驱之一张仁胜作为2001年大型舞蹈诗《漓江诗情》编导之一,在创作和演出过程当充分表现了他的“实景”理念。另外,广西演艺集团2018年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花界人间》(冯双白、佟睿睿编导)虽然不是由梅帅元或张仁胜直接参与创作,但其演出过程亦是运用了实景和3D技术,展现了当下舞剧演绎新的虚实、时间转换探索的形式可能。就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发展而言,广西少数民族舞剧既有整体的特征,又有广西地域特色的创作与演绎且拥有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广西经验与区域性思考。
(四)表征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现代化、多元化发展进程
广西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实践与探索的重要区域,在“民间传说+民族舞蹈”的标准创作模式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广西就以《刘三姐》(有1959年、2005年、2018年三个版本)、《灯花》(1984)、《妈勒访天边》(1999)、《百鸟衣》(2013)、《花界人间》(2018)等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作品呈现既有广西传统又有中国少数民族舞剧主流时代特征的探索之路。对9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舞剧的“舞蹈诗剧”和“舞蹈诗”发展潮流,广西也以可圈可点的大型舞蹈诗《咕哩美》(1997)、大型民族歌舞诗《漓江诗情》(2001)、大型壮族舞蹈诗剧《花山》(2014)作品,呈现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在“舞蹈诗剧”和“舞蹈诗”创作层面上的广西经验与广西模式。可以说新时期以来这些诞生于广西地域内,具有广西地域特征、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的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以一种相对完整的地域舞剧创作、发展及转型之路表征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现代化、多元化发展进程。就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创作与探索而言,广西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具有重要的区域价值与表征價值。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经过广西地域内各艺术院团的努力与探索,广西在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创作与实践方面都诞生了代表性的作品,并取得了较好的业界认可。在这种既传统又有时代探索特征的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创作过程中,广西各艺术院团积极进行广西地域内的民间传说、民族舞蹈与壮剧、桂剧、彩调、文场等姊妹艺术元素有效嫁接、移用、混搭,既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呈现了具有广西区域特征的经验与思考,更建构了广西地域内少数民族舞剧、“舞蹈诗剧”“舞蹈诗”创作的传承性谱系与脉络,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和中国舞剧发展现代化、多元化探索历程。
四、结语
就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二元架构而言,广西地域内各艺术院团以广西相应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和民族舞蹈为主体内容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呈现了中国少数舞剧创作的标准“样式”与审美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交响舞剧”“舞蹈诗剧”及“舞蹈诗”等理念影响下,广西各艺术院团也在自身具有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思维与经验之下,进行着具有广西多民族文化和壮剧、桂剧、彩调、文场等多元文化融合、混搭的“舞蹈诗剧”及“舞蹈诗”探索,这在整体上建构了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创作、转型及探索的时代历程,形成了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和民族舞剧的地域性、时代性、创新性的经验与思维。在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和中国舞剧新时期以来的发展进程当中,广西少数民族舞剧完整、多元的探索既贡献着地域性的舞剧创作经验与思考,同时也表征了中国少数民族舞剧或中国舞剧的现代化、多元化创作、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于平.从开放格局到开创新域——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舞剧[J].民族艺术研究,2019(1):104-125.
[2]叶笛.寻找中国舞剧的理性精神——记2018中国舞蹈高峰论坛暨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论坛[J].舞蹈,2019(1):15-22,14.
[3]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中卷(现、当代篇1911-2009)[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984.
[4]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60.
[5]卢广瑞.中外歌剧·舞剧·音乐剧鉴赏[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8.
[6]《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中华舞蹈志:广西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25.
[7]容小宁.超越·崛起:广西近十年来大型舞台艺术十大精品范例[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245.
[8]陈燕敏.从传统到现代——试析新世纪少数民族舞剧的演变[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5(5):52-55.
[9]吴晓邦.当代中国舞蹈[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30.
[10]冯双白.关于舞蹈诗创作中结构问题的思考——从大型舞蹈诗《咕哩美》谈起[J].舞蹈,1999(6):6-7.
[11]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
[12]贝林特.艺术与介入[M].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33.
[13]纪兰慰,邱久荣.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2.
[14]于平.花山的流韵壮乡的魂——观广西演艺集团大型舞蹈诗《花山》有感[N].中国文化报,2016-8-25.
作者简介:李颖涵,硕士,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