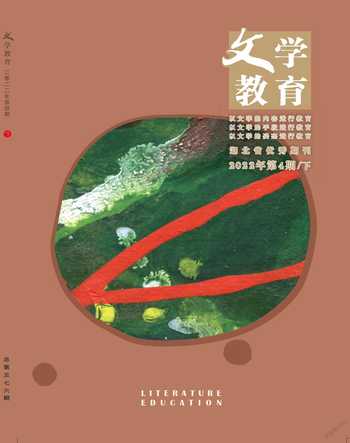汤婷婷《无名女人》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张盛美
内容摘要: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在其短篇小说集《女勇士》中讲述了与封建社会伦理秩序勇敢抗争的《无名女人》的故事。无名女人的悲剧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束缚的伦理语境以及不同个体对于突破伦理界限事件所做出的的不同伦理选择。作者运用文学想像回到其历史现场,为其伦理选择做辩护,歌颂了无名女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抗封建藩篱的勇气,同时也表达着自己在伦理困境中对于实现伦理身份建构的强烈诉求。
关键词:汤婷婷 《无名女人》 文学伦理学
当代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以讲故事为写作手段使得中国声音在异域文化中不再沉默。1976年,汤婷婷的自传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出版,引发热议,荣获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该书详细地描述了第一代美籍华人的经历,将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她的家庭漂洋过海到美国的经历巧妙结合。该书副标题为 “生活在群鬼间的少女的回忆”,共有五章:《无名女人》、《白虎》、《巫医》、《西宫外》和《胡笳怨曲》。尽管汤婷婷出生于美国,但其作品包含丰富的中国元素,蕴含深刻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关怀。年幼时母亲讲述的中国传统故事以及家族经历成为汤婷婷的写作素材,同时她也基于自身生活经历,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力图阐述东方伦理秩序下具备不同伦理意识女性的迥异命运。
《无名女人》(No Name Woman)是湯婷婷的处女作《女勇士》的第一篇。故事背景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婚之夜姑姑的丈夫远赴美国淘金,音信全无,但两年后姑姑却怀孕了,因而被指与他人通奸。家人也因此受到连累,遭到族人和村民的谴责与冲击。蒙羞的姑姑在生下孩子当晚便怀抱婴儿投井自杀。守活寡的无名女子为追求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打破身处的伦理禁忌,却终究难逃命运以及道德的束缚,生产后带着婴儿自杀,以死亡向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宣战,成为男权社会的复仇女。因此,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阐释小说所处的伦理语境以及伦理秩序,分析了主人公无名姑姑所面临的伦理冲突及其做出的伦理选择,从而发掘汤婷婷的家庭伦理观、两性伦理观以及社会伦理观。
一.伦理环境与伦理秩序
伦理环境(ethical environment)又称伦理语境,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从道德哲学层面出发,无名姑姑与婚姻关系之外的男人私通并怀有身孕,突破已为人妻的伦理身份,触犯了身处的伦理禁忌,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作为妻子,她没有尽到忠诚于丈夫的责任义务,藐视和破坏了正常的人伦关系。然而依据文学伦理学批评,若要探究无名女人越轨行为的真实动因,必须回到她当时采取这一行动的伦理现场,在客观的历史语境中,站在她的立场上审视动机与目的,进而从道德层面对其行为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在村民乃至家人的眼中,无名姑姑是一个可以被奚落、谴责,最后被遗忘的禁忌者。但只有真正的同她站在一起,她的委屈以及她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被理解。汤婷婷也运用想像试图复刻无名姑姑的历史现场,从伦理立场去理解姑姑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做出的伦理选择。也许姑姑是个一向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传统中国女性,奉家长的意志与素未谋面的小伙子定了亲。哪怕与她拜堂的是一只大公鸡,她也发誓这辈子都是他的人。但新婚丈夫远赴美国,她被别的男人强迫,难以逃脱遭强奸的厄运。在袒露自己怀孕一事后,被那个男人以及纠集的一帮人抄了家。但也有可能,姑姑继承了家族向外的强烈冲动,受够了凝滞的生活,主动越过了无形的伦理界限。在某个时刻,她遇上了那个让她心动的男子,于是她抛掉家庭,突破对于戒律的恐惧,奋不顾身,一心为爱。又或许她本就是个野女人,把大量的心思花在梳洗打扮上,试图以别出心裁的魅力吸引情人的接近。无名姑姑顺从内心的自然选择因为改变了其伦理身份、违背了伦理秩序,进而致使其陷入伦理困境。村民及家人只关注姑姑的悖德行为招致的不幸后果,并迅疾地采取惩罚行动以展现道德伦理的权威性,但却没有人真正地询问过姑姑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关心过姑姑作为独立个体的想法与感受,更不必说站在她的立场上探寻其行为实施的缘由。父权制、家长制强调家庭以及族群中的男性权威,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等级鸿沟尤其明显,无名姑姑乃至其他女性个体被迫沦为男性权威的附属品,难以完全按照个人想法主导个体生活。
作者试图回到无名姑姑所处的历史场景,站在她的立场上剖析其行为动机,同时也看到当时社会对于伦理秩序的推崇、对于女性权利的漠视乃至践踏。无论姑姑是何种性格,出于什么动机,被迫亦或是主动,其越轨行为冲击了原本和谐平静的村庄伦理秩序,并因此受到族人以及家人的谴责。中国人跟西方人在精神方面的最大差异就是中国人的伦理本位。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伦理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在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准则与规范,一般指已经形成并为人们所认同、遵守和维护的集体的和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标准。“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礼教仍是社会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戴婷婷,2014:115)。“男尊女卑”仍是社会两性关系的常态,“三从四德”是女性需要奉为圭臬的不二法则。传统中国社会尤为看重女子的贞洁,女人要守妇道、尽孝道。因此姑姑的越轨行为在其历史语境下违背了当时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放纵乃至放荡的存在,是家庭乃至村庄的耻辱。
二.伦理冲突与伦理选择
在人类文明之初,维系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无名姑姑坚持个人对爱情和美的信仰,突破伦理禁忌,不愿放弃成为人母的伦理诉求,最终导致追求爱情和人伦梦想的破灭,遭受到社会的唾弃和家人的遗弃。无名姑姑的个人追求与当时社会伦理秩序相悖,继而产生伦理冲突,在村庄以及家庭里引起轩然大波。
无名姑姑是中国男权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一个缩影,她的悲剧反映了所有“越轨”女人的痛苦命运。对子女的主婚权以及对家属的惩戒权最直接展现了无名姑姑所处的父权制家庭对女性运的干涉与掌控。在婚配这件事上,她没有选择权,因而嫁给了婚后便远赴美国淘金的丈夫,空有为人妻的身份。长期寂寞以及缺少束缚感使得姑姑在与其他男人的交往中伦理意识愈发薄弱,非理性与激情占据上风,最终突破伦理禁忌,并因伦理身份改变而陷入伦理困境。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陷入伦理混乱的局面,姑姑的悲剧都是时代的产物。父权社会下,女性向来都是受压迫的对象,她们没有话语权,沉默是她们的保护色,她们也习惯了沉默。无名姑姑被指通奸,在村人和家人的谴责侮辱中,她却始终没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从分娩到死去,姑姑始终把男人的名字埋在心中,从未责怪他没和自己一起受罚。为保全情夫的名声,她一个人默默生下孩子。出于良心和诚实,她应该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但是她如果说出了孩子的父亲,则会毁灭孩子的父亲。而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她愿意看到的,因此无名姑姑面临的选择是伦理两难选择。而孩子的父亲也确实从始至终没有站出来承担他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义务,甚至有可能已经成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姑姑的那批人中的一个。无名姑姑通过选择保持沉默和投井自杀的方式,与父权社会法相抗衡。
伦理秩序是村庄的至高法则,无名姑姑私通怀孕于她个人而言是耻辱,对整个家族甚至村庄而言也是名誉的玷污。对姑姑的惩罚先从村民开始。他们看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会断送未来,报应会落在后代头上”,于是他们要替天行道,谴责姑姑的败德行为,加快报应轮回。人们不关心谁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男人,“没有人说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讨论这件事”(Kingston,1976:3),却急于严惩这一“不规矩的女人”,“他们坚持要治她的罪,让她遭现世报应”(Kingston,1976:14)。处于当时伦理语境的村民做出了惩罚姑姑及其家人的伦理选择,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道德的、合乎规范的。他们借神灵庇佑的名义冲进姑姑的家,做着名义上驱鬼辟邪,实则是打砸抢掠的行为。姑姑的放纵遭此惩罚归根结底还是招致了村民的嫉妒。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通奸在乡村伦理语境中不单是心理的放纵,更是犯罪。村民们没有胆量突破长久形成的穩定的乡村伦理秩序,而姑姑践行了他们本能里想要实施却未成行的冲动。
无名姑姑所受的惩罚不仅来自有着地缘亲近的邻居的抨击谴责,更体现在拥有血脉亲缘的家人的咒骂、埋怨以及后来闭口不谈的遗忘。姑姑也是他们曾经珍视如宝的唯一的女儿,但却因此事被家人看做是害了全家的鬼,成为被否认的存在。“别告诉任何人你有个姑姑。你爸不想听到她的名字。她从来没有出生过。”(Kingston,1976:17)突袭抄家是对姑姑越界行为的惩罚,但更为深刻的惩罚,是自家人的故意遗忘,生前受辱,死后也不被饶恕。于个体而言,名字的作用和力量是巨大的。没有了名字,《无名女人》中的姑姑也就失去了身份。她被家族除名,不仅在族谱上,也在未来的生活里。因为她私通生子不仅是个人的耻辱,也使得家族蒙羞。家庭在这个故事中也同样充当了使这个“越轨”女人成为受害者的角色。他们剥夺她的权利,否定她的存在,禁止讲述她的一切事情,试图抹去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印记。
三.伦理诉求的身份追寻
美国华裔女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得汤婷婷的文学创作注定摆脱不了其身份、族裔、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双重性”的特征,既受到中华民族传统儒家伦理的的影响,又融合了美国契约伦理的规约。父母传达的中国传统观念与实际生活中接受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产生的冲突碰撞加重了她们对于文化身份的困惑感。在现实与虚构的文学叙事中,汤婷婷通过回顾与再现无名姑姑的伦理选择与伦理意识,在文学想像的伦理叙事中建构和彰显自身的道德意识、价值立场和伦理诉求,实现自身对家族历史、身份归属的追溯。
无名女人的故事是汤婷婷文化寻根意识的直接反映。汤婷婷将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主人公作为叙事主体,在异域文化的文学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汤婷婷出生并生活在美国,故乡于她而言仅仅局限于母亲所建构的故事世界。但父辈一直牵挂着的远方家乡以及刻在骨子里的身心记忆早已不着痕迹地影响了汤婷婷的生活。母亲讲述的家族故事串联起她与祖先前辈的关联,更使其开始探究自身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从单纯地听故事到创造性地写故事的转变便是汤婷婷在身处西方文化之下对于东方文化、家族传统的深度探寻。
无名女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汤婷婷受中西两种文化影响下不同于家族先辈的伦理认知与诉求。无名姑姑的言行于家族、村庄而言都是羞于提及甚至招致唾骂的丑事,因此他们努力地想要抹去她的存在,与她相关的记忆。即便是多年后母亲冒险将往事和盘而出,也会在故事伊始嘱咐女儿不要对外宣扬,将无名姑姑看作是赤裸裸的反面例子。因为在父辈心中,无名姑姑逾越了道德伦理界限,而这种逾矩行为破坏了宗族名声,不符合他们长久以来的伦理信仰。汤婷婷不熟悉也难以理解家乡传统中对于女性诸如三从四德等的道德伦理规范,甚至在描写相关场景或事件时借助了与中国实际有出入的文学想像做补充。因此在无名姑姑的故事里,她更多的看到的是身处封建藩篱之下女人追求自我诉求的勇气,最大化的表现了作为个体为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巨大努力。因而她愿意站在无名姑姑的时空场域思索她所作选择的合理性,并试图为其合理化做辩解。
对无名女人的书写叙事是汤婷婷试图突破自身伦理困境的勇敢尝试。母亲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本意是一种劝诫,一种警示,希望女儿以此为戒,不要像前人一样走入人生歧途,陷入道德困境。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汤婷婷却以文学为手段,传达与之相悖的教诲意义。她把无名女人看作是人生的勇者,在其身上感受到女人突破传统桎梏的勇敢与力量。面对族裔、性别的偏见,汤婷婷试图通过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向读者传达少数族裔的女性也有权利追求平等,打破世俗偏见,实现自我追求。复杂的文化身份使得汤婷婷陷于伦理两难的境地,但也为汤婷婷提供了看待事物的新角度,双重文化影响下有差异、碰撞,但也可以做到化解与融合。在书写无名姑姑如何进行自我选择的过程中,汤婷婷也在表达着试图化解自身身份问题的自我伦理诉求。文化双重性促使其在故事书写中探寻自身伦理身份问题,同时更成为其作家身份的亮点所在。从无名姑姑的伦理场域回到汤婷婷自身所处的伦理环境,相比传统道德对女性的伦理规约,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遵从本心的勇敢抗争更占上风,成为汤婷婷可以化用以应对自身生活困境的伦理启示。
“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Kingston,1976: 3)。某种程度上,汤婷婷遵守了对母亲的承诺,她没有将故事宣之于口,而是以文字的形式昭示世人。无名女人的故事只是母亲对年少女儿初潮时的告诫,但作者所处的社会伦理环境已不再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作者从母亲叙述的东方伦理传统的伦理身份和禁忌中品读出不一样的内涵。无名女子的悲剧在家人以及村人看来是耻辱,是避之不及的隐晦,但作为新一代美国华裔,作者眼中的无名女子成了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敢化身。无名女子是中国传统女性追求自由、勇于对抗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颠覆东方伦理秩序的女勇士。汤婷婷将无名女人故事诉诸于笔端呈现给读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父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抗和斗争。汤婷婷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子,一直以来也深陷中美文化夹击的伦理困境,在以文字讲故事的过程中,她也在“建构自身独立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观念,从而阐释其渴望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的伦理诉求”(李书影,2012: 40)。
参考文献
[1]Kingston, M. H.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2]戴婷婷.父权制度的双重统治——试析汤亭亭的短篇小说《无名女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02):115-116.
[3]李书影.伦理身份逾越后的悲剧与赞歌——评《女勇士》中的无名女子形象[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03):38-40.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32(01):12-22.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