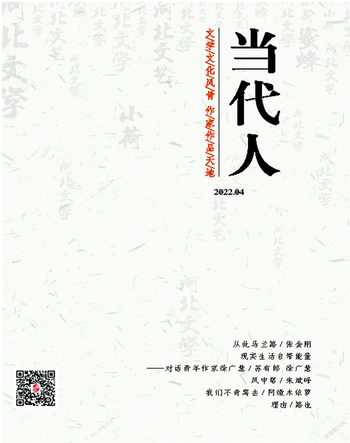我们不肯离去
他那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站着一支钢笔,金色的笔盖露在外面——这不是一个教书先生,这是我爷爷日常的穿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炊事员。他的钢笔经常用来记录多少个鸡蛋,多少斤肉,每个月开销多少等,我们曾在某个小本子上看到那些流水账。
不过现在,他不在我们眼前。他正在给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煮饭。现在是早上大概八点钟。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们的上学之路必须经过乡政府,爷爷煮饭的厨房就在这条路的坎下,炊烟就像其他人家的炊烟一样,总是朴素地流到天上去。炊烟里有肉味传来——肉质偏红的腊肉(他们多数时候在吃这个),新鲜的红辣椒和绿辣椒,新鲜的蒜头,晾干了水分但麻味不减的大红袍(花椒),然后是烧烫了的油锅,所有食材依次放到锅里翻炒,我爷爷的厨艺非常好,他一定是这么做的,我们通过嗅觉已经“看”到那盘漂亮的菜起锅了,香气四溢地摆在灶头一角。
我们不肯离去,站在路上,伸着鼻子,天不亮时下着雨加雪,现在完全只在下雪了。身上披着父母用破胶纸为我们制作的“风雪大衣”。“再过几天就放假了,知道吗?熬一熬就过去了,知道吗?”父母总会这么说,只要下大雪,他们就这么说,已经懒得找新鲜的话了,如果觉得很爱我们的时候,才会低头伸手抱一抱。我们踩在雪上,身体之外的地方还飞着雪花,包括炊烟,也被大雪打乱;我们有时睁不开眼睛,只能尽量睁开鼻子,让它在爷爷此时翻炒出来的香味里,不仅仅找一点想象中的温暖,也找一点饱腹感。走了一段长路,我们又累又饿,但尽量不说话,挪动脚步也不敢大声,我们的爷爷不太喜欢我们站在厨房背后闻炒菜的味道,这个样子只会让他觉得丢脸,让他以为我们又要像去年或者前年的某一次,跑到他的厨房里偷东西吃,他会睁着那双祖传的大眼睛瞪着我们的眼睛,再瞪着我们的嘴巴,他大概希望我们把吃掉的食物都吐出来。就是那样,我们的爷爷脾气好大,他跟别人的爷爷不太一样,我们都觉得他身上有大雪的味道,有时候更会坚信,我们的爷爷是个雪人。
我们不肯离去,就像这儿有一把刀子逼着我们的脖子,如果谁的头往前伸一下,谁的脚往前走一步,脑袋就会从上面滚下来。
锅里“欻”地一声,我们听见一瓢水下了锅,我们跟着一阵激动,因为接下来,爷爷会走到厨房门口大喊一声“吃饭了”。这三个字会把我们的心喊得“亮”起来。他会把这几个字的音调拖得尽量长一些,让每一个字都传进那些工作人员的耳朵里。
“吃——饭——咯——!”听吧,他开始喊了,用标准的方言那么有劲儿地喊道,像一只打鸣儿的老公鸡,在这个地方喊了差不多十年啦。我们听到了,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但,当然啦,就像我们妈妈说的,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但幸福并不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爷爷的喊声能听到的人都能听到,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跑过去吃饭。我们站在这块地方还不能使他发现呢,最好住在乡政府旁边的人家也不要发现,否则他们就会喊着我爷爷的名字说:“嗨,那不是您的亲孙子嘛,哈哈哈,您的几个儿子给您带来了不少后代呀,您可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只是他们看上去好像有点儿可怜。您的儿子们都是穷人,您的孙儿们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到您这儿正好走了一半,肯定是饿了,他们在家里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应该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对吧?就算吃了一大碗玉米糊糊,几泡尿就尿完了,恐怕大人走到这个地方也饿了,您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进去吃点儿东西呢?您以前一定没少让他们进去吃饭吧?瞧瞧,您在这儿煮饭,厨房里什么都不会缺,您随便匀一勺就够填饱他们的肚子,您不要觉得过意不去,这是人之常情嘛,您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炊事员,我们这些人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坐在那儿吃饭的人知道了也不便说什么,他们才不会计较那么一勺两勺饭,对吧……您一定经常接济您的儿孙们吧?”我爷爷会在那些人说了这么一肚子话走了之后……“哈哈哈哈!”……他会笑得比平时大声,让那些人走去老远还能听到,随后脸色就沉下来,就像我们伤了他的心那样,黑洞洞的夜空似的脸庞上那双发光的眼睛,直戳戳地看着我们,看得我们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他会什么都不说,或者问我们的爸爸干什么去了,是去哪儿要饭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没有人管,任由我们在这儿晃来晃去,像是来这里故意“戳”他的眼睛。
他最好别发现我们呀!
我们听到吃饭的人已经走到厨房门口了。大人们的嗓子里像是塞满了炸药,他们有时候说话特别大声。我们听到有人抽拿碗筷的声音,然后抽拿凳子的声音,随后,我们就开始想象到,那些一个一个的屁股落座上去,开始扒饭,开始夹菜,开始咀嚼……噢天呐,香味贯穿他们!
我们的爷爷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的人,出于一个老炊事员的本分,他要先看看吃饭的人的表情,看他们是不是吃得很满意,从那些愉悦的表情中,他可能會获得某种成就或幸福感;毕竟他最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厨艺,即便真正的职业其实是木匠。
我们稍微挪了一下脚步,轻微地,不踩出雪的声音,此时只剩下三个人了,我们的哥哥已经忍受不了吃饭声,拔脚走了。后来只剩下两个人——我,还有弟弟。我们两个站在雪地里不肯离去。主要是我弟弟不肯走。
他也不是不愿走,是他的脚不愿走。
我们姐弟只有一双鞋子,换着穿,大概每个人可以穿着鞋走两百米,然后脱下来给另一个人,反正总是有一段路,我们两个都要轮流打赤脚。轮到他赤脚的时候恰好走到爷爷的厨房背后。他还剩下大约一百米的样子才有鞋穿呢。
本来我们各有自己的一双鞋,他那双彻底坏了,鞋底不仅脱落,还碎了。是他一次一次往返在上学的路上给踩碎了。我们翻着那双破鞋仔细研究了一下,找根草捆绑也不行,完全没用了,就算我们的妈妈看见了也无可奈何,它甚至碎得有点可笑,因为实在是太碎了呀,那会儿我们实在忍不住笑起来,要不是天气冷得把笑声冻住,还打算多笑一会儿呢。我弟弟将鞋子抓起来,扔到了路坎下。我们的妈妈还以为那双鞋子至少还能穿一天,她明天再去借钱或者想办法缝一双。呵呵呵,她总是低估这些山路,就像我们的老师说的,人总是低估了生活……生,然后活。
我们听到有人吃完饭出了厨房。他们一定很暖和了吧,不仅脚感到暖和,整个身体都会暖和,对于他们来讲,天空也不再下雪了吧。
我弟弟的脚早已不知道冷,可能一个人要想暖和,只好与“冷”合二为一,成为“冷”本身。他跳了跳脚,有点站不动了。香味在风雪中早就散了,是我们的想象中还萦绕着那种丰富的味道。
我们稍微往前走了几步。
“该走了,”我说,“要迟到了。”
我弟弟继续跳脚,像是要在这儿玩雪。
“往前走一百米,你就有鞋穿了。”还以为这句话会给他带去多大的吸引力。
“再闻一会儿吧。”他说。
我们的妈妈说得对,食物才是人类的天堂。难怪她们成天在庄稼的丛林里忙得像只狗熊。
我们的爷爷突然就出现在眼前,他从断墙那边过来,断墙里面种了他的葱和蒜以及芫荽(这是以前,现在这个天气里啥也没有了),他肯定是在断墙围着的那一小块菜地里散步,背着双手,略微弯腰,在里面转来转去,就像村里那种转圈圈追自己尾巴的狗。他低头看着我们,就像老天爷下大雪覆盖我们。
我们应该这样做的,如果弟弟愿意配合的话,他这个时候最好突然咧嘴大哭,我再装模作样气呼呼地给他脸上来一小巴掌,让爷爷认为这是两个孙子走到这儿闹矛盾打架了,不是刻意站在这里闻别人的菜香。可是弟弟今天跟往日不太一样,他居然是一副有点气势汹汹的生气的面孔,他不是那种特别会表达自尊心的孩子,他只是气鼓鼓地,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想象他的怒火到了哪种程度。
爷爷非常淡定,不慌不忙地问我弟弟:“你咋啦?”
现在可有好戏看了,一个从来不会问我们“咋了”的人,居然问了,一个从来不表达愤怒和伤心的人,居然也表达了。我有点激动。
“我问你咋啦,你咋不说?”爷爷必须得到答案的语气。
弟弟抬高了脑袋,就像大雪覆盖的细草费劲但勇敢地钻出雪地,把脑袋的尖子戳到天上去了。
“你宰鸡给那几个人吃!”
“你说啥?”
“某某某家的娃儿!”
爷爷脸色阴沉沉。哈哈哈,我就知道,他会是这个样子。他最听不得我们提起某某某家的娃儿,那三个孩子可是寡妇某某某的孩子,他对他们比对他的儿子们都好,风言风语早就弥漫到每一个角落,他虽然一点儿也不顾什么,可是如果他的孙儿——我们——只要谁嘴巴里冒出相关的一个字,他就总会生气。他有一次杀鸡给那三个孩子吃,而当时,我和弟弟本来也很饿了,故意走到厨房门口,看看是不是可以弄到一口吃的,可我们看到的却是那样的场景——三个孩子正在狼吞虎咽。那三个孩子都是我们的校友,其中一个女孩子是我的同桌,随后,事情过了好几天,就在我们的课桌上,我有很多次几乎从她的嘴角边看到我爷爷宰给她吃的鸡爪子;反正,看到她的嘴我就生闷气。“他妈的!”这本来是我弟弟爱说的脏话,后来天天挂在我心里。我们的友情变得很尴尬,本身我是多么喜欢她,喜欢跟她一起聊天,喜欢与她去松树林找菌子,喜欢谈成年以后要去远方,并且,我也喜欢她的妈妈,那个可怜的丧偶的中年妇人,她总是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儿,我们路过她家门口,她会喊我们进去吃饭,有时候我们故意进去找水喝。有人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天天进去找水喝,没准儿能遇见你们的爷爷,当然自从有人这么指使我们进去找水喝以后,我们就不去了,大人们的心思总是比我们的心思复杂并且令人讨厌。后来就完蛋了,我和我的同桌,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根本无法正常交流,她知道我看见她吃鸡了,我也确实看见她吃鸡了,可她不知道如何解释那只鸡,我也不敢问。
我本来强制性地忘记了这件事,可是弟弟居然又把旧事翻出来,呵呵,就在这个时候,他赤脚站在雪地上,一副什么都不害怕的样子。
我们的爷爷脸色阴沉沉,我就笃定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还不快走,你们要迟到了!”
爺爷丢下这句话就走了。茫茫的背影留给我们,后背上落满了雪花,其实啊,他也孤零零的,有些可怜呢,大雪下在他身上,他又继续把雪下到地上,他只要回家,我们的奶奶就会无限次地数落他,说他是个野人,他也确实越来越像个野人。野人大概是不需要回家的吧,或者他时常觉得回家没有意义;可是野人也需要有人爱他吧,在这个世界上,他孤零零的,在此刻的大雪中,他孤零零的,只要有人爱他,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野人肯定没有人真正爱他,至少无法真正爱他,那些爱只是一场大雾,不然他为什么像个雪人一路掉着雪花,孤零零的。可我不能把这些话说给任何人,他们说,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弟弟吸了一口冷气,等到爷爷走得看不见身影,我们才从厨房背后离开。走了大概一百米,我把鞋子脱下来递给他,上学的路还很长,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弄明白了,一个人只有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们被大雪覆盖,路也被覆盖。
(阿微木依萝,彝族,自由撰稿人。已出版小说集五部、散文集两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