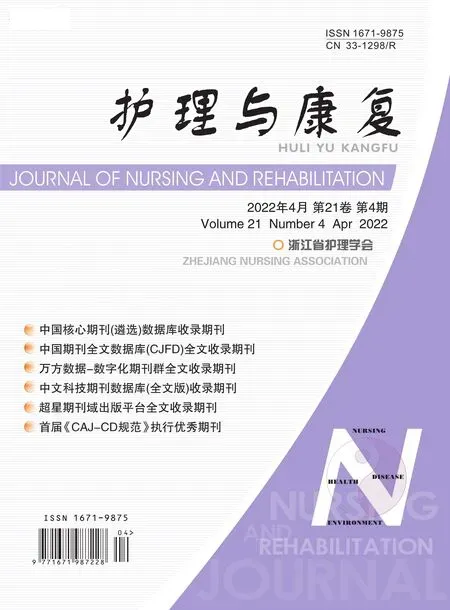抑郁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生存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姚 露,汪梦鑫,陈 姬,陈雪萍,林小迎
1.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 311121;2.浙江省时代养老服务评估与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1121;3.杭州金家岭金色年华退休生活中心,浙江杭州 310024
目前,我国有214.6万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1],但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低于家庭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2-3]。在养老机构中,随着年龄的增加,多数老年人面临机能渐进性下降、内在能力减弱的问题,其中,衰弱是较典型的综合征,指个体在多病因机制下保持机体稳态的能力被削弱,处于健康和失能的中间状态,严重影响生存质量[4]。此外,衰弱和抑郁密切相关[5]。由于衰弱所致肌肉力量减弱、活动和自理能力下降,老年人易产生健康和社会关怀期望,但在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多层次照顾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持续性满足[6],因此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出现抑郁。抑郁则可引起神经内分泌改变,引发病理反应,是生存质量的负性预测因子[7]。但衰弱和抑郁如何同时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并不明确。基于上述分析,推测衰弱通过抑郁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因此,本研究探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抑郁及生存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探究抑郁在衰弱和生存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7-9月选取杭州市3家养老机构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纳入标准:年龄≥60岁;入住养老机构满6个月;能够独立或者拄拐行走;认知功能正常;能正常沟通者;自愿参加本课题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严重精神、视力、听力、语言障碍者;合并有严重躯体疾病者。依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样本量需在100例以上,200例以上更佳[8],本研究拟定样本量为200例,考虑10%的样本流失率,最终计算所得样本量为223例。本研究实际纳入样本量为240例。本研究已通过杭州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伦理审批号20190072。
1.2 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问卷
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和健康状况资料(每周运动时间、患慢性病情况等)。
1.2.2简版老年抑郁量表(short for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
本研究采用唐丹[9]翻译的中文版GDS-15,量表包含15个条目,按“是”或“否”评分。计分范围为0~15分,得分越高则抑郁症状越严重。0~4分为无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分为中重度抑郁。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重测信度为0.73。
1.2.3衰弱表型量表(Frailty Phenotype,FP)
该量表包括自然体质量下降、步行速度慢、握力低、躯体活动量低及自诉疲乏5项指标。每项指标符合记1分,不符合记0分,计分范围0~5分。评分0分为无衰弱,1~2分为衰弱前期,≥3分为衰弱[10]。
1.2.4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评估简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Quality of Life Brief Scale,WHOQOL-BREF)
该量表包括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环境领域,共26个条目,均按1~5分计分,每一领域得分为该领域条目的平均分再乘以4,得分越高患者生存质量越好[11]。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0.88[12]。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时由研究者向老年人讲解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取得老年人的同意。不会写字者由研究者面对面访谈填写,问卷当场收回并检查是否填全。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40份,回收率为100%,剔除连续单一选项问卷或重复问卷7份,有效问卷233份,有效率为97.0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验证衰弱、抑郁和生存质量的相关性。采用Amos 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Bootstrap检验法对抑郁在衰弱与生存质量间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养老机构老年人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33例养老机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3.63±8.88)岁,一般资料见表1。
2.2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及抑郁和生存质量现状
233例养老机构老年人中,衰弱前期老年人99例(42.49%),衰弱93例(39.91%);轻度抑郁54例(23.18%),中重度抑郁17例(7.30%)。在生存质量方面,养老机构老年人生理领域得分为(14.05±2.45)分,心理领域得分为(14.14±2.53)分,社会关系领域得分为(15.09±2.22)分,环境领域得分为(14.87±1.88)分,总分为(58.15±7.69)分。
2.3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及抑郁和生存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抑郁和生存质量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

表1 养老机构老年人一般资料及衰弱与抑郁和生存质量的单因素分析(n=233)
2.4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及抑郁和生存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与抑郁呈正相关(r=0.562,P<0.01)。衰弱和生存质量总分呈负相关(r=-0.532,P<0.01);抑郁与生存质量总分呈负相关(r=-0.692,P<0.01)。进一步分析衰弱、抑郁与生存质量各领域的关系,衰弱与生存质量各领域均呈现负相关(r=-0.494~-0.386,P<0.01),抑郁与生存质量各领域均呈现负相关(r=-0.679~-0.520,P<0.01)。衰弱、抑郁与生存质量各领域间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及抑郁和生存质量各领域间的相关性分析(r)
2.5 抑郁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生存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单因素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建立以衰弱得分为自变量,生存质量总分为因变量,抑郁得分为中介变量,年龄和每周运动时间为控制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各拟合度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表明模型拟合理想,见表3。模型显示,每周运动时间可直接正向预测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年龄直接负向预测生存质量。控制年龄和每周运动时间两个变量后,衰弱对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140,衰弱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542,抑郁对生存质量的效应为-0.649,衰弱通过抑郁对生存质量的间接效应为-0.352,总效应为-0.49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71.54%。抑郁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生存质量间有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表4。
3 讨论
3.1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及抑郁和生存质量现状
本研究调查的233例杭州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中,衰弱的发生率为39.91%,高于南京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调查结果(30.7%)[13]。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两项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年龄差异所致。衰弱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本研究养老机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3.63±8.88)岁,南京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1.38±8.59)岁,故衰弱发生率略高。本研究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为30.47%,与张夏梦等[14]机构调查结果接近,但一项Meta分析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率为25.55%[15],提示本研究中的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发生率高于平均水平。本研究调查过程中,多名老年人表示入住养老机构后感知自身毫无价值,只是等待死亡来临,说明其出现了消极的自我老化感知。因此,护理人员应重视老年人心理状况,采取措施降低其抑郁水平。本研究中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4个领域均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生理领域最低,可能是由于养老机构老年人多病共存导致其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

表3 抑郁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生存质量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

图1 抑郁中介效应拟合模型(标准化)

表4 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
3.2 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抑郁对生存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抑郁与生存质量呈负相关(r=-0.532、r=-0.692,P均<0.01),与生存质量的4个领域呈负相关(r=-0.494~-0.386、r=-0.679~-0.520,P均<0.01),衰弱和抑郁呈正相关(r=0.562,P<0.01),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6-17]。这说明衰弱和抑郁都会影响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衰弱和抑郁程度越重,生存质量越低。衰弱对养老机构老年人生存质量心理领域和生理领域的影响较大,而抑郁对生存质量心理领域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累计健康缺陷理论,衰弱在躯体、社会、心理等方面均呈现非典型疾病表现,而躯体衰弱是核心[18],因此对生存质量生理领域的影响较大。而衰弱身份危机理论认为,衰弱老年人通过他人评价和自我感知这一阶段的变化,产生自我意象改变,压力和抑郁极可能是这一过程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19]。
3.3 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在衰弱和生存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将年龄和每周运动时间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抑郁在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和生存质量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抑郁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用系统模式理论解释,衰弱个体维持内环境稳态能力减弱,机体防御功能降低,三大防御线被破坏,即使是很小的压力刺激都可能穿过正常防御线甚至是抵抗线,导致严重的不良结局[20]。在生理领域上,衰弱个体表现为肌肉力量下降、行动障碍、耐力差等,直接降低了生存质量;另一方面因刺激引起悲伤、无助等抑郁的典型症状,从而降低生存质量。此外,抑郁的部分病理生理机制,包括慢性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等与衰弱重叠[21],例如炎症细胞因子不仅与肌肉力量下降有关[22],而且可能对多巴胺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抑郁、疲劳等,影响生存质量[23]。因此衰弱通过抑郁这一中介变量间接降低生存质量。目前,养老机构中的护理队伍更侧重老年人生理领域的照护,对于老年人心理领域的隐性需求,无法应答或应答无效,整体护理质量有待提高。建议养老机构重视老年人抑郁的调节,多倾听老年人内心的声音,观察老年人的日常行为,及时发现有抑郁倾向的老年人;通过外部干预调节老年人情绪,例如开办兴趣班,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自我效能,使其认识到老有所为,也可以组织老年人定期参加团队体育锻炼,改善衰弱,提高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