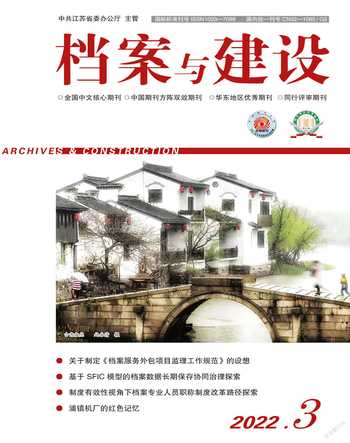南京图书馆藏韩国钧《朋僚手札》及其史料价值
夏林
摘 要:南京图书馆藏有韩国钧《朋僚手札》稿本两册,共收录书信56封,均未见刊布和利用。经考证,其作者是许鼎霖、贾士毅、蒋楙熙、胡广渊,成文时间在1913年至1918年间。两册《朋僚手札》所录书信为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和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朋僚手札》;韩国钧;史料价值
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又作止石,江苏海安人。韩国钧在晚清民国政坛地位颇为显赫,历任江苏民政长(后改称巡按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长、督办江苏军务善后等职。由于长期为官,韩国钧交友广泛,与朋僚多有书信往来。他生前十分注意收集此类书信,据称曾先后整理有百余册。韩国钧去世后,这些书信多有散失。目前留存的书信主要收藏于江苏省档案馆,系1987年由韩氏后人捐赠,共计57册。这部分书信于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1]根据这批书信,江苏省档案馆先后编有《韩国钧朋僚函札名人墨迹》《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两书,另中共海安县委宣传部编有《韩国钧朋僚墨迹》一书。笔者在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该馆藏有韩国钧《朋僚手札》稿本两册,当为百余册朋僚函札中散佚的部分。[2]
一、 《朋僚手札》的作者与成文时间
两册《朋僚手札》为线装,所收手札皆系原稿粘贴,封面题有“朋僚手札”字样但未署名。南京图书馆将之题名为《韩紫石朋僚手札》。查该手札的收信人被称为“紫石”“紫公”或“止公”,为韩国钧之字;所称“节使”“省长”的官衔亦与韩国钧相符。细察其内容,所述事迹与韩国钧的经历也是一致的。所以手札的收件人是韩国钧,这一点没有疑问。
南京图书馆在数据库中对两册《朋僚手札》做了标号,但从手札作者和成文时间来看,该馆的排序并不准确,兹将其重新编排为第一、二两册。第一册共收录手札30封,第二册共收录手札26封,总计56封。经笔者仔细辨识和考证,这批手札的作者有4位,分别是许鼎霖、贾士毅、蒋楙熙和胡广渊。
许鼎霖(1857—1915),字九香,江苏赣榆人,是清末民初“江北名流”,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与张謇关系密切。1913年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1914年2月,北京政府举办知事试验,任主试委员。9月,改任江北苇荡营督办,主持垦务。1915年10月15日病逝于上海。许鼎霖与韩国钧最早可能相识于奉天(现辽宁沈阳),时间是1911年。当时,许鼎霖继韩国钧之后任奉天交涉使。据8月4日奉天专电载:“奉天交涉司许久(九)香司使定于今明日接印,吉林民政司韩紫石司使俟交卸奉天交涉司后尚须勾留二三日方能赴吉林履新。”[3]许、韩二人既为前后任,且许接印时韩尚未离开奉天,二人有过会面是必然的。不过,此时二人估计还谈不上深交。民国成立后,二人先后返里,才有了更多交往。
贾士毅(1887—1965),字果伯,江苏宜兴人。民国初年在财政部任职,历任国税厅筹备处筹备员、编纂处主任、会计司司长、库藏司司长、参事兼赋税司司长。著有《民国财政史》《民国续财政史》等书。他在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期间(1913年2月至8月)曾视察江苏省财政状况,并与人合编《江苏财政调查报告》。[4]其时韩国钧正在江苏都督府任职,二人相识或在此时。[5]而后,韩国钧升任江苏民政长、安徽巡按使。作为财政部官员,又是江苏人,贾士毅与韩国钧有所往来是可以理解的。
蒋楙熙(1876—?),字奂庭,亦作焕庭,江苏吴县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蒋楙熙曾发布“劝告苏属州县各团体书”并任苏州巡警监,对于维护苏州秩序颇有功劳。[6-7]韩国钧担任江苏民政长期间,蒋任行政公署秘书长,1914年2月获署江苏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兼财政司长。[8]1915年,短暂出任浙江财政厅长,即被劾去职。[9]1917年11月27日,出任河南财政厅长。[10]蒋楙熙以善于理财受到韩国钧器重,据称韩就任安徽巡按使时曾拟调其赴皖任职,但格于形势而未果。[11]
胡广渊,生卒年不详,字渊如,安徽凤阳人,是凤阳明光地区大地主,在当地拥有较强的宗族势力。[12]胡广渊与韩国钧相识较早。1887年,二人同教读于江苏省六合知县吕宪秋署中。[13]韩国钧在《永忆录》中曾提及胡,说胡是凤阳诸生,“余初不知测绘学,在六合幕中,胡君渊如为余绘燕子矶形势一角于箑中,自是究心舆图”。[14]胡广渊在韩国钧就任安徽巡按使时,也致信说自己“承教最久”,二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以上诸人所致信件分别收录于《朋僚手札》第一册第1—21封、第一册第22—30封和第二册第1—8封、第二册第9—17封、第二册第18—26封中。第一册前21封手札中,仅有一封用规范字体署名“许鼎霖”,其余或未署名或署一字、两字。这些署名均为草书,难以辨识,但从字形上判断应为同一人。笔者认定这些手札的作者是许鼎霖,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两册《朋僚手札》其余来信均按作者编排,这21封应当也不例外。韩国钧将署名“许鼎霖”的手札夹杂其中,则这些手札当均为许鼎霖所写。第二,在这些手札中,该作者提及赣榆是其“乡里”,“政治会议昨日发夫马费”,知事试验“试官”“请假返岛”。综合这些内容,该作者应为赣榆人,曾任政治会议议员、知事试验考官并在青岛有居所,这些信息均与许鼎霖相符。[15]基于此,笔者认为那些署名当为“鼎霖”或“霖”字之草书。
两册《朋僚手札》所录书信大多署有月日,部分手札旁题有收信月日甚至年份。根据这些信息结合手札内容与其他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这批手札的起讫时间为1913年至1918年。这一时段正值韩国钧从担任江苏民政长到卸任安徽巡按使、归隐田园之际。四人与韩国钧书信往来,所谈内容不仅涉及地方政务,也论及“京师消息”;不仅涉及政治,也论及财政、实业和私人事务等等,颇具史料价值。
二、 《朋僚手札》的史料价值
第一,为研究民初政治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許鼎霖、贾士毅二人都在中央任职,对高层政治决策有一定了解和参与,他们在手札中多有透露,这些信息或增进或佐证了我们对民初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比如,政治会议是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设立的决策咨询机构。许鼎霖曾任政治会议议员,他对政治会议的评价与通常的认知不同。1914年1月22日,他在信中说:“政治会议已公决五案,人少无党见,故能速,非人才高于国会也。”许氏的评价当然不能全盘接受,但其中所彰显出的部分政要对议会政治的观感则颇为重要。在同一封信中,许鼎霖还披露了政治会议的讨论情况,对了解相关问题的决策过程很有帮助。
再如,知事试验是北洋时期为改良吏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此,学界已有专文讨论,但没有利用许鼎霖的手札。[16]事实上,许鼎霖两次担任知事试验考官,全程参与了知事试验的决策和运作。关于知事试验的决策,许鼎霖指出:
“考县知事,多不为然。负大名者固不愿考,且值大乱甫定,倘令得力知事一例应考,地方必又恐慌。况白狼已成流寇,何可為此试吏虚文?即必考论之,不过取在京浮薄少年耳,恐视同科举云。即用是,其祸必更甚于征兵也。同人多为秉公言之,已视此考为一种资格而用人则专责之民政长耳,并拟令民政长多保留免考,免致有经验之官因考见弃,此亦可谓委曲求全者矣,然亦何必多此一考也。”
秉公是指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字秉三)。这段源自决策者的一手资料表明,知事试验制度一经推出就遇到很大阻力,最终变成一种资格考试,且许各省民政长多保留免考。这就背离了知事试验制度建立的初衷,后来保荐免考的现象愈发严重导致知事试验沦为形式,不为无因。许鼎霖自己也不能免俗,他经常向韩国钧保荐免考知事,此类事实在手札中多有反映。
又如,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后,进一步图谋称帝,但最终在国人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忧惧而亡。对于这一过程,贾士毅多有论述。他还曾作为财政部代表列席过南京会议。这是护国运动后期由冯国璋主持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袁世凯企图通过这次会议,发动和诱使各省将军出兵镇压护国军,而冯国璋与拥袁派虚与委蛇,暗中策划迫袁退位。贾士毅对此次会议有较为详细的描述。1916年5月23日在信中说:
“华帅坚嘱列会代表,毅以部函仅限陈述财政为答,遂改为旁听员,以备咨询。开会数次,冯主总统问题由国会解决,张、倪主总统不宜退位,代表亦分三派,或主冯说、或主倪说、或临空立言,聚讼纷纭,遂有念二日无条件请南方罢兵,派员来宁与会议和之电。”
华帅是指冯国璋(字华甫);“张、倪”分指张勋、倪嗣冲,张勋派代表参加。这段材料佐证了现有关南京会议的叙述。[17]
这批手札还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江苏地方政治。许鼎霖作为江苏巨绅,十分关注地方政治。他经常向韩国钧保荐亲朋故旧,还与同时在京的张謇等人一道干预地方重大政治和人事决策,其手札为研究旅京苏籍官绅与江苏政局的关系提供了生动记录。比如,张謇、许鼎霖二人曾推荐仇继恒任实业司长,韩国钧另有考虑,因此嘱咐许鼎霖与张謇会商此事。1914年1月9日,许鼎霖回信道:“昨夕始见面,季老请公自定,未加可否。嗣于间接中探其口气,似以仇宜实业,于徐则以向未接谈不置一辞。”季老是指张謇(字季直)。韩国钧作为一省之长,任命人事还需探询张謇等人的口气,充分显示了张謇等人在江苏政局中的影响力。
许鼎霖的手札为认识这一时期的地方政治矛盾提供了重要线索。冯国璋担任江苏都督之后,与时任民政长的韩国钧矛盾日益滋长,最终迫使后者调职。关于此事,韩国钧在《永忆录》中仅有简略叙述。[18]许鼎霖在信中多次提及此事。1914年1月19日,他在信中说:“京师传言,公与大树意见已深,想不确。并云大树愿兼民政长,尤无稽。”2月10日说:“仲仁言,极峰闻小松督署索月费八万,甚不为然。”2月14日又说:“大树短处在袒护同乡门生。所谓负完全责任,只可听之于天,程德全、应德闳何尝不曰负完全责任耶?极峰亦以为虑,或有办法耳。江苏军费八百万,骇人闻听,不裁减无办法。小松已详言之,公入觐时面陈必可饬行以苏民困。”大树是指冯国璋,极峰是指袁世凯。张一麐,字仲仁,时为袁世凯机要秘书;张寿龄,字筱松,时任财政次长,二人均为江苏籍官员。
上引材料表明,冯韩矛盾主要集中在经费问题上。冯国璋向江苏民政当局每月索费8万元,每年军费800万,引起韩国钧及苏籍官绅的不满和抵制,因此冯氏想要亲兼民政长。许鼎霖最初不清楚底细,直至韩国钧致函解释才明了相关内情。顺便可以提及的是袁世凯的态度。许鼎霖的手札显示,袁世凯对冯国璋索要巨额经费是不满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冯国璋留任而韩国钧被调离,这说明袁世凯与冯国璋之间存在一种微妙关系。袁世凯不希望看到冯国璋扩充军备而坐大,但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他选择牺牲江苏地方利益来维系其与冯国璋的关系。
第二,为研究民初财政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民国财政史研究中,贾士毅所著《民国财政史》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事实上,贾士毅在与韩国钧通信时,也对中央财政状况和财政政策多有论述。他在信中谈及中央财政状况与税收整顿的关系,袁世凯、周学熙等人的财政主张,帝制运动与中央财政的破坏等问题,谈及土地清丈、江北厘金等具体问题。与《民国财政史》的记载不同,手札能够呈现政策制定的具体过程和各方考量细节。
兹举一例。由于民初财政奇窘,财政部拟通过整顿旧税、开征新税,以增加收入,但这个过程其实充满反复。1915年11月7日,贾士毅在信中指出:
“前次部递户税法,内分四等,大户年纳五元、中户二元、小户五角,极贫之民免纳;商店牌照税法,内分八等,最大商店年纳二十四元,次二十元、十六元、十二元、八元、六元、四元、二元,两案均由政事堂以时期未至暂从缓议送回。”
户税法、商店牌照税法之所以被打回,原因是“主座近以各省疮痍未复,不愿骤行增税,故部中政策亦随之稍变”。主座是指袁世凯。袁氏此举,除了考虑“各省疮痍未复”之外,可能还有顾及政治影响的因素。一方面图谋帝制,另一方面却突然加税,难保不引起反弹,这是袁氏不得不考虑的。当然在财政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完全拒绝加税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又有加征江苏漕粮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袁政府试图在财政与政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贾士毅还是1917年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财政部受贿案和诈欺取财案的当事人之一,他曾经专门致信韩国钧讲述事件原委。要想研究这一事件,贾士毅的这封信是需要利用的。除了贾士毅之外,蒋楙熙也长期在财政部门任职。他于1917年底出任河南财政厅长,就任后几次给韩国钧写信,对河南财政问题多有描述。
第三,为研究民初历史人物提供了补充资料。目前关于韩国钧生平尤其是民初这一段,主要史料来源是韩国钧所著《永忆录》和《止叟年谱》。但这两本著作毕竟都为当事人所著,许多事点到为止,两册《朋僚手札》可以补充现有叙述之不足。特别是这批手札还保存了韩国钧从安徽巡按使到卸任后的一些重要活动史料。
比如,成立泰源盐垦公司是韓国钧从事的一项重要实业活动,相关韩国钧传记必予介绍。[19-20]但是,这些传记研究对于泰源的早期筹划过程缺乏具体描述。从《朋僚手札》可以看到,早在1917年3月韩国钧就致信贾士毅提及“垦务一事”。16日,贾士毅复信对筹办垦务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
“现拟先从调查入手,如地质、河道、堤岸、购地价、地段、煎盐等项,必须派人实地考察,绘成地图及精密预算书。前项办有头绪而垦煎并营确可获利,再一面[举]选择要人经理购地等事,一面招股及筹商内部组织各项,而集款之难易一视预定计划之如何。”
贾士毅还表示准备日内联合京中友人说明大概,从事集款。此后,围绕此事,二人还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显示贾士毅是筹备泰源盐垦公司的重要人物,但现有研究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就笔者目力所及,除贾士毅外,这批手札的作者们留下的直接史料都比较少,因此这批手札是研究他们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依据。如许鼎霖作为“江北名流”,受到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关注,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这批手札,因此对于许鼎霖民初如何看待政治会议、如何参与议政、如何干预地方政局等问题不甚了了,颇多揣测之词。[21]
此外,这批手札提到的历史人物颇众,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謇、熊希龄、周学熙、张一麐、黄炎培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不甚知名但在当时也起到一定作用的历史人物,如张寿龄、段书云、黄以霖、应德闳、杨廷栋、孟森、蒋雁行、管云臣、王佐良等等。这批手札为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提供了不少素材。比如,许鼎霖在手札中多次提到张謇。1914年2月10日函曰:
“杨廷栋惯捏季名打电,闻近日部用密电致公之文甚多,乞留意。最好每收一电即用快信复全国水利局,季老当可亲收接洽。但季老为若辈所束缚,虽明知假电亦无可如何。惟令知之,可以谅我不能遵行之故耳。”
杨廷栋经常假名张謇发电,引起许鼎霖等人不满,这个信息值得张謇研究者留意。类似例子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 结语
书信是一种特殊的档案史料类型,作为近代国人的主要沟通工具之一,其内容具有私密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往往能透露出很多内幕信息,因此日益受到重视。韩国钧既与中央高层、军阀首领存在联系,又大量接触地方人士,其所收集、整理的朋僚函札数量巨大、系统性强。若能把这批函札完整地挖掘出来,无疑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江北运河治理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9LSC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3]江苏省档案局编:《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792页。
[2]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韩紫石朋僚手札》,南京图书馆藏。
[3]《专电》,《时报》1911年8月5日,第3版。
[4]汤虎君:《民国财政税务实践和研究大家——贾士毅》,《档案与建设》2012年第3期,第46-49页。
[5][14][18]韩国钧著、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海安分会校注:《永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61、24-25、66页。
[6]《蒋楙熙劝告苏属州县各团体书》,《中国革命记》1911年第5期,第8-10页。
[7]《蒋楙熙之辞职》,《时报》1911年12月4日,第6版。
[8]《江苏省行政公署训令第六百四十三号(院令蒋秘书楙熙暂代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及兼财政司长)》(1914年2月5日),《江苏省公报》1914年第213期,第13页。
[9]《蒋楙熙解职之一斑》,《新闻报》1915年7月27日,第5版。
[10]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第16卷政府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11]《财政蒋厅长调鄂内幕谈》,《时报》1915年4月27日,第9版。
[12]《汪雨相先生于1958年8月给中共嘉山县委、嘉山县人委关于嘉山设置原因及嘉山县解放前的历史情况的一封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嘉山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山文史第2辑 纪念汪雨相先生》,政协嘉山县文史委员会编印1987年版,第67-69页。
[15]1913年3月11日《时报》载:“许鼎霖昨到宁宣言,俟开会后即当决心辞职回青岛。”可见,其在青岛确有居所。参见《时报》1913年3月11日第3版。其他报刊亦有类似报道,参见《时报》1913年3月29日第3版、《新闻报》1913年4月4日第2版。
[16]毕连芳:《北洋政府第一届县知事试验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11-114页。
[17]胡雪涛:《南京会议与北洋政局》,《历史教学》2013年第12期,第42-47页。
[19]谢静:《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韩国钧生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50页。
[20]杨德志:《从晚清能臣到抗战楷模:韩国钧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03-107页。
[21]陈博林:《许鼎霖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361-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