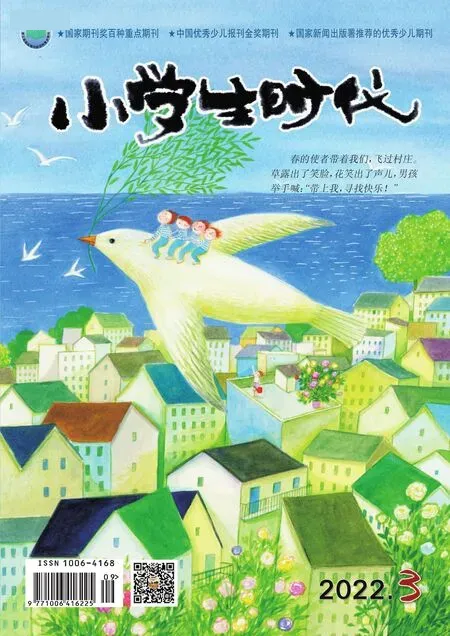回乡偶记
□项勇义
大年初一,又一次回到家乡。一进门,小米,一条伶俐乖巧的小狗,欢蹦乱跳地迎上来。院子里花气袭人,这是开得正旺的瑞香散发的香味。
满缸的米酒“镇”在那儿,缸盖移开的瞬间,酒香四溢。我会心地笑了。小时候,我曾偷偷地取缸里的米酒当水喝,一不小心就喝得酩酊(mǐnɡdǐnɡ)大醉了呢。
家弟钓来的野生鲫鱼,香油浸的鸡肉,老妈亲手做的艾饺、酱萝卜、豆腐皮饺子、油豆腐嵌肉,这些都是我平素在城里难以吃到的。面对一桌家乡菜,我竟然还有点贪心地跟老妈说,很久没吃到过水磨粉的、猪油白糖馅的带尾巴的汤团了。老妈说,可惜眼下没有水磨粉。
一说水磨粉,我很自然地想起以前摆在老房子堂前的那尊石磨,想起石磨牵动时四周吐出的麦芽糖似的糯米汁。等装在布袋里的糯米汁凝结,掰成不规则的一个个小块,晒干,再磨成粉。地道的水磨粉就是这样制成的。不用说水磨粉做的带馅的汤圆了,就是刚刚掰开的糯米块,就这么一煮,吃起来也润泽得很。
杭州人用艾草做艾饺,家乡人则用黄花艾来做。黄花艾比之艾叶,多了黏性,用黄花艾做的饺皮儿,也多了“藕断丝连”的韧劲。艾饺一般要在清明前后才可以吃到,没想到大年初一就能吃上冬笋丝咸菜馅的。家弟节前抽空在河湖钓鱼,顺便又在岸边采些黄花艾,所以就有了口福。
家乡的这些特色菜,真吃起来,如今也并没有多好的胃口,难以忘怀的其实是包含在其中的家乡的味道。
得空儿,我总喜欢到村头巷尾走一走,每次回乡都是如此,这次也不例外。每每我在村子里随意地走着,总能体察到村子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大到这边的老房子拆了,那儿的新房子盖起,这里的河岸修葺(qì),那儿的石桥重建……小到这家门口晒了梅干菜,那边的篱笆晾上了大白菜,这厢的花儿新开了,那头的果子结实了,这边的禾苗出穗了,那边的庄稼收割了……时光不经意地流逝,每次所见,村子的面貌也总在不断地刷新,有些改变是自然的周而复始,有些变化则是人为的永久的更替。村里的集市从无到有,再到初具规模。外地口音的人多了,道路和墙体变整洁了,小洋房替代了老房子……而我心头还装着一个记忆中的村子,不时地与现实中的村子一巷一屋逐一比对,时而欣喜,时而惋惜。这些零零星星的片段,又构成了我对村子的新记忆,丰满了、加深了我对它的全部印象。我这身在其外的游子,很明了这个村子正走在城市化的道路上,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或许生活在村里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村里的集市,人气越来越旺,已算得上是村里最热闹的所在,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周围工业园区的工人都到这儿赶集。我也会偶尔去逛逛,问问果蔬的价格,留意着什么时候杨梅上市,什么时候菱角上摊……这些并不是村里的出产。杨梅是邻村潘家陡的,菱角大概是皂李湖的,年糕随时都有,梁湖年糕是地方名产,附近已有多家专业生产年糕的厂家、作坊。集市是一个区域最有烟火味的场所,聚集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各个时节的天地精华,也最能呈现一个地方的风物人情。那些在时光里未曾改变的物产,总散发着记忆和乡土的味道。
晚上禁不起劝,喝了些酒,又和老妈家长里短唠了许久。夜深人静,便无端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人,都是久未见面了的村里的老老少少;事,也都是无关紧要的事。的确,从少小离家,到两鬓斑白,一转眼怎么就那么久了呢?免不了心生一些感慨。我的思绪,便从这位到那个,从这家到那户,从这条巷子,飞越到那条巷子,从这个村子,转到那个村子,从田野到山岗,从山岗到溪河,从春天到冬日,天马行空。思绪掠过乡的清晨、乡的黄昏,乡的晴日,乡的雨天,乡的热闹,乡的寂静,还有乡的悲喜……甚至久违了的乡村的漫天飞雪、水溢河道的情景都一一浮现。竟然分不清是记忆还是梦境。
院子里的大公鸡啼了,初春的清脆的鸟音婉转地响起,天色也渐渐明朗。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清晨,我倚着阳台的栏杆,眺望远处的那座凤停山出神,山岗上依稀可见一处寺庙。山岗上那个曾经多次被少年时的我们“占领”的碉堡,不知还在不在?如今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呼朋唤友,说登山就登山吗?
乡愁,大概就是记忆的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