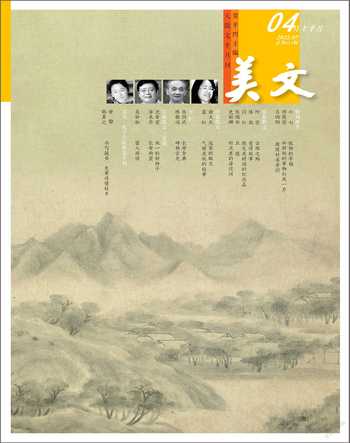朋友是时间的纪念品

闫红
《赠卫八处士》:真好,你我都还活着
我听到的最荒唐的一种说法是,杜甫可以学而李白不可以学,说得好像杜甫没有天才只有笨功夫,我的天,你倒是学学试试。
杜甫本人听到估计都得生气(另一个误会是,杜甫是个好脾气的人),人家可是说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估计是所有写作者的心愿,但没有几个人会像杜甫这样直接说出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杜甫很自信。
这可能是杜甫那些工整的律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事实上,杜甫最杰出的作品,同样是险韵诗成,神出鬼没,是陆游所言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就说他那首《赠卫八处士》的开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没有前因后果,简直是破空而出,但又觉得这十个字字字如铁,一下下夯到你心里去,像流星落地,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与之匹敌的不算多。
谁没有过类似的体会呢,在这世上,有多少至爱亲朋,说不见就不见,根本没商量,就像天上的参星与商星。参星属于猎户座,商星属于天蝎座,参星升起时,商星就会落下。用天理来证人情,更显得决绝而不容置疑。
这种分离有时候你是有知觉的,比如《红楼梦》里晴雯以为她和宝玉会永远在一起,但王夫人一声令下,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很快香消玉殒,与宝玉天人永隔,这是赤裸裸的悲剧。但还有一种分离是你无知觉的,那个人好像一直都在那儿,但你一抬头,发现他已消失在人海,也没有什么缘由,都没处说理去,更让人思之惆怅。
杜甫笔下这位卫八处士,很可能属于后者。处士者,隐居不去做官的人,卫八者,姓卫排行第八。这位卫八处士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在杜甫的作品也没再出现过,他和杜甫未必有怎样深刻的友谊。只是,乱世中,危机四伏,瞬息万变,单是“故人”两个字,就已经很可亲了。
据说这首诗写于公元759年的春天,之前这两年杜甫过得十分跌宕,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苦苦追随肃宗,肃宗大为感动,封他做了右拾遗,说来也算是念念不忘终有回响,皆大欢喜。但杜甫不是个识时务的人,以为从此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上书疏救获罪的房琯,激怒肃宗,于公元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告假回故居洛阳陆浑庄,从陆浑庄回华州时,他拜访了隐居在乡间的卫八。
卫八为什么会流落在这里?杜甫又是从哪里得到他的消息?可能就是一串串极偶然的机缘,将杜甫推到了卫八的面前。
别后经年,忽然见到以为早已失散的故人,那种惊愕不难想象,惊愕缘分的神奇,也惊愕乱世里彼此都还活着。原本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变得不寻常。“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乱世的大背景下,这场相聚,有着以惊惧为底色的温馨。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旧日呼啸而来,都曾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再见面,两鬓已苍苍。这几年去看望两老朋友大多已经成鬼,所以看见彼此都还活着,竟然有点意料之外的喜悦。一声惊叹中,有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滋味在胸中滚过。我何曾想到离别二十年,还能走进你的家门,离别时你还是个单身汉,现在儿女已经成行。
故人相见,是几重时空重叠,似真似幻,且惊且疑。你记忆中他总是二十年前的少年,然而他已经是一众儿女的父亲,这些儿女都很可爱,对于杜甫这个远道而来的叔叔,既恭敬有礼又热情亲切。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
怡然是愉悦的意思,但更加舒缓。“问我来何方”,这一句更妙,有居家者的好奇,也是对这个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叔叔分寸得宜的关怀。问候尚未结束,他们又去张罗酒浆。
你看,从行礼到问候,到准备酒菜,这一系列行为是不是如行云流水。我们用杜甫的视野看过去,作为老朋友,我们多么欣慰于老朋友的孩子们如此聪明善良和能干。
接下来的这个夜晚,也许是唐诗里最美的几个夜晚之一。
是的,唐诗里有太多美好的夜晚,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比如“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比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比如“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或是“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相遇,或是天高地阔,令人物我两忘,心旷神怡,但我最喜欢的,是杜甫与卫八处士相遇的这个夜晚,在动荡的角落里,在一场场离散的夹缝里,卫八倾其所有,款待了这个老朋友。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这场款待说起来也是寒薄,没有大鱼大肉,更不见世间珍奇,不过是冒着夜雨剪下春天的韭菜。据说这里面有个典故,东汉郭林宗自种畦圃,友人范逵夜至,郭林宗冒雨剪韭,作湯饼以供之。
但是我总觉得杜甫这句写的是实景,面对突然出现的老友,卫八来不及准备,家中物资可能也很匮乏,但匮乏也有一种美,会让人更珍惜手中所有。比如这冒着夜雨剪下的新鲜韭菜,才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的米饭,是最普通的家常饭菜,但香喷喷,热腾腾,在这一刻足以满足杜甫饥饿的胃和仓皇的心。
回想这一生里给你留下美好记忆的食物,是不是都跟昂贵的食材精致的烹饪方式无关?《红楼梦》里的茄鲞和鸽子蛋,不如《水浒传》里的二斤牛肉显得美味,因为《水浒传》写出了饥饿感,也写出了饥饿感被消除之后的满足感。杜甫也用十个字,写出他心中的万千滋味。
更何况,主人卫八说这相聚太难,一再殷勤举杯,两人接连喝了十杯,十杯也不能喝醉,感念故人这份深情厚谊。
酒量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东西,同样一个人,有时浅尝则醉,有时千杯不倒,是与当时的心情有关。杜甫未必是海量,但十杯下肚,也只是微醺,是他内心的激荡,消解了酒意,可以想象,卫八与杜甫,在那个夜晚,该是怎样的感慨万千,共话世事的山高水长。
这场家宴,是接风,也是送别,不只是卫八送别杜甫,他们其实也是在彼此送别。在古代,人本来就容易失联,乱世让一切更加失序,那么这一刻,就以往事下酒,温暖无法预知的明天。
杜甫把这个夜晚写得太动人了,让我想起小时候,晚上都准备睡下了,有亲戚或是父母的朋友突然登门,他们在灯下畅聊,温情中夹杂着一点紊乱感,无来由地让人感动。可能因为夜晚登门总是非常态,被收入“家人闲坐灯光可亲”的常态中时,有一种参差对照的动人。
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情感充溢的夜晚,该如何结尾呢?像杜甫这样有大才的人,写诗难的不是飞扬,而是降落,谁能想到杜甫用十个字就稳稳地降落了。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所有的都是在离别的照耀下,离别如一道阴影,让人不敢恣意快乐,但它又皴染着相聚时的所有细节,让它皱褶分明,楚楚动人。所以这首诗明写相聚,暗写离别,唯有离别铺底,相聚时的所有才更加深刻。
就像人生,以死亡铺底,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活着。
《别董大》:朋友是时间的纪念品
暑假里带娃去成都,特意去了杜甫草堂。那些屋舍自然是后来建的,但是很长的一溜诗碑值得驻足,我几乎是每一首都仔细地看了。
娃不耐烦,说看书不是一样吗?我说,是一样,但是好书太多了,如汪洋大海,能看到哪一本常常是缘分,你现在来到这里,遇到这些诗也是缘分,何不随缘一看。
娃被我的煞有介事弄得没脾气,只好陪我看过来。但是光看就行了吗?当然不是,老妈还要讲解!既然说是缘分了,何妨将缘分进行到底?好在当时比较早,草堂里人不多,有两三个人还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我猜测他们是被我的讲解吸引了。
直到走到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前面,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据说顾随先生讲诗词时,也常常只能感叹写得好。有一种好就是那么玄乎,像一片飞在半空中的羽毛,撩得你心旌摇曳,似乎触手可及,但你伸出手,又怎么都抓不到。
单看字面,这首诗写得太简单了。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玄宗初年有名的歌手,跟杜甫也算老熟人,安史之乱时,他和杜甫都流落到江南,在大好春光里不期而遇。看这二十八个字,都是白描,一点抒情的成分都没有。风景也是好风景,而不是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是在这微阴的晨光里看过去,没睡好的我,怎么有点想哭呢?也许,诗眼就是这“好风景”三个字,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还是好的,你还能在自然中找到呼应,感觉自己还有同类。“正是江南好风景”,写尽自然的无情。过去杜甫和李龟年见面的背景,是唐玄宗弟弟岐王的府邸,中書令崔湜弟弟崔九的客厅,是一整个大唐的繁华盛世,夜夜笙歌,纸醉金迷,谁会相信,坍塌就在一瞬间呢?
在记忆的废墟之上重逢,四目相对间,你们都知道失去了什么,长安已经失去昔日的颜色,但身处的江南,还只管好风景着,似乎要印证你们所有快乐悲伤的虚无。它无声无息地就消解了一切,这真是生命里的大无奈啊。
然而,也可以从另一面说,虽然花开花落,四季轮回,不为任何人任何事留步,但朋友依然是时间的纪念品,当他们出现,就会唤醒整个过去,让你想起,你曾如此深刻地活着。在唐诗里,这样的感触俯仰可拾,《江南逢李龟年》如此,高适的《别董大》也是如此。
先看这首诗: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是个雪天,黄云在天空堆积,延伸至千里之外,太阳被遮蔽,日光惨淡。很难说这是不是个好天气,对于在家里守着火炉的人,可能会引发“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怀,但是对于行路人,它让路途变得更艰难,也让远方变得更加莫测。但是又不能不出发,就像那天上的大雁,顶着呼啸的北风,继续自己的旅行。飞雪围绕在周遭,像是无所不至的阻击,这光景,犹如一种人生际遇,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不想走,又一步步被推着走,即将跟高适告别的董大没有这么艰难,但是也不容易。
高适没有明确说出董大何许人也,不过后人一般推测是琴师董庭兰,他在家排行老大,故被称为董大。董庭兰技艺极高,唐朝诗人李颀在《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说:“董夫子,通神明,深松窃听来妖精。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说他的琴声能够通鬼神,连妖精都要偷听他的弹奏。
可惜董庭兰一生清贫,六十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间度过,六十岁之后,他追随宰相房琯,充作他的门客,房琯很快失势,董庭兰也被迫离开长安。据说这首诗就写在这个时候,同样不得志的高适,在旅途中遇到失意的董大。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董大此时的处境,他年过六旬,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六十多岁也是妥妥的老人了。这个年纪不能在家安心养老,不得不出远门,真的是太残酷了。
如今通讯设施和交通工具发达,即使是去从未抵达过的远方,也不会显得特别陌生,你可能之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它已经有了解,何况世界已大同,万变不离其宗。
古代则不一样,他乡是真正的他乡,那种陌生感如铁板一块,又深不见底,无处查询,也没地方打听。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出远门,董大不可能不忐忑。
幸好他遇上了高适。高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同样是不怎么得意的。在《别董大之二》里他写道:“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他形容自己像一只鸟儿扇动着翅膀,只有自己心疼自己。他身处边缘,有十来年不去京城。大丈夫身处贫贱也没什么,只可惜今天我们相逢时候,连喝酒的钱也没有。
我们无从得知,高适当年和董大相识是怎样的情形,但是于此刻,一定有着莫大的落差。这可能是他们一生里最糟的一刻,他们都在逆境之中,在人生的大雪天里。所以,这一刻的高适特别能够理解董大的心情,他知道董大最为担心的,是那种茫茫无边的陌生感。
如何从这种担忧里解脱出来?那就是分析给他听,你即将抵达之地,没有那么陌生。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豪迈之极,也实用之极。可以做浅表地理解,可能这位董大很著名,不管到哪里,他都会遇到知音,遇到粉丝,这些人依然欣赏他敬重他,给他制造出一个熟悉的氛围。当然,诗人夸张了,即便董大就是董庭兰,也未必有名到这个程度。可是,人在窘境里,非常容易自我否定,稍稍夸大一点,是一种很温暖的体谅。
除了这层浅表的意思,这两句还可以进一步解读。董大以后会遇到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董大的才华,会让别人把他从人群里识别出来,对他另眼相看。
就像《水浒传》里,武松在阳谷县打死吊睛白额虎,县令识别出他是个英雄,后来被发配孟州,路过十字坡,他的谨慎机智,也让菜园子张青认出他不是凡人,到了孟州之后,小管营施恩也对他青眼有加,才华和爱情与咳嗽一样,都是瞒不住的。
不过,高适笔下的这个“识君”之人,未必一定位高或权重,即便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彼此心灵相通,都能给苦旅中人莫大的安慰,高适相信,董大将来一定会遇到许多懂得他善待他的人。应该说,这是给即将出发的朋友最好的祝福了。
我不知道他们之后过得怎样,但是因为对方的存在,这段不如意的日子,也会被诗意化吧。朋友不但是时间的纪念品,还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跌宕苦境在记忆里变得诗意盎然,朋友是命运赠予的额外的礼物,必须珍重接收。
说说林黛玉不喜欢的李商隐
这两天陪娃复习语文,七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看了就觉得,写作如打仗,有的字句像临时拉来的壮丁,凑数而已,稍有点风吹草动,就溃不成兵。好作品则字字都是精兵强将,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说以一挡百都算保守,集结起来更是瞬间技术爆炸。
这首《夜雨寄北》无疑属于后者。先看第一句这七个字:“君问归期未有期”。
君是谁呢?南宋洪迈编撰的《唐人万首绝句》里这首诗题目是“夜雨寄内”,意思是寄给李商隐的内人也就是妻子的。但也有人考证,在李商隐入东川柳仲郢幕府前,他妻子就去世了。又有人考证,李商隐可能早前还曾去过巴山……也许还会有新的考证推翻这个说法。
这不重要,我们知道李商隐是在巴山的雨夜里,写信给一个想知道他的归期的人就行了,他给的答案是:未有期。
三个字截住所有思念、期待和憧憬,李商隐看上去文弱,下笔倒是真狠:“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万重”……
整个世界都在说“你死了这条心吧,不会有任何结果”,他还要把这个话对自己再重复一遍,用各种精致的比喻,往自己心上插刀子。
深刻的绝望,出自澎湃的渴望。难怪林黛玉不喜欢他,林妹妹推崇的王维、陶渊明风格都是“淡而自然”,李商隐的诗,算是诗中浓颜系。
好了,都说了未有期了,这个话题算是过了。还能说点什么吗?就聊聊天气吧。“巴山夜雨涨秋池”,你在北方的寒夜问我的归期,我只能告诉你,我在南方的巴山夜雨里,感到秋天的池塘,逐渐涨满。
世间情意常在不相干的话里,说我这里在下雨,不过是想让你感受到雨中的我自己。
然而巴山夜雨四个字又加深了“无期”感,“巴山”“夜雨”,是重重叠叠的围困。李白说:“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世事无常加上重峦叠嶂,人类活在各种围困中,一点点主也做不得。
到这,算是把天彻底聊死了。可是,不知怎的,作者突然又起了兴致:“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纵然不知归期,隔着千山万水,但且让我想象一下,等到终于再见面的那一天,在西窗烛光下,我要跟你讲述我这雨落成潭的此刻。
有人把“却话巴山夜雨时”翻译成“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思念之情”,我感觉,简单了。“巴山夜雨时”是个整体概念,我愿意理解为,在我想念你的此刻,无法和你在一起,我要用记忆封存这光阴,待到再见面时,和你一起开启。那么原本平常的当下,将成为明日送你的礼物,用未来的目光来看,像被上帝赋予了光,楚楚动人起来。
这就是堆叠时光创造的奇迹。
堆叠时光,就是把不同时空堆叠在一起,著名的例子是《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多年之后”是未来,“那个遥远的下午”是过去,被一个隐形的“现在”连缀着。这个“现在”像是一双清醒的眼睛,将终极谜底叠加到初见世界的新奇之上,读起来,像吃拿破仑蛋糕,勺子一舀到底,奶油的细腻,酥皮的松脆,在唇齿之间清晰呈现,再混成妙曼的复杂。
就像时尚高手擅长叠穿一样,伟大的作家最懂得堆叠时光的妙处。比如《红楼梦》,作者是打了明牌的,一开始就提示结局,放弃悬念,是因为他知道,他能提供更高级的东西。
《红楼梦》里有几章写得温柔旖旎,大家一起赏红梅,吃鹿肉,咏白海棠,给宝玉庆生等等。青春恰好,所有人都在,有着时间和财富的双重优裕,他们开怀得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就像花在春天里不留余地地绽放。
然而,拥有上帝视角的读者,会感到结局像滤镜一样笼罩所有情节,所有欢乐都置于悲伤的色调之下,参差交错,悲欣交集。
也有几章写得热闹非凡,比如王熙凤捉奸,与贾琏撕破脸,闹到贾母那里,再比如芳官等人与赵姨娘大打出手,整一个鸡飞狗跳锣鼓喧天。想到这般热闹终究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寂寞,热闹也多了点层次。
可以说八十回《红楼梦》里的每一刻,都是两层时光叠在一起的。
李商隐也是爱堆叠,再举一例,像这首让人看不懂又放不下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锦瑟通常是二十五弦,有人说这里指的是弦断无知音的意思,二十五弦断成五十弦。这断得也未免太齐整了吧。
《史记·封禅书》里说早先是五十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李商隐可能就是忽然想起这说法,五十这个数字很敏感,因为接近于他的年龄。
这首诗是李商隐晚期作品,他去世时四十六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我很懂他的心态,虽然到五十岁还有几年,但说年近半百也不算太违和。看到五十这个数字,也像是与自己有关,想问那“锦瑟”一句,你为啥无缘无故地就五十弦啊?
一弦一柱拨出的都是似水年华,这是一首回溯过往的诗。问题是,他要回溯过往岁月里的什么?又有怀念妻子和朋友各种说法,我个人比较认同汪辟疆先生的说法,这是李商隐“年近五十时自伤生平的诗”,所以会被放在诗集的开篇。
不过汪辟疆接下来把“庄生晓梦迷蝴蝶”解释为:“以我的才华,不应功名蹭蹬到这样地步,他在怀疑到底是天命呢?抑是人为呢?”认为庄生梦蝶,重点在一个“迷”字,我又不太赞成了,“庄生”应和“望帝”一起看,写出人生无非是迷梦一场。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发现还是庄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种体验可能每个人都有,在梦里,你变成别的人,或者另外一种视角,醒来时一阵恍惚,不知道此刻到底是梦里梦外。有时我走在街上,看到前面的那个人,也会想,我其实也有可能是她,那么,真的有个我存在吗?我不过是以“我”以为的“我”存在而已。
尼采认为,视角决定事实,换言之,并不存在客观真相。如果人生不过是一种幻觉,一场迷梦,你也有变成蝴蝶的可能,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必那么执迷,可以洒脱一点点呢?
很难,就像传说中古蜀国的君王望帝杜宇,据说他死得很冤,具体原因已经渺茫难查,但他死后化为杜鹃,心犹不甘,啼到吐血的形象在古诗词里很常见。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们纵然不会执迷到吐血,但也度过了殚精竭虑执迷不悟的一生。
这两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中年人回首过往,清醒地望着执迷的自己,知道执迷终究是自己的命运。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两句照例有一大堆解释,但我不想援引了,反正也没有标准答案。看这字面,就静美之极。
“沧海”像是岁月漫漫,“明珠”是岁月里的珍藏,“有泪”二字来得感性,旧时光无论悲喜,都能让人有泪盈睫。但这情绪并不深入,下一句把镜头又拉远,“蓝田日暖玉生烟”,蓝田这地方据说出美玉,却不是要挖掘出来,打磨成和氏璧,送给不识货的尊者,晴暖的日子里,隐隐看到那玉气如烟,已经很美。
唐代诗人戴叔伦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好诗就像蓝田自有玉气,可远望而不可把玩,对于岁月不也是这样?过往美好得太不具体,看着令人惆怅。
没办法,最美好的总是已经逝去的,让人渴慕的总是隔着距离。到后来,很自然地有了这么两句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周振甫的解释是“这种感情可待成为追忆,只是在当年经历时已经迷惘”,也有人说这个“可待”可以解释为“何待”,“何必等待”的意思。其实这两种都差不多,都是站在当时的时间里,感觉到这些必然会成为追忆,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这一句叮咛,让时间叠加,心中不由惘然。
这种感觉,我也曾有过几回,或在异国他乡,或在熟悉的街角,莫名想对自己说:“记住这一刻,你将来会想回来的。”眼前场景迅速被定格成一帧照片,同时感到时间在指间流动,形成快乐与哀伤夹杂的惘然。
而李商隐的时光魔法还不止于此,他那首《碧城》说的是天上仙女的日常,有一句“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是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堆叠在一起。
“星沉海底”,对于人间是惊人的景象,仙女们却是当窗可见,“雨过河源”,落入凡间,也许是洪水滔天,也许是细雨轻飏,仙女们隔座看去,可能也没有太大差别。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讲的是人间与仙境时间感知的不同。这句诗,又展现出空间感的巨大差异。
有人说这首诗是讽刺唐代所谓女道士的放荡生活的,不管是不是女道士或者是不是讽刺放荡,李商隐通过堆叠时空,呈现出某种失重的、令人眩晕的甚至有金属感的后现代之美,在古代诗歌中,算得一个异类。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