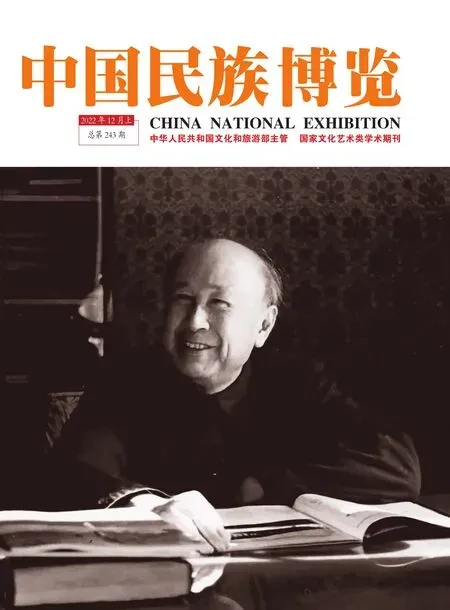机遇·逆境·出路
——“非遗后时代”敦煌石窟艺术的数字化传播
程澜欣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引言
佛教的盛行,催生了石窟艺术的发展。数千年前,石窟凿造的薪火最初沿着丝绸之路和江河古道,后渐次在中原大地传播开来。在艺术构成上,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的综合体;在价值构成上,石窟兼具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等。作为我国石窟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敦煌石窟艺术承载着绵延数千年的石窟凿建、壁画绘制、佛像彩塑的非遗技艺。
“非遗后时代”的车轮滚滚而来,伴随而来的还有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其中数字技术在非遗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壁画上动不了的“飞天”,在元宇宙里可以尽情歌舞;现实距离无法到达的洞窟,在网络上可以全景漫游。即使是随着时间流逝出现裂缝的岩体、渐渐生出酥碱等病害的壁画,在数字世界里也能恢复如新。现实中脆弱的非遗在数字空间尤为坚强。本文从“非遗后时代”大背景与数字赋权的传播背景出发,从“‘非遗后时代’非遗传播的数字化蜕变”“‘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机遇”“‘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逆境”“‘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创新路径”四个方面思考非遗数字化传播如何契合传播泛在时代的内在逻辑要求,从而增强传播能力和效力。
一、“非遗后时代”非遗传播的数字化蜕变
2001 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了昆曲;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通过;2004 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21 世纪初,国际上关于非遗定义与内容的逐步形成,各种非遗项目逐步活跃在中国公众的视野。2020 年12 月,“太极拳”和“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中国共有42个项目入选,数量居全球首位。
但把遗产发掘和列入名录并非最终目的,真正的保护从列入名录后才刚刚起步。[1]冯骥才于2011 年提出了“非遗后时代”这一概念,即完成了“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在“非遗前时代”,中国的非遗保护意识刚刚苏醒,非遗申报与急救工作几乎贯彻了整个时期,旨在挽救一些倾颓之势的古老非遗文化。在“非遗后时代”,申报非遗的热潮渐渐退去,一些本就小众又尚未受到关注的非遗在无声无息中烟消云散,一部分非遗在奄奄一息中稍稍站稳了脚跟,有了非遗的“名分”后,该如何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再次鲜活起来?传承不能断,保护不能松。于是,保护非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非遗工作的重点由“重申报”转向“重保护”。
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物质载体,现代科技大部分可以修复复原,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到了后继无人、人亡艺绝的境地,便很难找回,使其重现往日鲜活。如敦煌石窟艺术,若是石窟损了、壁画残了或是彩塑破了,后人通过学习钻研便能使其恢复如新,但真正的修筑石窟、彩塑、绘壁画等技艺若是失传了,现代技艺再高超,也难以跨越时空与当时的辉煌技艺相提并论,数千年敦煌石窟艺术的“原汁原味”便只能消逝在风沙里了。
非遗保护这股绳,丝丝缕缕都离不开传播。非遗传播,既为传承服务,又为保护服务,其重要性就在于,在非遗依然“活着”的时候,让公众感知非遗文化的灿烂魅力,让有志之士燃起传承非遗的斗志,让重视非遗的意识炙热如烈阳。非遗的“非物质性”的特殊——以人为载体,使其区分于其他文化遗产。作为传播的中心纽带,传承人对非遗来说尤其重要。旧时的传承人以家族为单位,以乡土为领域,以师徒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授技艺。这种传统的传承结构下,传承空间也较为狭小闭塞,多为遥远偏僻的村落,加之媒介生态的相对贫瘠,极其依赖人的“在场”,传播效果非常有限。而在“非遗后时代”,原有的传播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新媒介的介入。媒介的日新月异既改变了非遗传播原有的语境,也构建起了新的传承语境。借助数字技术,非遗文化打破了时空限制,不再是被“封印”在高语境的“文化琥珀”中。这些技术的加持,让非遗既有实体空间内具身传播的效果,又克服了实体传播的时空限制。[2]不仅有电视剧、综艺、纪录片等在线随时点播;还有了短视频(微电影、微纪录、15 秒微视频)、网红直播、数字特效、AR 与VR 逼真呈现,吸引受众享受沉浸式体验。[3]
二、价值彰显:“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机遇
(一)从局域认知到广域传播:数字技术扩大受众范围
突破物质性传播的束缚,数字化、虚拟化成为文化传播领域延伸出的新方向,数字技术为非遗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新机遇。将数字技术嵌入到非遗的保护、传承、传播中,从而达到一个“减”、三个“加”的目的:减少使用与损坏、加固保护、加添艺术魅力、加强文化意义。典型代表如“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是国内首个实现“指尖探索”敦煌石窟的应用,由敦煌研究院、腾讯和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打造。小程序内云上壁画、今日画语、语音导览等“科技+文化”组合成为爆款,上线两个月游览量便累计突破了1200 万人次,相当于以往莫高窟最高游客量的数倍。此外,该程序在上线一个月后,又进行了版本更新,添加可配音的“敦煌动画剧”——九色鹿、善事太子等为动画剧演员,用户则是配音演员,除了自娱自乐外,还可以邀请好友一同参与,充分利用人际传播与社群传播,成功引发了巨大的社交裂变效应。从具象形态到文化符号,从个体感知到集体记忆的转换,敦煌非遗与社会成员的联结程度日渐紧密,及其所承载的民族集体记忆的扩散程度在不断加深。
(二)从“在场”到“转场”:数字技术再造非遗空间
吉登斯认为“脱域”(disembeding)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体身份建构脱离了地方的经验社群,进入全球混杂、流动、碎片化的经验场景中[4]。鲍曼则把“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作为现代社会的特点,认为时空已经“变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动态的,而不再是预先注定的和静态的”[5]。在当下“脱域”与“流动”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非遗不再依附于在场,存在方式与传播空间多元化,线上线下多点开花。
2016 年,敦煌研究院推出“数字敦煌”资源库,利用VR 技术,实现线下石窟的线上立体呈现。通过运用摄影采集精度为300DPI 的技术,将10 个朝代的30 个洞窟、4430 平方米壁画再现在网络空间。高清数字图像与文字组合成洞窟的数字“身份证”,多维度呈现丰富了传播的视觉语汇,空间感的强化使受众产生强烈的临场感和更为真实的视觉冲击,满足了全媒体时代视觉文化的需求。在全景漫游中,壁画、佛像、藻井、顶等一览无余,甚至实地观赏无法触达的角角落落,也能实现数字化触达。
不止步于线上景观的构建,数字化传播的触角也延伸到了线下空间,并使得线上线下联系得愈发紧密。2020 年,敦煌莫高窟洞窟实现了“窟外看窟”,借用华为的人工智能河图平台,将高精度壁画和洞窟三维模型在华为AR 地图中与真实景观合二为一,实现实体洞窟与虚拟体验有机穿插的展示方式。在虚实交织的观赏过程中,飞天场景恍若眼前,虚拟洞窟仿佛触手可及,既跨越了时空的囿限,活化态势赋予受众极强的互动仪式参与感,又避免了游客过载等带来的洞窟不能承受之“重”。可以说,数字化传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复活”非遗文化,使其跳出“千年标本”的局限,成为活了千年的生命。
三、出场逻辑:“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逆境
(一)数字泛化,形式反噬内容“本真性”
数字技术可以投射、模拟原生态的非遗“本尊”,这种形式消解了虚拟与现实的场景边界,实现场景耦合。但数字技术是工业生产的产物,追求机械化复制后的表层快感,其展现出来的文化兴趣是蜻蜓点水般的浅尝辄止。在传播实践中,形式与内容的平衡难以把控,极易掉落到视觉表象的陷阱中。以数字敦煌为例,对敦煌莫高窟的传播主要以高精度数字图像为主,辅之以其他少数交互式、沉浸式节目,呈现出碎片化、单薄化的特征,大多仅停留在视觉层面,难以承载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内容重点着眼于莫高窟中的艺术元素——物质文化,而隐藏在物质背后的非遗技艺——非物质文化存在感薄弱。在这种空间内,莫高窟被压扁成景观,只皮毛化地抽取了物质层面,而不是非遗。
此外,沉浸在数字技术中的受众,总是被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的感官刺激所吸引,被游戏体验感所带来的自我愉悦感所环绕。然而所有的传播形式应当只是载体,如果一味沉浸于游戏中,那么非遗传播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的问题。如敦煌研究院与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杨玉环“遇见飞天”、瑶“遇见神鹿”和貂蝉“遇见胡旋”的游戏皮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敦煌文化美,但这种美仅停留在虚拟的游戏体验上,很难深入人心。大多数游戏用户在下线后,并不会专门去了解游戏皮肤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非遗”是依托原生语境而生长和存续的,在网络中,在进行“非遗”展示和传承时,将其从原生的生活场景中剥离出来,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所重构的象征性符号,以数字单元和相似分类系统、规则对其进行分割,再依循现代生活方式和技术传播要素对其进行组构,受众会通过自身理解对未出现的“非遗”信息进行想象和补充,在接受过程中对“非遗”的信息产生碎片化的理解,这不利于“非遗”完整文化形态的传达。[6]
(二)受众泛化,“一视同仁”抹除差异化
随着小众化传播的应时而生,传播从瞄准大众转向瞄准“分众”。1985 年,日本著名研究机构“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出版的《分众的诞生》一书,首次提出了“分众”的概念。“博报堂”指出,基于“划一性”的“大众”社会,正逐渐分化为个体化、差异化的小团体,即“被分割了的大众”现象,因而被冠以“分众”这个新名词。[7]大众的分化,对传播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要求,非遗传播也是如此。
就敦煌石窟艺术的非遗传播来说,受众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多是依靠“内驱型”受众——对非遗或敦煌石窟非遗本就怀着无比的好奇与热爱的受众,而缺乏“新生型”受众。综观其传播,传播结构较为简单,受众往往被看成一整体,而受众间的差异性被忽视。无论是“云游敦煌”小程序,还是“数字敦煌”网站,都是面对大众的横向传播。在这其中,受众被“一视同仁”,都被默认为敦煌非遗的热爱者前来接收数字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面对的不仅是本土受众,还有海外受众;另一方面,同一片地理区域内的受众兴趣点,联结紧密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遗传播过程中,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细化受众,而不是遵循传统的带有权威与距离感的填鸭式灌输。虽然在“敦煌诗巾”中用户可DIY 丝巾已经显露出了受众分化的趋势,但培育“新生型”受众之路仍任重道远。
四、进阶路向:“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一)传统非遗与现代美学和鸣
在全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多元泛滥,与非遗传播相结合的探索已有许多,但技术的出现并非是为了改变非遗的内核,而是为了将非遗现代化,使其更贴近现代受众的生活。数字化转译要时刻警惕工具理性膨胀,深层挖掘传统非遗的“非物质”层面价值,让价值理性焕发出光芒,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路径便是使非遗与现代美学相融合。
事实上,敦煌非遗传播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开始了初步探索。2022 年6 月,敦煌研究院和腾讯联手打造了首位数字敦煌文化大使数字虚拟人伽瑶。将莫高窟壁画中声音婉转如歌的神鸟“迦陵频伽”、《都督夫人礼佛图》和《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诸多古典元素相融相织,结合动作捕捉、全实时驱动加渲染、真实毛发与实时布料解算、面部驱动底层算法优化等数字技术,塑造了一位能说会道、能歌善舞、具有西域风情的虚拟人。活灵活现的虚拟人作为传播载体,相较真人而言,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但如果虚拟人只用作讲解,便是在这条道路上半途而废了。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虚拟人、虚拟空间活态展现“非物质”的一面。如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复现一个原始石窟,创造敦煌石窟的工匠虚拟人、画师虚拟人等,重现敦煌石窟的形成过程。或者与VR 技术相结合,打造一款成为敦煌石窟工匠的虚拟现实游戏,用户穿戴好设备,足不出户便可在另一端自主体验非遗技艺。
(二)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播交织
当非遗跨区域、跨民族、跨国家传播时,应当首要考虑非遗传播的针对性、适应性和融合性。“非遗”传播的认知,是传播者“自认”与受众“他认”共同作用的结果,传播者与受众在知识体系、体验和观念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理解和创造。[8]此时,“一刀切”式的传播已不再适用,分众式的传播较为妥切。从横向来说,本土受众与海外受众的文化传统与审美存在差异。就接受文化方式上,本土受众喜含蓄蕴藉,能够细品文化及其象征意义;而海外受众,在没有了解文化底蕴的情况下,很难理解文化的真正意义。因此非遗在向海外传播时,需要将其“外化”成海外受众易接受、易理解的形式。此外,在向本土传播时,也不能照搬“老一套”,推陈出新、顺势而为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
从纵向来说,受众又可分为“内驱型”受众与“新生型”受众。每个内驱型受众就像在水面激起涟漪的石头,是传播的大节点,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推出一圈圈波纹,将潜在受众变为“新生型”受众,形成有层次、有次序的传播结构。可借鉴的有真人秀节目《上新了·故宫》,明星为“内驱型”受众,带动粉丝成为小节点的“新生型”受众,如此一来,传播结构进一步延伸,“新生型”受众不断“繁衍”。豆瓣上超 8 分的评分,显示了这个多级传播结构的成功。
五、结语
非遗是否能永存永生,后面应该画上问号;非遗可以在数字空间里永存永生,后面可以画上感叹号。在传统传播时代,媒介与交通运输等时空限制的存在,造成了有价值的艺术的传播乏力,只能囿于局部地区,形成非遗文化的区隔现象。在网络传播时代,非遗通过网络的普及,使其受众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9]在过去,敦煌石窟非遗是古老遥远的存在;在现在——“非遗后时代”与数字技术同频,敦煌石窟非遗是“近在眼前”的鲜活存在。与传统媒介相比,非遗的数字化传播可达到其传播效果的“N 次方”。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留存非遗、传播非遗、传承非遗,将成为保存保护非遗、激活非遗生命力的有效路径。
同时,当数字技术降临,如何使其与非遗深度交融,而不是碰撞,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技术赋权往往会带来双面结果,因此,当数字空间提供了让人跳出时空局限,沉浸与体验的条件时,非遗传播依然要强调对数字技术的扬弃,在传播中要适当控制数字技术与文化内涵的距离,以技术示人,以文化动人,避免数字泛化带来的形式大于内容。由于网络生活的丰富多彩完全依赖于“技术逻辑”,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构建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这就需要以“以人为本”的总体逻辑来贯彻未来社会的线上构建。[10]此外,对受众的研究应更近一步,抛弃模糊受众差异性的传播,对受众进行分层培育。
总之,在非遗后时代,非遗数字化传播应该努力冲破困境,抓住时代机遇,使非遗“活 ”在数字空间,以展示、表演、体验和教育等多种功能形态展示,在人、物、场之间创造新型生态关系。使受众从仰视到平视,从观看到参与再到传播,甚至成为新的传承者、传播者,并吸引带动新的受众。同时,也让非遗内容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多维立体传播,从中不断汲取活水,糅合新的时代元素,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