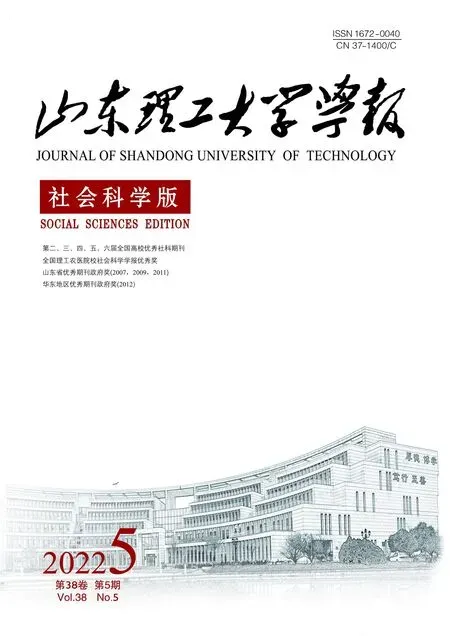底层人的精神世界书写
——葛琴现代小说创作论
董卉川,满 怡
葛琴,1907年12月生,江苏宜兴人,卒于1995年。葛琴的文学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处女作《总退却》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北斗》的第2卷第2期。葛琴以中短篇小说写作见长,作品数目众多,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磨坊》《总退却》《一个被迫害的女人》《结亲》《葛琴创作集》等。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葛琴写作的现实意义。冯雪峰认为《总退却》正面刻画了“上海战争及战争中的民众生活……以描写在战争中的兵士的转变及退却时的兵士的愤懑和失望为主题,作者在决定主题的中心上,可以说是能够抓住了核心的,并且在全篇中作者的精神都集中于自己的目的的”[1]。茅盾也对《窑场》和《总退却》的现实意义作出过高度评价,“与其读工整平稳不痛不痒的作品,我宁愿读幼稚生硬然而激动心灵的作品。对于葛琴的《窑场》和《总退却》,我的感想就是如此”[2]。孙瑞珍则认为葛琴的小说,“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3]。而当代学界对于葛琴的研究其实并不算丰富,相关研究的数量较少,涉及范围不广。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聚焦“葛琴”和“鲁迅”之间的关系,二者总是同时出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多数人认为葛琴的创作离不开鲁迅先生的殷切鼓励。她的创作,不仅是对鲁迅先生揭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继承,也有着新的发展。除此之外,现有的对葛琴的研究多数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即关注其在战争中的文学创作经历和积极影响,在此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总退却》也是学者们热议的对象。她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对劳动人民经历的真实写照。葛琴在关注现实人生、描写抗战烽火、揭露黑暗社会的同时,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与敏锐思维,深入到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之中。葛琴试图建构底层人的精神世界、提炼底层人的精神特质、剖析底层人的精神困境,由此书写底层人精神世界的全貌,使其现代小说具有了典型的精神分析写作的特征与气度。
一、底层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鲁迅曾经说过,葛琴小说的写作“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4]3。其创作诚如鲁迅所言,始终秉承着将笔触指向社会底层民众的写作主旨,“与大众人民结合……为人民,为大众”[5]149,描写了以农村为主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各种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
葛琴首先将视角集中于最易被侮辱被损害的儿童与女性。如《磨坊》中的小林儿、《犯》中的发茂、《骡夫丁大福》中的阿松,他们都出生于农村中的贫苦家庭,由于生活所迫,自幼被父母送去做学徒或童工,终日辛勤劳作,却被虐待欺侮。如《客地》中的铁铁、《一个荒唐的梦》中老蔡的儿子,他们或是父母双亡而流离失所的孤儿,或是母亲早逝又被失业陷于困境的父亲狠心丢弃的幼童。如《一个被迫害的女人》中的寡妇周嫂,因失去了丈夫的庇护而在家乡被迫害,只能外出谋生。如《伴侣》中,失去丈夫的女人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孩子只能狠心将其遗弃在医院。如《药》中,身患重病却被丈夫嫌弃甚至虐待的双林嫂。如《教授夫妇》中,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却终日被丈夫鄙视辱骂甚至殴打的素梅。其次,葛琴将视角集中于其他的底层民众,如《一天》中,从农村来到城市报社做工的阿二。如《蓝牛》《路》中,失去土地、失去经济来源后,只能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的农人蓝牛和金山。如《总退却》中,十九路军中奋勇杀敌的普通士兵寿长年、小金子。如《罗警长》中,被警察抓走的罢工工人李阿毛。如《雪夜》中,不幸失业又被同伴偷走毕生积蓄的老路工驼五叔。如《骡夫丁大福》中在逃荒途中被迫卖掉儿子、又被田主虐待的长工丁大福等。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学的主潮以“大众”“民族”“国家”等宏大词汇逐渐取代了对“个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个人”的灵魂与心灵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以路翎、无名氏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式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种叙事范式及其带来的困境,葛琴的创作,也试图对此种新创作潮流进行呼应。葛琴的现代小说,对底层人精神世界探索描摹的比重,要远大于对外在的黑暗现实和阶级对峙的描写剖析;在心灵探秘的过程中,某些作品中的情节、冲突被淡化甚至趋于消解。
以《枇杷》为例,小说力图挖掘的是小溜儿的精神世界,一切的情节铺陈、冲突设置均是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建构来服务。村中地主的孩子米粉囝囝故意拿新买的枇杷去嘲笑羞辱没吃过枇杷的小溜儿,不但使小溜儿怒不可遏,更使他对无法吃到一个枇杷而耿耿于怀,陷入了偏执甚至疯狂的精神困境之中。葛琴设置的穷人孩童小溜儿和富人孩童米粉囝囝的冲突,并不是为了呈现阶级对峙,而是一种借冲突去建构主人公渴望吃枇杷而不可得的精神世界的行文布局。小溜儿的乡邻陈七嫂同样家境贫寒,却有钱从麻子那里购买枇杷,因此,小溜儿未能吃上枇杷的根源不在于阶级的压迫,而是父亲的嗜赌如命。小溜儿的赌鬼父亲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小溜儿的银项圈都抢去作了赌本,令本就穷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即使枇杷丰收,价格低廉,小溜儿的母亲依旧无力为儿子购买一个枇杷,最终小溜儿因误食了过多别人吃剩的枇杷核而中毒殒命。《枇杷》呈现的是小溜儿渴望吃枇杷而不得的精神世界,《药》与之类似,呈现的是主人公双林渴望买到第四副中药而不得的精神世界。穷困的失业石场工人双林到处借钱,想为患病的妻子购买四副中药,他向相熟的工友老七借钱买了一服药后,再去借钱买药,被小肚鸡肠的七嫂羞辱一番。始终无法凑齐第四幅药钱,令原本就痛苦无比的双林陷入了疯狂苦痛的精神困境之中。如果说《枇杷》中还存在某些阶级对立的成分——小溜儿和米粉囝囝的冲突,在《药》中,这种阶级对峙或阶级压迫已完全消解,只剩下对双林精神世界的描摹。
《一天》建构的是阿二的精神世界。葛琴揭示了主人公所具有的“阿二精神”[6]——病态国民性,展现了阿二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以及自卑自大的病态精神。阿二在得到赴城市报馆做工的机会后,兴奋异常,幻想自己将和村中的权力阶层吴少爷平起平坐。但是到了城市后,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被称为小工,又令他自卑懊恼不已。“小工,‘工’还要加上一个‘小’,不就是这种田人家的放牛小伙计吗……一想起就困也困不着。总之,这个低卑的名目,非想法换它一下不可”[4]11。当一个同乡来到城里拜访他时,阿二又把自己当做了高高在上的城里人,看不起同乡,“得意地望着那个乡下佬”[4]11。在揭示阿二病态国民精神的同时,葛琴也力图呈现他精神世界中的其他成分与侧面。阿二并不完全是“阿Q”,他的精神中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他也期望能在城市中努力工作,站稳脚跟。阿二在报馆认真做工,奈何身边的同事小扬州、猫儿驼背、鬼头麻子等人,尽是些下流无耻、偷懒耍滑之辈。作为刚离开土地的农民,阿二依旧保留着农民的勤劳,看不惯他人的懒惰,尤其是当自己做好分内工作还要被这些无耻之徒冷嘲热讽后,阿二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精神困境。精神上的苦痛甚至压过了自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阿二在最后竟放弃了报馆中的工作——放弃了稳定的收入、放弃了向乡邻炫耀的资本,毅然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只为实现精神的解脱。当他离开报馆、离开城市时,愤怒、痛苦的精神变得“平心静气”[4]38。
在关注底层人现实困境的同时,葛琴实则更为关注底层人的精神困境。以淡化外部冲突、消解情节纠葛的方式,转向了对人精神层面的细致描摹,由此试图建构底层人的精神世界。
二、底层人精神特质的提炼
葛琴对底层人的精神特质——“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提炼,“心理活动的那种在一定期间内能够表明各种心理过程的独特性的一般特征,这种特征既决定于所反映的现实的对象和现象,也决定于个性的过去的状态和个别的心理特性”[7]。葛琴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展现以往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孤独、痛苦、悲哀等心理状态外,还提炼了那个年代底层人的其他精神特质——愤怒与疯狂。葛琴笔下的底层民众首先处于一种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并且这种愤怒的心理状态不被情绪主体压抑在内心,而是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外在行为加以表达。
在《总退却》中,寿长年始终处于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愤愤地”[4]73,源于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寿长年将自我愤怒的心理状态外化为具体的行动——斗殴与杀戮,先是殴打了分配捐赠品不公的士兵,又在某次战斗中,殴打并杀死了一个胆小畏战的上校军官。《枇杷》中的小溜儿也总是处于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同样源于对现实——无法吃上枇杷的强烈不满。当小溜儿与地主的儿子米粉囝囝发生冲突后,并不隐忍退让,而是像寿长年那样将愤怒的心理状态外化为具体的行动——辱骂斗殴。他先是辱骂米粉囝囝,在对方逃跑后又捡起一个石块想要朝对方的脸上掷去,当追上对方后,便准备狠揍他,“握着一个拳头便死命的扑了过去”[8]51。在《罗警长》中,当其他罢工工人在罗警长的威逼利诱下,纷纷放弃当初罢工时提出的诉求时,只有工人李阿毛始终处于一种愤怒的心理状态,“依旧是充满着那种不可遏制的愤怒”[4]242。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大资本家的走狗罗警长,李阿毛将愤怒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外在的行为,首先是对罗警长的怒斥,“滚滚滚他妈,走走狗”[4]242,其次是对工友们的鼓励,“什么鸟XX,不许咱们工人罢工啊!?咱们要干就干!”[4]242罗警长派手下将他带走,资本家又将他辞退,愤怒的李阿毛并未妥协与畏惧,继续将愤怒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外在的具体行动,又来到另一家工厂,勇敢地参与了新一次的工潮。
《罗八堂之死》中的小学教员陈国涛也始终处于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源于对罗八堂等汉奸恶行的不满,“暴怒地一跳,两只血红的眼睛,挑战似盯住罗八堂”[9],愤怒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外在的具体行为便是他在偶遇罗八堂后,发疯似地挥舞起一条女人的内裤,对其进行示威和侮辱。《一天》中的阿二看不惯报馆里的一切,始终处于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内在的愤怒转化为外在的具体行为便是击打和出走,先是通过猛烈捶打制版机来发泄内心的怒火,又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以排遣心中的愤怒和郁结。《路》中的金山也总是处于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愤怒的火星直从他眼睛里射出来”[4]178。金山的愤怒既源自贫困现实的压迫——公路的修建,占据了他的农田、终结了他谋生的手段;更源于母亲对自己的不理解,“听老娘的骂话,比打了他的耳光还难受……老娘也太不谅解他”[4]178。为了谋生,也为了缓和与母亲的关系,愤怒的金山选择了同阿二一样的排解之路——出走。阿二是从城市回到乡村,而金山则是从乡村去了城市——上海做工。
当葛琴笔下底层人愤怒的心理状态到达一定临界点后,愤怒就会转变为疯狂,有些底层民众还会在神志不清、精神失常之时,做出各种可怖的行为。
《枇杷》中的小溜儿在误食了大量他人吃剩的枇杷核后,变得神志不清,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心中无法释放的怒火使他在精神失常时变得极度疯狂,将母亲当作了仇人米粉囝囝,对母亲拳打脚踢,发出疯狂的咒骂。《总退却》中的小阿金在受伤后,发了高烧,也像小溜儿那样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精神状态之中,心中被压抑的怒火与不满彻底释放,疯狂地乱喊乱叫,疯狂地殴打照顾他的护士和好友寿长年。《药》中的双林在从工友老七那里借钱未果又被七嫂羞辱后,变得异常愤怒,回到家后,看着卧病在床的妻子,愤怒的心理转化为疯狂的精神状态,不仅狠命殴打妻子,甚至一度精神失常,想要掐死妻子。《教授夫妇》中的罗中达本就看不上目不识丁的妻子,妻子从乡下来到重庆后的言行举止,更是让他觉得颜面尽失,对妻子无比愤恨。因此,罗中达始终处于一种愤怒的心理状态之中,“愤怒地一震”[5]13。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前风光的教授罗中达,如今陷入了食不果腹、连烟都抽不起的窘境。当妻子为了罗中达不被饿死而去和饥民一道抢了米店的米带回家后,迂腐的罗中达竟然觉得妻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觉得妻子根本配不上自己,也不配做一个人。他不仅对妻子说着最恶毒的诅咒,进行无情的殴打,“一巴掌劈在她脸上……一拳落在她胸上”[5]23,甚至还想要像双林那样杀死妻子,“恨不能一口吞了她,立时取消她做人的资格”[5]25。
《犯》中在县城做学徒的发茂被师父诬陷殴打后,逃回了家。发茂终日受到师父的虐待,内心愤怒无比,这次又遭受了诬陷和殴打,已经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他在路上偶遇了同村的小泥鳅,小泥鳅随口询问发茂为何此时回村,这无心的发问,使本就郁闷敏感、恼羞成怒的发茂变得精神失常。平日老实善良的他瞬间失去理智,一把将小泥鳅摔倒,对其拳打脚踢,甚至拖着小泥鳅想把他带到后山杀死。他像双林和罗中达那样,最终清醒了过来,对自己的疯狂举动表现出了深深的悔恨。而寿长年杀死军官的行为与双林、罗中达、发茂试图杀死各自妻子以及小泥鳅的行为相比,并不是一种相同的心理状态。双林、罗中达、发茂的举动是在疯狂的心理状态下发出的精神失常行为,当他们清醒之后,立即表现出了悔恨与深深的自责。而寿长年则是在愤怒(在其本人为正常)的心态而非精神失常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杀戮,他自始至终都是清醒且冷静的,从他平日喜欢斗殴的言行举止中便可见一斑。
以寿长年、小溜儿、李阿毛、陈国涛为代表的底层人,不再是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逆来顺受者,他们以愤怒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和迎击黑暗社会和剥削阶层的压迫与欺侮。与之相对的则是罗中达、双林、发茂,他们在现实困境的压迫下,没有像寿长年、小溜儿、李阿毛、陈国涛那样进行反抗,而是将怒火与怨气撒向了爱人与朋友,在疯狂中苦痛地挣扎。
三、底层人精神困境的解剖
葛琴提炼和呈现了底层人疯狂的心理状态,并进一步揭示出此种心理状态的生成与他们的潜意识息息相关,“潜意识是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础。潜意识是一个大的范围,其中包括着较小的意识范围。任何有意识的事物都有一个潜意识的初级阶段;潜意识可以停留在那个阶段,但必须被认为具备精神过程的全部价值”[10]606。在葛琴笔下,大部分的底层人最后都会变得精神失常、神志不清,虽然有某些外在因素使然,实则是由自我的潜意识所驱使。
在《枇杷》中,小溜儿因大量误食了别人吃剩的枇杷核后导致神志不清,彼时精神失常的小溜儿向着他的母亲高喊:“我要打你,我要打你,打死你这——打!”[8]65此时的小溜儿已经分辨不出母亲的形象,错将母亲当作了羞辱过自己的米粉囝囝,小溜儿所发出的恶言实则指向的是自我潜意识中的仇人。小溜儿的现实欲望是能够吃到枇杷,但始终未能实现。因此,吃过枇杷且以枇杷对他进行羞辱的米粉囝囝,成为了小溜儿潜意识中最为痛恨的对象。此时的小溜儿处于精神失常之中,错将母亲当作米粉囝囝,不仅辱骂还要殴打母亲——米粉囝囝,“小溜儿猛地飞起一个拳头打在妈的眼角上,露出几个可怕的大牙齿,好像还要去咬她似的”[8]66。现实中的小溜儿原本可以痛打米粉囝囝泄愤,但在准备殴打他时,却被米粉囝囝家的成年家丁阻止。为了讨好少爷米粉囝囝,那个成年家丁对小溜儿进行了殴打报复,令小溜儿内心的欲望——殴打米粉囝囝非但没有能够得到释放,反而积蓄得更深。因此,当小溜儿神志混乱时,潜意识驱使他去辱骂殴打米粉囝囝——母亲。小溜儿精神失常后的疯狂言行实则是潜意识驱使自我完成的欲望投射。
《总退却》中的小金子,受伤后发起高烧,导致神志错乱,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他向着照顾自己的护士和好友寿长年高喊,“拉我做什么?……老子偏不退!……老子死也死在此地!”[4]114。小金子发出的呐喊,也是由自我的潜意识所驱使。小金子同小溜儿一样,欲望——反抗侵略者的行动被压抑。十九路军的普通战士与敌人激战正酣,并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却意外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性格强硬的寿长年能够通过殴打乃至杀死胆小怯战、临阵脱逃的上校长官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怒火。但性格软弱的小金子无法像好友寿长年那样向长官发泄怒火,只能把不想撤退和继续抗敌的欲望压抑,服从命令。这些平日被压抑的欲望——对撤退命令和畏战长官的不满,以及反抗侵略者的决心,成为了小金子的潜意识。当他神志错乱后,这些潜意识得到了彻底释放,“什么道理呀,……我们打了几十天了啊!……为什么叫老子们退?……偏不退!……打死你这个黑良心的!”[4]115神志不清的小金子以为自己依然在战场奋战,“老子们要打矮鬼……你们就放机关枪!……放火!……开枪!开啊!……长福!长福!……给我一发!”[4]115这是小金子潜意识的终极外化,葛琴以小金子精神失常后的言行,歌颂了十九路军普通士兵的英勇无畏,以及与日寇殊死战斗的赤诚之心。
《药》中的双林在试图杀死妻子之时,意识是不清醒的,像陷入梦境之中,“突然,他吃惊地一跳,好像做醒了一个大大的恶梦,睁着两只发红的眼睛,无可奈何地捧着他老婆的头”[8]90-91。梦的本质是“不加掩饰的欲望满足”[10]120,双林在自我“恶梦”中的所作所为也是欲望的典型投射。他无力承担妻子治疗所需的四副中药费用,再向老七借钱买药时,不但被拒绝还被七嫂羞辱。生活的重压、他人的羞辱,使双林萌生了杀死妻子的念头——欲望。他认为自我人生苦痛的源头是患病的妻子,只要将妻子杀死,就能终结自我的苦痛,摆脱悲哀的命运。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双林去实施杀妻的行为,理智让他压抑这种欲望,“它可以在白天产生但又被排斥,在这种情况下,被留到夜晚的欲望是未被处理但也是被压抑的”[10]545,但这种欲望早已转化为双林的潜意识。七嫂的羞辱则是触发双林进入梦境——疯狂精神状态的开关,他回家后,看着床上呻吟的妻子,进入了“梦境”之中,潜意识驱使他将压抑已久的欲望释放,狠命地掐着妻子的脖子。几乎要将妻子杀死之时,妻子胸部膏药的解开则成为他由梦境(疯狂)回到现实(清醒)的关键,他看到膏药下妻子乳房上那可怖的伤疤后,无比悔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和自责。因此,面对妻子的击打,他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让妻子尽情痛击自己,“‘你抓吧,把我的眼乌珠也抓出来吧……总怪是我……’双林的脸,便紧紧地贴在老婆的脸上,大家看不见大家的脸,老婆的眼泪在脸上淌着,双林的眼泪直往肚子里咽着”[8]91。证明他已彻底清醒,摆脱了疯狂的精神状态。
对小溜儿、小金子、双林精神失常状态下所做出的疯狂行为的细致描摹,揭示了葛琴对底层人隐秘心理的深度挖掘,由此实现对底层和个人精神的解剖和分析。同时,葛琴又将个人精神困境与外部现实相结合——贫困的生活和黑暗的社会压迫是导致他们疯狂的重要缘由,由此实现了社会现实与个人精神分析相结合的创作主旨。
四、结语
葛琴甫一出道便得到众多名家的首肯,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葛琴创作了数目众多的小说,她的文学创作浸润着中国现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葛琴,试图通过对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书写,挖掘与思考造成底层人苦痛矛盾、愤怒疯狂灵魂的社会以及个人根源,绘制底层民众的社会精神史和个人精神史。葛琴的文学创作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人物长廊增添了新的画像。“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葛琴的作品,能够推进葛琴研究的深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亦是一种有益的拓展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