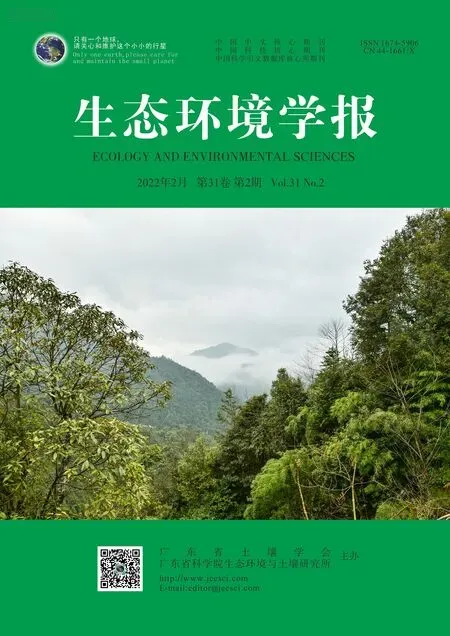水环境中糖皮质激素的环境行为及生态风险研究进展
张云 ,舒抒,罗鑫,钟琴,邹华 *
1. 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 江苏省水处理技术与材料协同创新中心/苏州科技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9;3.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无锡 214101
“重视新污染物治理”是中国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题中之意。在众多新污染中,甾体激素(类固醇激素)是一类强效的内分泌干扰物,这类物质在多种环境介质中被广泛检出(Sacdal et al.,2020;Zhong et al.,2021),其在环境中的累积会导致鱼类、两栖动物等生殖率下降、性畸形,甚至出现种群数量减少(Leet et al.,2012;Leslie,2017),因而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根据细胞内结合的受体不同,甾体激素可分为雌激素(Estrogens)、雄激素(Androgens)、孕激素(Progestagens)、盐皮质激素(Mineralocorticoids)和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以下简称GCs)五类,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雌激素,而对其他种类激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 GCs的相关研究尤为稀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甾体激素药物销售额以每年10%—15%的速度递增,其中天然和合成的GCs消费量稳定增长,GCs的使用量是雌激素和雄激素的 10倍(Runnalls et al.,2010;Liu et al.,2012a)。在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的背景下,GCs因能够有效降低新冠确诊病人的死亡率(Horby et al.,2021)而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其使用量在未来若干年内仍十分可观。因此 GCs的环境归趋和潜在的生态影响不容忽视,亟待开展相关研究。
常见的GCs及其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它们同其他甾体激素类似,都具有环戊烷多氢菲结构,不易挥发且具有一定疏水性,易于吸附和生物富集,但同时又具有羟基等多种亲水键,因而具有复杂的理化性质,这些理化性质增加了其在环境中迁移转化及生物利用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GCs的环境来源和目前的污染水平进行概述,对已有关于GCs的环境行为及生态毒理效应的研究进行总结,为进一步展开GCs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对评估和控制GCs的潜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图1 常见糖皮质激素分子结构Figure 1 Molecular structure of frequently detected glucocorticoids
1 环境中糖皮质激素的来源与污染现状
1.1 来源
环境中GCs的来源总体分为医药废水、养殖场废水和畜禽粪便、污水处理厂出水和剩余污泥三类,其中医药废水和养殖场废水中 GCs的含量较高,污水厂出水的含量较低。
制药厂和医院作为GCs的生产和使用单位,是其进入环境的主要点源之一。医药废水检出的GCs主要有地塞米松、倍他米松、泼尼松、泼尼松龙、甲基泼尼松龙、可的松和氢化可的松,其中合成GCs的种类较天然GCs多、含量较高(Schriks et al.,2010;Ammann et al.,2014;Creusot et al.,2014)。制药厂废水中地塞米松、甲基泼尼松龙、泼尼松龙和泼尼松贡献了主要的糖皮质活性,其中地塞米松和甲基泼尼松的质量浓度可分别达到 2.9 μg·L−1和1.26 μg·L−1(Creusot et al.,2014)。医院废水中地塞米松和倍他米松质量浓度高达 1.72 μg·L−1,泼尼松和泼尼松龙质量浓度达 1.22 μg·L−1,其余 GCs质量浓度为 ng·L−1水平(Ammann et al.,2014)。
随着规模化养殖的迅速发展,GCs被大量用于动物疫病防治和肌肉催长,使得畜禽养殖场废水、水产养殖场水也含有较高浓度的GCs。养猪场冲洗废水中检出氢化可的松 590—1310 ng·L−1、泼尼松龙 88.6—1390 ng·L−1、地塞米松<1.27—260 ng·L−1和可的松 44.4—87.2 ng·L−1(Liu et al.,2012b)。此外,养猪场粪便中检出氢化可的松和泼尼松龙最高可达 (175±8.7) μg·kg−1和 (32.0±7.1) μg·kg−1,奶牛粪便中检出泼尼松龙 (8.5±1.4) μg·kg−1(Liu et al.,2012b,2012c;张晋娜,2019),若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或还田,则可成为GCs的潜在污染源。淡水水产养殖场主要检出氢化可的松,质量浓度最高为34 ng·L−1,海产养殖场水样中检出泼尼松龙 40 ng·L−1和可的松 3.5 ng·L−1(Liu et al.,2017a、2017b)。
污水处理厂进水中的 GCs主要来自于人体的天然分泌或未代谢完全的药物,例如,成人尿液中的可的松质量浓度可达 66 μg·L−1、氢化可的松达24.2 μg·L−1(Gouarne et al.,2004)。而目前的污水处理工艺不能将所有GCs去除,出水中仍然含有一定量的GCs。国内外污水厂出水中检出的主要GCs包括氢化可的松(0.19—122 ng·L−1)、可的松(未检出—95.4 ng·L−1)和泼尼松龙(0.17—190 ng·L−1),此外,检出泼尼松、皮质酮、曲安奈德(Triamcinolone acetonide)和地塞米松的质量浓度低于 50 ng·L−1(Chang et al.,2007、2009;Fan et al.,2011;Liu et al.,2012a;Ammann et al.,2014;Isobe et al.,2015;Jia et al.,2016;Weizel et al.,2018;沈晓艳,2016)。其中,氢化可的松的含量和检出率较高,这可能由于其既是人体自然分泌的主要激素之一,也是多种常用药物的主要成分。此外,污水厂污泥中也检测到多种GCs,若不能妥善处置,也可能成为环境中GCs的潜在来源(Fan et al.,,2011;Liu et al.,2012a)。
1.2 水环境中的糖皮质激素
表1汇总了河流、湖泊和近岸海域等各类地表水体中检出GCs的情况,检出水平较高的GCs包括可的松、氢化可的松、泼尼松、泼尼松龙和地塞米松,这与在来源中检出的主要种类一致。天然GCs可的松在北京一些河流的检出率可达 100%,平均质量浓度可达 173.8 ng·L−1(Chang et al.,2009;Shen et al.,2020;郭文景,2015)。氢化可的松在多个水体中的检出频率也很高,平均质量浓度为2.37—6.04 ng·L−1(Chang et al.,2009;Zhou et al.,2016)。此外,氢化可的松的代谢产物二氢可的松和四氢可的松的检出率也较高,含量占天然GCs的7.7%—39%(Shen et al.,2020)。氢化可的松的前体物质醋酸氢化可的松也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在北京清河中的含量比氢化可的松高出1个数量级(郭文景,2015)。由此可见,在研究GCs的环境赋存时,其前体物及代谢产物的含量和污染特征不容忽视。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痕量的GCs被检出,其中曲安奈德、布地奈德、曲安西龙(Triamcinolone)、利美索龙(Rimexolone)等质量浓度也可达到几十 ng·L−1。

表1 地表水中检出的主要糖皮质激素Table 1 Major glucocorticoids detected in surface water
沉积物是各类污染物在水环境中一个重要的汇,GCs也在不同水体的沉积物中有检出,含量为μg·kg−1水平。如太湖底部沉积物中检出可的松、氢化可的松分别为 5.85、1.10 μg·kg−1(Zhou et al.,2016),中国南海流沙湾、海陵岛等水产养殖区沉积物检出氢化可的松不高于 1.70 μg·kg−1(杨雷等,2019)、泼尼松龙不高于 2.64 μg·kg−1(Liu et al.,2015)。Creusot et al.(2014)在制药厂附近河流的沉积物检测到高浓度的GCs,其中泼尼松、泼尼松龙、甲基泼尼龙、氢化可的松、可的松以及地塞米松均达到 mg·kg−1量级,地塞米松质量分数最高,可接近90 mg·kg−1。沉积物中累积的GCs具有潜在的风险,水力扰动以及环境条件的变化可能引起GCs的缓慢再释放,从而对河流水质产生长期影响。
地表水中GCs的时空分布受到点源、面源分布以及气候条件的影响。通常接近污染源的区域GCs含量较高,如近制药厂出水口的河流中GCs含量远高于其他河段(Creusot et al.,2014),人口密集河段的 GCs含量高于人类活动稀少的河段(谭丽超等,2014),广东海陵岛附近靠近污水厂出水口、养殖场及旅游区检出的 GCs含量远远高于离岸区域(Liu et al.,2015)。由此可见,环境中GCs的升高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此外,一些研究也观测到地表水中GCs浓度的季节性变化,如氢化可的松在太湖水中的含量为冬季高而夏季低(Zhou et al.,2016),在南海流沙湾海域中也是枯水期比丰水期高(杨雷等,2019),GCs的季节性变化与污染源释放量、降雨量以及不同相态间分配行为的变化相关,针对某一区域的GCs溯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除了地表水,地下水中也检出一定量的GCs,尤其是在干旱地区,以污水厂出水或再生水作为地表水补给时,污染物会随水流渗入地下水,从而造成污染。如中国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中检测到不同种类的GCs质量浓度可达几十甚至几百ng·L−1(郭雅婷,2020)。虽然在地下水中检出GCs的频率和浓度比地表水低(Xiang et al.,2020),但地下水作为重要的饮用水源之一,一旦被污染造成的健康风险不容小觑,而且地下水修复难度大、修复成本高,应予以重视。
2 糖皮质激素在环境中的归趋
2.1 不同相态间的分配及迁移
GCs进入水环境后面临着在液相、固相及有机质等不同相态间的分配、吸附、解吸、交联等过程,这些过程对其迁移能力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雌激素、雄激素等,针对GCs的研究非常有限。表2汇总了代表性GCs与其他类甾体激素的有机碳归一化吸附常数(Koc)和正辛醇-水分配系数(Kow)以进行比较。Liu et al.(2012a)通过EPI Suite估算了几种常见GCs的logKoc,发现天然GCs与合成GCs的logKoc值均比较接近,在1.30—1.57之间。Zhou et al.(2016)在太湖水和沉积物中检测出多种GCs,据此计算出的未平衡状态下的分配系数pseudo-logKoc比Liu et al.(2012a)估算的值大 0.38—1.71,相当于实际条件下的pseudo-Koc比理论估算的Koc大2—50倍。目前尚缺乏针对沉积物等环境固体介质对 GCs的吸附平衡的系统研究,实验测定的GCs的Koc理论值有待补充和完善。相比之下,前人对雌激素、雄激素和孕激素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这三类激素的logKoc约在2.13—4.16之间(见表2),明显大于GCs,说明GCs具有较强的亲水性,这一点从Kow的相对大小得到印证。Gineys et al.(2012)发现GCs的logKoc与logKow之间相关性很弱,推测其吸附机理是疏水键和氢键的共同作用,而非单一的疏水性分配和ππ相互作用。综上所述可推测,相比于其他类甾体激素,GCs更易于在水环境中迁移传播,也可能具有更高的生物可利用性。鉴于其亲疏水性均具备的特质,这一推测有待进行实验验证。

表2 四类甾体激素的分配系数比较Table 2 LogKoc and logKow of four groups of steroid hormones
以开发高效吸附材料为目的,前人尝试用化工中和污泥、鸡蛋壳、斜发沸石和改性生物炭对GCs进行吸附,相关结论对推测其在环境中的迁移性能以及影响因素有一定参考价值。结果表明,提高GCs初始浓度会增加吸附剂的吸附容量,但降低吸附速率,升高温度会使分配系数变小(Pavlovic et al.,2017),酸性条件有利于增加吸附剂对GCs的吸附(Mohseni et al.,2016),投加负载纳米零价铁的生物炭可提高河床对GCs的吸附速率和容量,从而增强截留作用,减少对地下水的污染(向雅芸,2020)。
2.2 转化及降解
GCs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衰减速率不同,占主导的机制亦不同。从污水厂排出的GCs沿受纳河流呈现明显的衰减趋势,且夏季的衰减速率比冬季快。由于GCs易溶解于水相,有学者认为光降解的作用对于地表水中GCs的衰减非常重要(Daniels et al.,2018)。即便在污水中,GCs在 80 mJ·cm−2强度的 UV254照射下可达到完全降解(Jia et al.,2016)。但也有研究报道,合成GCs如醋酸可的松在3.21 mW·cm−2强度的UV375照射下浓度没有明显降低,需要催化剂 TiO2存在才可明显降解(Romao et al.,2015)。光降解GCs的适合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降解途径也尚未明晰。
GCs在河流或地下水含水层中的降解由微生物起主导作用,不同含水层中衰减速率的差异可能由有机质含量和微生物群落组成不同造成的(Wang et al.,2018;Li et al.,2019;向雅芸,2020)。氢化可的松和地塞米松的降解速率相当,半衰期分别为3.96—7.22 d和3.12—6.13 d,总降解率分别为94.5%和 96%,其中微生物降解占 90%以上(Li et al.,2019)。微生物群落的不同导致氢化可的松的降解途径也不同,目前报道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A环(参见图1)的双键先加氢饱和再断裂开环,二是先将 D环的支链氧化成羰基,然后再羧酸化进行开环,通常先从A环开环的降解途径对降解速率的影响更大(Wang et al.,2018)。总体来说,合成GCs比天然GCs难降解,尤其是含氟的合成GCs,脱氟开环成为降解的限速步骤。有研究表明,在含水层中加入负载纳米零价铁的生物活性炭,能提高微生物对含氟GC曲安奈德的降解速率达两倍多,而在自然条件下曲安奈德的降解速率非常缓慢(Xiang et al.,2022;向雅芸,2020)。此外,通过生物电化学方法,可实现地下水中地塞米松和硝态氮的同步去除(郭雅婷,2020),为受GCs污染的地下水修复提供一定的参考。
不同 GCs的可生物降解性和相对降解速率可从 GCs在活性污泥或畜禽粪便堆肥中的降解情况获得参考。在好氧条件下,泼尼松龙、曲安西龙、倍他米松、醋酸泼尼松龙以及醋酸氢化可的松可在4 h内完全降解,而含氟GCs曲安奈德和氟西奈德(Fluocinolone acetonide)24 h仅降解 50%左右(Miyamoto et al.,2014),这与前面的结论一致。在厌氧条件下,初始浓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GCs的可生化降解率。氢化可的松与可的松的降解率随初始浓度升高而降低,氢化可的松的降解率显著高于可的松,泼尼松的生物降解率随初始浓度升高而升高,而地塞米松没有明显降解,4种GCs都很难彻底矿化为CO2和CH4(崔波蕾,2018)。有研究发现GCs的持久性较孕激素和雄激素强,堆肥结束时GCs总浓度不降反升,说明在堆肥过程中GCs可由其他类甾体激素转化而来(Zhang et al.,2019;张晋娜,2019)。总体而言,GCs在堆肥等人工处理条件下的降解途径尚需进一步研究,含氟GCs在自然环境中可能成为潜在的持久性污染物,其归趋行为及强化处理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之一。
3 糖皮质激素的生态毒理效应
GCs由肾上腺皮质分泌,是脊椎动物压力反应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主要功能激素,通过与GCs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s,GRs)结合调节基因的转录,发挥生物学活性(Patchev et al.,1995;Anacker et al.,2011)。GCs参与脊椎动物的多项生理过程,如控制能量代谢、免疫功能、压力反馈行为等(Coutinho et al.,2011),从而影响机体的功能和平衡。目前,GCs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但作为新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待进行系统评估,因此本节将重点放在GCs对水环境的潜在风险,相关毒理研究多以鱼类为模式生物。
3.1 行为变化及生长发育损害
GCs的环境浓度通常远远低于其急性致死浓度,对于水环境的潜在风险学者们更关注的是环境相关浓度或亚致死浓度的毒理效应。暴露于外源性GCs下可导致鱼类出现行为异常或损害鱼类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能力。例如,通过食物或水暴露于GCs的虹鳟鱼(Oncorhynchus mykiss)和斑马鱼(Danio rerio),其运动能力、攻击和抢夺食物的行为会被抑制,对光的敏感性也有所降低,从而处于不利的生存条件(Gilmour et al.,2005;Xin et al.,2020)。GCs可通过影响糖类、脂质、氨基酸的代谢途径,导致金头鲷(Sparus aurataL.)出现体质量减轻、体型偏小的症状(Jerez-Cepa et al.,2019)。但对于肝脏的影响则呈现不同规律。斑马鱼幼鱼暴露于地塞米松后肝肿大和脂肪肝的鱼类数量显著增加(Yin et al.,2017),而成年黑头呆鱼(Pimephales promelas)暴露于倍氯米松二丙酸酯后肝体指数却显著减小(Lalone et al.,2012)。不同结果可能受试验物种、生长阶段及GCs种类和浓度影响,有待进行系统研究。此外,多种鱼类暴露于地塞米松后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雄性化特征,产卵频率和繁殖力均下降,受精后的胚胎发育不良,后代畸形率增加(Lalone et al.,2012;Guiloski et al.,2015;Miller et al.,2019)。
3.2 分子水平的毒理变化
除了行为和生理功能的变化,近年来的相关毒理研究多侧重于分子水平的影响,旨在通过酶或基因表达的变化揭示 GCs产生不良效应的内在机制并预测潜在风险。暴露于GCs后酶活的变化通常与调控体内化学物质的代谢以及氧化应激反应有关。例如,地塞米松可以改变虹鳟鱼肝脏中细胞色素酶CYP450的活性,使肝微粒体 CYP3A蛋白显著升高,从而影响外源化学物质、脂肪酸、维生素等的代谢(Burkina et al.,2015)。南美牙鱼(H.malabaricus)通过食物暴露于地塞米松后,肝脏中的谷胱甘肽浓度以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谷胱甘肽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的活性升高,表现出氧化应激反应,而生殖腺中的谷胱甘肽浓度和GPx、GST活性却降低(Guiloski et al., 2015)。
在基因表达层面,暴露于GCs后通常鱼类肝脏细胞中相应的受体基因会显著上调,且呈现一定的剂量效应(Kugathas et al.,2013)。发育中的斑马鱼幼鱼分别暴露于地塞米松、泼尼松龙和曲安西龙后,fbxo32、cry2b、klhl38b3个基因在所有暴露组中均显著上调,可作为环境浓度下GCs暴露的生物标志物(Chen et al.,2017)。鱼类雌性个体出现雄性化与性激素受体基因、卵黄蛋白原(Vitellogenin,VTG)基因的表达变化有关,如倍氯米松二丙酸酯可使雌性黑头呆鱼肝脏中的 VTG表达显著下调;通过食物暴露于氢化可的松后,美洲黑石斑鱼(Centropristis striata)性腺的芳香酶cyp19a1a调控基因显著下调,使得睾丸激素水平升高(Miller et al.,2019)。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可将宏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应用到GCs的毒理学的研究中,有助于进一步识别GCs的响应基因以及水生生物的应对机制,这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3.3 复合效应
近年来,多种污染物的复合效应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尤其对于微/痕量污染物,其特点是环境浓度低,单一作用时无显著毒性,但多种污染物混合后可表现为加和效应甚至协同效应,从而对水生生物造成毒害。目前文献已报道的GCs的复合效应主要表现为由混合物中强效的 GCs占主导或是加和效应。合成GC丙酸氯倍他索比天然GC可的松强效,混合作用于斑马鱼胚胎时对生理指标的影响与丙酸氯倍他索单独作用时的活性相当,但对心率增加以及pepck1基因上调具有加和作用(Willi et al.,2018)。鲤鱼(Cyprinus carpio)分别单独暴露于丙酸氯倍他索和丁酸氯倍他松(clobetasone butyrate)时对血清中游离氨基酸浓度的调控效应相当,联合暴露时接近加和效应(Nakayama et al.,2014)。丙酸氟替卡松(fluticasone propionate)、曲安奈德和丙酸氯倍他索 3种合成 GCs的混合物对斑马鱼幼鱼的 GCs响应基因的调控具有加和作用(Willi et al.,2019)。此外,GCs与其他类甾体激素混合可表现出加和效应甚至协同效应,例如,雌性黑头呆鱼同时暴露于雌雄孕糖四类5种甾体激素,每种激素的浓度均低于其最低效应浓度,但联合暴露导致产卵率显著降低;当每种激素设置在抑制产卵率18%—40%的浓度水平时,联合暴露会导致黑头呆鱼产卵被完全抑制(Thrupp et al.,2018)。单一的氢化可的松、丙酸氯倍他索暴露下,成年雌性斑马鱼的条件因子(体质量/体长×100)和性腺指数没有产生显著变化,但同时暴露于丙酸氯他索、曲安西龙、雌二醇、雄烯二酮和孕酮的混合物后,这两项指标均明显降低(Faltermann et al.,2020)。目前GCs的复合效应仅限于不同GCs以及与其他甾体激素的混合,与其他类别中能够参与糖类代谢调控、干扰内分泌或免疫系统功能的污染物的复合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水环境中 GCs的来源相对比较明确,这对进行源头控制、削减环境输入是比较有利的。GCs在水环境各类介质中普遍存在,甚至在地下水及含水层中都有检出,说明其迁移能力较强。当前研究多报道的是常见的几种GCs,然而其前体物及代谢产物的环境赋存和污染特征研究较少,代谢产物的生态毒理效应尚不清楚,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领域。GCs亲疏水性基团兼具,与亲水和疏水性的介质及其他污染物均可发生相互作用,但当前的环境行为研究仍未较好地解答悬浮颗粒、有机质等复杂介质对 GCs环境归趋和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及机理,GCs与其他污染物(包括当前的研究热点纳米颗粒、微纳塑料等)在界面吸附、共同迁移、降解转化等环境过程中的竞争或协同行为也未见报道。此类研究涉及多学科交叉,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但有利于完善人们对GCs的环境归趋的认知,值得进行开拓和深入研究。在毒理研究方面,GCs作为多种药物的主要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被研究得较为充分,而其生态效应则多以鱼类为受试生物,对其他营养级生物的毒性乃至食物链和生态系统影响被研究得较少。未来研究可借助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手段,确定更多具有代表性的毒性终点,从而对GCs进行更加系统的生态风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