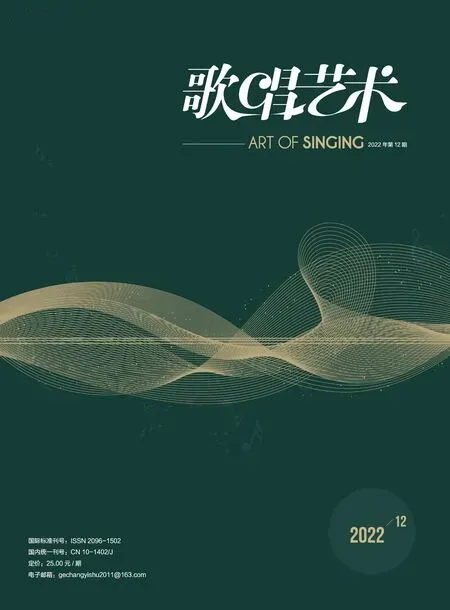喜歌剧
〔美〕查尔斯·罗森著,杨燕迪译
1778年12月12日,莫扎特在曼海姆写信给父亲,说那里正在制作一种新型的带音乐的戏剧,并提到制作人邀请自己为这种戏剧作曲:“我一直想写这种戏剧。我记不起是否告诉过你,我第一次在这儿时有关这类戏剧的事情?那次我看过这种类型的戏上演了两遍,非常非常喜欢。真的,完全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戏会很没有效果。当然你知道,其中没有歌唱,仅仅是念白,而音乐像是在宣叙调中那样作为某种辅助性的伴奏。有时台词是说出来的,而音乐继续,这效果非常好……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认为大多数歌剧宣叙调就应该像这样处理——仅仅是偶然唱出来,当歌词能够完美地被音乐表现出来时。”①这封信也许不应该仅仅根据字面意义来判断:莫扎特打算征服巴黎音乐世界的企图刚刚以惨败告终,而现在他面临着最憎恨与最担忧的事情——回到萨尔茨堡。他的热情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努力,试图说服正在萨尔茨堡等得不耐烦的父亲,从实际出发,自己最好暂缓回家,眼下可能还有其他希望?但是,莫扎特的态度,他的试验性探索,还是显露无遗。他对所谓“音乐话剧”(melodrama,有音乐伴奏的说白)的可能性感到欢欣鼓舞,而他对戏剧效果的感觉绝不仅仅限于声乐。相反,他对音乐作为戏剧动作的对等物与音乐作为歌词的完美表现这两者之间作出了清晰的区分。②更具重要性的是第一个概念,而他会摒弃歌唱而启用说白,如果这样做可以让动作更为有效、生动。
《扎伊德》(Zaide)中运用了一些很有效果的音乐话剧手法,直接指向了《菲岱里奥》,但我们绝不要忘记《后宫诱逃》中佩特里罗(Pedrillo)的小夜曲被突然打断的片刻,以及奥斯敏(Osmin)歌曲中的说白处理,或者《魔笛》中帕帕盖诺(Papageno)在准备自杀之前计数到三的片段,否则就会丢失莫扎特曾有一段时间对这种手法非常感兴趣而写下的一切。然而,莫扎特从未丧失进行试验的渴求,以及他的那种敏感——在歌剧中,音乐作为戏剧动作的重要性应该高于音乐作为表情的手段。这并不是否认莫扎特为人声写作的技艺,也不是否认他对于复杂花腔的喜爱。然而,面对那些希望显摆自己歌喉之美妙的歌手的虚荣心,莫扎特并不总是一再忍让。尤其在重唱中,如《伊多梅纽》中的伟大四重唱,他坚持歌词应该更多是说出来而不是唱出来。③莫扎特在曼海姆时对“音乐话剧”手法的短暂兴趣显示了一个年轻作曲家的热情,此时他刚刚发现,就满足歌手和表现情感而论,舞台上的音乐可以做得更多,同样能够将情节和复杂曲折卷入其中。但在莫扎特写作美丽、动听但较少为人所知的《假园丁》时,他对这一观念仍是一知半解。
18世纪早期的风格已经能够对付歌词文本自身所能提出的任何要求。亨德尔与拉莫的歌剧音乐能够转化任何片刻的情感和情境,但是这种音乐却未触及动作和运动——简言之,即任何非静态的东西。奏鸣曲风格为表达最具动态的舞台音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这种说法仅仅是因为没有考虑在奏鸣曲风格发展中歌剧风格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显得过分简单。意大利喜歌剧(opera buffa)尤其具有影响力,而古典风格在描绘喜剧情境和喜剧姿态时运作得最为得心应手。
这种风格之所以特别适合表现戏剧动作,是因为下列三点:第一,对乐句和形式作清晰表述,因而赋予一部作品以一系列明晰而有别的事件发生的品格;第二,主和属之间更强烈的对极化,这使得在每部作品的中心有更为清晰的张力提升(以及相关联的和声区域有更明确的性格,这也可被用来表达戏剧性的意义);第三,但绝非最次要的是,节奏转换的运用,它允许织体随着舞台上的动作进行发生改变,但又不会在任何意义上破坏纯音乐的统一性。所有这些风格特征都属于该时期的“无名氏”风格;它们是1775年那个时段音乐的“通用货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莫扎特是第一个以系统化的方式真正理解这些风格特征对于歌剧的重要意义的作曲家。从某种角度看,格鲁克是一个比莫扎特更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他的风格塑造更多来自一种对自己时代传统的倔强拒绝,而不是坦然接受。但是也正是这种原创性,妨碍了格鲁克企及莫扎特在处理音乐与戏剧关系上所达到的自如和流畅。
注 释
①引自《莫扎特与其家人书信》(Letters of Moxart and his Family,London, 1966),艾米丽·安德森(Emily Anderson)编订。
②在1780年11月8日的信中,莫扎特反对在咏叹调中用旁白的想法:“在对话中,所有这些都很自然,因为旁白的几个词可以说得很快;但在咏叹调中,歌词必须重复,旁白就会效果很差,即便情况并非如此我也偏好一个不被打断的咏叹调,参见《莫扎特与其家人书信》,第659页。
③1780年12月27日的信,参见《莫扎特与其家人书信》,第699页。
——寒窑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