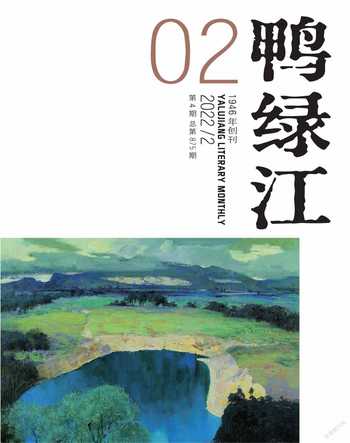等待
麦子珩
没想到在这看似干燥的冬夜却下起了雨。
我急忙躲进一家窝缩在城市边缘角落的饭店。当我正在犹豫是否要在此处解决我的晚餐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从厨房里走出来,看样子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你好,你想吃点什么吗?”
“您有什么菜就给我上什么吧。”
“什么都可以吗?”
“是的,辛苦你了。”
庭院里有一个小孩在玩耍,他将凋落在地上的鸡蛋花捡起来。一朵一朵地抚平,平整地放在小竹篮里。我愈觉得阴冷,但是院里的小孩像是没知觉似的,木讷地在积水的地板上走来走去,脸上的表情无比平静温和。
我不忍心看他那彤红的小脚丫还浸湿在刺骨的水里,这样下去孩子肯定会感冒的,说不定那白嫩的小脚会长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冻疮。
“大姐,院子里的小孩是您的儿子吗?”
“对,他叫小土豆。”老板娘从厨房探出头,微笑着回答我。
“您也是,这么冷的天还让孩子穿着拖鞋在花园里边玩水啊。”
老板娘赶紧从厨房里出来,便看到孩子在院子里踏着水花,凛冽的夜风呼呼地刮起孩子头上柔软的头发。
男孩被妈妈像小鸡一样拎在手里,我才发现他原来是这么瘦小。他的皮肤很白,虽然矮小瘦弱,但脸蛋还是粉嫩光滑的,像只刚出生的小羊羔,软绵绵地依偎在妈妈的怀抱。
我原本以为面前这位大姐会和其他妈妈一样,轻声斥责孩子的调皮捣蛋,但事实却并不如我想的那样。大姐将孩子从自己的怀中轻轻地放到椅子上,拿出一条干净白毛巾,细细地擦干了孩子的脚。在这个过程中母子俩没有说过一句话,孩子也很安静,只盯着两只小手掌里的鸡蛋花。
两朵在冬季还能存活的鸡蛋花,花形扁小,不像一般鸡蛋花那般花瓣厚大,更不如别的鸡蛋花一样色彩鲜明。这两朵鸡蛋花花色暗淡,五片雪白的小花瓣坚强地相互依偎着,在花瓣中央渗出一点儿鲜嫩的浅黄色。它们看起来很脆弱,如果被旁人一把摘下,它们或许便会散落一地,而小男孩似乎看懂了这两朵小鸡蛋花,他用短短的手指温柔地捧起它们,小鸡蛋花似乎找到了归宿,静静地伫立在男孩的指尖,仿佛那才是它们生长的土壤。
最终打破寂静的是母亲想给男孩换下湿掉裤脚的裤子,男孩看见母亲手里的裤子却不愿意了。“小土豆,你的裤子已经湿了,一直穿着会着凉会生病的。”母亲轻声地哄着男孩。男孩却怎么也不肯换下身上的这条有黑白格子的裤子。
“我喜欢这条裤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虽然软绵绵的,但更如雪松一样清冷。
男孩母亲叹了口气,“这天气,衣服裤子也干不了呀。”她似乎注意到我的眼神,扭头望向我。我们对视了。我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便赶紧回避了她的眼神。她却毫不在意,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这孩子只穿有黑白格子的裤子。”我忍不住望向她,大姐只是微笑着。
突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对我说:“真不好意思,都忘了您是来我们店里吃饭的了。刚才菜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给您端出来。”
“哦,没事儿,我不着急的。”
“来咯来咯!”大姐给我端上了一大碗丝瓜瘦肉粥,一碟炒米粉,还有粉蒸排骨,“今天比较晚了,厨房里剩的食材也不多了。您试试看味道还满意吗?”她手里拿着端菜用的大铁盘子,站在圆形餐桌的旁边等我的回应。
我便拿起筷子试了一口炒米粉,喝了一大口瘦肉粥。大姐的手艺很好,外面的炒米粉都过于油腻,吃得人满口肥油,但是今天的炒米粉油量适中,口感很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但又有肉丝的香味儿。丝瓜瘦肉粥应该是熬了很久,绵绵的,丝瓜的清甜渗进粥里,咸瘦肉腌制得恰到好处。
“大姐,您做的菜都好吃,我这儿也没什么需要了,您快去照顾孩子吧。”
“好嘞好嘞,您要是有别的需要随时叫我。”
我正对着饭馆里的旧式挂钟,这看起来已有不少年头的挂钟被挂在这面有些斑驳的白墙上,秒针安静地转动着,它不像别的时钟一样冰冷——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我每每看着秒针一顿一顿地走着,便会感到心慌,特别是当我一个人下班回家,疲惫地躺在床上时,听着秒针的声音,便更觉凄凉。眼前的这个旧式挂钟,它的钟摆左右摇晃着,它像世界上另一个独立的存在,有自己的世界,安稳平和地在属于它的空间里生活着。
现在已经将近11点半。饭店的灯依旧亮着,水还流着,院墙上的电表还在工作。大姐将餐厅里外都打扫了一遍,男孩不吵闹着要回家,只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我看时间已经不早,便打算结账。结账的时候,我看周围已经没有别的客人,看来大姐他们是为了等我才这么晚打烊。“大姐,真不好意思,今晚因为我,你和孩子才这么晚回家。”
“其实不是的,我们每晚都12点才离开店铺,就算没有客人也是一样的。”大姐边说边用吹风机把男孩湿掉的裤腿吹干,“孩子喜欢听墙上挂着的这个挂钟在12点的报时声,只有听到才肯和我回家睡觉。”
“孩子喜欢?”
她此时己把男孩的裤腿吹干,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暖和。小土豆用小手摸了摸被热风烘干的裤腿,浅浅地笑了。他离开我们谈话区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此时己不再看着手中的鸡蛋花,而是盯着窗外。
“你看,他在听钟摆的声音。”大姐接上我们刚才的对话,“他不只是喜欢,对于他来说,每晚12点的报时声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难以理解她话中的意思。此时离12点还有15分钟。
“小土豆是个特别的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医生。医生说小土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但是小土豆并不严重,旁边的人也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他是个安静乖巧的孩子。”
墙上挂着的时钟的钟摆左右摇晃,此时离12点还有10分钟。
“有人和我说国外有医生治疗这个病症特别好,让我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但我还是决定自己照顾他。”
“我只是偶尔会心疼他没有朋友的陪伴。之前有个小女孩和她妈妈来我们店里吃饭,她也是不爱说话,小土豆却主动靠近她,牵着她到院子里摘花。我们都很惊讶,后来妈妈告诉我,小姑娘被诊断出有自闭症,她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小土豆是唯一一个能走进她世界里的人。”
“后来呢?”我忍不住追问,眼看墙上的挂钟的时针不断趋近12点。
“后来,小姑娘的家人决定带她到国外看病,最后离开的时候,小土豆好像一切都明白的样子。他牵着小姑娘到院子里,给她摘了好几朵鸡蛋花,默默地看着她。”
男孩坐在一旁,专注看着手里的两朵鸡蛋花,他正在等待12点的钟响。
“小土豆在等她,在等待這件事上他一直做得很好。”
室内沉默。我听到了挂钟里时针一顿一顿的声音,我不再心慌,而是在一声落后,期待另一声的出现。在剩下的一分钟里,钟摆不紧不慢地将时间倒数,我看见男孩澄澈的眼中那一束光亮。在他密闭且空白的世界里,12点的报时声是他此时的唯一期待,他眼中的渴望是人最原始的追求。
“当当当……”醇厚沉稳的报时声从古老的挂钟里传出,它更像是从一个遥远的神秘领地传来的信号。安抚着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特别的孩子们,声音的振幅和这些孩子们的心跳声对上频率,开启了独属于他们的密语,浅唱和低吟绕在他们身边,小土豆听见了,或许那位小姑娘也听见了。
听到报时的钟声响起,男孩眼中有着了然于心的豁然。他的眼底是一面镜,它映照着生命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