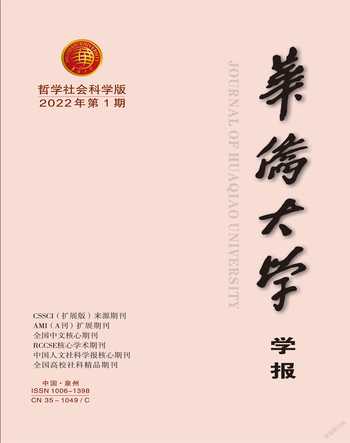汉赋与“一带一路”

摘要:汉赋以铺陈为文,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域外名物,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汉赋中的域外名物包括动物、植物、器物等,它们具有鲜明的域外地理属性,从陆路或海路被带到中国,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构成汉赋书写的重要内容。汉赋对域外名物的书写,表面上看是基于汉朝政府经略西域、南海取得了成功,但实质上是中西方文化主动交流的结果,呈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原产中国的“桃”为例,经波斯传至古罗马,不迟于公元79年成为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古城壁画上的内容,与汉赋中的“桃”构成共时呈现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汉赋;域外;名物;古罗马;壁画
作者简介:蒋晓光,华侨大学文学院/华文文献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赋学、先秦两汉文学(E- mail:jiang33608@126.com 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课题“华文文献学的构建与实践”(HQHRZD2019-01)
中图分类号:I207.224;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1-0149-08
两汉时代是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炽热的大汉精神在四百年中凝练并大放异彩,甘延寿、陈汤上疏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固《封燕然山铭》曰:“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浑朴、庄严、典重、勇武之气充盈天地之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四百年间产生的文学作品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尤以汉赋最为典型,贺昌群先生指出,“即以世所盛称之汉赋论,其庄严凝重之气,与六朝赋体之轻倩流丽,亦绝不可同日而语”(《汉唐精神》),汉赋彰显出喷薄而出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自信。赋体文学最擅“体物”,以描摹物类著称,汉赋中的名物体系是表现汉赋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对汉赋书写“一带一路”沿线名物的考察,释证汉赋的独特魅力。
一汉赋中的域外名物书写
自张骞通西域后,东西方的交往日渐频繁,人们一方面引入外来物品,同时也在加深对它们的认识,而汉赋中的域外名物书写正是对人们这一认识的反映。汉赋对域外名物的书写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外来动物的描写,以此类为最多。班固《西都赋》写到:“西郊则有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皇家园囿极其广大,里面还有各种珍稀动物。《文选》李善注曰:“《汉书》宣帝诏曰:九真献奇兽。晋灼《汉书注》曰:驹形、麟色、牛角。又《武纪》曰: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宝马。又曰: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又曰:条枝国,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甕。”以上文献有待细致解读。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灭南越国后所置郡,隶属交趾,在今越南北部。麟,本为传说中的瑞兽,九真之麟大约是长颈鹿,原产地在非洲,为九真郡人所献。大宛在今中亚地区,《汉书·西域传》载:“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又“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武帝获马后作《西极天马之歌》,可见一时之盛。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方向,《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汉代的条支在今西亚伊拉克、叙利亚境内,能生出和瓮一般大小的蛋,那只能是鸵鸟,其原产地也在非洲。据载,定远侯班超曾从西域献来“大雀”,“大雀”就是鸵鸟,于是班昭奉旨作了一篇《大雀赋》。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还有“騊駼”“橐驼”,《史记·匈奴列传》“其奇畜则橐驼……騊駼”,由此可见,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各种珍禽异兽汇聚于汉廷。其后,黄香《九宫赋》称“骑师子”,“师子”即狮子,原产非洲。及至汉末,杨修作《孔雀赋》,祢衡、曹植、阮瑀、王粲、陈琳、应瑒均曾作《鹦鹉赋》。祢衡《鹦鹉赋》首句称“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阮瑀《鹦鹉赋》言“秽夷风而弗处,慕圣惠而来徂”,鹦鹉是否为中国固有尚有争议,但此处明确标识的均显示鹦鹉来自域外。
二是对外来植物的描写。其中以葡萄最为著名,司马相如《上林赋》“樱桃蒲陶”、李尤《德阳殿赋》“葡萄安石”、张衡《七辩》“蒲陶醲醁”、王逸《荔支赋》“西旅献昆山之蒲桃”、张紘《瑰材枕赋》“有若蒲陶之蔓延”,今日所写之“葡萄”,古人有蒲陶、葡萄、蒲桃等写法,显然可见是外来语的音译,语音即可见为外来物品。而李尤提到的“安石”,全称“安石榴”,即今日所称“石榴”,原产西亚地区,又称“若留”“若榴”,张衡《南都赋》中即有“梬枣若留”,至西晋张协曾作《安石榴赋》、潘岳作《河阳庭前安石榴赋》。石榴多籽,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在汉末,曹丕、曹植及其身边的文人如王粲、陈琳、应瑒曾同题共作《迷迭赋》,王粲《迷迭赋》曰:“惟遐方之珍草兮,产昆仑之极幽”,昆仑是对西域的泛指,“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言其从西域来到中土;迷迭草,《法苑珠林》引魚豢《魏略》云:“大秦出迷迭”、《广志》曰:“迷迭出西海中”,原产地中海沿岸,能制香,故为文人所玩赏。
三是对外来器物的描写。《论都赋》中提到“瑠璃”,《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出琉璃。与《迷迭赋》相同,曹丕《玛瑙勒赋》《车渠椀赋》也是同题共作,但现今仅见有曹植作《车渠椀赋》、徐幹作《车渠椀赋》、王粲作《马瑙勒赋》《车渠椀赋》、陈琳作《马瑙勒赋》《车渠椀赋》、应瑒作《车渠椀赋》,以上作品都是建安时代的。曹丕《玛瑙勒赋序》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玛瑙在当时主要从西域传来。陈琳、王粲亦作《玛瑙勒赋》,可见诸人同题共作是受命而有意为之的。曹丕《车渠椀赋序》:“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车渠,此处指一种宝石,用海中动物的躯壳制成,主要产自今印度洋及西太平洋。“西域”“西国”,均表明以上物品来自遥远的西方,屬于广义上的“西域”。
班固《西都赋》所叙实则是以远方贡物来彰显汉朝的盛德,既是名物的展示,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体现,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尚书·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獒与白雉被进献到中原,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明永乐年间,南亚榜葛剌、非洲麻林等国进献麒麟,夏原吉作《麒麟赋》,文曰:“臣闻麒麟瑞物也,中国有圣人则至”,远方物品的入贡,标志着统治者威名的远播和外邦的心悦诚服,自汉以至明清,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此外,勒、椀、香是日用品,主要为彼时贵族、文人所玩赏,但也寄托了相应的政治情愫,曹丕的“薄六(西)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迷迭赋》),曹植的“夷慕义而重使,献兹宝于斯庭”(《车渠椀赋》),均将新奇之物的输入视为受到了中土文明的感召。新事物的出现,并进入到文学书写之中,对于拓展文学题材和文学意境都是大有益处的。从汉赋对域外名物的书写来看,汉赋正以其开放性显示出汉文化的魅力和自信。
二域外名物书写的历史成因
欧亚大陆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自古以来就有着亲密的文化交流,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均有记载,但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来看,汉赋无疑是各体文学之中,最早以较大篇幅来书写中外交流的一种文体,其所反映的文化地理空间,正与今天人们熟知的“一带一路”吻合。汉赋的名物书写,尤其是对域外名物的书写,是以中外文化的成功交流为基础的。
汉帝国的对外交流,以陆路而言,经过河西走廊,抵达西域。在汉代,将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称为西域。西域也有广狭之分,狭义的西域则是向西以葱岭附近为界限,而广义的西域,直至西亚甚至更远的地区。西汉自立国始,即受到匈奴的威胁,但至武帝时不断发生改变。在正面与匈奴作战的同时,希望拉拢西域诸国从而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于是有了张骞的“凿空”之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来了精彩的域外信息,愈加使汉武帝重视西域这一战略要地。匈奴既是汉朝的威胁,又长期控制西域各国。自武帝以来对匈奴作战不断取得胜利,而匈奴内部也发生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入朝成为了对匈作战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在宣帝、元帝时三次入朝,实际上也对西域局势产生影响。
此前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俱屈服匈奴而不善待汉朝使者,“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宣帝于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单于入朝,尤其是北匈奴郅支单于被悬首长安,西汉政府对西域诸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管理也愈见成效,声威不断从中亚而影响至西亚。据《汉书·西域传》言,“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身挂汉印的官吏、王侯及其所在城邦已纳入汉朝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无隶属关系的地域也与汉朝建立了相应的外交关系。东汉建立后,起初对经营西域不甚积极,“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建初)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间以班超贡献最大,《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齎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一般认为“大秦”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汉朝使者甘英行经“条支”(今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安息”(今伊朗境内),临大海而返。虽然没有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近东地区的了解,共同构成当时人们的知识体系。《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西域各国的物产,许多已进入赋家视野,同时也包含了中西方的交通与往来,择其重点而录之:
哀帝元寿二年,(乌孙)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
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
(建初)六年……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
(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和帝时,(天竺国)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顺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磐复献师子、封牛。
提及的名物包括师子、大鸟或安息雀、象牙、犀角、玳瑁、封牛等,對当时的中国而言,都属于较为新奇的事物。宣帝以后匈奴单于入朝仍然不断,但乌孙国大昆弥与匈奴单于在哀帝时同时入朝,之所以“汉以为荣”,除了匈奴曾是北边最大的威胁外,乌孙在西域曾一度“最为强国”,是所谓外交上的巨大硕果,而更加遥远的条支、安息、大秦、天竺诸国也遣使来朝。需要说明的是,“日南”是汉帝国的最南方边境,位于今越南中部地区,从“日南徼外”来献的大秦、天竺,走的就是海路。关于海上的道路,《汉书·地理志》记载甚为详细: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齎黄金、杂缯而往。……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燿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一记载表明,中国到印度的航道是极为畅通的。除了当地国家主动与中国交往,中国的使者也会购买域外物产,比如明珠、璧流离等,而当时中国使者从海路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则是“已程不国”,在黄支国之南。《汉书·西域传》总结称:
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珠崖七郡”及牂牁、越巂是将东南、西南边地化为内郡,而天马、蒲陶之后的物品,基本都是来自域外,种类极为繁多,多为中土所无。正所谓“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缘此,赋家根据政治现实营造出了丰富的中外交流的画面。
杜笃《论都赋》就提到了“黄支”“天督”(天竺),均在今印度境内,描写的名物有象犀、蚌蛤、瑠璃、玳瑁、觜觿等。张衡《东京赋》云:“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是古人根据距离王城远近而划分的,按韦昭注,“要服”距离王城在三千五百里至四千里之间,为“九州之界”,“荒服”距离王城在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之间,为“九州之外”,此处“要荒”即指极远之地于“孟春元日”来洛阳朝觐并献上贡物。李尤《平乐观赋》曰:“尔乃大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遝归谊,集于春正”,这里也是描述春正月的场景。西汉与东汉均设有平乐观,宣帝元康二年,乌孙使者入汉迎娶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平乐观确有与外邦共乐的功用,“殊方重译,绝域造庭”与“四表交会,抱珍远并”表达是同一内涵,“重译”是因语言不通而辗转翻译,“四表”指四方极远之地,作品是在表现万邦来朝的场景。班昭(曹大家)《大雀赋》赋序曰:“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根据《后汉书》多处记载分析,这里的“大雀”就是“安息雀”,来自安息国的鸵鸟,其文曰:“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作者借助远方异禽来歌咏汉德,展现的是四方来朝的政治图景。
实际上,外邦名物的输入,可能是朝贡的原因,更多是为了民间贸易而前来。《剑桥中国秦汉史》曾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托词”,因此就实质而言,汉朝与西域、海外的往来,更多呈现出的是文化的交流。“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处于某种适当的順从状态的手段”,从本质上说,作为媒介的“贡物”或者说是汉赋里的“名物”将中外交流连接起来了。
三作为个案的“桃”:汉代辞赋与罗马壁画艺术的共时呈现
在古罗马,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之后,与庞贝古城一起被淹没的还有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古城,一千多年后,人们在古罗马的赫库兰尼姆古城发现了画着桃子和玻璃水罐的一幅壁画,如图1:
这幅画至少在公元79年已经完成,甚至更早。桃枝、桃叶以及果实都画得细致、逼真,与中国乡间所见的普通桃子别无二致。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桃枝和叶子呈青色和亮色,仿佛刚从树上摘下,绘画者将之绘画在墙壁上,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它的喜爱,甚至还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桃子与玻璃水罐》最初所在的位置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涂满墙壁的壁画中的一幅。这幅画近似正方形,周围有风景画、叙事题材的绘画和一些装饰纹样围绕,……主体的桃子在赭色台阶和深色背景的映衬下,轮廓明晰,色彩鲜活;果实饱满富有光泽……”,作为一幅静物画,反映的是当时民众富足、宁静的生活。
那么古罗马的桃子从哪里来的呢?从词源上看,简单来说,古罗马人的拉丁语把桃子叫做“波斯(即Persicum)苹果(即mālum)”,说明古罗马人认为桃子是来自波斯的,之后则简化用国名称呼水果,经过演变,进而就有了英语里的“peach”即桃子。事实上,中世纪以后欧洲人才认识到,桃子起源于中国,而现代生物学也给予了证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指出:
水果里主要以桃和杏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这两个礼物或许是绸缎商人带去的,首先带到伊朗(公元前二百年或一百年),从那里再到亚美尼亚、希腊和罗马(公元第一世纪)。在罗马迟至罗马帝国的第一世纪才有这两种树,……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最先种植这种果树,这却是一件历史的事实。
桃子原产中国,然后传至古罗马,劳费尔所言年代与壁画的创作时间大体吻合。东西方的交往是相互的,并非只有传入中国的各类名物,实际上,来往东西方的商人、军士们也将原产中国的物品传播到了西方。以桃为例,其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周南·桃夭》对桃之花、果、叶进行了描写。汉赋里也提到了桃,西汉扬雄(前53—18)《蜀都赋》:“诸柘柿桃,杏李枇杷”,这里的“桃”是果实,东汉崔骃(?—92)《大将军临洛观赋》:“于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杨柳猗猗”,此处是写桃树枝条。前代的文学经验为生于汉末、长于曹魏及西晋早期的傅玄(217—278)专门做一篇《桃赋》奠定了基础,“有东园之珍果兮,承阴阳之灵和;结柔根以列树兮,艳长亩而骈罗”,写出了果树的茂盛和桃花的艳丽,“华落实结,与时刚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则是对果实以及品尝后的体验进行的比较形象的描述。辞赋作品对果实口感的体验,正与壁画中咬了桃子一口形成十分鲜活的对应。《中国伊朗编》称首先将桃带到伊朗,也就是当时的安息帝国,实际上,这其中必须经过西域地区,以西域为中转站,向葱岭以西的西方传播。
《大唐西域记·至那仆底国》记载:
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告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至那仆底”因迦腻色迦王在此地收容汉地质子即人质而得名,所谓“汉封”,大意是指汉人居住的土地。迦腻色迦王是贵霜帝国的君主,其所处年代尚有分歧,多数倾向在公元1-2世纪期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其所收容的质子来自“汉”,一般推测可能是当时隶属于汉帝国的西域地区。那么“桃”称“汉持来”,“梨”称“汉王子”,说明西域地区是一个重要向外传输的基地,因此这些水果方才往西抵达安息,往南到达贵霜。梨在汉赋中也曾出现,《文选》左思《魏都赋》刘逵注引“司马相如《梨赋》曰:‘唰嗽其浆’”,张衡《南都赋》“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说明梨在当时也已进入文学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赫库兰尼姆壁画对桃子的描摹与汉代流行的画像石的平面画法不同,显得极为立体和逼真,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关于桃子的彩色画作了。《文心雕龙·诠赋》称赞赋具有“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特点,中国辞赋作品中的桃子与古罗马画作中的桃子正形成对读与互文的关系。扬雄主要生活在西汉末年,卒于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崔骃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与古罗马壁画桃子和玻璃水罐产生的时期(最迟至78年)大体在一个时间区间内,可以将汉代辞赋与罗马壁画对桃子的描摹看作在艺术上的共时呈现,形成文明互鉴的基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自汉以后,历经魏晋、隋唐,直至明清,赋体文学仍然积极扮演着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以清代为例,李光地作《眼镜赋》、纳兰性德作《自鸣钟赋》、章桂馨作《电报赋》等等,都是对泰西新来名物的描绘。相传清代的广东嘉应(今梅州)人罗芳伯到达南洋后曾作《金山赋》,所述“金山”即今印尼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因当地产金矿,故有“金山”之名,赋的创作时间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堪称“海外华侨第一赋”,是抵达南洋之后对当地风物的直接描摹,在赋体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赋体文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以致在外译时经常将之译为“Fu”,然而比较有趣的是,一些学者用汉语翻译外文作品时,也会借用“赋”这一文体的名称,例如将泰国古典叙事长诗Lilit Phra Lor译作《帕罗赋》,“《帕罗赋》是以泰国古典诗歌中的‘立律’体写成。‘立律’包含了两种韵文形式——‘莱’和‘克龙’,这两种韵文交叉出现,其间又有韻律衔接”,显然这是对两种文体进行比较之后进行的命名。因此,赋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从名物开始,还应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来进行研究。
On Hanfu 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Taking the Name Writing as Example
JIANG Xiao-guang
Abstract: Chinese Hanfu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names, which reflects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t that time. The foreign names in Hanfu include animals, plants, utensils, etc., which have distinct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ut of China. They were brought to China through land or sea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Chinese culture, form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writing of Hanfu. The writing of foreign names in Hanfu is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the Han govern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in fact the result of the activ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shows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aking the “peach” originated in China as an example, it was passed from Persia to ancient Rome and became the conten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Herculaneum mural before 79 AD. It forms a synchron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ach” in Hanfu and has a unique artistic charm.
Keywords: Hanfu; foreign name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责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