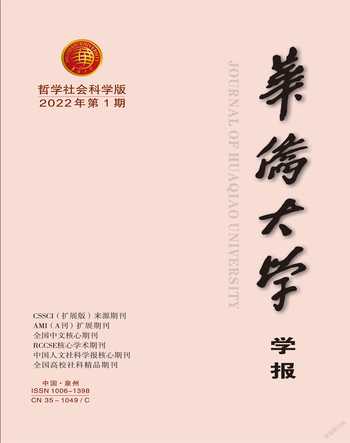从神权到帮权:建筑空间媒介的权利生产
李俐 张恒



摘要:妈祖庙宇在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不仅是信仰的祭祀空间,也是最高的帮权机构。以新加坡天福宫为考察对象,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解析天福宫从“神权”中心转变到“帮权”与“神权”双中心的过程,并根据福柯的空间规训理论,通过对天福宫建筑空间的形态、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室内装饰和楹联匾额的分析,讨论“帮权”与“神权”的运作机制,认为天福宫作为权力的空间媒介,联结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习俗、经济、教育、政治等社会要素,从而维护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稳定,帮助华人在移民地谋求生存与发展,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空间媒介;新加坡天福宫;建筑空间;神权;帮权
作者简介:李俐,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厦门市生态建筑营造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园林景观(福建 厦门 361021;E-mail:cathenc@163.com)。张恒,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厦门市生态建筑营造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研究方向:园林景观。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南传统建筑艺术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机制研究(FJ2018B152)
中图分类号:TU252;D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2)01-0029-08
一空间的媒介转向
以往对于空间的认知主要是强调其物质性特征,到20世纪末,对空间社会性的讨论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将空间视作各种社会关系与文化冲突的集结,强调空间的社会意义,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在涉及“空间转向”的诸多空间批评话语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批评思想分别是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米歇尔·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与意识形态,空间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生产。米歇尔·福柯参考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空间规训”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场域也是权力运行的载体和工具,文化意识形态则论证了权力在空间中运行的合理性,认为应从“空间视角来铺陈其权力——知识,建构身体的叙事,权力——知识只有通过各种空间的安排才可能发挥其支配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德布雷提出“媒介学”,认为对于媒介的认知不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媒介实际上是一种中介化过程。媒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体,而是担保思想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是散播和传递信息的渠道,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关键节点和中介。“媒介具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意义,即“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來,形成网络(即社会)”,“将以前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媒介被视作一种“关系”,具有连接社会关系网络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空间与媒介具有相通性,两者均可视为社会关系的载体。任何形态的空间都留有人类生活与存在的印记,同时连接着当下不同的人类关系,交织着人类活动与交往的传播过程。 妈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信众。19世纪初中国东南地区海运发达,许多华人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谋生,这些移民促成了妈祖信仰在新加坡的传播。新加坡有多达30座庙宇祠堂崇祀着包括妈祖在内的数十位地方主神,其中天福宫是由闽帮华侨筹建的具有代表性的妈祖庙宇之一。天福宫不单是新加坡华人祭祀的空间,也是代理殖民政府处理“帮群”社会事务的空间,成为“神权”与“帮权”运作的场所,因此也必然与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密切联系。以往对天福宫的建筑空间研究多集中于其形式审美与建构逻辑等物质空间问题研究,较少讨论天福宫的社会性特征。然而,脱离其社会性特征来讨论天福宫建筑空间显然是片面的。从文化传播的语境考虑,将天福宫的建筑空间视作权力的媒介载体,解析其在联结新加坡华人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社会要素的过程,将使我们对天福宫这座重要的华人庙宇有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二天福宫作为空间媒介的权力建构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初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成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清代大批移民下南洋,这些南洋移民在出海和抵达目的地后,都要酬谢妈祖的佑护并祈求妈祖保佑在此安居乐业,家乡人禽平安,他们是妈祖信仰在南洋地区传播最主要的推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的南京条约把厦门和福州设为通商口岸,厦门很快发展成为福建对外贸易的中心。1860年的天津条约,使得英美两国可以在中国招募劳工,厦门变成大批劳工输出的口岸。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是当时华人劳工的集散地,这些因素促成新加坡闽籍华人人口的大幅增加。这些华人大部分所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目不识丁,说同样方言的同乡就自然而然地聚合在一起,福建人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中最大的族群。与此同时,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避免建立不必要的行政系统而消耗大量人力、财力,赋予华人充分的自治权,鼓励各个帮群自我管理本帮事务,因此“帮权政治”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主要的社会生态。
这一背景下,一座由闽籍富商筹建的妈祖宫庙——天福宫诞生。福建会馆安排在天福宫内,解决闽人教育、医疗、丧葬、纠纷等一系列个人、家庭和群体的现实问题。当时在新加坡至少有三位华侨商人起着甲必丹的作用,他们是陈笃生、陈金声和陈金钟,而此三人均曾为福建会馆领袖,他们在作为闽帮帮主的同时,还是殖民当局的代言人。因此,天福宫的帮群自治性,可说是中国本土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殖民当局授予部分管治权力二者结合的产物。天福宫在承担“神权”功能的同时,也建构起了闽帮族群的“帮权”中心,成为列斐伏尔所说的政治工具的空间媒介。天福宫作为权力媒介的空间,是被闽帮华人族群中的权力精英阶层所规划设计,具有“意识形态(因为是政治的)和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的属性”,是权力施展的中介物。天福宫作为帮权意识形态构建与政治认同生成的场所,规训和影响着当时新加坡华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区别于以往大众媒介的传播形式,呈现出空间媒介特征。
三天福宫作为空间媒介的权力生成逻辑
对天福宫的建筑空间媒介的权力建构进行认知,关键在于对其权力生成逻辑的解读,解析天福宫如何通过“神权”作用于华人社会,进而巩固“帮权”的过程。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提出空间分析的三元概念: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利用这一理论将有助于理解天福宫空间生产的逻辑顺序:首先,空间实践是指个人和社会群体日常的、微观层面上的空间行为。早期的天福宫原址上所建造了一座小型的妈祖庙宇用于妈祖祭拜,在这一层次上的空间属于华人群体微观层面上的日常活动空间,是一种“空间实践”,属于天福宫作为“神权”中心的萌芽阶段。其次,空间的表征是指权力精英构想的空间,是权力意识形象化的过程。随着闽帮势力在新加坡社会的不断强大,闽帮权力精英组织捐建天福宫并筹划将福建会馆这一最高“帮权”机构设置于此,试图利用天福宫的“神权”的感召力巩固“帮权”,将天福宫的宗教性与帮群的政治性合二为一的过程属于空间的表征,是“神权”与“帮权”整合的过渡阶段。最后,表征的空间是指“空间实践的参与者具身其中,操弄并挪用各种空间意义和权力运作的方式,共同创造了一个具象化的活空间。”建成后的天福宫不但承担祭祀的功能,还具有处理帮群事务的作用,是闽帮政治精英运作权力的空间,在这一层次上的天福宫成为权力的空间媒介,属于权力的表征空间,这一阶段也是“神權”与“帮权”中心的最终生成阶段。三种空间层次对应了天福宫权力空间媒介的萌芽、过渡与生成阶段,体现了天福宫作为空间媒介的权力生成逻辑。
四“神权”中心的萌芽——天福宫建成背景
妈祖庙作为我国沿海居民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信仰空间,是妈祖信仰作用于空间的日常实践活动,反应出沿海居民已有的文化内涵。19世纪20年代,许多华人远渡重洋登陆新加坡,也使得妈祖成为当时新加坡华侨社会中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1810年在新加坡直落亚逸海湾边就建成了祭祀妈祖的小庙,韩槐准在《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所述“古代南洋各角落,华侨人数未多之时,贩海之船舶一到其地,憩息无所,常建简陋之亚答屋,以资登岸之用,同时可供奉其所迷信之水神,后华侨人数登岸渐多,资力渐福,乃改建巍峨庙宇。”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实践”反映出使用者已有的文化意义,包含了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每一种社会形式的基本空间特征,它保证人们空间活动的连续性和凝聚性。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移民数量排名依次为:闽、潮、广、琼、客,不同的社群由于所说方言不同以及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差异,形成不同的“帮群”认同,使得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妈祖信仰也具有明显的帮群特征。而同一地缘社会构建的妈祖信仰可看作是一种“空间实践”,反映了族群对其的信仰认同,信仰认同也成为帮群认同和凝聚的工具和手段。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的凝聚性“暗含了一个特定的“能力”(competence)和一定的“表现”(performance)……”,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具有的共同实践的潜在“能力”(competence)和具体的外在“表现”(performance), 同一地缘社会的妈祖信仰可以理解为列斐伏尔所述的内在“能力”(competence),不同帮群的妈祖信仰实践的差异化特征,则是“能力”(competence)的具体外在“表现”(performance):例如福建人称为“妈祖”,海南人又称“婆祖”,客家人则称“水母娘”等。由于来自于同一地理空间的人群趋向于祭拜相同的神灵,也使得妈祖庙宇后来实际上成为许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帮权庙宇,如潮州人建立的粤海清庙是一座供奉玄天上帝的上帝宫和供奉妈祖的双子庙,是当时潮州人的总机构;而新加坡海南人的琼州会馆天后宫,也是主奉妈祖的;天福宫祭拜的主神是妈祖,也是福建会馆所在地。妈祖帮权庙宇构建了不同帮群华人精神生活上的群体感,也成为妈祖信仰“能力”的外在“表现”。
五“神权”与“帮权”整合的过渡阶段——天福宫的筹建
19世纪新加坡的福建帮主要以操厦门语音系的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的福建人为代表。在业缘上属于商人阶级。在19世纪新华社会里,福建帮不仅在人数上压倒其余各帮,也是财富最雄厚的一帮。闽籍富商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通过对帮群的公益事业进行物质援助以获取帮群内权力的“象征资本”,从而获得华人社会的声望和地位。1840年以前,恒山亭是闽帮侨领主持的埋葬吊祭客死异乡华人的公共墓地,成为早期的闽帮总机构。当时闽帮侨领绝大多数来自马六甲,与华丽的马来西亚青云亭相比,恒山亭的规格显然不能与当时财力雄厚的闽帮地位相匹配,因此闽帮政治精英“希望一个‘规模宏敞的议事场所。”这使得构想中的天福宫将是具有管理、福利及联络同乡活动等多项社会职能的“帮权”中心。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表征作为一种被构想的,概念抽象化的空间,是精英阶层利用符号、话语和概念等知识对于空间理性的改造活动的产物,实际上体现出权力阶层对空间的控制过程。此时的天福宫是闽帮权力精英控制与构想的空间,具有权力等意识形态的特征,属于空间的表征阶段。在这一阶段,妈祖信仰作为一种原乡性的内生信仰在闽帮内部发挥着不可被忽视的作用:闽帮侨领利用妈祖信仰感召性,扮演组织者的角色筹建天福宫:根据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记载,天福宫1839年始建,1842年最后完工,工期历时3年,参与捐建的人数达400余人,主要是闽南人和船主,捐款总额约计4万银元。陈笃生和薛佛记两位富商分别捐银3074元和2400元,而后成为天福宫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度的闽帮侨领——天福宫大董事。透过天福宫这一妈祖信仰“神权”中心的兴建,闽帮实现了“帮权”与“神权”整合的过渡,天福宫也实现了从“空间实践”向“空间表征”的转变。见图1,图2(图1来自网络,图2—图8来自杜南发编著《南海明珠天福宫》2010年)。图1天福宫现状图219世纪20年代天福宫直落亚逸街景
六“神权”与“帮权”中心的形成——天福宫的建筑特色
建成后的天福宫既是妈祖祭拜的“神权”空间,又是被闽帮政治精英主管的“帮权”空间,属于列斐伏尔所说的权力表征的空间,而这两种权力的运作与发挥则可以通过天福宫建筑空间的等级性、内聚性与功能的复合型以及建筑装饰与楹联匾额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神权”的中心——天福宫空间形态与装饰图案
1.空间的等级性
天福宫是闽南传统的大厝,在建筑序列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宫庙大型建筑体系等级明显的特征:建筑空间具有明确的中心轴线关系,有较强的序列感形成等级差别。天福宫在轴线上依次布置一埕二院、三殿两护厝。根据不同的建筑功能要求,天福宫有着不一样的建筑尺度与形式,从而形成空间序列与节奏的变化:首先,天福宫的前殿(三川殿)为抬梁式单檐三川脊顶,面宽三开间,燕尾形的屋脊形式繁复而精巧,虽然尺度并不大,但明显区别其所处街道的其他建筑。其次,正殿是整个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建筑,面宽五开间,为抬梁式重檐歇山顶,装饰华丽,供奉由湄洲分灵的妈祖神像。重檐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较高的建筑形式,突出了主殿的威严与雄伟。主殿位于天福宫的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图3天福宫空间布局示意所谓“居中为尊”,凸显出妈祖在天福宫祭祀神中属于最高级别。最后,寝殿位于正殿正后方,单体量比正殿小,装饰上比前殿和正殿朴素,屋顶为单檐硬山三川脊顶,供奉的陪祀神为千手观音像。天福宫建筑群的左右配殿为硬山平脊顶形式,供奉的闽南地方化神灵,在配殿左右对称建有德庆楼和崇文阁,为八角三重檐攒尖顶。
福柯认为空间的等级性有利于权力的规训即权力的运作,天福宫作为“神权”场所,从祭祀妈祖主殿的位置、建筑体量上昭示出妈祖信仰支配性的最高等级地位,空间的等级性体现出妈祖信仰的权威性。(见图3)
2.空间的内向性
天福宫属于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空间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特征。天福宫内有二进院落,通过院落的空间围合,有效串联了前殿、正殿以及东西厢廊、寝殿等建筑。正殿前面的院落面积较大,是主要的祭祀场所,后殿围合的院落比正殿狭小,是天福宫中相对私密的院落空间。福柯指出权力的规训“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规训)的保护区。”。院落空间作为承载妈祖祭祀等仪式活动的主要空间,具有内聚性与排他性,内向性的院落空间明确地传达出“我们”本帮群与“他们”异帮群、“内部”与“外部”的分野。天福宫常年祭祀仪式主要有农历新年节庆、妈祖诞、孔子诞、观音诞、保生大帝诞、关圣帝君诞等。闽帮华人借助每年循环往复的祭祀仪式而聚集于此,内向性的院落空间强化了个体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使得妈祖信仰认同就如同一种权力关系网,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内向性的天福宫院落空间成为妈祖“神权”发挥的载体,形成了“神权”的空间规训(见图4、图5)。
3.室内的装饰图案
图6天福宫的室内装饰图案 在中國传统文化中,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宗教观,具有功利化特征。妈祖信仰的出发点是祈求神明保佑,包括生前死后,在生求保平安,万事如意,死后求神明引进天国,因此天福宫作为妈祖庙宇,在装饰纹样上主要是体现出吉祥祈福的文化主题。天福宫主要通过谐音、寓意象征的手法将抽象的妈祖信仰通过图案符号具象化。例如三川殿上两侧窗花四端的四只蝙蝠谐音“赐福”;佛手瓜谐音“福寿”;葫芦谐音“福禄”。天福宫正殿檐下左右四个木作绘有大旗、彩球、纸笔、方印,谐音旗(祈)求(球)必(笔)应(印)。另外,天福宫的装饰图案中还有白头翁象征白头偕老,莲花象征高贵和清纯,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象征君子的品格,花瓶和牡丹象征富贵平安,凤凰象征吉祥富贵,仙鹤苍松象征长寿平安,石榴象征人丁兴旺等。天福宫装饰图案的选择与组合是基于华人所认同的妈祖吉祥祈福的文化内涵建构的,天福宫通过室内装饰图案将抽象的妈祖祈福成为具象的空间体验,从而构建了基于妈祖信仰的文化语境,强化妈祖“神权”的信仰。(见图6)
(二)“帮权”的中心——天福宫空间的多功能性与楹联匾额
1.空间的多功能性
天福宫在功能上不但具有祭祀功能,同时兼顾会馆、早期华文学堂等社会职能,在空间功能上具有多义性。首先,天福宫在筹建的规划中就天福宫内划分出会馆的空间,天福宫东配殿中设有“画一轩”是“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门楣上挂有“会馆”的匾额。自 1840 年至 1915 年,早期的闽帮侨领均在这里处理华社事务,协调商务,筹募赈济善款甚至为族人主持婚姻注册,例如天福宫大董事薛中华任内就“成功地调停了福清、兴化二籍车夫打斗事件”,在华人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天福宫成为闽帮最高的管理机构,闽帮侨领在此商议闽帮重要政事时,都在妈祖神权的见证下,成为政治合理性的重要宣誓。据《叻报》:“诸神列于殿上,诸商坐于殿下,宫门内外人山人海,几无容足之地,齐声喝彩,神人共听”。其次,图7早期的崇文阁作为华文学校挂有
“宣讲圣谕局”的招牌天福宫配殿的崇文阁是新加坡早期的华文学校,而崇文阁的捐款主要来自闽帮富商侨领(见图7)。早期崇文阁的华文教育都是以闽南方言教授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国学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崇文阁碑记》:“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德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为文章,变鄙俗为风雅”。崇文阁所教授的中国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些经典读物作为一种文化规训,隐形地塑造影响着年轻的华人学生。天福宫利用华文教育与日常帮群管理等政务性职能形成微权力,渗透到华人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中。正如福柯所述:这种微权力“它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权力生产性话语、知识话语与道德话语。”天福宫划分的功能性空间则有助于“帮权”以微权力的形式发挥。
2.楹联匾额
图8光绪三十三年(1807)御笔亲书“波靖南溟” 在辛亥革命以前,对于新加坡各帮侨领而言,其权力的获得除了经济资本、帮权内所拥有的象征资本以外,还有就是是否获得满清政府的表彰与认同。天福宫的匾额为45件,楹联为12对,其中有晚清皇帝以及高官敬献的楹联匾额,以示官方对天福宫妈祖信仰和其帮权地位的认同。例如光绪皇帝为了表扬天福宫的闽帮侨领捐款赈灾泉州水灾,于光绪三十三年(1807 )御笔亲书“波靖南溟”(见图8)匾额,这一匾额高置于天福宫正厅之上,成为镇宫之宝;三川殿有钦赏蓝翎福建闽安中军守备林天从于同治七年(1868 )敬立的“恩流海国”;光绪十二年(1886 )由新嘉坡领事馆花翎四品衔分省优先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敬献“显彻幽明”;1894年赐进士出生四品衔直隶司曾福谦敬献对妈祖神明赞誉的对联“惟神极航海千百国生灵,庙宇宏开,籍舆三山联旧雨。此地为涉洋第一重衡要,帆樯稳渡,又来万里拜慈云。”闽帮政治精英作为权力主体,引入具有清政府政治权力意味的匾额楹联作为符号,将权力意识形态融于天福宫的建筑空间中,强化了天福宫作为“帮权”中心的意识形态工具价值,也昭示了天福宫作为权力空间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使之成为“帮权”运作的空间媒介。
天福宫经历了“神权”中心转变到“帮权”与“神权”双中心的过程,其建筑空间的形态、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室内装饰和楹联匾额体现了天福宫的权力空间运作机制。作为“神权”中心的天福宫,利用妈祖信仰的祈福文化对族群内民众寻求现实平安幸福的愿望予以精神撫慰;而作为“帮权”中心的天福宫,不仅利用闽帮政治精英雄厚的财力为帮群提供慈善、教育等社会公益服务,还利用闽帮政治精英作为殖民政府代理者的身份处理公证与仲裁等帮群事务。2008年英国学者索尼亚·列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将现时代定义为“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时代”,认为媒介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媒介“是由它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媒介是一种隐喻,它为我们建造和呈现出一个可见的世界和空间,并构成我们观念中生活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天福宫作为权力的媒介空间邀约了新加坡华人族群的文化习俗、经济、教育、政治等社会要素,维护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稳定,帮助华人在移民地谋求生存与发展,呈现出其作为权力的空间媒介,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积极意义。
Authority Produced in Architectural Space:
Taking Tianfu Temple in Singapore as Example
LI Li, ZHANG Heng
Abstract: Mazu temple is a worship space for beliefs in the modern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and also the highest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s authority. Taking Tianfu temple in Singapore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and combining with Lefebvres spatial ternary dialec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anfu temple from the center of “religious authority” to the double center of “communitys authority”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According to Foucaults spatial discipline theo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form, the spatial multi-functionality,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the couplet plaques of Tianfu te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s authority” and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holds that as a spatial medium of authority, Tianfu temple connects the elements of cultural custom, economy, education, politics and others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thu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helping the local Chinese to seek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mmigrant areas, and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Keywords: space media; Tianfu Temple in Singapore; Tianfu temple; architectural space; religious authority; communitys authority
责任编辑: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