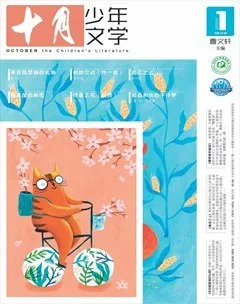零花钱
小时候我的零花钱很少,常常连文具都舍不得买。
那时一根水笔芯要一块钱,相当于二十颗硬糖或者三块彩色橡皮或者两包干脆面。而一瓶墨水才两块多钱,所以,很自然地,我一直用钢笔写作业,非常复古,也非常省钱。
有一次舅舅给我和表弟买玩具小汽车,他满面春光地说正赶上特价,一个才两块五。我却心疼得很,连连哀叹:“天哪!这也太贵了!太贵了!”舅舅的得意瞬间僵在脸上,哭笑不得,不知该夸我懂事还是骂我抠门——花的是他的钱,我是心疼个什么劲儿?
还有一次是和外公去超市,看到货架上一排闪亮的“3+2”饼干。那种厚厚的夹心饼干当时还是时新玩意儿,我没吃过。一包饼干三块二毛钱,而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五块,买包饼干简直像要割我的肉!使不得,使不得……
外公看我可怜巴巴地凝视又毅然决然地走开,心情大概是既欣慰又心酸,然后,然后……就二话不说给我买了!而且很豪迈地买了三包!(家里有两个表弟,我有什么他们也必须有什么,否则就是不公平。)
三包饼干九块六毛钱,在我眼里,那可是一笔巨款!内心足足震撼了好几天。因为舍不得,我每吃一块都要缓上几天,搞到最后饼干都放潮变软了也没吃完。
那包饼干的奶油夹心是柠檬味儿的。心潮澎湃地抠出一块,郑重其事地咬下一口,内心虔诚而富有仪式感地咀嚼,闭上眼睛沉醉地回味,末了还要闻一闻指尖残留的香气……那种吃饼干的体验,堪称童年一绝。长大后,国内外各种类型的饼干我都吃过不少,可再精致再高档再美味,也吃不出当年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了。
还是回到穷这个问题上。
因为穷,我从小喜欢硬币多于纸币。纸币轻飘飘的,捏在手里毫无安全感,装在口袋里说没就没;而硬币沉甸甸的,有厚度,有硬度,有温度,掉在地上动静不小,那声响让人心里相当踏实。小学时,我不知花了多少年,终于攒了满满一存钱罐的硬币,就算有人拿着几张百元大钞来,我也是死活不肯换的。珍贵的,是那漫长时光中一枚一枚的努力、克制和期盼,是日积月累的情感,至于到底攒了多少钱,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当然,纸币也有好处——它善于隐藏,因而可以制造惊喜。从洗干净的牛仔裤口袋或者遗忘已久的单肩包里,意外地掏出几张叠成小片的纸币,哪怕只有三五块,我也会像中了彩票一样激动万分。
可惜如今盛行手机支付,别说摸硬币,我起码已经三年没见过钱了……
为什么小时候我的零花钱那么少呢?因为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更重要的原因是,妈妈觉得我手里可自由支配的钱不需要太多——教材和作业本学校已经发了,铅笔橡皮钢笔她给我买了,一日三餐也都在家解决了,我好像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可是……一个月五块钱也太夸张了吧!就算一天只花五毛钱,一个月也要十五块钱啊!
话又说回来,多亏了当年穷,我很少吃零食。校门口小卖部的那些零食……有健康的吗?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嚼辣条,喝汽水,啃干脆面,或者吃一些红的绿的圆的扁的猜不出味道的东西,我暗自吞咽口水。食欲攒得够够的,放学回到家,多吃一碗饭那是不在话下。妈妈做的菜其貌不扬,没有零食那么刺激感官,但非常可口,营养健康。
吃不起零食不算啥,但买不起喜欢的文具,实在是令人沮丧啊。
文具店里的一切我都喜欢,彩笔啦,文具盒啦,便签本啦,橡皮啦,胶水啦,三角尺啦……只要踏进去,一时半会儿就别想出来。在我眼中,那些东西不是普通、实用的学习用品,而是玩具,是珍宝,是艺术品,是快乐的源泉。小时候我有许多梦想,其中一个,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文具店。
对我来说,封面漂亮的笔记本是很贵的,内页有彩绘图案的更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过节、过生日)才允许自己买一本。曾经和小学同学逛文具店,她零花钱多,出手相当阔气,笔记本不是一本一本地买,而是一摞一摞地买,看得我两眼发直。“不!”我在心里喊,“这不是笔记本的正确打开方式……”
大人们很不解:为什么要买精致的笔记本?学校最普通的作业本不够写吗?“因为我想把日记写在更厚实、光滑、细腻的纸上啊!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记录下的时光,它们配得上更好的,不是吗?”听了我的理由,他们却更加迷惑了。
十三四岁开始摸索着写诗,那时做过最奢侈的事,就是把诗写在我能负担得起的最精美的彩色信纸上。该朴素时朴素,该舍得时舍得,关键要看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因为很少买文具,那些漂亮崭新的水笔和橡皮,我买回来常常舍不得用。新的都藏在家里,带去学校的全是些“残兵败将”,偶尔有同学打开我的文具盒参观,最后都皱着眉头还给我,那嫌弃的眼神好像在说:“你活得也太粗糙了……”但这也有好处。如果有同学不小心把我的笔弄坏了,我一点儿也不心疼,反而还挺高兴——终于有理由把新笔拿出来替补啦!欢天喜地,心安理得。
不知为何,文具店里最吸引我的,永远是贴纸这种美丽而无用的东西。贴纸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透明的,半透明的,不透明的;纸质的,塑料的;薄的,厚的,立体的,表面带亮晶晶涂层的;简单图形的,动画人物的,影视明星的……只有我想不到,没有贴纸做不到。
小学时我很少买贴纸,上初中后零花钱稍多些才开始买,特别是那种一块钱一大张的纸质贴纸,非常实惠。嗯,这下终于舍得拿出来用了。
贴纸揭下来,贴在哪里都可以,它们生来随遇而安。当然,课本和作业本是万万不能贴的,会被老师批评。那么,就贴在文具盒、日记本、水杯、书桌、床头柜……甚至自行车上。是的,我上初中时骑自行车上学,除了轮胎和车座,整个车都被我用贴纸裹满了。花花绿绿炫目多彩,完全配得上“壮观”这个词,骑出去超级拉风!
遇上班级联欢会之类的演出,有同学会把贴纸贴在身上当饰品:那些凸起的纯色小圆点,可以贴在耳垂,当作耳钉;长条形的贴纸可以环住手腕,乍一看还以为是手镯。既便宜又方便,满足了小女生的爱美之心。贴得轻松,可揭下来的时候恐怕就不太好受了,汗毛动不动就扯掉一大片——咝——不敢想下去。反正我从没往自己身上贴过,我……我还是更愿意贴在自行车身上。
囊中羞涩如我,逛文具店尚且力不从心,逛礼品店就更无能为力了。那些可爱的玩偶公仔,动辄几十块上百块,是我童年时代遥不可及的梦。大人偶尔也会给我买玩偶,但很少,而且都小得可怜,顶多当个钥匙扣。我总惦记着买一只那种比人还高的大熊玩偶,大人们每次都无情地拒绝:“家里没地儿放!它睡床上你睡哪儿?再说,它那么大,脏了怎么洗?”后来我长大了,有钱买大熊了,却也迟迟没买,原因竟和大人们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说来也怪,那些年最常陪我逛礼品店的,不是闺密,而是小我三岁半的表弟。我俩都穷,平时是小气鬼,但若碰上给家人买礼物之类的事,那可是毫不马虎。
有一年,为了给外公买生日礼物,我俩风风火火跑了好几条街,逛了好多家店,忙活了整整一上午。原本商量着买衣服,或者皮带,或者吃的,后来都一一否定了:衣服太贵,皮带太丑,吃的东西拿回去肯定是大家一起吃,外公什么也留不住。
选择,对比,纠结,软磨硬泡地跟老板搞价……最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俩居然请人给外公刻了一枚印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刻章的大叔慢条斯理,一边刻,一边向我们嘚瑟他那些上好的印章材料,丝毫不介意我俩是小学生,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等我们带着礼物跑回家,摆了一桌的饭菜早就凉了,家人正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们呢。大人们匪夷所思,气不打一处来:外公不会画画,也早已不练书法,要印章干吗?瞎花钱,还耽误那么长时间,害得家人急得发疯。外公却笑吟吟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回来就好!快吃饭吧!”
有一年过母亲节,我在商场给妈妈买了一套裙装,印象中是浅绿色,带白色蕾丝,质地厚实。那是我第一次给妈妈买衣服,还挺紧张,从钱包里抽出唯一的百元大钞时,手都有点儿抖——过年的压岁钱大部分进了银行,只留下了这么孤零零的一张——有种掏空了家底的豪气和悲壮。然而还不够。于是把平时攒的几十元也搭上。这下彻底身无分文了。收银的阿姨不禁对我刮目相看,然而并没有因此给我打一点儿折扣。
衣服拎回家,妈妈正在做饭,我探头进厨房,故作镇定淡淡地说:“给你买了个礼物。”她把菜炒好才出来看,明明很震惊,却也若无其事地把语气压得很平:“还怪贵的……你还挺舍得……”
大概是过十岁生日那年,表弟送了我一个当时很流行的音乐水杯。白色厚实的陶瓷马克杯,杯身印着两个小人儿,杯底用蜡封了一层,里面藏着纽扣电池和小喇叭。杯子一拿起,音乐就会响,一放下,就不吱声了。杯子自带杯盖,还有一根细细的搅拌勺——是喝咖啡用的,虽然我当时连咖啡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一个音乐杯!我怎么配得上如此贵重的礼物?!拿到礼物时我不可思议地摇头。之前在礼品店见过,好像卖十块钱,是我两个月的零花钱啊!真不知道表弟怎么舍得买……
或许是小时候穷的缘故,我习惯了相对节俭的生活,没有很强的物质欲望。读大学时,别人一个月生活费一两千,我最多只花四五百。在同龄人大批地买衣服和化妆品的时候,我的钱要么存起来(用于旅行或不时之需),要么拿去买生活必需品和书籍。
现在工作了,虽然收入不多,但最起码在文具店消费是没什么压力了,放肆一下也不用担心破产。从学校门口路过,我有时会忍不住走进文具店“扫荡”一番:水笔,贴纸,便签本,精致的笔记本,甚至没什么机会用到的同学录……买完放在家里写日记用,几年也用不完吧?管他呢!过瘾就好!反正花的是自己的钱,大人也管不着。这时才由衷地觉得,嗯,长大还是蛮好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从中感受到的快乐,似乎也没有从前那么强烈了。一沓进口的精美贴纸,远不如从前一小片劣质贴纸来得激动。
小时候,很少的零花钱就能带来很多的快乐。不明白啊,那时的快乐,怎么就能那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