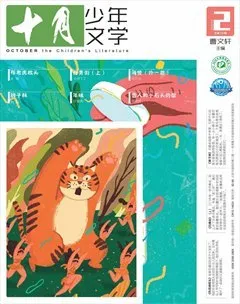年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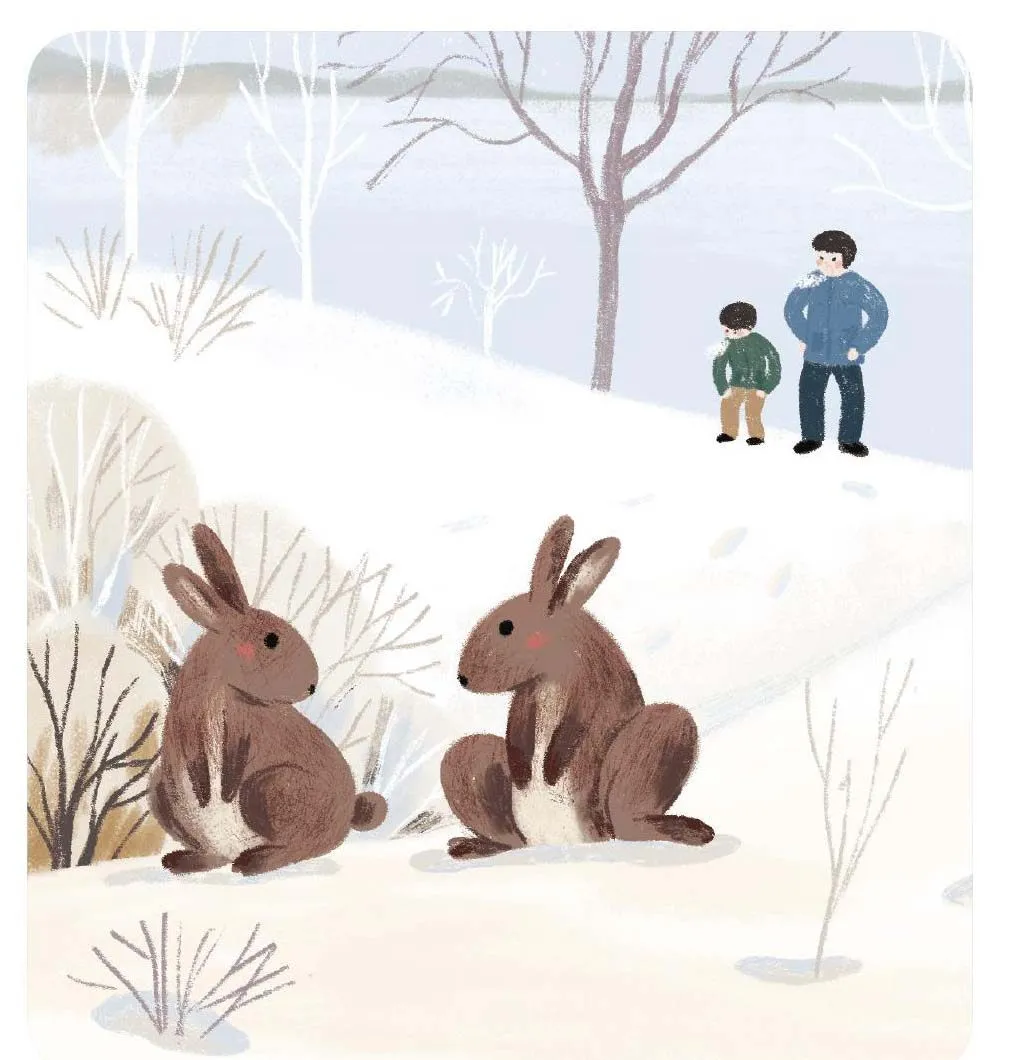
寒假到了,寒假到了,北方一入冬就开始上冻,地会裂开手指宽的口子,田野里的稻谷开始收割,堆积在打稻场里的稻垛像一座座金黄色的城堡,等打稻机轰隆隆日夜不停地响过半个月后,打稻场空了,这个时候新年也快来了,年的味道会一点儿一点儿地浓起来。
杀猪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猪,到年底的时候就成了美味佳肴。看杀猪是男孩子们的专场,但更多时候我是躲在家里听,猪歇斯底里的叫声总是让人害怕。这个时候妈妈总是打发我去捡木头,她让我多捡一些炖猪肉时用。我提着箩筐拿着斧头往街巷里走,杀猪就在街巷里,黑猪被绑着四条腿躺在矮脚桌子上哼叫着,旁边是有说有笑的杀猪人,天气太寒冷,他们的胡子上挂满了冰碴儿。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邻居家的小孩跟着我到田野里捡木头,他们其实是为了吃猪肉才帮着我找枯树桩的,力气大的孩子帮我抡起斧头把树桩一块块地劈下来,又有人抢着帮我捡到箩筐里。有时两个人为了抢一块木头还要争吵一番,好像谁捡得慢了就没有肉吃。我们时时刻刻惦记着杀猪那边的进展,“我好像听到猪叫声了。”“不会传这么远的,说不定已经给猪拔毛了。”有人嗅了嗅鼻子,“我闻到猪肉味了。”有时遇到已经被荒火烧过的木桩,木桩上残余的焦炭能够当作笔来写字,我们会掰下一大块,故意把炭黑涂抹到额头、脸蛋和手背上,好像我们谁脸上的污黑越多,谁在捡柴火时付出的辛苦就越多。等我们争先恐后地跑回家时,大人们已经围着桌子开始吃肉喝酒了。
我们把木头搬进厨房,厨房的大锅里是炖好的猪肉,其实妈妈是不想让我看杀猪,才让我去捡木头的,家里的木柴是足够的。大人们喝着酒,我们几个孩子围着小桌子吃起肉来,肉很香。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孩没有跟我们去捡木头,站着看完了整个杀猪过程,这时也被妈妈叫了过来一起吃肉,他们就给我们讲起了整个杀猪过程,怎么放血、吹气、拔毛、开膛,我们很羡慕他们胆子大。
突然一个男孩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告诉我说我妈妈还掉眼泪了。我先愣了一下,很快就想起黑猪是春天时买来的猪崽,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是妈妈给它拔的野菜,喂着长大的,宰了吃肉她是舍不得。这样一想,我的鼻子也有些发酸,夏天时黑猪还生过一场病;它还趁家里没人时从猪圈里逃跑出来过一次,把后院菜地里的蔬菜全咬坏了;后来入秋时为了让它长膘,我还偷过别人家的青玉米,被家里大人训斥过……我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是收获的喜悦和欣慰。我吃了几口就帮着妈妈在灶火旁烧火,她正在炼制猪油,灶洞里绛红色的火光投在墙上亮堂堂的,照在我的手指头上亮晃晃的。
炸黄糕
我们这一带的黄糕是黍米做的,每家年前都要准备一大缸。爸爸每年春天都会在玉米地里留出一小块地种点儿黍谷,秋天收的黍谷纯粹为了炸黄糕。黄糕需要包馅儿,有咸味的黄豆馅儿和甜味的糖馅儿、红豆馅儿。我的任务是去村里田家豆腐坊要酸汤,这种酸汤是用来调制黄豆馅儿的。黄豆也是自家地里产的,秋天晾晒透了,由农具连枷拍打下来,再打碎成很细的黄豆糁子。黄豆糁子由豆腐坊里专门点豆腐的酸汤浸泡略微发酵后,再放到锅里加上葱花、盐巴炒制,直到散发出浓浓的豆香味。
要酸汤这个活儿就落在了我身上,可我并不情愿去,因为我与豆腐坊田家的小儿子田玉华是同班同学,田玉华绰号“豆腐王”,他哥哥是“大王”,他是“小王”,我曾跟田玉华在班里打过架,还把他耳朵和嘴唇给打破了,当时他那比我们高两个年级的哥哥拽着我的耳朵到了班主任办公室,我被罚站了半天,还请了家长,向田玉华道了歉。后来我在班上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只是故意跟着班里孩子凑到一起喊田玉华“豆腐王”。
“怎么还不去?去得晚了,酸汤就没有了。”爸爸一直在催促我,我端着盆子慢腾腾地出了家门。
等我挨到田家时,田家门口已经排着长队,这种酸汤的发酵制作是田家祖上传下来的,平时是用来点豆腐的,数量有限,隔段时间才会发酵制作一次。我赶紧排进了队伍里,等我顺着长队往前一看,豆腐坊里冒出热腾腾的白色雾气,雾气里正有一个男孩在为人舀酸汤,那个男孩就是田玉华。我的胸口咚咚咚地打起了鼓,要是轮到我了,田玉华不给我舀酸汤怎么办,会让我颜面扫地。我只好低垂着头硬着头皮往前走,我扭头看到后边也有认识的同学,那些同学做着鬼脸低声说着“豆腐王”,我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
很快就轮到我了,田玉华先是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但又很平静地给我舀了酸汤,并没有因为那件事而为难我,我顿时感到了些许愧疚。我张大了嘴巴想说点儿什么,却说不出口,正巧豆腐坊里又熟了一锅豆腐,腾腾的白雾又冒了出来,正好把我和他罩住了,他一笑,我也尴尬地一笑,这一笑谁也没有看到。风来了,雾气散了,我一抬头正看到他的哥哥就站在他的背后,怒气冲冲地盯着我,我端着酸汤赶紧跑了。
我走在半路上,有些得意地吹着口哨,边走边伸出舌头舔着盆子里的酸汤,酸酸的,我总是忍不住去舔。我回到家里时正赶上使用,甜馅儿的黄糕都包好了,妈妈开始用酸汤制作黄豆馅儿,爸爸开始油炸黄糕,黄糕的香味和炒制出的豆香味在屋子里飘逸着。黄糕刚出锅,照例是要给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伯伯叔叔家、舅舅家和邻居家每家送一碗的,这一天我就从村东走到了村西,又走回来,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但我一直想的是田玉华为什么没有计较那次打架的事。
写对联
对联是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贴的,爸爸的毛笔字在村里家喻户晓,快到年底时亲戚朋友都要把写对联的红纸送到我家,红纸都是事先裁好的,每家卷成一个小捆,扎起来,写上名字,毕竟有六七十户人家,避免错混了。爸爸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别人写对联,每天会写到深夜。
每年都是我帮着爸爸打下手,爸爸端坐在写字台前,毛笔、墨水和砚台规矩地摆着,我帮着揭开未写字的红纸,一张张递过去,并把写好的对联放到炕上晾干。每次从爸爸手里接过对联时,我都小心翼翼的,因为墨没有干,震动几下或者端不稳了都会把字打花,不美观,爸爸看到了还要重新写。
爸爸的毛笔字写得秀逸清雅,他一丝不苟地写着,我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看着,旁边火炉上的壶水噗噗地冒着热气,墨香味在屋子里飘荡。爸爸写了这么多年对联,从来都是提笔就写,每写完一家的,我最后会把长长短短的对联卷起来,捆扎好,以免与别家混淆了,有些还要事先用铅笔标出上下联,以免不懂意思的人贴反了。爸爸写了这么多年对联,从来不收钱。
我看得多了,手也痒痒起来,也要求写,可爸爸不同意,这些对联都是给亲戚朋友写的,爸爸得拿出最高的水准,怎么肯让我在别人的对联上练习呢。爸爸笑着说,只有我写的毛笔字过了他这关才行。我找来另一支毛笔也像模像样地在废纸上练习起来,爸爸偶尔会掉过头来指导我几句,怎么握笔,怎么顿笔,带钩的字怎么写,可爸爸总是摇着头笑,写了没一会儿,我已是满头大汗,没想到写毛笔字这么累。
我就坚持了三天,第四天就松懈下来了,直到爸爸把所有的对联都写完,我写的毛笔字也没有过了爸爸这关。不过爸爸总算允许我写十个,这些都是家里的对联,我坐到爸爸坐着的地方写起来。我边写边想字的结构,写着写着,突然不认识写完的字了,一恍惚好像不是这个字。我写完了把对联摆到一起,让爸爸评论,爸爸哈哈大笑,烟灰掉落了一身。我再一细看,有的字像要栽跟头,有的字好像被肩膀上的东西压得矮下身去,有的字则瘦得好像几天没有吃饭,我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再也不敢写了。
等到所有对联都写完的时候,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儿就是为各家送对联。骑着自行车就像一个邮差,从村东跑到村西,按着铃铛叮叮当当响,每到一家都会受到赞扬,好像这些对联都是我一个人写的,这份荣耀是我一个人的。
我想等我再练习练习,明年就能给别人家写了,我特意又买了两瓶墨水,每天写十几张,可慢慢地我把写毛笔字的事忘到了脑后,直到有一天我在家门口看到地上的冰块怎么全是黑色的,回到家才发现,妹妹把我的墨汁当染料玩耍了。
要账
那年三十那天,爸爸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每家打完稻谷后都会剩下很多稻秸秆,村里的稻秸秆都会卖给有三辆马车的朱家,朱家把稻秸秆运到城里卖掉,朱家还差我家四十五块卖稻秸秆的钱。大伯家卖给朱家的稻秸秆钱是堂哥要回来的,爸爸让我去要,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人要过账。过年被人要账是很丢人的事儿,所以大年三十去要账的话,欠账人碍于面子,一般都会立刻还账。爸爸看我不太情愿的样子,他说就让堂哥带着我去要钱,我只能点头。
堂哥家在村南边的戏台子后面,正好离朱家不远。当我去找堂哥时,堂哥却说先让我自己去试试。我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先去,朱家有两个儿子,比我大五六岁,淘气是村里出了名的。当我到了朱家门口时,来要钱的人足足有二十几个大人,屋里挤满了人,有的人只能站在院子里说话。我被挤在大人堆里,朱家两个儿子故意把院子里的大白鹅放开了,这些大白鹅看到陌生人就追着咬起来,大人们不怕,可我被大白鹅追着跑到了大街上,朱家两个儿子笑得前仰后合。
又来了一个大人,我跟着这个大人又跑了进去,可是那几只大白鹅又追上了我,我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了屋子里,大人们陆续拿着钱走了,等到我时朱家却说没有钱。朱家两个儿子故意把大白鹅又放进了屋子里,我怕被大白鹅咬,只好委屈地出来了,哭哭啼啼地往回走,遇到了等着我的堂哥。
“堂哥,你怎么跟朱家要的钱?”我心有不甘。
“咱们是小孩,朱家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堂哥诡异地笑着,“我要是帮你要到了,你分我二十块钱,朱家的大白鹅可厉害了!”
我点了点头,已经替爸爸自作主张了。
“看我的!”堂哥带着我又去了朱家,堂哥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有人吗?我来替我叔叔家要卖稻秸秆的钱!”
朱家无动于衷,朱家的两个儿子又放出了大白鹅,大白鹅呱嘎呱嘎地叫着,伸着长脖子像几支箭一样朝着我和堂哥直冲过来,我躲到了堂哥身后。只见堂哥临危不惧,使出了杀手锏,他倏忽间就捏住了大白鹅的长脖子,顺手抱起了一只大白鹅,撒腿就跑。我这才反应过来,朱家两个儿子看到后急得直跺脚,追了出来,手里拿着四十五块钱,塞给了堂哥,堂哥这才把那只大白鹅还给了他们。
“你这招真厉害!”我很佩服堂哥。
堂哥笑笑:“我家的稻秸秆钱也是这样要回来的,没办法,朱家故意耍赖。”
我心服口服,按照约定我给了堂哥二十块钱。当我回到家把这些告诉爸爸时,爸爸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听说,朱家把那几只大白鹅悄悄地养在了别处,它们再也没有在院子里出现过。
压岁钱
初一拜年时每家都有每家的路线,这些路线会把村里的亲戚朋友家全部串起来,如果把每家的路线画到纸上就是一张密集的网。每年我们孩子们照例都是在村西的爷爷奶奶家集合,堂姐、堂哥、堂妹、我和妹妹,给爷爷奶奶拜完年后就开始串门拜年。村里分布着十几口泉井,井里流出的溪水像树枝丫一样在村里迤逦,村里人都是沿溪而住,所以整个村里的路就像一个迷宫,堂哥已经研究出了一条拜年的最佳路径,我们小孩子都是跟着堂哥走,几十家亲戚每家都不能落下,一圈走下来既不累又省了时间,最重要的是该得到的压岁钱都得到了。
每年都要去二爷爷家,不但因为二爷爷是医生,德高望重,更紧要的是二爷爷给的压岁钱多。而且每年二爷爷都要提问我们唐诗,他家里的书架上有很多泛黄的线装书,里面全是古诗。二爷爷提问唐诗时会先吟诵几句,谁要是能说出剩下几句就会多给谁压岁钱。有一年就问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堂哥憋了半天也没有接出来,我脱口而出,多得了很多压岁钱。后来我就发现二爷爷家有一本《唐人选唐诗》,只是文字是竖着排列的,还是繁体字,念的时候从上到下,好像爬树一样,从树上下来,再爬到树上,我明白了二爷爷考的诗歌肯定都是从这本书上出的,我就把这件事记到了心里。
堂哥总是找我玩砸“宝”,所谓的“宝”就是用书页纸交叉折叠起来的纸方块,放在地上轮流砸,看谁能把谁的“宝”砸得翻过身子,就算赢了。玩着玩着,我突然发现一张“宝”的背面竟然有“唐诗三”这三个字,我赢了“宝”,拆开一看,是《唐诗三百首》的封面,我恍然大悟,这是堂姐的书。堂姐已经上初中了,肯定是堂哥偷了堂姐的书叠的“宝”,我决定要把堂哥的“宝”都赢回来,这样把所有的“宝”都拆开了就是《唐诗三百首》这本书,这本书不是繁体的,字很好认,我要是能全部背诵下来,肯定能得到二爷爷的夸奖,随便二爷爷考哪首诗都不怕。
我追着堂哥把“宝”赢回来,越赢越多,我把赢到手的“宝”都拆了,铺开,压得平平展展,并对照页码重新排了顺序,却发现中间少了一页,从目录页看缺少的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早发白帝城》,我想一定是堂哥自己把这页藏起来了,可堂哥说没有。我和堂哥打了一架,直到爷爷发脾气了,堂哥也没有拿出来。
后来,奶奶要做豆酱,揭开炕席准备把煮熟的黄豆放在烘热的炕上发酵时,才看到一张又黄又黑的纸压在炕席底下,每天烧炕,纸快煳了,变成了灰黑色,正是《唐诗三百首》里缺少的那页。我在灯下努力辨认着,黑灰与黑字融为一体,其中一首诗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让奶奶帮我把积攒起来的几百页纸用针线沿着书边缘装订成了十几个小册子,这样每天都能背诵几首,时间长了,所有诗已是滚瓜烂熟,所以每年在二爷爷家我总能拿到比堂哥他们更多的压岁钱。
每次拜年最不想去的就是二奶奶家的四大伯那里,四大伯是鳏夫,而且人很懒,我们早就听大人说了,他家里的三亩多苹果园不好好管理,本来苹果结得很多,他也不修剪、不打药、不除草,到了秋天连半亩地的也收获不了,屋子里的地也是坑坑洼洼的,十几年不修补。开始几年我们这些孩子都有点儿看不起他,后来他牙齿掉光了,一说话就漏风,走路颤颤巍巍的,他再给我们压岁钱,我们都不想要了,更多的是觉得他很可怜,不忍心要他的钱。
茄子秸秆
新衣服是每个小孩新年必能实现的梦想之一。那年,爸爸妈妈给我买了西装和皮鞋,过年穿起来比夹克有气势多了。但是北方的冬天有零下十几摄氏度,孩子们需要穿着棉裤、棉衣和棉鞋来御寒,我突然穿起了西装和皮鞋,是经不起冻的,没过三天,手、脚和耳朵都冻坏了。
等晚上回到家里,围坐在炉子边,脚和手一受热,红肿起来的地方就开始发痒。屋子里越暖和手脚越痒,总想用手抓,越抓越肿,冻疮膏也不起作用。只穿了三天的皮鞋不能穿了,因为脚肿得伸不进去,即使伸进去了也无法走路。
爸爸妈妈很着急,又痒又不能抓,而且时间长了还会留下冻疮伤,每年一到冬天就会红肿。爸爸只好为我去地里找茄子的秸秆,我们当地人用茄子秸秆煮出来的热水泡手脚治冻疮,很管用。爸爸去地里找了半天才回来,却没有找到,种茄子的人不多,有的话也在收秋的时候砍倒了,焚烧掉了。爸爸又听说鸽子粪煮出的热水能消肿,而且还能去掉冻疮的病根,是一个偏方,可收集鸽子粪更难。
我坐在炕上手脚痒得直哼哼,爸爸坐在炉子旁边抽烟边回想着,夏天时村里谁家种了茄子,村东村西,村南村北,一块地一块地地回忆,终于记起来一些,还在纸上一一画了个大概,一共有十来处,爸爸笑着说明天就能找回茄子秸秆。
谁知夜里落了一场大雪,雪很厚,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院子里白皑皑一片,我的手脚在被窝里暖了一夜,倒是不太痒了。爸爸执意要去村外地里找茄子秸秆,正月里根本不会有人去村外田野的,要是让人知道会被笑话。爸爸吃了饭就出门了,我也跟着去了,落到雪上的阳光像流动的流苏,大地白茫茫一片,只有那些大杨树粗略地划分出了田埂、水渠、田间大小路,爸爸在前,我在后,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寻找着。
“大雪掩盖了大地,更难找了。”我不停地抱怨着。
爸爸眯缝起眼睛朝远处看着,别说茄子秸秆了,连地里的荒草都看不见。爸爸无奈地笑着,我们从最北边又向东折去,大海捞针,爸爸索性玩起了雪,我们打起了雪仗,无边无际的雪都是我们的,我们边跑边大声笑。
“那边有两只野兔!”爸爸惊讶地叫着,指挥我往另一边跑,“快!那边!”
我们把两只野兔追得团团转,后来实在是跑不动了,那两只野兔居然也停下来,扭头瞪着我们,好像在盘问我们“不好好在家里过年,跑到野地里干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斜着穿越整个田野,无意中从覆盖着雪的地里踢起了几个茄子秸秆根坨,茄根上留着镰刀割断时留下的痕迹,镰刀割断的一般都会打好捆运回家里当柴火。爸爸仔细辨认着这块田地,突然想到这是村南老梅家的。我们径直找到了老梅家,老梅家的门口垛满了茄子秸秆,我们喜出望外,爸爸进去跟老梅家人说明了缘由,老梅家人送了我们好几捆,我连着泡了三五次茄子秸秆煮的热水,手脚上的肿渐渐地下去了,再也不痒了。
山西梆子
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九村里都会请戏班子来唱七天戏,戏是请给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仙“三官爷”看的。附近这些村子也只有我们村子每年请戏,所以我们都认为“三官爷”就住在我们村子里,保护着我们村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我们这里离山西近一些,每年请的都是山西梆子,剧目大概就是《打金枝》《卷席筒》《二进宫》《蝴蝶杯》等名剧。
唱戏班子一住就是好几天,戏台子后面就是堂哥家,正好堂哥家的西屋空着,唱山西梆子的戏班子就寄宿在那里,我和堂哥一来二去就跟那些唱戏人混熟了。戏台子幕布后就是他们化装的地方,堂哥带着我每次都能跟着唱戏人进去,看他们怎么化装,从背后看他们怎么唱戏,那些伴奏乐器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在戏台子后面看戏反而没有了趣味,好像一切都明白了就没意思了,倒是村里其他孩子很羡慕我们。
唱戏这七天中的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晚上要“察街”的。“察街”就是晚上六点提着“三官爷”的两个灯笼,由唱戏班子、村里爱唱戏的人、孩子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村里的街道走一圈。我和堂哥会事先到唱戏班子那里“打脸”,“打脸”就是画简单的脸谱,会在鼻子、眉心的地方画一个紫色的石榴。“察街”开始了,有踩高跷的,有扭秧歌的,到了每个泉井边时要放鞭炮。“察街”就是让“三官爷”沿着村里街道看看,为每家每户祈福,我们总觉得那两个灯笼就是神仙的眼睛,灯笼里摇曳的烛光就是“三官爷”在点头眨眼,只有察完街了,晚上那场戏才正式开始。
戏台子下人山人海,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村外南边是桑干河,河边有成片的海棠果树,那么多的海棠果没人要,我和堂哥准备把海棠果做成糖葫芦,到戏台子下面去卖。我和堂哥去那里摘了满满一箩筐海棠果,一回到奶奶家就开始熬糖稀,爷爷和奶奶已经去看戏了,等糖稀熬得差不多时,才想起没有穿糖葫芦的竹签子。堂哥突然一拍脑门,他想起了夏天的竹帘子,竹帘子里全是长竹棍,截断了正好做竹签子。我和堂哥在奶奶家翻找出了折叠好的竹帘子,把竹帘子拆解成了一大捆糖葫芦竹签,把做好的糖葫芦插到事先用稻草秸秆扎好的靶子上,大摇大摆地到戏台下卖起了糖葫芦,生意很好,我和堂哥挣了很多钱,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个夏天的竹帘子。
看戏是奶奶的最爱,她看得津津有味,可我和堂哥听了这么多年戏,从来就没有一次听懂过。奶奶个子矮,为奶奶事先占个好位置成了我和堂哥每天最重要的活儿。每场戏,奶奶都是最后离开的那几个人之一。看戏这几天也是邻村晚辈外甥、外甥女来看望爷爷和奶奶的时候,白天要在家里接待客人,奶奶就没办法出来看戏了,总是问我和堂哥今天白天是什么戏,要是听说是往年看过的剧目,她一定会嘀咕,“肯定没有那年那帮戏班子唱得好。”
那年十五晚上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晶莹剔透的雪花在灯光下像舞蹈的精灵,奶奶看得越来越起劲,我和堂哥陪在奶奶身边,每个看戏人的帽子上都顶着一座小雪山。看戏的人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唱戏的人没有停,我和堂哥都有些想回家了。
“奶奶,戏高潮已经过去了,还不走?”
“再看会儿。”戏台子下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但看到奶奶她们聚精会神的样子,唱戏的唱得更起劲了。我和堂哥都在打哈欠,直到最后散了戏,奶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和堂哥搀扶着奶奶,奶奶却不让,“没事,刚下的雪不滑。”我和堂哥担心地跟在奶奶的身后,脚下的雪嘎吱嘎吱地响着。
六年级那年的腊月,我得了阑尾炎,哪里也不能去,眼看着就要到年底了,病还是不好,每年孩子们该做的那些事我一件也做不了,在家里很烦躁。年三十的时候,堂哥又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本《红楼梦》,我问了半天他才说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初一那天堂哥给我把压岁钱拿回来了,因为我没办法出去拜年,他帮我代拿着拜年时亲戚们给的压岁钱。他再次来时,戏台上又开始唱戏了。
“今年唱的什么戏?”
“还和往年一样,《卷席筒》什么的,没什么新鲜的。”
“还是往年那拨唱戏的?”
“换人了。说是往年那些人去大同唱了。”
其实唱哪出戏,我们也听不懂,好像我们很懂戏的样子。因为不能出去,我就在纸上抄写起了《红楼梦》,抄了整整一个正月。
与年有关的事还有很多,那时妹妹喜欢收集各色糖纸,我就用糖纸换妹妹的钱,在她那里糖纸比钱有价值;放鞭炮时总是抢着点火,鞭炮响完了,还要再仔细寻找没有响过的;我和堂哥一致认为过年时天上有一种叫“年”的外星人来袭,放鞭炮、烟花是与外星人大战;看爸爸妈妈如何虔诚地祭拜祖先;每个孩子必须遵守过年的一些避讳,不能哭,三十晚上不能动剪子……等戏台子上的戏唱完了,年才能算彻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