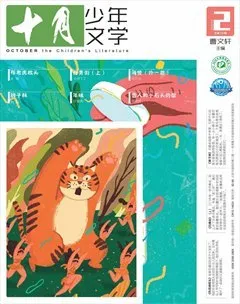碰撞想象与现实 启迪创作和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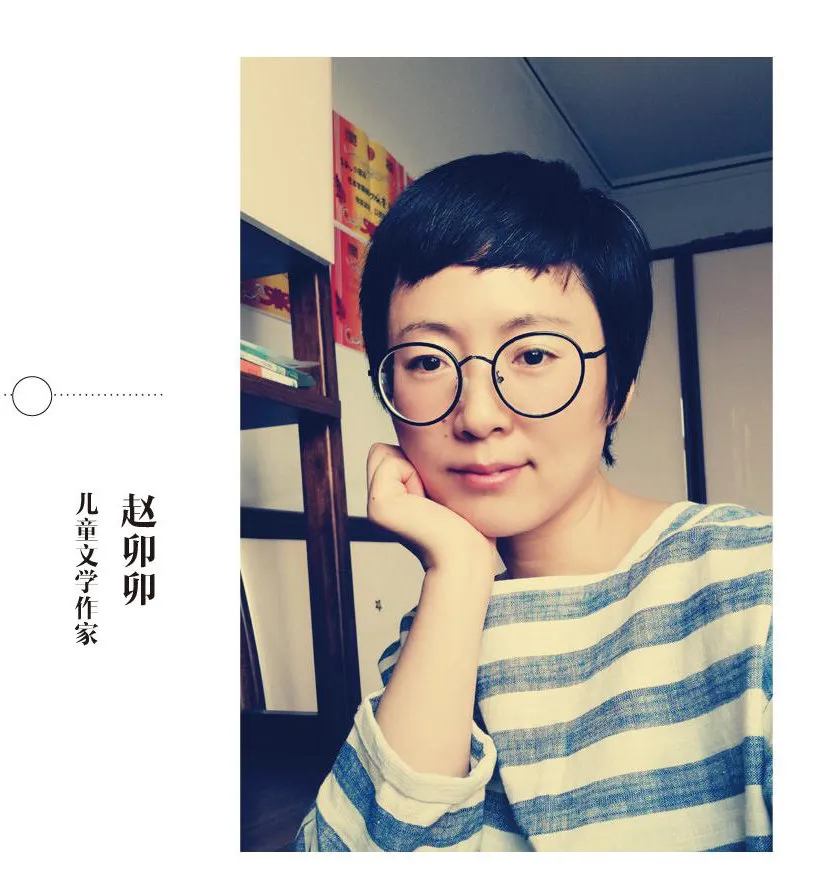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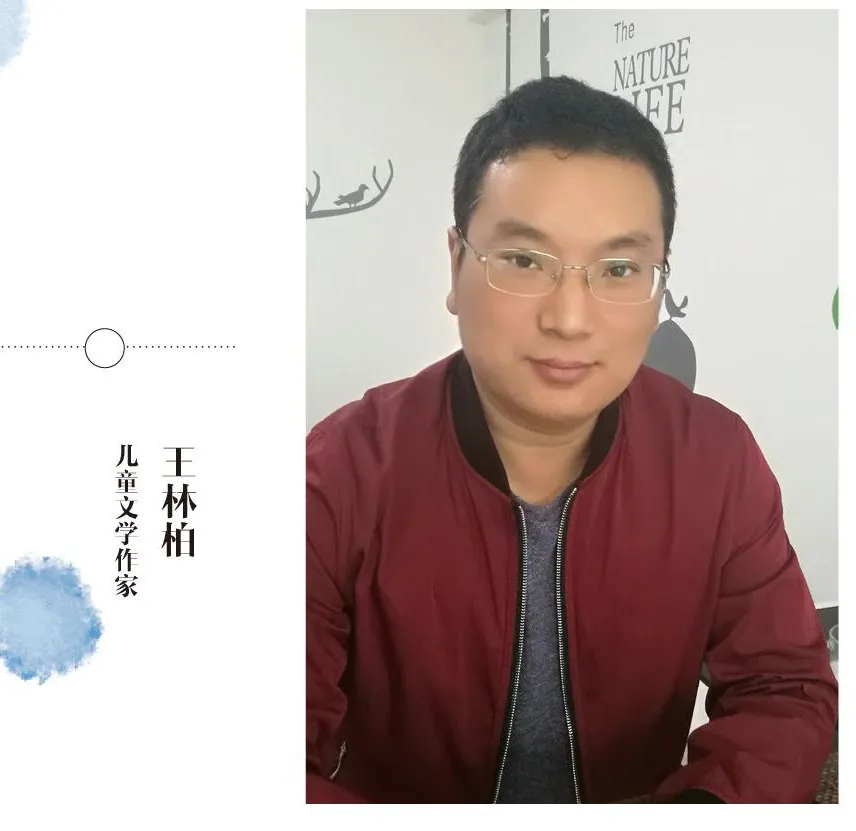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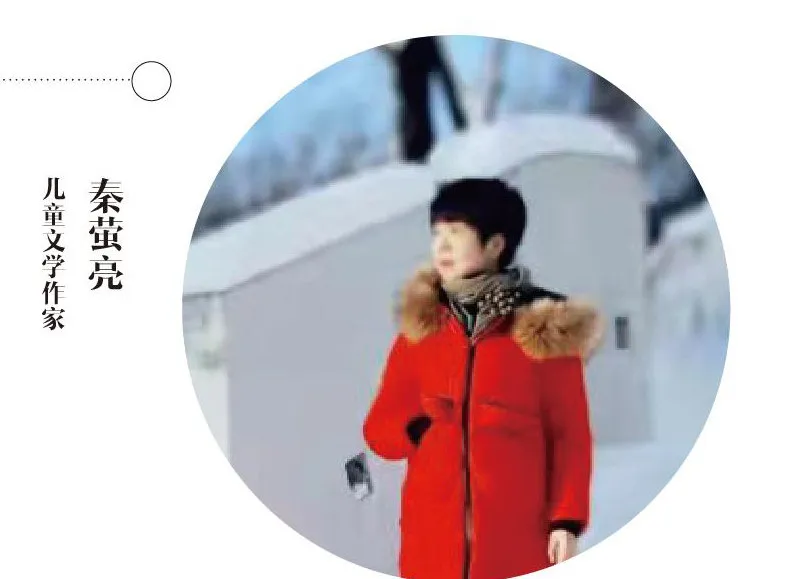
本期话题:
关于童话和幻想小说的关系,以往的探讨已经有很多。一般来说,童话运用幻想和想象营造出一个自成逻辑的世界,而幻想小说则运用某种手法将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连接起来。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是否会对童话和幻想小说进行明确地界定?您觉得这两种体裁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如何处理好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关系?
童话与幻想
秦萤亮
儿童文学作家
我的创作是以幻想为主,间或也有童话。以我来说,“童话”和“幻想”这两种文体的区别,就犹如“儿童”和“少年”的区别。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但界限却又不是那般清晰。谁能断言,“儿童”和“少年”之间的分野,究竟设立在什么地方呢?而一个孩子,又是在哪一年中的哪一天、哪一个时刻跨越了这条分界线呢?
我想再以绘画来打个比方。童话有一点像是不受任何技巧、任何概念所束缚的儿童画。在这里,作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神奇世界,没有透视和解剖,也没有远近和景深,只有生机沛然的色彩和元气淋漓的笔触。一个红色圆圈,可能象征着光芒万丈的太阳,象征着灼热和遥远;一条粗粗的蓝色蜡笔线,则可能象征着遥远的地平线,象征着蓝色天空的逐渐消融。
幻想,则有一点像是引入了基本绘画技巧的作品。我们在画面上运用各种技法,以线条、色彩、阴影和擦痕,塑造一个似幻还真的世界。这世界的真实程度,则依作者个人的笔力,与每人眼中不同的风景而定。简单地说,当童话那自成一体的世界,被现实的光影所渗透进来,在那明暗交界的地方所诞生的,就是幻想。
《卖火柴的小女孩》形式虽是童话,背景却比大多数幻想作品更为严峻凝重,其笔触之简练、情感之沉痛,也更加惊心动魄。东方的《西游记》或西方的《哈利·波特》则以现实主义的严谨精神,专心营造作者专属的幻想宇宙,这种横绝万物的气概,也体现了“童话”的精神。而这,也许就是我作为普通作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方向。
童话是云,幻想小说是雾
连 城
儿童文学作家
童话可以无所依凭,幻想小说则要基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遵守社会的运行规则。不过我也无法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除非它们的特质非常明显。以个人创作为例,在《百里香和甜菜根》中,鬼狒王七十三世在自己的背上以血肉培养出一种甜菜根,甜菜根可以随意播种,然而拔掉甜菜根,留下的坑洞是通往异世界的,几个异世界由于甜菜根的出现,像连环套一样钩连起来,居民穿行其间,猫头鹰载人飞行,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似乎生来如此,理当如此,我把它归为童话。
《打春鸡》中,布鸡变成真鸡,是因为得到了春神句芒的帮助;《卖甜酒的狐狸》中,狐狸并非生来就有“神通”,其幻术是通过刻苦修习得来,而且就算幻术了得,也无法摆脱衰老和死亡,寿命和普通狐狸一样;《布老虎枕头》是写物老成魅的故事,然而它们的“超能力”不是必然获得,是偶然获得,也并不愿意被人类发现自己“木秀于林”。这四个故事都是5万字,但只有《百里香和甜菜根》是童话,其他算幻想小说。
从前有一种说法,“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武侠世界里的人,不事生产,消费动不动豪掷千万;隔空驭气能伤人性命,轻功无视地球引力……太多明显“不合理”的情节,呼为童话是合适的。因为幻想小说更“合理”一些。
童话和幻想小说的界限有时候并不分明,我认为童话是云,飘在高空;幻想小说是雾,更接地气。在某些地方,比如高山,雾就是云,云就是雾。
“真”幻想与“假”童话
赵卯卯
儿童文学作家
幻想小说,它首先是小说,然后是幻想,它具有小说的特质,从现实生活中发芽生长,但无论“它”最终成长为什么样子,在这个过程中,它都要遵守一些“现实”规则以及我们普通人的“思维逻辑”方式,在这个世界里,所有超越人类能力范围的能力,都需要通过“学习”或者其他途径来获得,比如说《哈利·波特》中的站台以及魔法学校,《纳尼亚传奇》中的魔法壁橱,等等。
而在童话里,却没有任何的“束缚”,童话一旦产生,便是合理的,它不需要你去解释为什么猫会说话,为什么树能行走,为什么山水万物有它们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因为这些都存在于童话当中,它是跳出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作者自创的世界,不需要遵守其他人的规则。
幻想小说读上去更像是“真实”的事件,而童话却是永远不能成真的“假”故事。
有时候幻想小说、童话会像两条平行而流的河水,但有时候它们又会交汇在一起。
童话也可以来源于现实,童话也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产生,而幻想小说中也能找到童话的影子,比如《奥菲利娅的影子剧院》,它既很童话(影子具有生命),但同时又具有幻想小说亦真亦幻的特质。
在我的创作中,其实我很少去真正、明确地区分这两种创作形式,因为不管是幻想小说还是童话,它们都是“幻想”创作后的产物,它们只是手段,服务于我们的故事,而我作为一个作者,只要为读者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便足够了。
心所在的位置
王林柏
儿童文学作家
正如量子物理有薛定谔的猫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之困惑,儿童文学亦常有“童话”与“幻想小说”之辩争。很多人希望画一条明晰的线去区分“童话”与“幻想小说”,最好不要像光,既呈现“波”的性质,又呈现“粒子”性质(波粒二象性)。
安房直子《狐狸的窗户》,猎人从现实走入幻想世界,又从幻想回归现实,但定位为童话更合适;《小王子》虽然涉及外星球及外星人,但应该没人将它归类为科幻。
“童话”与“幻想小说”的界限到底在哪儿?我以为,任何一个故事,或体现人性,或反映历史或时代特征……都有现实为根,不存在无根之木—完全脱离现实之幻想。幻想也许是根之枝叶延伸,也许是根之花朵绽放,也许是花香吸引的那只蝴蝶。对我来说,故事与现实的粘连度(也就是我们读故事时,心所在的位置)是判断作品体裁的依据。《皇帝的新装》现实映射如此深刻,《夏洛的网》故事以现实的农场为背景,但我们的心处在童话世界中;星新一的故事充满奇思妙想,无论发生在外星球还是未来,总归缺少一些童话的诗意和轻盈,让我首先想到现实,无论如何也想归类为小说。
当然,这种粘连度本身也是薛定谔的“粘连度”。一个故事的背景、人物、情节、语言……甚至其中的某一句话,都可能会影响感受。
作为一个作者,我创作一个作品,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最自然、最贴切地呈现出自己最想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故事。可以如蟋蟀,脚踏大地,鸣声在夜空;也可以如风筝,身在蓝天,维系在大地。作品像光,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