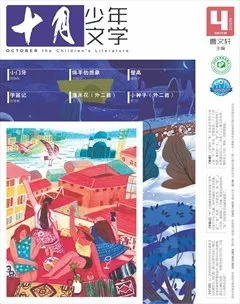周晓枫的童年叙述
《小门牙》的作者周晓枫在散文领域耕耘多年,业绩突出。近年来开始涉足童话写作,亦不乏关注。我也关注她的创作,但说实话,对她的童话创作我更多的是警觉和挑剔,当然也可以说是客观评价。我关注的点不少,但最关注的是她的童话适不适合儿童阅读,会不会太“深”,也即她的童话有没有童年性。具体点儿说,就是她的作品是外在的、刻意的、游离的童年点缀,还是融入作品内里的童年叙述。
我们先看看《小门牙》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简单说,这是一个精灵故事,一个小门牙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精灵谷生活及其与人类交往的故事。小门牙们的主要工作是吃梦,有的梦很长很长,吃一个撑得不行,有的梦很短很短,不够吃。梦要趁刚做好的时候吃,要不然咔嚓一口下去,只咬到一嘴空气。在精灵谷,除了吃梦的小精灵,还有捕梦师和神通广大的计梦师。
任何人都离不开梦,但大人的梦与小朋友的梦不可同日而语。梦在小朋友那里是非功利、有趣的,是亲密的伙伴。换句话说,作品所讲述的是一个儿童容易接受、喜欢、好懂的故事,是很“浅”的故事。“浅”,是故事很重要的前提。有了这样的“浅”,如果接下来作品有可能“深”的话,自然也就不让人担心了。事实上,故事的发展也的确如此。精灵谷是小门牙们的天堂,也是小门牙们的家园。这里的一切是美丽的、如诗如画的、如梦如幻的;这里的一切又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有悲有喜的。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有梦想就有希望。每个小精灵都可以战胜胆怯,战胜胆怯就可以变得勇敢,变得勇敢就可以成为调梦师。其实,要说“深”,也并不“深”,谁都知道勇敢是一种优秀的品质,这都是“常理”, 但恰恰是“常理”的讲述、推演和展示,才是让人信服的“深”,不是吗?
不过,虽说这个故事适宜儿童阅读,但还不够,我们还要看看作者如何来讲述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有共计七章,七万余字,整个故事读下来,作者依然有恰到好处的表现。且举三例。
例一,人物出场安排。在第一章人物出场时,作者一一介绍了小门牙、小羽毛、小音符、小翻和小滚,还介绍了捕梦师。“天啊,人物太多了吧?都快记不住了!别急,我保证:你绝对不会把各种角色弄乱了。”对于一时半会儿还不起作用的计梦师,作者仅提及名字,一笔带过,留个伏笔。“但计梦师的事情,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否则,会破坏讲故事的氛围,会影响听故事的情绪。”直到需要计梦师出现的第五章才给予介绍和描述。这样的叙述安排,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整个故事架构的掌控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对儿童线性阅读习惯的了解和把握。
例二,具象跟进。作者在讲述故事或描述人物时,最后总会落到一个实体的具象上。比如作者介绍捕梦师独特的捕捉能力:“他有一个特制的圈网,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梦冻住,就像吹泡泡时的泡泡能短暂卡在圈环里一样。”通常来说,讲述到这里,应该也可以了,但作者没有,她还继续往下说:“拿什么装那些梦境呢?只能用蝴蝶羽化以后剩下的空蛹,不能用其他的容器。捕梦师的动作敏捷,他飞快地把捕到的梦放到蛹衣里,然后飞快地缝合……”很显然,这个具象就是“空蛹”。由于“空蛹”的出现,捕梦师捕捉梦境的能力变得更为形象生动了。
例三,童年语义。“当黑夜沉得晚风都吹不动,没有谁愿意留在外面,鬼气森森”这样的语句,不乏周氏散文特点。但这样的语句也仅仅是有特点而已,看不出明显的读者意识。我想说的是,只有当上面的语句与后面的语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时,叙述的童年性才能够清晰呈现出来。这就是作者在“鬼气森森”后面加了一个“的”,“鬼气森森的”,一下子让阅读的“硬”转“软”了,更重要的是紧接着作者来了句“真让人害怕啊”,这就完全进入了儿童读者的阅读节奏和方式。成人文学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叙述,但放在童话里就恰如其分了。
这就是周晓枫的童年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