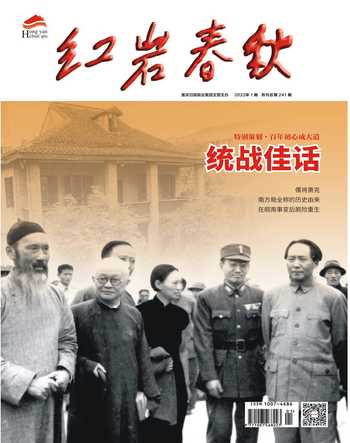彭德怀的重庆之行
熊飞宇



抗战时期,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为解决河北问题,曾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所谓“河北问题”,是指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为抢夺八路军的政权和地盘,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由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激烈斗争。
赴渝会谈
1938年12月下旬,彭德怀到西安出席蒋介石原定在此召开的西北和华北将领会议,并打算与蒋介石面谈解决河北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就此指示彭德怀:“在要求划某些地区行政权给八路军而谈判顺利时,或有必要时,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磨擦。”
12月24日上午11点,蒋介石在西安接见了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略谈数事。因汪精卫出走安南(今越南),蒋介石急于起行,便约彭德怀到重庆详谈河北问题。于是,彭德怀乘机抵渝。
12月28日,彭德怀在重庆面见蒋介石。据《彭德怀年谱》记载,两人会谈的成果有:蒋同意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与彭到河北调查解决河北磨擦问题;敌后民众工作归军队做;下次军事会议上讨论八路军要求扩编为三个军的问题;以萧劲光为河防司令;八路军在敌后可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维持行政系统。
《彭德怀传》也有记述:“同年(1938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将领会上曾约彭德怀去武昌和他单独会谈,要求八路军在敌后出击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作了积极的响应。现在,蒋介石关心的是要限制八路军,见了彭德怀就根据鹿钟麟、张荫梧(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等人告的状,责怪八路军建立冀南、冀中抗日政权是破坏行政系统。彭德怀列数鹿、张在河北破坏抗日团结的事实作答,列举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陈述敌后战场对牵制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的重要。最后商定,河北磨擦问题由蒋介石电天水行营主任(辖一、二战区)程潜派大员与彭德怀一起赴冀南解决。”
程潜原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被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与彭德怀数次会面后,程潜决意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与彭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彭德怀与蒋介石会谈前后,重庆《新华日报》曾刊文声援。1938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短评《八路军的胜利》,指出“八路军在华北坚持长期抗战,曾有多次大捷。而最值得重视的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配合友军,与民众密切合作,每天每时,随时随地都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完成了和完成着消耗敌人,配合全国友军作战的任务”,“单就十、十一月两个月的战绩总结来看”,即以事实“粉碎了那些有意散布诬蔑八路军的一切谰言胡说”,“我们相信八路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在朱、彭总副指挥率领下,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更大胜利”。
12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再次发表“本报山西專电”——《发展敌后游击战,八路军活跃华北,冀鲁豫各省敌伪迭被歼灭》。
拜会冯玉祥
因鹿钟麟系冯玉祥旧部,1939年元旦,彭德怀特意拜会在重庆的冯玉祥,以谋求问题的解决。关于双方言谈,冯玉祥在日记中记录得很详细:
十一时,彭德怀先生来见,满面风光,著(着)灰布军装。相见握手后,我首先说辛苦了,我替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谢谢您,您那里打的(得)很好。彭说:副委员长身体很健康,我也替全数人民祝福,副委员长在抗战上作了很大的推动工作。我们都很清楚的,前几天也把汪精卫讥骂得太厉害。我说:今天上午的会(即上午九时的最高国防会议)多数人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彭说:国家危急到这样子,意见仍有纷(分)歧,真是可惜!一位党国要人也这样昏暗,真是国运多阻啊!
谈到鹿瑞伯(即鹿钟麟)那里的情形,彭说:在广州失陷武汉放弃后,鹿先生那里几有动摇。因平汉线兵力原薄之故也,有许多地方和八路军有意见纷(分)歧的,用的人多不妥当,如申保春,颇能干,即把他挤走了,这是很可惜的事。用着一位张荫梧,常说“与八路军是要对抗的,反抗的”这样的话。张荫梧在鹿先生那里是弄不好的。我说:张为人我略知道,鹿不知为什么要用他……前天瑞伯来电说:“有许多地方捆绑我的脚,饭尽弹绝,困难至多。”我就知道他是有了阻碍了。
彭说:我还要请副委员长给瑞伯去电注意这些不必要的磨擦。我答应彭先生下午写亲笔信请彭带去,一面也给鹿去电报。彭和我约电码,我应以晚上送去,彭说三日即可行程。
1939年6月上旬,鹿钟麟赴辽县(今左权县)下庄八路军驻地,与彭德怀会谈。会后,彭德怀说:“河北问题不在鹿钟麟先生身上,两王(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王孝绪、省教育厅长王承曾)才是关键之所在。”
1940年,鹿钟麟辞去本兼各职,飞抵重庆后,即见冯玉祥。谈起河北的失败及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冯玉祥埋怨他:“我要你深入敌后与八路军合作,发展一些部队,谁要你管他那些混账办法。”
不久,鹿钟麟被蒋介石委任军事参议院参议,闲居歌乐山,常与进步人士往来。
发表演讲
在渝期间,彭德怀对各报记者、文化界朋友及新华日报社同志作了关于华北抗战的演讲。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之崩溃是必然的,而且为期也不在远,中华民族之解放,已现出曙光,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克服困难,加紧团结,抗战必然胜利。”同时强调:“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的精诚团结,和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国共两党,唇亡齿寒,休戚相关,绝不可有丝毫摩擦,妨害抗战……必须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相互交换由中华民族血的结晶而得来的经验和教训。”
演讲结束后,“全场振奋,热烈的鼓掌历二十分钟之久”。
1939年1月8日,《新华日报》以《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为题,在第三、第四版上刊登了彭德怀的讲话,介绍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发展生产、英勇斗争、收复失地的情况,包括民众工作的目的与概况,反对汉奸及与敌伪军斗争,华北战争形势前途的估计,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意义,坚持华北抗战胜利的条件等。
为与“讲话”前后呼应,当天,《新华日报》特发表社论《华北抗战的经验》,并在报头两侧各摘录其中一段文字。文章强调:“华北的抗战,晋察冀和晋察热冀南和冀中等区域的存在、发展和巩固,证明了在敌人后方创立抗日根据地,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发展与巩固成为由现在过渡到战争相持阶段及将来反攻时期的重要战略支点。” “華北的抗战,也说明只有革命的民众运动才能产生革命的军队,只有革命的武装与民众亲密合作,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武力。”
之后,彭德怀的讲话以《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为题,连载于《申报》1939年1月15日第二、第六版,1月16日第二版和1月17日第二版;后又收入上海文献丛刊社编《文献》卷之五,于1939年2月10日出版。由此可见,彭德怀在渝发表的演讲反响热烈,影响深远。
然而,《新华日报》所刊彭德怀的讲话,署“于鸣笔记”,《申报》刊载的内容却署“彭德怀讲,于鸣凤记”,《文献》则署“彭德怀讲,于凤鸣记”。实际上,“于鸣凤”和“于凤鸣”均是误称。
于鸣,即郭于鸣(1916—1940),又名欲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后,始任外勤记者。1939年夏,正值重庆大轰炸期间,《新华日报》奉令疏散,于鸣留市区工作。1940年2月26日,于鸣积劳成疾,不治而亡。其文章与报道,多见于《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
查史求证
彭德怀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在重庆的这段时间,是否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过接触,尚待进一步证实。
1938年春,中共中央派周怡来重庆,在机房街设立八路军重庆通讯处,又称联络处。1939年1月,通讯处改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并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钱之光任处长,周怡任副处长。笔者查《钱之光传》,并无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待彭德怀一事。
与此同时,叶剑英作为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及十八集团军驻重庆联络代表,于1938年12月中下旬随周恩来从桂林抵达重庆,但《叶剑英年谱(1897—1986)》也没有在渝接待彭德怀的相关记载。
不过,据《一个老记者的经历》载,时任《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与《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在彭德怀抵达重庆后的“两三天”,经周怡同意,于苍坪街《新华日报》营业部后面“一间半明半暗的屋子”,做过一次采访。访谈自下午开始,至日暮时分结束。彭德怀向他们介绍了晋察冀边区、晋东南和晋南抗日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及整个华北战场抗日战争的形势。因军事将领的行踪需要保密,《新民报》与《大公报》均未公开报道此事。
笔者又翻阅《周恩来年谱(1898—1949)》,查找彭德怀在重庆是否与南方局联系过,但未见著录。
1939年1月4日,彭德怀由重庆飞抵成都,转乘汽车去西安。但据《申报》1月8日第四版刊载的《彭德怀公毕返陕》称:“八路军副军长彭德怀,来重庆与最高军事当局会谈后,顷已由重庆起程返陕北复职,今日(即7日)由成都飞西安。”
1月14日,《申报》又据“本报重庆十三日专电”,于第三版发表《彭德怀由渝返前线,华北士气大振》:“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氏,最近奉命来渝,报告军事情形及请示一切机宜”,“已于十二日安抵前线某地”。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