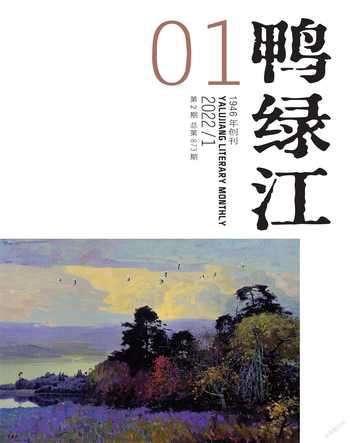排爆人(短篇)
翠山乡已进入寒冬时节。
乡政府南侧有栋二层小楼,门楣上硕大的警徽告诉人们这儿是公安部门,警徽上方有国旗迎风招展,这里是翠山乡公安派出所。
翠山派出所的管区有67平方公里,包括13个行政村、29000口人,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虽然治安情况比较复杂,但近年来综合整治到位,用大数据研判、视频监控全覆盖,翠山乡已连续多年没发生过刑事案件。派出所连续五年荣获省、市先进单位的称号,用所长老李的话说:“这是翠山派出所全体民警用智慧和辛苦换来的平安稳定。”
李所长50岁出头,身体健壮,一米八的大个儿,方脸上的汗毛孔比常人要粗。他脸色微黑,鼻直头略显得大,像是支撑双眼的底座,把五官调整得周正。他从警30年,当所长也有19个年头了。
临近中午,老李从外面巡岗检查回到办公室,脱下帽子,没来得及掸掉霜花,门就被推开了。
“所长,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若不能及时化解,恐怕会发命案啊!”来人带着一股寒气,是副所长王威,他很着急,话说得又快,脸涨得通红,呼哧带喘的。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老李示意王威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王威喝了一口,忙说:“所长,上午我和刘晨下去了解情况,去了金家村。到村部见村主任佟快嘴、妇女主任和会计几个人正闲聊。会计李娟叨咕:‘我看华存义这小子要出事,听他邻居刘二狗听导咕,如果张启良在12月末还不把医药费和误工费赔给他,今年大年三十就砍死张启良全家……’我和刘晨认为这是个隐患,所以我俩没再往别处去,立马回所。这事得及时处理,解了他俩的梁子,万一这小子真干出杀人的事呢?这可是颗定时炸弹!”
听完王威汇报,老李心头一沉,这件事马上占满了脑子,派出所千头万绪的一些事,霎时被挤出思绪。他掂量着,现在正是年末,临近春节,管区内不能出现任何案件,任何可能引发个人极端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的事,都会给辖区群众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派出所也无法向上级和辖区群众交代。尤其今年是社会矛盾排查整治年,如果因为矛盾没排查出来,排查出来没化解好再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2013年李生全家被殺的情景,瞬间又浮现在老李眼前。
那时老李刚调到翠山派出所才四天。金家村的李生与邻村的妹夫肖奎山因土地承包后的归属权产生分歧结怨,矛盾日深。那年冬天,肖奎山对一起放羊的邱瘸子说:“如果明年李大抠(李生)还不把那三分地给我种,等开春他起第一根垄时就杀了他全家。”可肖奎山的狠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重视,所以惨剧发生了。
第二年4月,正是翠山乡群山吐翠、梨花满山、布谷催春的时候。
21日,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天色阴沉,灰蒙蒙的,能见度不足50米,云雾如素带般在半山腰盘旋缭绕,解冻后的田野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当时,李生正在西沟山自己的承包地上吆喝着黄牛扶犁备垄、耕地抢农时呢。
中午时分,肖奎山从地边的松林蹿出来,手拿利斧从背后袭击,砍断了大舅哥李生的脖子。随后他又趁雨窜至金家村,闯进李家,用同样的手段,将李生老婆、儿子等人砍死。五条无辜的生命,惨死在罪犯肖奎山斧下。肖奎山自知法网恢恢,逃进山里自缢而亡。
每想起这个灭门案件,老李的心就像滴血一样痛,心情也像这山里的冬天一样苍凉寒冷,有一种鲜活生命在眼前惨死的悲怆。在农村,极端案件往往只因一些小事酿成。一些人小农意识强,思想狭隘偏激,邻里或村屯之间常因一些小打小闹、鸡鸭鹅狗、墙头地脑、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滋生矛盾而怀恨在心。天长日久,积淀膨胀,不及时发现化解,就可能导致恶性案件发生。农村存在的这些隐患,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想到这些,老李心急如焚。
他回过神,看了看被撂在一旁的王威,“你们还没吃午饭吧?先去吃饭!等我了解清楚后,再想辙解决它。”看着满脸疲惫的部下,老李心头一热。同事们为了防控疫情、稳控人员已连续奋战六天了,不能正常休息。王威和刘晨都新婚不久,因为每天执勤巡逻、办理案件,都一个多月没休假了。今天这个事又会给民警工作添重加码了,但手下兄弟的办案水平和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心里有数。
下午1点,老李拿起桌上电话,打给了金家村:“佟主任,你马上来趟派出所,有事想和你聊聊。对了,你来我这儿的事先保密。”他担心佟主任“快嘴”,一再嘱咐。撂了电话五分钟,佟主任像被风吹来一样,嘴快腿也快。坐下调侃几句后,老李马上问:“佟主任,你村的华存义最近怎么啦?”
听派出所所长问华存义的事,快嘴表情立马认真起来,忙说:“华驴子今年7月被五味村的张启良给打了,当时有人从中说和,张启良当时也答应赔医药费、误工费什么的,华驴子就信以为真,没报案,直接去医院看病了。住院住了挺长时间,光治伤就花了3000多块。出院后华驴子向张启良要钱,可张启良不讲究,戏耍人。出院半年多,华驴子追了数次,张启良今天说明天给,明天又说后天给,就这么搪塞推托,至今华驴子分毛没见。其实,谁都能看明白,张启良根本就没有给钱的意思,他在忽悠华驴子。最近他俩在电话里又对骂了。华驴子给张启良的最后期限是春节前,如果到时还不给就剁了他全家。所长,华存义这小子外号‘华驴子’,性格暴躁,办事认死理,想事一根筋,他说了就能干出来。现在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村里也怕出事,已经分别找他俩唠过好几次了,但张启良油盐不进,就是‘不掏兜’。华驴子白挨了打,能拉倒吗?再说村里村外的,华驴子以后咋抬头见人哪?还不得窝囊死?他俩老这么顶着也不是个事呀!所长,你们派出所给过问过问呗,别再整出李生家那样灭门的惨案。”
“华存义没来报案,他去乡综治办和司法所没?你们向那儿反映这事没?”老李问。
“向乡司法反映啦,没调解得了,况且华存义也不想经官,就想和张启良死磕了。”佟主任讲出了华存义为什么要行凶的缘由。
“挨了点打就要杀全家?目无法纪啊!”老李长叹一声,“等派出所了解了解情况,你们村和五味村还得继续做工作,稳住华存义,控制事态发展。”老李欲擒故纵地应和着。
快嘴走了,老李心里却暗潮涌动,思绪难平,如果不及时化解处理掉这事,一桩血案看来不可避免。面对这颗“定时炸弹”,派出所需要做“拆弹手”,做“排爆专家”。
第二天早晨依旧清冷,老李换岗后,呼着白气,两眼遍布血丝地回到了办公室,进屋后感到脑子发涨,知道血压又高了。他不敢怠慢,吃了两片降压药,没来得及洗漱,带着换岗回所的王威、陈彬,开车直奔金家村。
入冬,村里人起得不早,可进了华家院里,华存义已经在圈里喂牛,头发、眉毛、胡子上挂着霜花。华存义40多岁,眼睛略大,嵌在倔强的圆脸上。他的鼻尖、嘴角微翘,中等身材,较粗壮,是农村中所谓的“车轴汉子”。见有警察进院,他嘴里问着话,神情却很紧张。王威走到他跟前:“老华,这是我们所长,来请你到派出所去一趟,找你了解点事。”华存义虽然不知道要向他了解什么,却也配合,马上把草料桶拎回屋里,手在棉袄襟上蹭了几把,满脸狐疑地跟着一行人到了派出所。
上楼进屋,老李热情让座,又倒了杯热茶,屋里气氛显得亲切、轻松。不一会儿,这个执拗的农民被感动得一脸惶恐,手足无措,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老李让王威两人先回避,自己与华存义闲唠一会儿,见华存义没有了戒备和不安,就切入了正题:“听说你被人打了,有这事吗?”
听李所长问自己被打的事,这位汉子语气带着凄苦回答:“有,五味的张‘缺筒’,我眼眶子被他打得缝了6针,住了20多天医院。”“为什么不来派出所报案呢?”老李问。“当时有朋友从中间说和,‘缺筒’也答应给我赔医药费和误工费,我就没报案。现在真他妈的后悔,这狗人,事都过去七八个月了,他分毛没给,还到处卖狂说:‘就打他了,想讹钱不好使,爱咋咋的,哪告哪有人!’把我耍了!这亏我肯定不能吃,不行就一命抵一命了,我家哥儿仨,死一个还剩俩呢!这仇必报!我再让他嘚瑟几天。”华存义两眼喷火,气得手直哆嗦,话没说完就倾身埋头,抱着脑袋伤起心来。
老李察言观色,华存义语速较慢,性格急,且明显带有愚、鲁、蛮、倔、犟,典型的黏液质型人。
看着眼前愤怒悲伤的华存义,老李明白,这颗“定时炸弹”几乎已经设定好了时间,如果任时针跳动,爆炸也许就在近期。安静的五味村,正面临着一场血光之灾。那时,村中宁静祥和的氛围将被击碎,这让老李着实担忧。他思考着对策,“你没有去法院告他吗?”老李又给华存义续上茶水,继续与他聊。
“去了,法院说没有当时现场的证据材料,没有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不给受理。再说打官司得花不少钱,还得托人搭人情,一折腾就是一年半载的,咱老农民耗不起。不告了,和他掐了。”华存义愤愤地回答。
“那今天你就报案,派出所帮你一回,张启良不敢不听公安局的吧?”老李不紧不慢地给华存义出主意。
“派出所还能管这事吗?我当时也没报案,都过这么长时间了。”华存义抬起头试探着问。
“没超过六个月,派出所可以受理,我们帮你。另外,你不能老把杀人挂在嘴上,这是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属违法行为。如果有人举报,你会被追究的。”老李微笑着提醒华存义。
“哦……那就报案吧,经官!‘缺筒’借他两个胆也不敢和警察较劲!”华存义有些迟疑,也有些希望。从脸色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正在斗争。但所长老李坚定的神态,让他感到了正义的力量,好像自己遇见了打抱不平的好汉武二哥,心里隐隐地有了依靠。
“好,既然这样,你就得听派出所的。现在我们给你受案,再领你去做伤害鉴定,待调查取证结束后,给你一个说法。你看怎么样?”
“那行,就听你们的,这我明白。如果你能把‘缺筒’整趴拉膀了,我领全家人跪着管你叫爹!”老李听后哈哈大笑,对华存义说:“你就不怕输了吗?”华存义咧了咧嘴,态度虔诚:“不怕,我解恨就行!”华存义这几句,让老李松了口气,华驴子这股洪水,暂时被引入了可控的管道,起码不会泛滥成灾了。
老李喊来王威、陈彬,让他俩到办案区给华存义录口供材料,办理案子受理等相关手续。华存义怔怔看了看他俩,半信半疑地走了。
第二天,老李安排陈彬领华存义去市局法医鉴定所,给华存义的伤做鉴定。
稳住了华存义,老李紧绷的神经稍有宽松,对能化解这起矛盾信心倍增。根据华存义的口供,老李交代王威几人这案办理的方法,大家依计而行。下午,五味村的张启良被依法传唤到派出所。
老李早在审问室等了,他要看看张启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启良的眼睛不停地上下左右溜着,溜见坚固的铁椅、冰冷的手铐、闪光的警灯、审问桌前威严的警官。他平生哪见过这阵势,有点魂飞魄散,卖狂自擂的劲儿全没了踪影。所长老李的眼睛一直盯着他,沉着冷静的脸不怒也有震慑力。瘦高个儿张启良的身体因紧张仿佛矮了一截,两腿发抖。刀长脸已呈蜡灰色,大嘴占了多半块脸,把鼻子挤得像一条蚯蚓趴在那儿,不细看以为这人没鼻子,难怪人送外号“缺筒”。
审问开始,王威、刘晨先对张启良进行一番启发教育,张启良领悟力挺强,没用民警“挤牙膏”,便从头开始交代:“我是打华驴子了。但有原因,2019年7月份吧,我姐与华驴子及几个老爷们儿喝酒,有人使坏灌她,结果喝得胃出血,被送医院抢救,花了好几千元。我怀疑是华驴子出的阴招,我寻思都上下堡住着,不该把一个女的灌住院了,就挺恨他,所以,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事也凑巧,三天后的上午,我在金家村村部附近的朋友郑军车里唠嗑,华驴子从这儿路过,郑军和他打招呼他就过来了。我看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冲他骂:‘这年头交狗都别交人,狗都不会咕咚人,把个女人灌住院了算啥能耐……’华驴子见我指桑骂槐,质问我骂谁呢,当时我手里拿着手机,抬手没几下就把他左眼眶打出血了,后来被郑军几人给拉开了。当时华驴子满脸是血,可能伤得不轻,加上郑军和朋友给圆场,我就假装答应让华驴子先看病,花的药费和其他损失我全赔偿。华驴子也就没去派出所報案,直接去住院了。
“出院后华驴子管我要钱,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给,但他老磨叽我,最后我干脆就放横了。他不要杀我全家吗?我就和他‘骨碌’了,钱我一分不想给。”
张启良供述了他的违法事实。老李没听他讲完,起身回办公室,随手在网上查了查,张启良没有前科,是初犯。
键盘响过,口供录完,王威马上把材料上楼送给了老李。看完张启良的供述,老李让王威再把华存义找来,核实那天喝酒的事。
半小时后,华存义来了。华存义讲:“7月12号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到堡里的小吃部喝酒,碰巧‘缺筒’他姐和闺密也在,见我们进来,她就提出拼桌,因为我们也认识就凑一桌喝了。喝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原来跟我来的一个朋友是他姐婚前恋爱几年的男朋友,要定亲时,因张启良的父母彩礼要得太多,就黄了,二人无奈各自成了家。可他姐现在离了,把离婚怨在我朋友身上,说现在的处境都是他整的,借酒盖脸骂骂咧咧数落人家没骨气,就和人家摽着喝,不停地干。我拦都拦不住,她是自己喝住院的,不是我灌的。”
华存义走了,根据他的口供,老李又安排民警,找了当时参加喝酒的人取了四份证实材料,结果事实与华存义讲的基本一致。
至此,经过几天的调查核实,案件已基本清楚。于是,老李给五味村迟主任打电话:“老迟你转告张启良,他姐住院不是华存义灌的,而是她自己喝多导致的。另外,他的行为是报复伤人,要被从重处罚。”
事情顺利地查办,老李心里多了几分踏实,排除华存义这颗“定时炸弹”已成竹在胸。
12月11日上午,陈彬取回了华存义的伤害鉴定一一轻微伤。王威依所长安排,再次传唤张启良,一是向他告知鉴定结果,二是了解他对赔偿的态度。
下午1点,张启良按时到了派出所,上楼见到老李扑通就跪下了,哭丧着脸说:“李所长,迟主任把我姐喝酒的事向我讲明白了,我又找我姐问清楚了,我冤枉了华存义,错打伤了人家,请你高抬贵手,饶我这一回!钱我全赔。现在我听你的,让我怎么的都行,就别让我进去了,求求你了!”老李说:“要看华存义能否谅解你,把鉴定告知书签了吧。”张启良起身诚惶诚恐地在告知书上签了字,之后陈彬告诉他回去听候处理。张启良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离开了派出所。
翌日上午,华存义兴冲冲来了,陈彬把他领进了所长办公室。华存义开门见山:“李所长,张缺筒服了。昨儿个上午,他主动上门找我赔礼道歉,还给了我5000块钱,彻底灭火啦!没有派出所,那‘缺筒’根本不会赔我钱。既然钱给了,我就不追究他法律责任了。谢谢所长!谢谢派出所!我是特意来告诉你们的。”老李笑了,问华存义:“事解决得你满意吗?”华存义频频点头:“满意,十分满意。”“那你两天后来派出所,把调解协议书签了。”老李提醒华存义。华存义欢喜地走了,老李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是没有。
12月15日上午,华存义夹着面锦旗来派出所了,在接见大厅碰见了刘晨,他急忙把锦旗展开,红艳艳的锦旗很漂亮,“村民结仇怨,警察破坚冰”十个烫金大字鲜艳夺目,华存义全部心意都写在这面锦旗上了。
老李走出办公室,代表派出所接了旗,也接受了华存义对翠山派出所的感激。华存义提出与所长合影,做永久的感念。无奈,刘晨只好用手机对准了人和旗。
拍完照,华存义低头不停地搓手,嗫嚅着说:“李所长,如果不是你管了,我这事可能今天也出不了头,还差点干出蠢事。不但张启良他家破人亡,我一家也没个好。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有事得靠你们依法办,别钻牛角尖,以后遇事我要心胸大点,做懂法懂理的人!”
这时,王威调侃道:“华存义,你不说事如果我们管好了,你管我们所长叫爹吗?”华存义一点儿也不抵赖,大声说:“你们都是我爹!”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老李连忙制止了大家的玩笑。
半个月排除了华存义这颗“定时炸弹”,老李如释重负,感到无比轻松和惬意。
窗外,偶尔传来村里孩子们燃放鞭炮的响声,悦耳清脆。翠山乡平静如常,五味村安然无恙,家家准备过年了。
作者简介:
徐宝国,男,20世纪60年代生于抚顺,现从事公安工作。曾在国内报纸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20多万字。现任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抚顺市作家協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