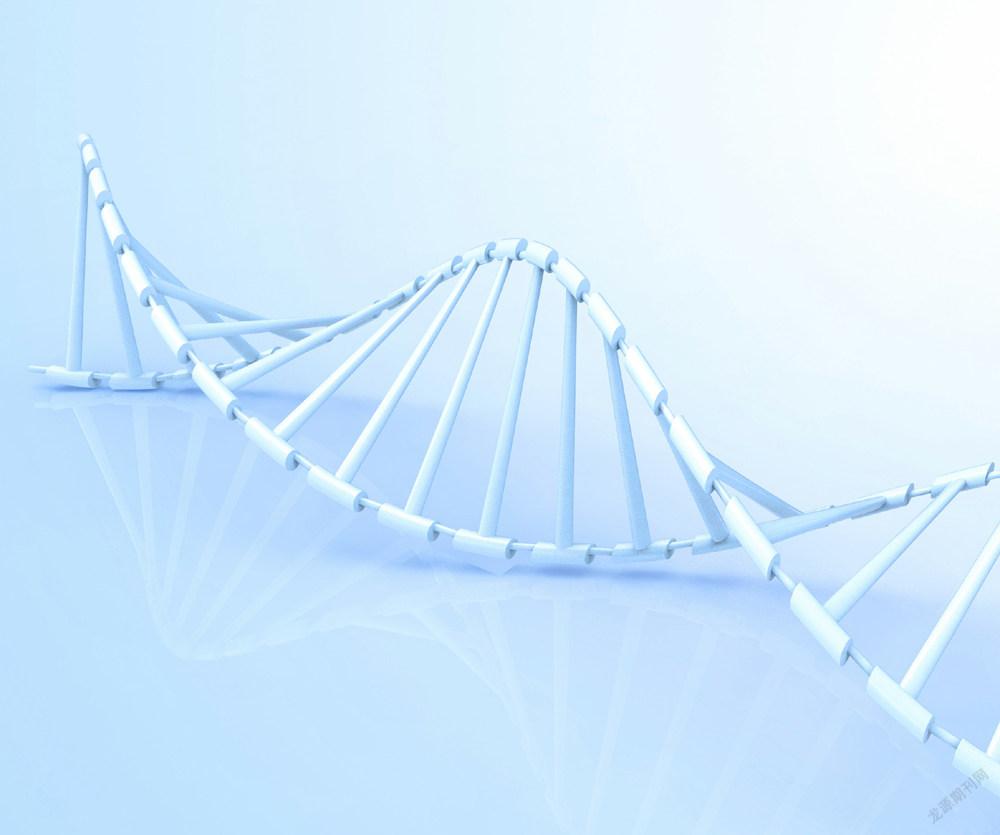细菌
不管是细胞数量,还是拥有的基因数量,寄生在人体表面和内部的细菌都远超人体本身。现在,科学家正在思考:掌控人体的,到底是我们还是那些共生细菌?
生物学家曾认为,人体是一座生理之岛,完全可以自行调控身体内部的运转。我们的身体能分泌消化酶消化食物,合成营养物质维护身体组织和器官;可以感受到自身发出的信号,比如饥与饱;免疫细胞能识别危险的微生物(病原体),向它们发起进攻,同时避免伤害到自身组织。
但在过去十多年中,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并不是一座自给自足的世外小岛。它更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一个庞大的社会。在我们的身体内,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它们寄生在我们的皮肤、生殖器、口腔,特别是肠道等部位。实际上,人体细胞并不是人体内数量最多的细胞,共生细菌的数量是人体细胞的10倍。由微生物细胞和它们所包含的基因组成的细菌群落,不仅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反而对人体有益,能帮助身体进行消化、生长和防御。
小小的细菌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生物学家已经对人体内数量最多的一些细菌,进行了深入研究。最近,他们又开始研究其他细菌。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身体的功能。也让我们更清楚,为什么有些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比如肥胖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提到身体内的微生物,人们通常会想到病菌。事实上,研究人员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只关注那些有害病菌,忽视了那些有益的细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萨基斯·K·马兹曼尼安认为,这源于我们的一些错误认识。“孤芳自赏迷住了我们的眼睛,人类自以为拥有所有保持健康所需的功能,这些有益细菌虽然不属于人体,却相伴我们一生,它们是我们身体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体内就有一个微生物群落,当然,这些细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是在与周围环境接触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己的共生细菌群落的。一般说来,子宫内没有细菌,所以生命之初的胎儿是真正无菌的个体。但是,当新生儿通过产道时,母亲体内的共生细菌,就会转移到婴儿身上,并开始繁殖。随着与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还有床单、毯子、宠物等的接触,婴儿体内的细菌会变得越来越多,到婴幼儿晚期,我们体内已经形成了地球上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
大约5年前,科学家开始研究这种微生物生态系统。当时他们面临一个难题——肠道内的细菌已经习惯了以群居方式、在无氧环境中生存,单个细菌在开阔的培养皿中根本无法存活。现在,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研究人员不再研究细菌个体,而是改成研究细菌的基因——即链状DNA和RNA的结构。由于DNA和RNA可在常规的有氧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因此科学家可以从人体中提取细菌样本,再从样本中提取遗传物质进行实验分析。
每种共生细菌都有自己的“身份证”——16S核糖体RNA基因,在每种细菌中,这种基因都不一样。该基因可以编码核糖体中特定的RNA分子(核糖体是细胞中负责合成蛋白质的机器)。科学家试图通过确定这类基因的序列,打造一本“人体细菌手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体内有哪些细菌,和别人体内的细菌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要做的,是分析细菌群落中的其他基因,搞清楚哪些细菌在人体中比较活跃、有什么功能。这项工作也非常复杂,细菌不仅数量巨大,在提取过程中它们的基因还会混在一起。鉴定一种基因属于哪个菌种很难。相对而言,鉴定一种细菌基因是否活跃就比较简单了。幸运的是,在最近十年中,我们有了更强有力的计算机和超快的基因测序仪,只要不怕麻烦,完全可以完成过去无法完成的细菌分选和分析工作。
在美国和欧洲,各有一组科学家利用这种新技术,对人体内的细菌基因进行统计。2010年初,欧洲小组发表了他们对人体消化系统中细菌基因数目的统计结果——330万个基因(来自1000多个菌种),差不多是人类基因数量的150倍(人类有2万~2.5万个基因)。
在研究人体内细菌群落的过程中,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比如,你几乎找不到细菌群落组成完全一样的两个人,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人类基因组计划已证实:所有人的DNA99.9%都是相同的。看起来,细菌基因的变异对人类个体的命运、健康、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胜于我们自己的基因。不同人的体内,细菌种类和数量虽然大不相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体内的、发挥关键作用的有益细菌基因其实都差不多,尽管这些基因来源于不同的菌种。另外,即使是最有益的细菌,如果它们在不恰当的地方大量滋生的话,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如,细菌跑到血液中,就会导致败血症;进入腹部器官之间的组织网络中,就会导致腹膜炎。
几十年前,通过对动物肠道消化作用和合成维生素的研究,人们第一次发现,细菌可以造福人类。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维生素B12可以帮助人体细胞产生能量、合成DNA、制造脂肪酸,但形成维生素B12的酶必须依赖细菌才能生成。科学家在许多年前就知道,肠道内的细菌可以分解食物中某些难以消化和吸收的成分,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人体的共生细菌群落中,还有两种细菌能影响人的消化和食欲。
多形拟杆菌的名字可能来源于希腊姐妹会或兄弟会,它是一种最优秀的碳水化合物降解细菌,能够将许多植物类食品中的大分子碳水化合物降解为葡萄糖和其他易消化的小分子糖类。人体中没有基因可以合成降解碳水化合物的酶,而多形拟杆菌的基因,能合成260多种消化植物成分的酶,从而帮助人体高效地从橙子、苹果、土豆、小麦胚芽等食物中提取营养素。
通过对小鼠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多形拟杆菌可与宿主发生相互作用,向宿主提供营养物质。研究人员先将小鼠饲养于一种完全无菌的环境中(保證它们不携带任何细菌),然后再让小鼠与多形拟杆菌接触。200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多形拟杆菌通过食用多糖分子,即结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而存活。多形拟杆菌会让这些营养物质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也就是它们的排泄物),为小鼠提供养分。通过这种方式,细菌从那些本来无法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中得到了热量,比如燕麦片中的膳食纤维。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要获得相同的体重,那些没有携带多形拟杆菌的小鼠,需要比携带了这种细菌的小鼠多吃30%的食物。
对共生细菌的研究还使一种病原菌——幽门螺旋杆菌重获好名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医师巴里·马歇尔和罗宾·瓦伦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在胃内酸性环境中旺盛生存的少数病菌之一)是引发胃溃疡的病原菌。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持续使用非类固醇消炎药(NSAID,阿司匹林就是这类药物)是导致胃溃疡的常见病因,所以细菌引发胃溃疡的新发现,很快就成了当时引人注目的新闻。从那以后,应用抗生素治疗胃溃疡就成了一种标准的临床治疗方法。很快,由幽门螺旋杆菌引发的溃疡发病率就下降了50%多。
但是,纽约大学的内科和微生物学教授马丁·布雷泽认为,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布雷泽教授研究幽门螺旋杆菌已经25年了。“与别人一样,刚开始我也认为幽门螺旋杆菌只是一种病原体,但几年之后,我认识到,它实际上是一种与人体共生的有益细菌。”1998年,布雷泽和同事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对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它可以调节胃酸水平,创造既适合它生存也适合宿主(人体)的环境。比如,当胃酸分泌过多时,幽门螺旋杆菌会大量繁殖,同时细菌内的cagA基因开始产生一种蛋白质,使胃部减少胃酸的分泌。不过,对于易感人群来说,cagA有一种不好的副作用,会加重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溃疡。
十年之后,布雷泽发表的另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幽门螺旋杆菌不仅能够调节胃酸的分泌,还有其他作用。科学家早已知道,胃可以产生两种与食欲相关的激素:一种是告诉大脑人体需要进食的饥饿激素,另外一种是提示胃已经饱满,不需要再吃的瘦素。“早晨醒来时,你会感到饥饿,这是为你的饥饿激素水平高的原因,”布雷泽说,“这种激素告诉你需要进食。用过早餐后,饥饿激素水平就会下降。”科学家将这种生理过程称为(饥饿激素的)“餐后减少”。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布雷泽和同事比较了两组受试者饭前饭后的饥饿激素水平:一组携带了幽门螺旋杆菌,另一组则没有。结果很清楚:携带幽门螺旋杆菌的人,饭后饥饿激素水平会降低;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则没有这种能力,这意味着,幽门螺旋杆菌可以调节饥饿激素水平,即食欲。遗憾的是,其中的具体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一项对92名退伍军人的调研显示,使用抗生素致使幽门螺旋杆菌消亡的人,比那些未受感染、同等条件的人,体重增加得更快。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饥饿激素水平不能适时下降,导致饥饿感延长,进食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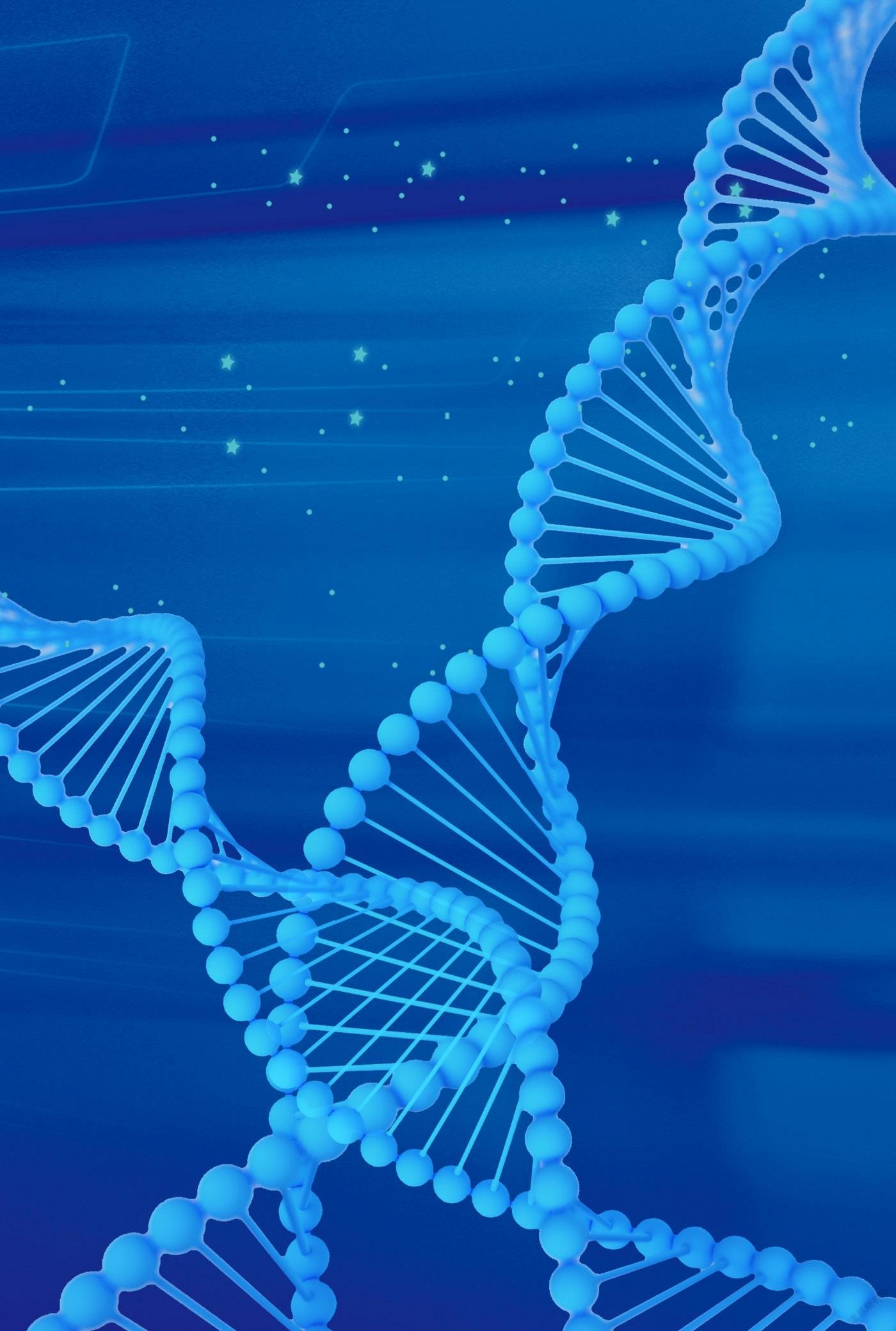
80%的老一辈美国人,体内都携带有耐酸的幽门螺旋杆菌。而现在,只有不到6%的美国儿童,在检测幽门螺旋杆菌时,结果为阳性。布雷泽说:“这一代儿童是在没有幽门螺旋杆菌调控饥饿激素的情况下长大的。”而且,由于这些儿童经常使用高剂量的抗生素,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大多数美国医生都用抗生素治疗儿童中耳炎。布雷泽猜想,可能正是由于青少年大量使用抗生素,改变了他们肠内细菌的组成,才导致儿童肥胖症日益增多。他认为,在细菌群落中,不同的细菌会分别对人体脂肪、肌肉和骨骼干细胞产生影响。而让青少年使用抗生素,会消灭某些特定的细菌,干扰正常的生理信号传导,最终导致脂肪细胞过剩。
随着幽门螺旋杆菌和其他细菌的不断消亡,高热量食品越来越多,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人体内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肥胖症流行呢?对此,布雷泽说:“我们还不知道微生物群落对肥胖症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我敢打赌细菌对人类的影响决不是微不足道的。”
布雷泽认为,广泛使用抗生素并不是破坏人体细菌群落的唯一祸首。从上世纪开始,人类社会生态学上的一些改变对此也有影响。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剖宫产进行分娩的孕妇数量急剧增加,使一些重要的菌株无法通过母亲的产道传递给婴儿(在美国,超过30%的新生儿是通过剖宫产分娩的;而在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城市女性在生育时都会选择剖宫产)。还有,现代家庭规模都很小,兄弟姐妹不多,这意味着细菌传递给小孩子的途径也减少了。另外,饮用水净化工程虽然拯救了数百万因饮用水不卫生而染病的人,但也减少了我们与那些共生细菌接触的机会。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一个日益萎缩的微生物世界中出生和长大。
在研究多形拟杆菌和幽门螺旋杆菌的過程中,即使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会引出复杂的答案。比如,这些细菌在人体内做什么?如果更进一步探讨,人体是如何作用于这些外来细胞的?那问题就更错综复杂了。我们都知道,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区分自己的细胞(自我)和拥有不同基因的外部细胞(异物),并自动排斥后者。这样看来,我们身体的生物防御系统,本应该向数量巨大的共生细菌主动开战才对。为什么肠道内的免疫细胞没有这样做呢?这一直是免疫学领域一个悬而未决的谜。
科学家发现,一些线索指向一种非常新颖的观点:经过20万年的进化,人体内的细菌群落和免疫细胞已经达成了和平共处,也就是一种平衡。在过去的亿万年中,经过不断磨合,免疫系统已经进化得既不会具有过强的攻击性(进攻自己人),也不过于放松(放过敌人)。例如,T细胞会在识别和反击入侵人体的病原体时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炎症反应(肿胀、变红、发热等)。但是,人体在产生大量T细胞后,又会很快产生调控性T细胞,抵消促炎T细胞产生的效应,缓解炎症。
正常情况下,调控性T细胞会在促炎T细胞肆虐之前迅速发挥作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兹曼尼安称,“问题是,这些促炎T细胞抵御外敌时采取的措施,比如释放毒性化合物,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组织。”幸运的是,调控性T细胞会产生一种蛋白质来抑制促炎T细胞。最终使得炎症反应减弱,免疫系统不再攻击人体自己的细胞和组织。一旦好斗的促炎T细胞与平和的调控性T细胞之间达成平衡,人体就会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
多年来,研究人员都认为这种自我平衡的系统,完全是由免疫系统生成的。但是,马兹曼尼安和同事发现,一个免疫系统是否健康、成熟,取决于有益细菌是否一直与其发生作用。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细菌可以使我们的免疫系统运转得更好,这可能是一个颠覆传统的观念,”马兹曼尼安说,“不过,事实越来越清楚:免疫系统后面的驱动力,正是那些共生细菌。”
马兹曼尼安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大多数人(约70%~80%)体内都有一种细菌——脆弱拟杆菌。这种细菌可以释放消炎物质,帮助免疫系统保持平衡。他们以免疫系统有缺陷的无菌小鼠为研究对象,这种小鼠的调控性T细胞在功能上存在障碍。当研究人员向小鼠植入脆弱拟杆菌后,这种啮齿类动物的免疫系统可以恢复正常,促炎T细胞和抗炎T细胞之间重回平衡状态。
这其中的机制是什么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对脆弱拟杆菌表面伸展出的几种糖分子进行了研究,发现起作用的就是这些糖分子。2005年,马兹曼尼安和同事证明:这些分子中,有一种称为多糖A的分子,可以促进免疫系统的发育成熟。不久后,他们又发现,多糖A可以给免疫系统发信号,使之制造更多的调控性T细胞,后者再告诉促炎T细胞不要攻击脆弱拟杆菌。相反,那些缺乏多糖A的脆弱拟杆菌在肠内黏膜层中则无法生存,因为免疫细胞会把这种细菌当作病原体攻击。
2011年,马兹曼尼安和同事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详细描述了上述效应中的分子反应,第一次阐明了微生物与哺乳动物之间的共生现象。“脆弱拟杆菌对人体非常有益,帮助我们弥补了人体本身DNA的不足,”马兹曼尼安说,“很多时候,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号施令,进行操纵。”但是,与许多病原体不同的是,这种操纵并不会抑制或减弱我们免疫系统的性能,相反,还有助于免疫系统发挥功能。我们体内的其他细菌,也可能对免疫系统有相似的作用。他提醒说:“这只是第一个例子。毫无疑问,还会有更多的例子出现。”
遗憾的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脆弱拟杆菌与幽门螺旋杆菌一样,正面临灭绝。“所谓的社会发展,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完全改变了我们与微生物世界之间的联系,”马兹曼尼安说,“在努力使自己远离病原体的同时,我们也断绝了自己与有益微生物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我们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脆弱拟杆菌的例子中,代价可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如果没有多糖A对免疫系统发送信号,令其产生更多的调控性T细胞,那些好斗的T细胞就会攻击它们所撞见的任何东西,包括人体自己的组织。马兹曼尼安认为,近年来免疫系统疾病,比如克罗恩氏病、I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发病率提高了七八倍,就与有益细菌的减少有关。“导致这些疾病的,既有自身原因,又有外界原因,”马兹曼尼安说,“我相信外界原因就是共生细菌群落,它们的改变正在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微生物群落发生改变,脆弱拟杆菌和其他抗炎微生物减少,进而导致调控性T细胞发育不良。对那些遗傳学上的易感人群来说,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疾病。
当然,以上描绘的只是一种可能。现阶段的研究只能说明,共生细菌数量的减少与免疫疾病发病率提高之间存在关联。但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就很难分清了。以肥胖症为例:一方面,人体内固有的细菌数量减少,导致了自身免疫疾病和肥胖症的发病率直线上升;另一方面,这些疾病也使体内环境不再适宜共生微生物生存。马兹曼尼安认为,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肠道内细菌群落的改变导致了免疫性疾病发病率提高。但是,“这还有待于科学家进一步验证,进行相关研究,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阐明隐藏在其后的机制,”马兹曼尼安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工作。”
(编辑/高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