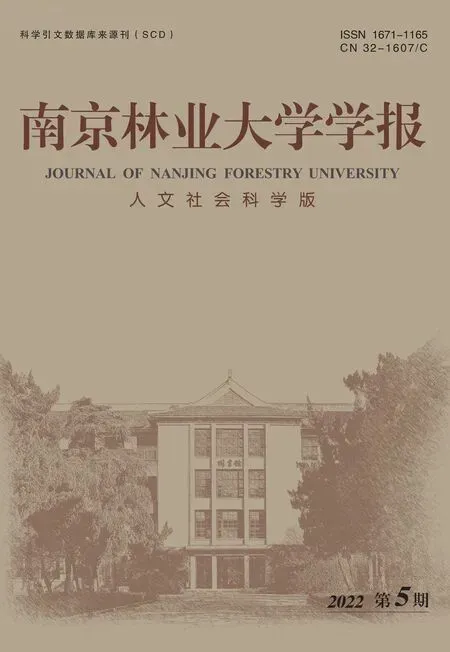当代美国生态戏剧:回顾与思考*
袁家丽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作为一个戏剧议题在当代美国戏剧中早已有之,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但真正把“生态戏剧”①戏剧领域有几个与生态相关的术语,ecotheater/ecodrama 是常见的用法,前者是“生态剧场”,侧重剧场实践,后者是“生态戏剧”,侧重戏剧文本;green theater 翻译成“绿色剧场”,泛指与社会、自然环境危机相关的剧场艺术;sustainable theater是“可持续剧场”,更多指的是剧场物质材料、剧场管理的可持续性。为了叙述方便,本文统一用“生态戏剧”一词,包含剧场实践和戏剧文本两方面。作为一个戏剧类型来界定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及生态批评领域的纵深演进分不开的。纵观整体,美国生态戏剧发展同时并行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对生态戏剧的理论探索、批评研究;另一条是生态戏剧的文本创作、剧场实践。批评研究为剧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剧场实践为批评研究提供案例支持,两者互为充实、相得益彰。本文通过简要梳理近50 年来美国生态戏剧理论探索的重要节点,阐明生态戏剧概念的演进,继而从主题内容和剧场形态两方面分析美国生态戏剧的剧场实践及观演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引发对生态戏剧当代价值的思考。
一、美国生态戏剧的理论探索
美国生态戏剧的理论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生态戏剧”概念的提出阶段。一般认为“生态戏剧”(ecotheater)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美国街头戏剧表演艺术家玛雅特·李(Maryat Lee)。但实际上,李的EcoTheater 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戏剧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EcoTheater是她在1975 年创立并执导的一个地方实验剧场的名字。该剧场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辛顿镇,是她将城市街头戏剧搬至农村郊区的一种尝试,本质上是一种反主流剧场。她在1983 年的一篇文章《唯愿一事》(“To Will One Thing”)中阐明了EcoTheater 的确切涵义。她开宗明义地写道:“如果要定义EcoTheater,我首先会说,eco 来自希腊语,是home(家)的意思,而theater也是来自希腊语,意为‘a place for seeing’(一个可供观看的地方)。”[1]47她还强调,“seeing 不同于looking,它是一种可以富有想象性地揭开表面的能力,一种我们所渴望的让不可见变得可见的能力”[1]47。因此,“在这种意义上,EcoTheater 是一个能够看见(seeing)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的地方。它是一面镜子,一扇窗户,有时又是一扇门”[1]47。从玛雅特·李的定义中可以看出,EcoTheater当初使用时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与生态危机、环境保护等议题相关的戏剧,而是借鉴了ecology的词源学意义,即“研究居住地或栖息地的学问”。本质上,李的EcoTheater是一种旨在倡导走进乡村田野、就地取材、用素人演员来表演的“乡土剧场”(indigenous theatre)。这种剧场创作理念作为一种先锋实验剧场,突破传统戏剧镜框式的舞台布景和表演,将演出环境设置在开放的空间中,打破观众和舞台的疆界,拉近观众和演员的距离,从而创造出一种更为互动的新型的观演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李的EcoTheater在创作理念和表演形态上更接近美国戏剧理论家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所提出的“环境戏剧”(Environmental Theater)的概念。“环境戏剧”本质上并非是关于环境的戏剧,而是一种突破传统舞台表演形式和观演关系的实验剧场,主要是对戏剧表演空间的新探索。两者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革新美国七八十年代的传统剧场。尽管李的EcoTheater 与生态环境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它涉及对戏剧艺术的本质和核心意义的探索,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戏剧的到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构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所创立的EcoTheater 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生态戏剧概念的发端。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探索,这是生态戏剧的分水岭,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戏剧》(Theatre)杂志在1994 年发表的“戏剧与生态”(“Theatre and Ecology”)专刊,它预示着生态戏剧概念逐步走向理论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该刊特邀嘉宾美国生态戏剧领军人物巫娜·乔都睿(Una Chaudhuri)所写的文章——《那湖里必多鱼:走向生态戏剧》(“‘There Must Be a Lot of Fish in That Lake’:Toward an Ecological Theater”)。在该文中,乔都睿首先尖锐地指出,美国戏剧长期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为他们将自然作为人类活动的场景或背景,造成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割裂。她继而提出要抵制将自然作为隐喻来使用,承认自然界“是独立的存在,有巨大的力量”[2]30。她最后呼吁戏剧应承担起揭示这种力量的责任。乔都睿的这篇文章指明美国生态戏剧存在的问题及愿景,定下了它的基调,并“打开了一个话语的空间,提供了一个从生态视角回顾戏剧史、戏剧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立场”[3]xiii。可以说,“戏剧与生态”专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生态戏剧正式进入理论探索阶段。
然而,据美国生态戏剧领域另一位领军人物特蕾莎·梅(Theresa May)后来的观察,这期专刊的发表虽掷地有声,但在之后十年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究其原因是“部分在于传统”[4]84。梅指出,美国戏剧领域之所以没有出现像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这样专注于自然写作的诗人,是因为没有亨利·大卫·梭罗(H.D.Thoreau)这样的前辈。[4]84生态戏剧在这个时期是一个理论探索和实践培育并行的阶段,其内涵特征还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此时戏剧表演的主战场仍在地方小剧团和民间表演机构,原创生态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正如《戏剧》杂志主编艾瑞卡·芒克(Erika Munk)在1994 年专刊的发刊词中所言:“(生态戏剧)是一片历史有待重新改写、风格有待重新讨论、语境有待重新构想的广阔领域。”[5]在一切都“呼唤重新阐释”的20世纪末,生态戏剧的变革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是生态戏剧理论朝纵深发展的阶段。针对生态戏剧在20世纪的美国主流剧场所遭受的冷遇,特蕾莎·梅于2005年提出两个策略:一是“将生态批评视角运用于经典戏剧作品的评论中”,二是“认可生态戏剧的原创作品”[4]85。梅的策略在两方面得到了实践:一是戏剧领域涌现出大量与生态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理论著作,讨论戏剧与环境、动物表演、气候变化等议题,深化并细化了生态戏剧的理论内涵及主题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乔都睿及其合作者出版的有关跨物种表演、气候变化的论著,重点分析舞台上跨物种表演的伦理意义以及围绕气候变化主题的剧场实践案例;二是出现了众多以绿色、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戏剧团体、协会、联盟,合力挖掘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戏剧项目,培养新一代的生态剧作家和导演,并建立可持续发展剧院,比如致力于环境人文和艺术研究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由百老汇45 家剧院发起、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绿色剧场为目标的“百老汇绿色联盟”(BGA:Broadway Green Alliance),由导演兼剧作家尚塔尔·比洛多(Chantel Bilodeau)发起的一系列“艺术与气候项目”(Arts&Climate Initiatives),由导演伊恩·盖瑞特(Ian Garrett)和米兰达·莱特(Miranda Wright)联合创办的旨在为艺术文化领域提供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可持续发展艺术中心”(CSPA:The Centre for the Sustainable Practice in the Arts)以及致力于为儿童提供有关科学、自然和环境类教育戏剧的“常青树戏剧社团”(Evergreen Theatre Society)等。这些致力于生态戏剧领域的协会、联盟、社团大多是国际组织,呈现了生态戏剧领域多维发展、跨国合作的新特征。
在众多项目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比洛多牵头组织的“艺术与气候项目”(Arts&Climate Initiatives)。该项目致力于通过戏剧创作、资源分享、学术研讨等方式让受众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动物所造成的影响,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保护地球生态。在该项目的倡导下,比洛多带领团队筹划创作八部围绕北极沿海八国气候变化的组剧——《北极圈》(The Arctic Cycle),目前已完成三部:《希拉》(Sila[Canada],2014)和《前进》(Forward[Norway],2018)、《不再有哈维们》(No More Harveys[USA],2022)。与此同时,比洛多还创办了“艺术家与气候变化”(Artists and Climate Change)网站,分享在艺术领域致力于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国内国际组织、大学学位项目和课程信息;她还发起了两年一度的“气候变化剧场行动计划”(Climate Change Theater Action),专注于阅读、上演有关气候变化的短剧,并将他们结集出版,目前已有两部戏剧集——《照亮前方:气候危机短篇戏剧集》(Lighting the Way:An Anthology of Short Plays About the Climate Crisis,2020)和《希望在何处?——气候变化短篇戏剧集》(Where Is The Hope?An Anthology of Short Climate Change Plays,待出版)。无疑,比洛多及其团队的项目为全球尤其是北极圈的气候变化危机找到了艺术表达的出口,让更多的戏剧观众参与到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
美国生态戏剧的理论探索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分散到聚焦、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过程。最近,特蕾莎·梅在新著《舞台上的地球问题:美国剧场的生态与环境》(Earth Matters on Stage: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n Theater,2021)里又提出了“生态剧构法”(ecodramaturgy)的新理念,即“(从剧构法层面)在北美剧场内渗入环境保护意识”[3]xv。这一理念预示着生态戏剧不仅要在主题内容上彰显生态意识,而且要在戏剧创作方法以及表演形式中渗透生态意识,将其扩展至剧场实践之中。事实上,随着生态戏剧理论发展的深入,美国生态戏剧的剧场实践也逐步完善,并进一步夯实生态戏剧理论探索的成果。
二、美国生态戏剧的剧场实践
美国生态戏剧的剧场实践同样历经演变,可以从主题内容和剧场形态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主题内容方面,美国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戏剧主要把自然当作背景或隐喻来设置,比如,上文中提到的玛雅特·李的EcoTheater 实验剧场、爱德华·阿尔比普利策获奖戏剧《海景》(Seascape,1975),都以自然为背景探讨人的问题,这时候的生态主题还处于戏剧创作和舞台表演的边缘位置。到了90年代,生态议题开始逐渐聚焦于酸雨、温室效应、森林砍伐、杀虫剂滥用、物种濒危、有毒物质等主题,主要是回应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所控诉的化学农药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物种灭绝等问题以及对环境保护运动所提出的各类诉求的回应。这一时期生态戏剧实践的主战场是唐宁·克莱斯(Downing Cless)所说的“草根剧场”或“民间剧场”(grassroots theater)[6]。另有一部剧作值得一提,即罗伯特·申坎(Robert Schenkkan)获得普利策奖的戏剧《肯塔基组剧》(The Kentucky Cycle,1991),这部戏剧由9个系列短剧组成,展现了位于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坎伯兰高原上三个家族200年间(1775—1975)的争斗与纠葛。这部戏剧以史诗般的恢弘书写了美国家庭的变迁史以及美国社会的发展史,揭示了美国边疆拓荒行为对资源的滥用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创生态戏剧,为生态戏剧挤入美国主流剧场撬开了一扇门。
到了21 世纪,美国的生态戏剧主要围绕人为的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可持续发展、社区与文化的多样性、人类与动植物的关系、人类与土地、人类与非人类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对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从主题内容上可以看出生态议题已经从舞台边缘走向舞台中央,从背景隐喻转向主旨探讨,并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从舞台实践上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剧作的舞台改编,比如,易卜生的《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1882)、契诃夫的《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1903)等,分别从生态批评视角重点呈现剧作中的水源污染、植被破坏等环境议题,探讨百年前的剧作家超前的生态意识和敏锐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是原创生态戏剧,它主要依托戏剧节和戏剧项目来推动,比如享誉北美的EMOS 生态戏剧节(Earth Matters on Stage:Ecodrama Playwrights’Festival),它可以说是美国原创生态戏剧的摇篮。
EMOS生态戏剧节由特蕾莎·梅和拉里·弗里德(Larry Fried)于2004年创立,大约每三年举办一次,由各大学承办,邀请美国和加拿大的剧作家、导演和剧评人评选出优秀的生态戏剧剧目,并安排一、二等奖获奖作品进行工作坊式的剧场演出(workshop productions)。该戏剧节至今已举办过五届,获一等奖的作品有罗伯·库恩(Rob Koon)的《奥丁的马》(Odin's Horse,2004)、E.M.刘易斯(E.M.Lewis)的《灭绝之歌》(Song of Extinction,2009)、尚塔尔·比洛多(Chantal Bilodeau)的《希拉》(Sila,2012)、M.E.H.刘易斯和安妮塔·钱德瓦尼(M.E.H.Lewis &Anita Chandwaney)的《渴》(Thirst,2015)、克里斯特尔·斯基尔曼(Crystal Skillman)的《瑞恩和佐伊拯救世界》(Rain and Zoe Save the World,2018)。最近一届原定于2021 年在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举办,但因新冠疫情推迟到了2022 年11 月,不过获奖作品目前已在该网站上揭晓。320 部参赛作品中有6部获奖,其中,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作品分别是杰西卡·黄(Jessica Huang)的《第二次大死亡来临之前的传递》(Transmissions in Advance of the Second Great Dying)和凯瑟琳·格温(Kathrine Gwynn)的《美国动物》(An American Animal)。前者是一部史诗级的预言剧,通过讲述2045年地球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交互命运来展现全球变暖问题,而后者则是一部关于孤独、生存、恐惧和联结的戏剧,讲述美国黄石公园内外人类、狼群、鹿角兔之间捕杀、生存与关联的故事。这两部获奖作品都是通过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动、纠缠来展现物种生存危机以及地球命运共同体内部各种生命之间的深度联结。
EMOS戏剧节之所以很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创立者特蕾莎·梅在美国生态戏剧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近20年,是该领域的倡导者和研究专家。该戏剧节的选题指南可以算是对戏剧领域里生态议题的范畴界定,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生态戏剧的风向标。EMOS 网站首页上还声明了办节宗旨和目的:“戏剧和表演艺术必须回应环境危机。EMOS呼唤和培育新的戏剧作品和演出,寄望他们帮助我们在一个不只有人类的世界里重新想像人类的位置。”[7]特蕾莎·梅本人也在网站首页贴出了自己对生态戏剧节参选作品的期待:“EMOS寻找这样的戏剧作品:能够活跃、转变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经验,激励我们更仔细地聆听、吸收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有关生态社区的理念。”[7]这些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戏剧宗旨和内涵的粗略界定,为生态戏剧的发展定下了基调。此外,该戏剧节在评审参赛作品的同时,还举办生态戏剧学术研讨会,邀请北美知名戏剧专家做主旨发言,并出版会议论文集。目前第一部研讨会论文集《表演与生态读本》(Readings in Performance and Ecology)已于2012 年出版,由雯迪·艾伦斯(Wendy Arons)和特蕾莎·梅共同主编。该论文集涉及生态批评、生态表演、动物表演、生态激进主义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案例,“是第一部在物质层面(而不是隐喻层面)探讨表演和生态相互关联的著作”[8]。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使EMOS生态戏剧节既富含舞台实践探索,亦饱有学术理论创新。该戏剧节业已成为推进生态戏剧领域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剧场形态上,美国生态戏剧是与美国当代剧场的实验革新同步演进的。21世纪之前的剧场表演多以镜框式舞台表演为主,采用拟人化的表演方式来展现动植物的生存困境及生态环境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展现濒危物种的戏剧都是演员戴上动物面具从而将动物拟人化来呈现物种问题。到了21世纪,表演形式逐渐从剧场镜框式舞台表演向“特定场所”(site⁃specific)的沉浸式表演转变。这种“特定场所”的沉浸式表演选取真实的或营造仿真的生态场景,观众可置身其中,切身感受、回应具体的情境,并与演员产生互动,这就导致了观演关系的变化。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变为肉身参与,打破与舞台的疆界,拉近观众和演员的距离以及观众与生态情境的距离,从而更好地实现生态戏剧介入社会公共议题的功能。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USULB)戏剧系师生于2008 年创作的一个生态戏剧作品——《绿色片段》(Green Piece)。该剧由三个短剧组成,主要探讨人与地球、森林、树木之间的关系,以回应常年肆虐加州的山火。它传达的寓意是:只有与地球深度接触,才能得到地球的滋养;随意砍伐,必然会遭到惩罚。这部组剧有两个特点:一是将演出舞台搭建在剧场之外,营造与主题相关的表演空间;二是让观众走进这个演出空间,与演员随时互动,也就是让观众肉身参与到特定的生态场景中,从而切身感受戏剧演出所要阐发的生态、环境议题。这种剧场形态,包括表演方式和观演关系的变化虽并非21 世纪所特有,也并非生态戏剧所特有,但针对生态议题导向的戏剧,这种剧场实践特别有意义,因为观众才是戏剧演出的目的所在。观众的参与,包括观看、倾听、互动才使得戏剧演出得以发生,并产生意义。
美国生态戏剧在主题内容和剧场形态上的演变和革新一方面彰显、回应了时代的更迭和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美国戏剧从业人员对生态、环境议题的敏感和执着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一代代戏剧从业人员逐渐意识到他们有责任用戏剧这一艺术表演形式来唤醒公众觉知,吸引他们参与到具体的情境中,以发挥戏剧介入社会公共议题的功能,从而实现它的社会价值。
三、美国生态戏剧的当代价值
那么,生态戏剧在当代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问生态戏剧可以改变世界吗?其实是在问戏剧可以改变世界吗?或者说,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吗?如果可以,何为?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气候变化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有国际、国内社会各个层级的政府机构共同协商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及措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例如,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CCC)就是从国际层面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而从微观层面上看,这些政策和方案的践行和实施说到底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而人的意识和行动是有个体差异的。如何让无数个个体能够更新观念、统一认识、有效行动,就需要文学、艺术发挥其作用了。美国生态戏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演进、发展可以说是积极探索、回应当今全球重要且紧急的生态问题的结果。除了学术价值外,它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生态戏剧作为“相遇”的戏剧。波兰戏剧导演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剧本对戏剧导演而言,其价值在哪里?以及戏剧在文学方面,它的任务是什么?格洛托夫斯基回答说,“戏剧的核心是一场相遇”[9]56,不仅是演员和自我的相遇,也是导演与演员以及演员与观众的相遇,同时也是个体与社区、个体与世界的相遇。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戏剧是戏剧与生态的相遇,同时也是演员与生态戏剧文本的相遇、观众与演员以及与舞台表演的相遇,进而与当今全球紧急且重要的生态议题的相遇。有了这场“相遇”,才催生出表演形式和观演关系的变化,才能引发观众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进而才有文学、艺术介入社会现实的可能。换句话说,生态戏剧作为一场“相遇”的戏剧,为我们关注、思考以至介入生态、环境等公共议题提供了场域和契机,让无数个个体直面当下,放眼世界和未来,反思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地球命运共同体中的位置和作用,进而作出恰当、有效的回应。美国生态戏剧在21 世纪戏剧舞台上的持续探索和蓬勃发展让众多热爱戏剧的观众接触、了解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促使更多的戏剧观众和戏剧团体参与到了解、宣传和保护地球的行动中。
二是,生态戏剧作为“事件”的戏剧。德国戏剧家艾瑞卡·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 在《表演的转变性力量:一种新美学》(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Performance: A New Aesthetics,2008)中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称为“反馈圈”(feedback loop),意即观众不是独立于舞台表演之外,而是蕴含其中,与演员同时置于反馈圈的两端,两者之间的互动共同促成了戏剧演出的发生。[10]163李希特进一步认为,“反馈圈”不仅促成了戏剧演出,还具有“自生性”,是“自生系统”(autopoiesis)。她借系统论中有关生命系统自我生产或繁殖的本能来强调“反馈圈”的“自我指涉性”和“衍生性”,指出戏剧演出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过程”[10]39。这表明,戏剧演出不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导演、剧作家、演员、观众、剧评人共同参与、互相作用的结果;戏剧表演也不再是静止的情景再现,而是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生成过程使戏剧具有了事件性特征,即强调演出的生成性、互动性、行动力和效果。[11]这也意味着观众的参与和互动至关重要,观众不再是坐在观众席上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戏剧演出必要的组成部分。
后疫情时代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观演方式扩大了戏剧演出的受众,畅通了观众与演员的交流、互动的渠道,增强了戏剧的事件性特征。尤其是依托戏剧节开展的生态戏剧更是一场“戏剧事件”,因为它使戏剧重回到它的诞生之所,在节日庆典中展现戏剧的“原初意义”,更能体现戏剧的本质特征。[10]161当代戏剧节的筹备、评选,获奖作品的展演,对作品及其演出的研讨,论文集的出版等,都使生态戏剧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生成过程,评选及演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作品创作的终止,它只是无数链条中的一环,其后续的效应会随着受众的参与而逐渐扩散开来。
格洛托夫斯基认为,说到底,“剧场表演就是由人类的反应、冲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促发的结果”[9]58。生态戏剧作为“相遇”与“事件”的戏剧,为人与生态情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交流、互动提供了场域,促成了戏剧表演的发生,而剧场形态和观演关系的转变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使之参与到舞台表演中,戏剧演出不再是封闭的情景再现,而是一个开放、动态、生成的戏剧事件,进而对参与者产生影响,实现戏剧的社会功能。
四、结语
美国生态戏剧历经50 多年的发展,在理论探索和舞台实践上已渐趋成熟,并产生了一定的价值、意义。但要使生态戏剧确实发挥其介入生态议题的社会功能,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因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问题,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是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伦理责任的问题。如同巫娜·乔都睿所说的那样,“生态危机根本上是一场价值危机,生态的决胜需要我们重估价值”[2]25。也就是需要我们从知识、思想、意识层面改变我们的认知,更新我们的观念,承担起我们在地球命运共同体中应负的责任。生态戏剧从再现性到事件性的转变意味着观众的参与,包括观看、倾听、回应都是一种责任,观众有责任和艺术家一起努力让戏剧发生,进而在知识、思想和意识层面对观众产生转变性的力量。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优势,用戏剧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探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书写“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是中国戏剧从业人员和戏剧观众需要共同参与、探讨和实践的新课题。美国生态戏剧的纵深发展会给中国戏剧界在生态领域的探索带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