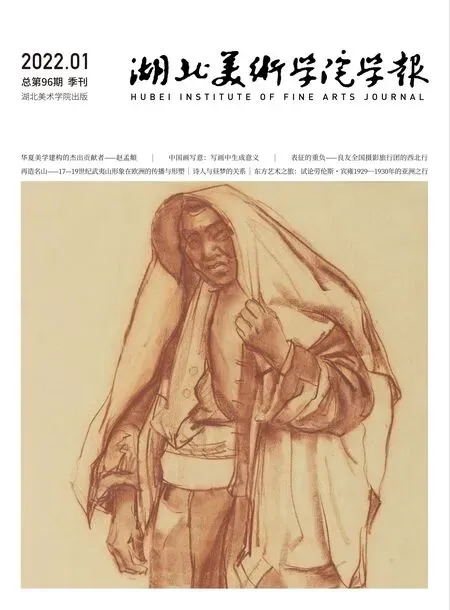试论清中期的写生理论与写实性绘画
王怀志 | 中国传媒大学
一、“写生”之概念与清中期写生理论出现的背景
中国绘画的“写生”由来已久。《左传》中“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的记载,是说将各地奇异的事物描绘出来,再将其形象铸造在礼器之上,被认为是古代对写生行为最早的记载。南朝时宗炳提出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姚最提出“心师造化”,唐代张璪进一步提出的“外师造化”等观念都包含了写生在内的绘画创作规律,即从客观事物中汲取创作原料,通过画家自身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并较为忠实地再现出来。虽然古人向自然造化学习的写生行为贯彻绘画史,但画学文献中出现“写生”概念的时代却较晚。唐彦悰有“受业阎家,写生殆庶”的说法,虽然唐人已有用到“写生”一词,但其含义和范围并不明确。“写生”一词频繁出现在宋人文献中,被用来指代花鸟画的一种画法类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讨论了花鸟画家黄荃与徐熙:“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又说“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他将黄荃一派的画法称之为写生,区别于徐熙一派的没骨画法。根据沈括的描述,这二者无论是在表现形态和表现技法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可见“写生”是一种细笔轻染敷色的画法类型,与“直以彩色图之”等其他画法类型相区别。宋刘道醇:“陶裔之写生,赵昌之设色”“文惠精于写生, 牛戬妙于破毛”等说法,无不着意于一种花鸟画之画法类型。随着时代发展,写生的指代范围也在扩大。元人庄肃《画继补遗》中记载赵孟坚“工画水墨兰蕙梅竹水仙,远胜着色,可谓善于写生”,是又将水墨画法称为写生,“写生”作为画法的范围亦随之扩大。
关于写生的另一种观念,是用以区别不同的画科,即根据不同画科分别命名时,以“写生”代指其一,明唐志契说:“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徐沁《明画录》:“写生有两派:大都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黄荃、赵昌,正以人巧不敌天真耳”,这里的写生“两派”,皆为花鸟画家,可见这里的“写生”就非关画法,只是花鸟画的代称。清李修易则以花鸟画家称“写生家”,亦是以写生为花鸟画之别称。
从绘画创作实践来看,写生是画家追摹自然景物,向自然造化学习,汲取灵感的艺术方式,绝不仅仅限于花鸟画。因此,“写生”从指一种花鸟画的画法进而指称整个花鸟画,至明清时期已有人将之扩大到人物和山水画中,使得“写生”一词,可以泛指一切师法自然的绘画行为。明胡应麟: “周昉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周昉以画人物著称,所谓“周昉写生”,当指周昉画赵纵侍郎相貌事,这里所谓“写生”,就相当于人物画之“写真”了。清初山水画大家程正揆论画时就说:“(画山水)善写生者,写活境不写死境”,此处“写生”一词亦运用于山水画中。不但如此,至清中期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还说: “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虽然《小山画谱》所论以花鸟为主,但此一“写生”概念,从得自然造化之“生动”出发,实际上至清中期,“写生”之范围和观念已可以涵盖一切师法自然的写生行为。各种以师法自然为特色的理论和思想,亦可以作为写生之理论来看待。
从绘画史的实际情况来看,经过明末清初画坛拟古之风的熏染,一部分画家专注师法古人,以笔墨为重,较少关注外在的物象和自然景物,确实忽视了师法自然的写生方法。但继之而起的恽寿平等人,重新回到古已有之的“写生”道路上,为清代中期绘画注入新风。恽寿平是清初以来最注重写生的人物,被称为“写生正宗”,他“以北宋徐崇嗣为归,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为写生正派,由是海内学者宗之。”可以说,以恽寿平为代表的画家们为写生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强调“写生简洁精确,赋色明丽,天机物趣毕集毫端”,重新将写实性注入绘画之中,既保留笔墨意趣,又强调画面的写实性,解决了徐渭面临的“问何鱼而不能答”“不知是何花”的困境。这是我们讨论清代中期有关写生理论及写实性绘画出现的重要前提和背景。
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之际西方绘画的渐次传入,带有西方特点的写生方法亦出现于中国画坛。至清中期,在统治者的调和下,中国传统固有的写生方法与西方的写生方法逐渐融合,呈现一种综合性,体现在清代的写实性绘画之中。清中期的写实性绘画主要集中在宫廷,它包括大量的纪实性绘画和部分实景山水画。为清代宫廷服务的画家一部分接受了清代统治者授予的官职或参与科举考试,成为宫廷的官员,同时兼及绘画。一些是服务于宫廷的职业画家和外国传教士画家,他们通过向朝廷进呈画作而得以进入宫廷画院。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出身、掌握了不同绘画技巧的画家们,或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或为了完成朝廷的某种政治性绘画任务,在统治者的旨意下绘制了大量的写实性绘画。清代中期这种写实性绘画的兴盛流行,或与此时期统治者的好尚和政治需要有关,或与外来因素的客观影响有关,但都毫无例外地在创作方式和手法上,离不开对客观真实物象的摹写——写生成为此一画史现象的重要特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画史现象的出现,也反映在清代中期的绘画理论之中。尤其是有关写生的理论论述,既是这一画史现象出现的理论基础,也反映出清代中期绘画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变化。
二、清中期关于写生的理论内涵
清代中期的画家和理论家们在经历清初正统派摹古风潮的洗礼之后,深刻感受到摹古的弊端,他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从摹古中走出来,在不舍古法的基础上,能得江山之助,画出鲜活生动的眼前景象,所谓“落笔要旧,景界要新”。早在晚明时期,董其昌就谈到了“以天地为师”的重要性,他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清初正统派画家虽然以董氏理论为圭臬,但他们显然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摹古方面。唐岱就提出“凡临旧画,须细阅古人名迹。……而临旧之法,虽摹古人之丘壑梗概,亦必追求其神韵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他强调画家向古人学习,不可以只追求与古人画面的“形似”,而更应学习其“神韵”。与乾隆皇帝关系密切的官员沈德潜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在为王冈龄题画中写道:“从来变化先追仿,画拟停云已及肩。灭没更超形象外,请看相马九方湮。”看古人画,学前人法,以此作为学习绘画的桥梁和关键,并且不囿于前人创造的“形象”。可见,清初以来,画家和理论家们皆深刻认识到,学古摹古仅仅只是绘画道路之开端,进此更需追寻“象外”和“神韵”。既然象外和神韵不能从摹古中得来,那就要在摹古之外不断拓宽绘画的道路。乾隆时人布颜图说:“灯下朽示宋、元诸家面目,并瞩董、巨二法,为画海之津梁,诸家之关钮,必先取之以开道路。”这是说,用古人之成法,仅于开路而已。其后,就需要画家习画的过程中,通过感受自然景物,将传统与所见之景互相印证。布颜图又说:“飞瀑鸣泉潺湲而下,在营丘,右中立,一一指证,皆心领默会,津津自喜。”画家对景作画,能熟练运用之前摹古习得的绘画方法,将技法与自然景物互相印证,重新解构传统的笔墨程式,提取笔墨因素和程式法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变“他法”为“我法”。
画家写生时所参照的古法,正是前人在写生中观察自然事物总结提炼得来的。可以说,“落笔要旧,景界要新”实际是清中期人对写生之“理法”的再确认。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如画人物,要有人形、五官、四肢;画鸟兽,要区别走兽、禽鸟的习性、状貌;画屋宇楼阁,就要区分建筑的样式、功能。对于石头、树木这种没有固定外形的景物,需要对客观事物进行概括,总结其中的常理,并针对不同的事物釆用不同的画法,突出它们特性。如此,画面才具有写实性。布颜图说:“法者理也,万物莫不由理而出,故有定形定像。……凡有所定形定像,皆在规矩绳墨之中,故画家皆可以法绘之。”又说:“初基之士,必从有法入手,若以树石为无定形定像,即率笔为之,将放轶乎规矩之外,终于散漫而无成矣。”布颜图虽然更讲求笔墨的有法与习学,但他注重“定形定像”,认为“定形定像”来自于“理”,故应有“法”可依。在写生的过程中,尊“理”守“法”,画家才能“定形定像”,从而把握不同事物的特征,提升自己描绘对象的能力,使图像可以较形象地指代所表现的事物,这是写实性绘画的一个基本要求。画家在写生的过程中,不断将前人之“法”与自身的观察所得物象之“理”相印证,变有法为无定法。正如方薰所说:“画无定法,物有常理”,是要画家在抓住眼前景物之“常理”的基础上,跳出前人的法度,实现艺术的创造。写生所实现的,正是从“物有常理”中跳脱古法的束缚,这也是解决清初以来摹古之风盛行下画风萎靡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方薰说:“不尚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务肖其神明也”“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形似作为神似的基础,需要画家具备一定程度的观察和写实能力。不能真实的描摹眼前事物,“肖其神明”也就无从谈起了。
清中期人还具体论述了写生的实际做法,他们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去观察和提取物象,做到“身历其际,融会于中”。其中,颇有特色的地方是提倡游观和对景观察的写生方法。
游观是一种相对动态的观察方法,所获得者将寓目之各种事物的印象,用之于绘画实践,虽不具体落实,却能够既得之自然,又合理剪裁,获得创作上的自由,是清中期所提倡之写生方法。明末以至清中期,山水游历之风日盛。当时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水中之舟显然能够为画家提供更稳定的环境。画家被指派或宦游途中实地游历,目识心记,写生完成稿本,再创作出实境山水,具有较为明显的写实性。画家们在游观中,对所见的自然景物进行取舍,根据他们的创作意图在自然景物中“抓取”。唐岱说:“今以几席笔墨间,欲辨其地位,发其神秀,穷其奥妙,夺其造化,非身历其际,取山川钟毓之气,融会于中,又安能辨此哉。彼羁足一方之士,虽知画中格法,诀要,其所作终少神秀生动之致,不免纸上谈兵之诮也。”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唐岱、沈源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虽然唐岱是王原祁的追随者,注重摹古和笔墨,但是作为清代中期宫廷画院的代表画家之一,“画状元”的名号表明了他深受皇帝的器重。他提出的“身历其际,取山川钟毓之气”作为绘画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对游观作为绘画创作方式的肯定。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起初是乾隆皇帝指派如意馆画师冷枚,画圆明园的各处殿宇处所,起稿画样,未能完成,后来又改令沈源画屋舍,唐岱画土山树石,后来周鲲等人共历时九年在1745年完成了这套图册。作为正统派余续的唐岱与职业画家冷枚、沈源等人实地游览、取稿,能完成写实性极强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图册,也许正在于他们的绘画思想和理论已有所转变,即强调身历其境和游观取象有以使然吧。
当然,游观并不是绝对的。沈德潜以旁观者的角度,提出自己对于游观的见解,“时有论画者,谓必看尽九州山水,日以造物为师,乃能罗天地之秀于笔端,犹太史公足迹遍天下,而文益奇也。其说固然。然名山大泽,未易遍游,如必登五岳,历台荡、武夷、庐阜、黄海、峨眉、罗浮诸胜,而后卓然成家,古今人盖不数见”。他认为画家需要游观,但是不必“看尽九州山水”,就能“罗天地之秀于笔端”。
对景直写是相对静态的观察和绘画方法,它在不同画科中都有体现,也更接近于西方绘画的写生。“对景”一词曾出现在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居山水间,尝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学李成笔虽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对景造意不取华饰,写山真骨自为一家”。这段文字记载了范宽山水画的创作方式为“对景造意”“写山真骨”,说明这种“对景”而“写”的山水画创作方式在中国画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绘画中的这种“对景”写生不是对景物外观的直接摹写,所谓“不取华饰”,更强调了观察后对对象的本质认识。
至清中期,在艺术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此类对景写生的例子。高其佩之孙高秉记述了其祖父的一件写生事迹:“狮不易见,画家以意为之。长毛大尾殊非本相,公曾为狮写生,足以为法。”狮子这种远在非洲的动物,在清代中期不容易见到,所以很多画家猜想狮子的形象是长毛大尾,但这并非狮子真实的样子。高其佩作为清代的重要官员,他是有机会看到外国进贡来的狮子,并对着狮子写生的。金恭在与好友黄钟的交往中谈到他:“十年未脱探春屐,山山花送兼花迎。兴来恰得老莲派,僮背作几随处画。”讲述了画家数年来在山中观赏梅花时动笔即兴作画,即是此类对景写生。
同时,一些理论论述也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观察和写生的方式方法。邹一桂就在《小山画谱》中提出了“四知”之说,总结了观察认识物象及其相应的写生方法。他提出了“随时体察,按节求称,各当其可,则造物在我”“物以地殊,质随气化”的思想,强调根据对象的生长时节、地域及其规律性来认识和观察对象,方能做到“生花在手”而“造物在我”。不得不说,邹一桂倡导的这种从研究对象的时令、地域及气候出发的,探究其生长规律的观察方法,是对写生观察方法的更高要求。在此基础上,邹一桂要求绘画者能够通过观察而“知物”,即按照所谓“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观察和研究对象,进而在写生中达到神完气足的程度。他说:“播种早晚,则花发异形,攀择损伤,则花无神采,欲使精神满足,当知培养之功。”这是说,观察和用心体悟写生对象的生长环境中 “人”的因素, 写生中就更能体现对象的精神性。在细致观察不同对象形态特征甚至到花瓣、苞蒂须心这些局部的基础上,做到“欲穷神而达化,必格物以致知”。在中国古代画论史上,这种对对象的观察研究的极度强调和极高要求,至清代中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写生既是一个收集素材的手段,亦是一种创作方式,因此,写生必须要有创作主体精神的参与。清中期的理论家们更从“兴”的生发谈到了写生中的创作问题,所谓“兴会所至,造物争奇”。
虽然清中期的写实性绘画多是宫廷画家在帝王的授意下进行的,从起稿到完成阶段都会受到特定的审美要求和创作需要的限制,某种程度上的确会减弱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情感因素,但即便是从写生而来的高度写实性的作品,也是需要“游”与“兴”的触遇来激发创作热情和灵感的。画家们尤其是山水画家向往“游”所带来的自由精神,追求庄子所说的“心斋”“坐望”的境界,以期实现对“道”的观照。在“游”过程中,“兴”的出现会促使他们目识心记,提升他们的观察力,进而产生写生的“画兴”。画家有了写生之兴致,他们往往或对景起稿,或基于古法参证实景,或根据视觉记忆进行再创作,迅速进入到创作状态之中。清中期的一些理论家就“兴会”与写生的关系进行了论说。
许行健在鱼翼《海虞画苑略》的序中这样说道:“况纵笔泼墨,机与神遇,兴会所至,造物争奇”,画家需要到实地游览,对所见的景物进行直接审美观照,遇到灵感的触发,便能够画出与客观世界“争奇”的物象。所以,如果将写生视作一种创作方式,那么它亦依赖于灵感的迸发,即 “兴会”的作用。对此,沈宗骞对于“兴会”的作用说得更为详细:“机神所到,无事迟迴顾虑,以其出于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难弦。其不可测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后乎此者窅不知其所由终。不前不后,恰值其时,兴与机会,则可遇而不可求之杰作成焉。”“恰值其时,兴与机会”,说明了绘画创作具有较为明显的偶然性,因此通过游观、对景或者参证的方法去寻找这种创作的良机就是每一个画家都会面对的问题。沈德潜“兴来写山水”的说法,即涉及到了这兴会与写生的关系:“徐君兴来写山水,绵绵延延势千里。无依无傍往而复,忽断忽续起兼止。”正因为“兴”的难求,画家才需要更多实地观察自然景物,将感受表现在画面中。由这样的方式创作出的画作,当然也是不乏真情实感的。
在“兴”的作用下,画家无论是对景写生还是游观、参证所创作的作品,都在逐渐突破前人的束缚。邹一桂《山水观我》图册是他官黔中地区时,在路途中写生创作的画作,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画中自序“沿流峭壁颇觉动人,乃稿而笥之,俟暇,欲为图以嗣粤游之册”,可知此作是画家由景而起兴,对景写生而完成画稿,其后再予以润色完善并最终完成的画作,这种景物—兴会—写生—创作的模式在清代中期普遍存在于画家的创作活动之中。“归来衫袖重,携稿上鸣驺”,既说明画家所画稿本之多,更表明了画家之创作,其实都是这种景与兴会,援笔而画的写生方式所得。这样的作品,更能让人充分感受到画家纪游的真情实感。邹一桂1752年扈从盘山归来后创作的《太古云岚图》也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由兴会而写生的绘画模式。画中题识“壬申春仲扈从盘山即景恭画”,表明了当时的季节,亦表明此画是对景而作。画面的前景中间分布了数棵正在盛开的桃树,左侧前景还有几棵泛青的柳树。画家并没有在前景安排太多树木,用干笔少量皴擦出前景山石的走势。画作的中后景逐渐向远景推进,两条溪流蜿蜒而下,一条连贯到前景,另一条则流入前景的庄园中。庄园由围墙划分出来,画家在院子里画了松柏树,中后景的树木则寥寥带过。《太古云岚图》画面虽不及《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缜密工致,但画家似乎更在意画面的活泼之感,突出了写生的生动感,画面前后疏密有致,既有写实性,又保留了笔墨趣味,可见这种创作模式的优势和魅力。
《小山诗钞》中描述了邹一桂的一次写生经历:“山行霡霂是晴天,牛背夷童带雨眠。此日青畴喜沾足,数峰烘出米家颠。谁能破墨画高峰,远近烟岚试浓淡。我是九龙山下客,一帧烟雨嗣南宗。”此诗既是画家游历的记录,也可以看出画家在特定的“兴与机会”的情况下是如何在“烘出米家颠”“泼墨画高峰”的意象触发下“嗣南宗”的。画家虽标榜自己仍为南宗,但这种触遇而发的写生活动,显然是突破清初四王的摹古之风而相隔云泥,它使得画面更加贴合现实,具有明显的写实性和生动感。

太古云岚图 邹一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清中期写实性绘画的发展与繁盛
清代中期有关写生的理论论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清文人的那种刻意追捧“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绘画观,也为清代中期绘画发展带了明显的变化。
诚如詹景凤《玄览编》所言:“画极于宋,自宋而下,便入潦草。至于国朝,又草之又草矣。”那种“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即兴式、顿悟式的绘画观深刻影响了画家们对待写生的态度,他们不再以“五日一水,十日一石”的苦功来磨炼自身的观察方法和写实能力,却对精工细笔的写实性绘画抱以负面、鄙夷的态度。这其中既有统治者审美趣味的引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画家的理论和实践自觉。他们或多或少地在讨论如何提升写实能力及其方式方法,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这些理论认识。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清代中期的画家们特别是宫廷画家们重新将写生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词臣画家和宫廷职业画家为主体的画家群体如蒋廷锡、邹一桂、冷枚、焦秉贞、王幼学等人,在重新发掘写生的方式方法的同时,又接受了海西法,将之广泛运用到绘画创作中,创作了大量的写生性绘画,写实性绘画在清中期得以某种程度的复兴。

塞外花卉图卷(局部)蒋廷锡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盘山十六景(局部) 董邦达 辽宁省博物馆藏
江南地区的写实性绘画也与宫廷画家群构成了一种联动关系。有很大部分服务宫廷的画家来自江南地区。被誉为“写生正宗”的恽寿平就出自江苏常州,虽然他终生未入仕途,靠四处奔波卖画为生,但他的没骨写生路数经由其传派画家带入宫廷,成为宫廷写实性画风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在恽寿平之后的写生画家,据蒋宝龄的《墨林今话》记载:“恽南田后,写生一法自以蒋文肃公为最,恒轩相国继之,同时无锡邹小山宗伯,以清艳之笔,竞美艺林”,以蒋廷锡(文肃公)、蒋溥(恒轩)、邹一桂(小山)三位活动于宫廷的词臣画家最有代表性。他们身居高位,经常与皇帝在诗画上进行交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在宫廷画院中的同乡画家,据郏抡达《虞山画志》中记载就有数人,其中有余省、余穉兄弟,周安节,姚匡,薛周翰等画家,还有画家被官员招入幕下成为代笔,“潘林……花卉翎毛师马栖霞,蒋文肃招致幕下,凡进呈花鸟卷册皆出其手”。潘林师法蒋廷锡的同乡马元驭,却被蒋廷锡招致幕下,替他完成大量的应制花鸟画。从传世作品看,这些画家多长于写生,能运用各种写生方式方法从事创作。他们汇聚在宫廷,客观上促成了清中期写实性绘画的兴盛。
清中期写实性绘画的繁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适应和满足了政治的需要而被大量的高规格地创作出来。清代中期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蓬勃发展,这些都为写实性绘画的繁盛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一书的序中明确了清代宫廷绘画的功能和范围:“国朝踵前代旧制,设立画院,凡象纬疆域,抚绥挞伐,恢拓边徼,劳徕群师,庆贺之典礼,将作之营造,与夫田家作苦,藩卫贡枕,飞走潜植之伦,随事绘图”。绘画与文字、书籍相比更加形象,更容易起到宣扬和教化的作用。清代统治者要求画家用写实的形式记录下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使得宫廷的画家们必须通过大量观察与写生,创作出写实的绘画图式。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向其他宫廷画家传授的“海西法”,亦是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法,同样在宫廷中流传开来。官至工部侍郎的年希尧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完成了介绍西方透视学的绘画著作《视学》,也可以看作是清中期写实性绘画创作的指导性工具书。正如年希尧在书中所说:“余故次为图公诸同好勤敏之士,得其理而通之,大而山川之高广,细而虫鱼花鸟之动植飞潜,无一不可穷神尽秘而得其真者,毋徒漫语人曰,真而不妙,夫不真又安所得妙哉?”不同的绘画风格在帝王审美趣味的黏合下,互相融合,呈现出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写实画风。或者我们不能简单称其为中西合璧风格,但显然,清中期的统治者是高度认可了传统画法与海西法相结合而创作出的写实性绘画,是更具有纪实功能的图画,能更好地满足宫廷的需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塞外花卉图卷》是蒋廷锡进献给康熙皇帝的一幅写实性绘画。该作品中没有描绘常见的牡丹、荷花等植物,而是详细描绘了66种在塞北荒寒之地生长的植物种类,经过画家细致地观察它们的外观特征,经过与植物志等书的鉴定,可以精确鉴别其中的55种。之所以能够精确鉴别其中的大部分植物,得益于画家对植物外观特征的把握上,画中描绘的植物具有明显的写实性。蒋廷锡将此画卷进献给皇帝,以此作为纽带来增进君臣之间的关系。据张庚《国朝画征录》所载,邹一桂也曾绘制百花卷,上面每种植物赋诗一首进呈皇帝,而皇帝亦赐题绝句百篇。这些画作无不从客观物象出发进行写生和描摹,以满足某种宫廷和政治需要的面目而出现。
二是配合重要园林、行宫及有关工程建设或者朝廷重大活动而大量绘制相关主题的写实性绘画。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皇帝皆大力修建皇家园林和行宫,这些园林和行宫是在参照江南地区园林的基础上灵活仿建而成的。康熙、乾隆二帝在南巡途中,也会不时地指派随行画家绘制大量纪实性的绘画作品。这些画作既要如实描绘帝王见到的江南美景,又要方便作为日后在北方仿建江南景物和园林的参考,因此实境山水和园林绘画就成为这些写实性绘画的主要题材。虽然这些皇家园林和行宫中的建筑和景观已不复存在了,但以之为主题的大量写实性图画则可以见出当时此类绘画的繁盛。
始建于康熙时期的避暑山庄、圆明园,和乾隆时期在盘山修建的静寄山庄以及皇城所在的紫禁城,在康雍乾三个时期都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这一过程中,还以这些皇家园林和行宫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写实性绘画。以盘山为例,盘山行宫是乾隆皇帝经常驻跸的行宫之一,它自乾隆九年(1744)开始修建。乾隆皇帝经常指派宫廷画家前往写生,务求写实,“行宫地居最胜,模写宜详,而山中一峰一水之奇,务期刻画,无取仿佛。凡得图四十幅,图各为之说,不惟为搜奇剔隐之资,亦足考古证今之助。”在《钦定盘山志》的序中说明了皇帝建设园林的初衷:“朝曦夕霭,皆承盛世之光华,寰宇亿万里中,福地洞天会见山灵之踊跃”。可见皇帝这类园林和行宫画与皇家园林、行宫一样,主要是描绘统治者治下的盛世美景,供其观赏,故皆得以实写。
《清档》中还留有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二十六日“传旨着沈源、董邦达往盘山行宫等处,起稿画图呈览”的一条特别记载,董邦达在此时或者稍后绘制了《盘山十六景》并得到乾隆帝的定名。乾隆还命慎郡王允禧画盘山山色,并题诗相赠:“吾叔诗才素所知,于今学画画尤奇。同来胜地宁无意,为写山容更咏之。”《钦定盘山志·山行即景》中还记载了一次帝王参与的写生经历:

《钦定盘山志》卷——盘山全图蒋溥等
“泉带东西自高下,山分向背变寒暄。田盘四面皆方正,拱极都环紫盖尊。但看松姿皆入缋,不须花发始吟春。侍臣携有清华侣,诗画兼能为写生。携董邦达来令为田盘全图兼欲修新志也。”
诗为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驻跸盘山时,“携董邦达来令为田盘全图兼欲修新志也”,是为修《盘山志》而携董邦达前来盘山写生而作,此次乾隆即命董邦达绘制了《盘山志》的志图。从董邦达绘《盘山十六景》到绘制志图,可以看出这些围绕行宫、园林为主题的实景绘画在清代中期的繁盛与发展情形。

盘山十六景(局部)允禧
四、结语
清代中期的写生理论与清中期的写实性绘画,反映了清代中期绘画史、画论史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由于写实性绘画的再次兴盛,较高地提升了画家们观察能力和写实能力。实写的需要也再次激发了清代画家们对师法自然造化之理的再认识和讨论。他们关于写生的种种理论和认识,反过来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地增强作品的写实性。
写生性绘画在清中期的繁盛和发展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一改明清以来文人画过于重视笔墨而轻忽可观物象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笔墨趣味的基础上,又不断以写生的方式探求对自然造化的写实性表达。这一绘画史与绘论史现象,是值得总结和深思的。当晚清及民国时期画家们面对西画冲击,不但探索绘画新路之时,当代中国画因过分写实而广受诟病时,清中期的写生理论及写实性绘画的繁盛发展,或许都是极具启示意义的。
① 徐渭在《旧偶画鱼作此》中说:“我昔画尺鳞,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参见徐渭. 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59。
② 聂崇正将清代宫廷绘画按题材分为纪实性的绘画和装饰性的绘画,又将纪实绘画分为三类:记录人物相貌;记录事件经过;记录动、植物。详见聂崇正. 清朝宫廷纪实绘画[J]. 紫禁城,2014(3):2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