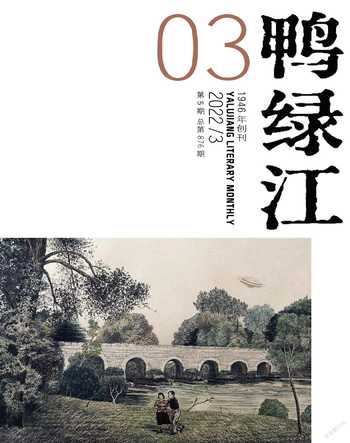糍的粑
车子已经出了校门,她又想起少拿了一份资料,只好兜一圈,在前面的路口掉头回来。再次出来时,天已黑净,通过挡风玻璃看到城市的天际线模糊不清,楼体的轮廓棱角全无,像逐渐融化的冰激凌。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一个老人正横穿马路,身边车流穿梭。她莫名愤慨,斜刺刺停下来,堵住大半个车道,让他慢慢地走过去,任凭后面喇叭声响成一片。
往前开了一段,车速又慢下来。前面是一场车祸,一辆霸道剐倒了一辆电单车,骑手丢盔弃甲,坐在地上。霸道车主在一旁焦急地打着电话,应急灯闪烁,宛如霓虹。她知道自己不应该乐,但忍不住从心底生出一丝窃笑。
来到上步市场的时候,市场已经散了,她可以直接把车开进去,开到那个叫“天翼”的小店门前。上步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甚至算不上专门市场,它只是一段平常的小街。原来的肉菜摊都是沿街摆放,常常堵得水泄不通。后来集中清理,实行门店经营,所有的档口都被赶进了店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特有的景象:同一家店铺,里面经营小吃,外面卖水果,或者一边是摩托修理铺,一边是蔬菜摊;也有半边杀鱼、半边卖牛肉的。“天翼”本来卖手机,关张之后被一对卖牛杂粿条的夫妇接过来,店名不变,只粉刷了一下内壁,摆上几张桌子,就支起了生意。过了一段时间,粿条店又分出一小块地方给一个卖蔬菜的外地女人。女人像大风吹来的种子,一来就生了根,摊子虽小,却风生水起。
“祁老师,”女人热情地叫道,“今天想吃什么?”
“还有些什么?”
“今天有你最爱吃的。”女人从摊位下拖出一个泡沫箱子,里面是新鲜的芦笋,已经削好皮,白嫩嫩、翠生生,煞是可爱。看得出来,这是特意给她留的。她乐了,“要是我不来呢,岂不浪费?”女人温厚地一笑,“不来就不来呗,你那么忙。放心吧,干别的不行,卖菜我还是有办法的。”
她心头一热,暖流涌动。半路上她还真动过心思,尤其是看到那家拉面馆,想起那羊肉汤的味道,她几乎靠了过去,要不是旁边突然蹿出一辆车把她吓了一跳,没准儿她都吃上饭了。反正今天老公出差,儿子住校,也没有人需要她照顾。可转念一想,正因为没人需要照顾,正好照顾照顾自己。她想起了那句流行的广告词:女人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一路上,她冒出了很多想法,又一个个湮灭。最后决定为自己做一桌子菜,慢慢吃。她其实吃得不多,要的就是那种仪式感。上次体检,其他一切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肠胃也不太好。人到中年,她常常想起陆文婷大夫,当年看小说,哭得稀里哗啦。她本来是要选文科的,阴差阳错选了理科,还读了物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后悔选错了专业,教了二十余年书,慢慢悟了道:物理也好,究天人之际,通万物之理。
“那天的东西怎么样,好吃吗?”
“那天?”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糍粑啊。”女人说。
“哦……好吃,”她稍一迟疑笑着回答,“多谢哈。”其实她根本没吃,东西还在冰箱里放着。她记得那天刚买了一条桂花鱼,备了三菜一汤,她觉得已经很丰盛了,就随手把那袋东西放进了保鲜层。还有另一个原因,对这种陌生的小吃,她有点束手无策,是蒸是煮,是煎是炸,拿不定主意。她想等问过女人之后再做打算,不承想回头就忘了。她明显感到,这几年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一念至此,她马上想起了一件要紧的事,转身到车上拿了一个塑料袋回来,递给女人:“这是给苜子的书。”女人的女儿叫苜欣,小名苜子,伶俐乖巧,真像是从开满苜蓿花的田野上走来的小兽。前两年,小姑娘还在妈妈的菜摊旁摆起一副小桌凳写作业,那专注的样子让人既喜爱又心疼。偏偏女人铁石心肠,要求极为严苛。有一次她看见苜子拿着一张试卷在做,顺口问了一句:“考多少分啊?”女人的脸唰地黑下来,她买好菜,刚转过身,眼角的余光即瞥见鞭影一闪,竹条打在孩子身上,啪的一声。她浑身一颤,感觉那鞭子就抽在自己身上。按她早年的脾气,直接就冲过去,劈手夺了鞭子。但那天她只是身形稍稍一顿,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随后几天,她头脑中满是孩子瘦小的身影。终于有一天,她买好菜,主动对女人说:“如果有空,就让孩子晚上到家里去学习,反正我也备课、批作业,顺道给辅导辅导。”女人自然千恩万谢,每周准时领着孩子去。
事后想来,她总觉得自己有点冲动。这些年,虽然没有开过补习班,也没给满大街的教育机构打过工,但隔三岔五帮朋友的孩子答疑解惑也算家常便饭。认真捋起来,苜子是她唯一主动提出来的,真是自找麻烦。丈夫对此颇有怨言:“咱差那两个钱?”她说:“不是钱的事。”“你要喜欢女儿,咱们再生一个?”她愣了一下,“你说真的?”“假的,”丈夫自嘲地笑笑,“折腾不动了。”她也涌起一股心酸,在这事上,他们不是没有犹豫过,但作为公职人员,当年并没有太多选择。政策一放开,他们也兴奋过一阵,最终还是偃旗息鼓。不过她帮助苜子,跟喜欢女儿没关系,就算面对的是一个男孩,她也帮。丈夫看她发愣,安慰说:“放心吧,我理解你、支持你,只是注意分寸。知道的说你热心,不知道还以为想赚钱想疯了,连摆菜摊的务工人员也不放过。”她说好。心里纠结了几天,她找了个机会,特地向母女俩申明,补课是免费的,纯粹帮忙。女人口头上连连推辞,私下里也做着准备,她经常让孩子提点东西上去,有时候是新鲜的蔬菜,有时候是家乡的小特产,例如一块腊肉、两片熏鱼,或者一袋笋干。当然她也没让她们吃过亏,家里的紫菜、墨鱼干、小银鱼之类常作为回礼塞进苜子的书包。
这算是一场交易吗?她权衡过。答案不确定,似乎是,又不全是。女人一向热心,不仅对她,对所有的顾客都笑脸相迎,常把自己的私货拿出来跟顾客分享,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暖心,所以她的回头客多,走货量大,每天都忙得像陀螺。如果说女人不会算计,肯定是假的,但并非所有的算计背后都隐藏着深远的企图。她宁愿相信女人的淳朴。
丈夫是工商局的,副股级,科员,在办公室工作,并不参与执法,不过他警惕性高。他警告她,帮忙也罢,但来路不明的东西无路如何不要收。她私下揣摩,女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男人是工商局的?她確信自己没有说过,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他们住的就是工商局的集资楼,虽说年月深久,很多工商局老员工已搬出去了,有的房子已转了两三次手,但大家还是习惯把这里叫“工商楼”。其实他们也已在桥东新区买了二套房,只是贪恋这边上班方便才没搬走。否则,也没这些事。
她曾经问过苜子:“你爸爸呢?他在哪里工作?”小姑娘也说不清楚,只知道爸爸妈妈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去批发市场拿菜,回来之后,妈妈开张做生意,爸爸上楼叫醒他们姐弟,洗漱、用餐,收拾好,送到学校,然后去上班。苜子的描述,让她想起了“凌晨四点钟的洛杉矶”。那是科比的梗。儿子喜欢篮球,对NBA的众多巨星了如指掌。有一次,突然冷不丁冒出一句:“你见过早上四点的洛杉矶吗?”她猝不及防,愣住了。儿子就头头是道地给她讲科比的故事。科比死后,儿子放声大哭。她还记得那天清晨,那场发生在遥远天际的坠机事件,在他们的小家庭中投下了一颗悲伤的炸弹,儿子的哭声让她鼻子也酸酸的。她并不关心籃球,更不是什么科蜜,她只是感叹生命的脆弱。那一整天,她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悲悯,像一坨发酵的面团,不断膨胀。她好几次轻轻揉着自己的胸口,借此捧手作揖,暗暗地祈祷。为科比,也为众生。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病,她感觉自己对一切苦难和弱小有着越来越深切的同情,甚至由此迸发出强烈的保护欲。丈夫有时候跟她开玩笑:“你以为是谁啊,真想母仪天下?”她自己也笑了,自嘲道:“庸人自扰。”
苜子没有让她失望,顺利升入一所重点初中。女人知恩图报,趁她买菜的时候,悄悄把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塞进了袋子里。她发现之后,立即送了回去,严肃地告诉女人不准搞这种小动作,说不收费就坚决不收。女人慑于她的凛然正气,又或许是被她的大公无私感动了,脸红了一下,眼睛竟有些湿润。此后,女人给她小东西更勤了,而且似乎有意观察她买菜的偏好,一旦有她喜欢的菜,质量好的应节时蔬,都替她留一份。她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她十分受用,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不过即便如此,她还是拒绝了女人提出的继续辅导的要求。打心眼儿里说,她喜欢苜子,这孩子身上有股子劲儿,让她欣赏,她愿意帮助,前提是必须保持一定距离。是的,距离。无论是邻居的眼光,还是社会的风评,甚至是自己的私人空间,都需要考虑。她还记得一天放学后,校长叫住她神神秘秘地说:“祁老师,有一件事想向你核实一下。”她愣了片刻回答:“您请说。”校长清了一下嗓子,严肃道:“听说你在私下给人补课?”她的脸一下涨红了,冷冷地问:“谁说的?”校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没有就好,这种事很敏感,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她虽然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冷不丁给人一问,心里那个别扭,比吃了绿头苍蝇还难受。当然这只是一个诱因,以她的性格,完全可以不把风言风语当回事。她考虑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角色,大包大揽、无私奉献显然都不可持续。最后一次,她对苜子说:“我会尽量找一些学习资料给你,而你需要独自去面对许多事情,没人可以帮你一辈子。”孩子很懂事,对着她鞠了一躬,“谢谢您,祁妈妈,我会记住您的。”那一刻她心都化了。
婉拒女人之后,她有好一阵没去买菜。后来觉得不妥,自己太敏感了,硬生生把一个彩色的世界还原成了黑白两色。于是,重新大大方方地去。她在心里想好了,如果女人不给她好脸色,她就从此不再去了,也不用再背负任何包袱。事实证明,是她多虑了,女人依然热情,甚至比以前更加热情,似乎在为自己提出的无礼要求忏悔,不过这只是她的猜想,女人从来没有流露出这个意思——有些话是不好明说的,说穿了,大家都尴尬。
那一阵,她也在暗中担心,生怕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那样就算她有一千条理由,也难以原谅自己。好在苜子挺争气,在强手如云的重点中学,苜子还是能基本保持在上游。这让她为自己庆幸,也为苜子一家感到高兴。今年春节的一天,天朗气清,她和老公手挽手在江边散步,远远就看到苜子一家。他们刚刚从老家回来,菜摊还没有开始营业,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时光,四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温情的笑。苜子的弟弟,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举着一个哆啦A梦的气球,跟爸爸互相追逐,来回奔跑,兴奋得像一头撒欢儿的小兽。苜子妈妈很高兴,连说:“有缘有缘,我正要去找您。”原来他们从老家带了一些腊肠、腊鸭和熏肉过来,准备分一些给老师。她急忙道谢,推辞说:“之前已吃过,还是留给孩子们吧,正长身体呢。”苜子说:“祁妈妈不用客气,原本就预备着您的一份。”她看得出来,孩子说的是实话,这一家子真把她当成了一回事,并非偶然碰上做个顺水人情。
感动归感动,她还是坚定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她不愿意占他们的便宜,哪怕自己曾经有恩于人——那又怎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她不希望他们一家背上任何包袱,换句话说,她不想成为别人的包袱。苜子显然没想那么复杂,孩子的执念单纯而热烈。老师的一再推辞,让她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做错了,显得局促、不安。无奈,她只好答应,晚饭过后去“家访”。这原是缓兵之计,她的计划是先答应下来,等拖过了时间,再打个电话向他们道了歉,这事就算完了。但苜子接下来的话让她改变了主意。苜子说:“祁妈妈您还没到我们家看过呢,再不去,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她心头一震,忙问:“为啥?”苜子说:“我也说不准,只是有点担心。”她心头一软,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真的很脆弱。孩子亲热地叫她“妈妈”,多么亲密、多么美好,而她们之间那若有若无的联系,却像风中飘荡的游丝,纤细、缥缈。
“你们要搬走吗?”她问孩子的妈妈。
“是拆迁,听房东说有开发商看中了那块地,正在跟村里人谈判。”卖菜的女人说,她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原来如此,”她松了口气,“没事的。”她知道,那片城中村被纳入改造范围已经传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动静。这种事,说到底还是利益的博弈,以她的智识水平判断,动迁那一片密集得像蜂巢似的房子,对开发商而言,无疑是一件费力难赚钱的事。苜子似乎半信半疑,她拉住老师的手,有些感伤,“如果真拆迁,我们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孩子舍不得她。她亲昵地摸摸孩子的脑袋,笑道:“就算不拆迁,你们也不可能长久住在这里。至少你要读高中、上大学吧。这里只是你人生的一个小小驿站。”她还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其实,谁又不是一个站一个站往前奔走呢?她觉得这话就像挂在枝头尚未成熟的苹果,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酸涩了。
那天晚上,他们吃完饭,真的如约前去。丈夫还特意带上了一袋干贝、一包橄榄作为手信。苜子一家租住在市场背后的村民自建房里。得益于庞大的流动人口,城中村的居民大多当起了包租公包租婆,就像电影《功夫》里元华元秋饰演的那两个角色。为了多赚钱,这里的房子尽量利用每一寸空间,握手楼、接吻楼比比皆是。出租屋大多采用公寓式管理,配电梯。第一次走进这片庞杂丰富的社区,他们都有点惊讶,狭窄的巷道里,还隐藏着更大的市场:理发店、按摩店、火锅店、士多店、窗帘铺、煤气灌充点,还有各式各样的餐饮店,麻雀般大小,清一色的美团风,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他们对望一眼,又会心一笑,都读懂了彼此的意思:原来那些手机上丰富多彩的餐食,很可能就来自这里,来自这个仅一街之隔,却从来没有光顾过的社区。空气中新鲜、热辣又带着油腻味的气息让他们忍不住打了两声响亮的喷嚏。
这里的公寓名字也很有意思,半岛、香格里拉、维多利亚、红宝石、鸿鑫、蓝钻,各种光鲜的名字用彩灯做成闪亮的招牌。苜子家在香江公寓,五楼,门禁系统是可视的,电梯较小,但干净、亮堂,运行平稳。这大大刷新了他们对出租屋的认识。苜子一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仅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套房里洋溢着满满的喜气。言谈中,她像小时候带着儿子做拼图一样,慢慢拼出了这个家庭的全貌:一对四十来岁的中年夫妻,儿女双全,既不富足,也非寒酸。女人经营小摊,勤劳持家;男人在一家不锈钢制品厂上班,干抛光的工种。他说他常常戴着两层口罩干活儿,口罩极度缺乏那会儿,他手中的几十袋存货一下子奇货可居,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来求他,很是风光了一阵,可惜没有生意头脑,不知道大捞一笔。他们听后都笑了,笑声里是赞许,是尊敬。
趁着上厕所的工夫,她特意观察了一下厨房和卫生间等细节的地方,发现卫生工作十分到位,显然不是为了迎接他们临时突击的成果,由此可见,女人骨子里就是一个爱整洁的人。这让她心里又多了一层好感。尤其让她赞赏的是,屋子里随处可见的不锈钢制品,统统被擦洗得锃亮锃亮的,使这蜗居散发出某种奢华的光芒。
这一次的拜访满载而归,夫妻俩把从家里带来的土特产都分出一份,塞了满满一个礼品袋,以至于随后几天,她一直想着法子把家里的礼品找出来掂量一番,像蚂蚁搬家似的送到菜摊上。丈夫笑她:“你可真够累的。”她说:“没办法,这是我的原则。”丈夫懂她,对等一直是她恪守的信条,在这一点上,她从不肯让步。当然也无须让步,做人清清爽爽,绝不亏欠别人,心里也坦然自在。
虽然礼尚往来的日子不短了,但糍粑这种东西,她还是第一次看到,甚至是第一次听说。那天女人把东西给她,她也没太注意。现在重新提起来,她忍不住多问了几句。女人说:“这种东西不难做,但麻烦,需要用糯米在石臼之中不断地捶打,还要配花生和芝麻。我自己会做,但没那个条件,也没那工夫,这是苜子她姥姥做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她还记得,八十多岁的人,亲手做好了,托一个老乡带过来。”听女人说得动情,她很不好意思,暗想,回家一定得好好品尝一番。
回到家,她特意从冰箱里拿出那袋东西来,仔细研究。女人很细心,包了两层,里面是保鲜袋,外面是一个印着“福”字的黄色塑料袋。打开来,里面有十几块像萝卜糕一样的东西,摸起来软软的,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没有特别的气味。上网搜了一下,才基本弄明白。第一次试做,她挑了三块,根据网上推荐的烹饪方法,选择了炸,还特意找出红糖,融化后淋上去,看起来很像那么一回事。
赤橙黄绿青蓝紫,她给自己弄了满满一桌,虽然量都不大,花样却很丰富。看着自己的战绩,她很满意。尤其是炸糍粑,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她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两张图,预计着吃完饭发个朋友圈。她并不是一个爱嘚瑟的人,更不会把朋友圈当日记本,但今天,这充满烟火味的场景真让她有点动情了。放下手机,她夹起一块糍粑,优雅地咬下半块仔细品尝,嚼着嚼着,那口香糖一般软泥泥的糯米团深处,竟冒出一股酸味来。她有点迟疑,因为从来没吃过,她并不确定这正常与否,又吃了两口终于确定,变质了。她不甘心,又夹起一块咬下一角尝了尝,这会儿更明显。她放下筷子,抿了一口可乐,笑了:这一番心血,终究是错付了。
她想起了卖菜的女人,想起了她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心里涌起一阵遗憾,甚至愧疚。那必定是一个淳朴的族系,勤劳和灵巧在一辈辈女人手中传承。她记得女人之前送来的腊肉,那个香啊,炒起来能熏染整栋楼。丈夫一回家就说:“搞什么呢,我在楼下就闻见了。”可是这次,她竟忘了,实在罪不可恕。收拾垃圾的时候,她还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把剩下的糍粑都塞了进去。
朋友圈是不能发了,她拿起手机随便刷了一下,看到一个闺密在做头发,一下有了主意。她要去把自己这颗脑袋好好拾掇拾掇,眼见得都生锈了,顺便也把垃圾袋扔到十字路口的垃圾桶,眼不见,心不烦。说干就干,这是她多年职业生涯养成的毛病,靠着这个,她一路走来,在教学上收获了累累硕果,也收获了满满情谊。很多学生毕业多年后,还记得她这个雷厉风行的祁妈妈。
做头发的是一个细心的小姑娘,手脚利索,技术也不错。闺密给她推荐了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被她笑着骂了回去:“老不正经。”做完头发,像换了一个人,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觉得有点陌生,不敢相认。闺密说:“这就是你,好好欣赏一下吧,要不就真老了。”
回来的时候九点多,经过十字路口,一个熟悉的身影远远就映入眼。是卖菜的女人,她明显是扔垃圾的,扔完却不走,还站在垃圾桶旁边,犹疑不定。徘徊一会儿,竟俯下身去翻动着什么。她原本揚起手,准备打招呼,见此情景自然不敢造次。又走了几步,她突然恍悟过来,心头猛地一震,气血上涌,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烧灼感。近了,更近了,只见那女人解开她亲手系好的袋子,从中拎出小袋东西来。袋子上的“福”字在路灯下依稀可辨……就在女人抬头的瞬间,她一闪身躲到一棵行道树背后,直到女人凝重的身影开始往回走,她才从树荫里踅出来,稍稍犹豫,快步追了上去。在一片三角形的楼影下,她看到女人窸窸窣窣地打开袋子,埋下头,自顾自吃起来,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棵随风摆动的芦苇。她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响,炸开了。不知道从哪里腾起来的一股力量,让她真想不顾一切地冲到女人面前。她相信,如果时光回溯二十年,甚至十年她都可能干出来。但现在,强劲的想象让她感觉疲惫,双腿发软,不由自主靠在一堵厚实的墙上,紧贴着粗糙的马赛克砖,把身体缩在一根生锈的水管后面,无声地哭起来。
女人终于消失了,巷道幽暗。她积蓄起力气,钻出来,慢慢走过去,站在女人刚刚站过的地方,楼影的三角形已不再完整,像被女人啃过一样,边缘参差。她缓缓蹲下去,在被啃噬过的影子边缘摸了摸,一股冰凉的、尖锐的刺痛从指尖直透入骨。
巷陌如蚁穴一般细密深邃。黑暗中,她裹着四周空无一人的阴影,拐弯抹角,摸索前行。终于转到了市场街,路过菜摊时,看到两个白色的泡沫箱子还在,储积着一片薄薄月光,像一堆剥落下来的白菜叶子。她心头一拧,纠结着,明天还要不要来买菜。
【责任编辑】陈昌平
作者简介:
张勇利,四川人,现居广东潮州,中学高级教师,潮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文联《韩江》特邀编辑。已在《四川文学》《鸭绿江》《福建文学》《特区文学》等刊发表小说多篇,曾为《鸭绿江》“新青年?新城市”专栏重点推荐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