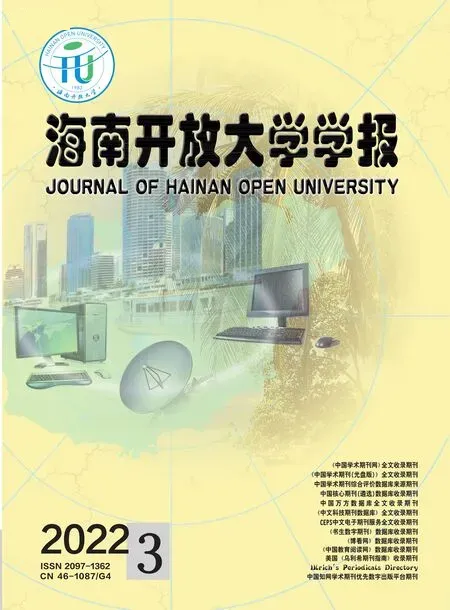从女佣看《旧东家》中性别与阶级的隐喻
张萱萱
(1.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82;2.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 200072)
岛崎藤村在明治三十二(1899)年四月来到信州北部的小诸义塾担任乡村教师。受到乡村生活的感染,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写实主义倾向,在创作上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旧东家》发表于1902年,是岛崎藤村的小说处女作[1]。小说以女佣阿定的视线作为叙述视角,以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在荒井家的帮佣经历和太太阿绫的出轨事件。由于小说中对偷情场面的露骨描写、并将其与歌颂天皇的场景并峙的反讽设定、以及对原型人物木村熊二/华子夫妇造成的名誉损害,该作品在发表一个月后,以败坏风俗罪遭到了明治政府的查禁。
《旧东家》的先行研究在考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时多集中于对原型人物的考证,或是从人的性本能——情欲和嫉妒的角度进行分析。作者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结合了自然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风格,在人物细节的刻画上尤为精妙,然而在描写作品的高潮部分——女佣终于下定决心向太太复仇的心理活动时,仅仅以一句:“我终于露出了女人的本性”来刻画其心理动机,不免给人一种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及隐隐流露出的经验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2]。
岛崎藤村曾在其他作品中谈到《旧东家》是自己“写实主义倾向孕育出的最初的产物”,选择一位与自己思想、阅历、社会地位相距甚远的女佣的眼光作为叙述视角,确实能反映作家对客观创作的追求。但不可否认作家局限于自己的身份立场,在刻画不同性别阶层的人物时会产生视线的盲点,导致一种基于性别和阶级的刻板印象[3]。因此笔者通过对作品中女性角色主体性的挖掘,分析男性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固定模式,揭示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本论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女佣阿定的身份特征、叙述特点、以及女佣与太太二元对立的人物构造来解读作者的写作策略与作品中性别与阶级的隐喻。
一、女佣阿定的身份特征
我娘带我离开家是三月初二——山村里都选定这一天外出。那天刮着风,微微地扬起地上的尘土。我们踏着夹杂着干沙粒的灰色泥土,朝着小诸走去。我娘头上包着一块新手巾,脚上穿着麻草鞋,我提着一个淡绿色的布包袱,跟在娘的后面。为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娘儿俩才能这么走在一起呢!?我心里感到又是害臊,又是难过。当我们从青郁郁的麦地旁经过时,那些脸色同地里的泥土一样的庄稼人,停下手中的锄头,好似故意地瞅着我们。一条宽阔的北国大路直通小诸。走上大路心里才感到轻松些。许多过路的行商围聚像过去去驿站似的茶亭里休息。当时正好在砍伐大路两旁的名贵的落叶松,大树倒地的声音,树枝折断的响声,搬运工人的吵闹声,弄得大路上好似在打仗一样。[4]
这是作品中阿定回忆自己从柏木村来到小诸的主家帮佣时沿路看到的风景。这一路上由农村风景到城镇风景的切换,预示着这位农村少女从“农民”的世界来到了“商人”的世界[5],并且从道路两边正在进行的工事和对小学校这样的近代建筑物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小诸正向着近代商业都市快速地发展。
阿定帮佣的主家荒井家同样是一个商人家庭,荒井家的老爷是银行家,盖新式房屋、娶东京女子做太太、并且立志要将东京的风气移植到小诸来,从服装打扮到言谈举止,革除一切旧弊。许多先行研究中提到作者将小诸作为小说舞台背景时特别着重描绘其商业特征[6],如中山弘明指出:小说将小诸作为金钱和物资流通的据点,描绘其“商人道”,有着美化近代金融资本运作的隐蔽作用[7]。作品中荒井家的老爷被誉为“动一动小指头就能调动小诸商业”的人,托老爷的福,小诸的商人们腰包鼓鼓的,银行甚至打造了一座光辉夺目的金杯来表彰老爷的功勋。荒井家来往的客人也都是“镇议会议员、大地主、商店老板、新闻记者”这些小诸的头面人物[8]。可以说作者在创作时充分展现了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日本城镇及农村生活带来的影响。
从荒井家的家庭结构来看,一对夫妇加上一个女佣、一个看门的老爷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新式小家庭。主家与阿定签订的同样是雇佣式的契约,当时女佣人的工钱每年18元左右,但阿定只要求主家赏赐一点太太的旧衣服,另外给做几身合适的好衣服,因为阿定的娘担心拿工钱的话会被阿定的爹拿去喝酒挥霍。
阿定在作品中经常回忆自己在农村时的艰苦生活:
柏木一带的女人要在佐久的山岗子上生活,跟恶劣的天气打交道,一辈子要帮着男人干沉重的活儿。就因为干这种沉重的活儿吧,我娘、我婶娘姨妈,都有一副倔强急躁的脾性。我打十三岁那年就跟我娘下地干活。和我差不多年岁的姑娘还在拖着鼻涕,跳猴皮筋,而我已经开始懂得人世间的悲欢苦乐了。我家里孩子多,做小买卖又不在行,我爹游手好闲,根本指望不上,我娘虽比男人稍胜一筹,但靠她一双手还是维持不下去,只好让我到人家帮工糊口。[4]180
从阿定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当地的农村妇女承担了相当重的体力劳动,并且不止在农村,在小诸这样的城镇上,也是类似的情况。作品中提到小诸是养蚕的地方,家家户户几乎没有不养蚕的,可以说养蚕的收入是当地人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到了春蚕的季节,老宅子的女佣们“胸前挂着灰色的麻袋,出外去摘桑叶”的情景在作者的散文集《千曲川风情》中也有着同样的记载:“腰上插着称、背着麻袋的人们,从诹访、松本等地向这座镇上涌来[9]。客栈里一时挤满了买茧子的人。这伙人背着蚕茧向各个客栈走去,给各条街道平添了不少活气。”[10]
然而,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散文中,小诸商业繁盛的背后,是当地妇女“就好似松井川河谷里的水车,每天都那么转个不停。男人可以在长长的冬天游手好闲,女人还得不停地干活”的严峻现实。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小诸这样以养蚕收入作为支柱产业的商业城市,还是周边以农耕收入作为生活来源的广大农村,妇女都是主要的劳动力,正是她们勤勤恳恳缩衣节食日夜不停地劳作,才支撑起了小诸繁华商业都市的表象[11]。她们不仅在家庭中承担了生育及家务劳动这样的再生产,为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剩余价值,还参与了社会劳动,却不掌握生产资料、不参与收入分配。不仅如此,阿定的娘还要担心阿定帮佣的收入被丈夫喝酒胡乱挥霍掉,在与丈夫争吵时哭喊着:“打死我吧!要打就打死吧!”。阿定的爹在作品中唯一一次登场是喝醉之后登门向阿定的主家讨烟,边抽边显摆自己要去花柳街送艺妓,称自己清醒时也是个“好样的”体面人。
作家虽然竭力秉持“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写”的自然主义创作理念,但在描写小诸近代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新面貌的同时,却暴露出当地妇女在父权制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下艰辛的生活状态。这可以说是作品以女佣作为叙述视角,从底层劳动女性的身份立场进行观察和叙述时呈现出的特殊效果。
二、婚外恋的隐喻
《旧东家》是通过女佣阿定的回顾性叙述,以太太阿绫的出轨事件作为小说的主线来展开的。这位来自东京的太太给小诸当地保守的风气带来了一片“开化、奢侈”的新风潮:小诸一带的女性将沉重的农活和家务视为自己的义务,“天没亮就起身”“天空刚发白就下地”,阿绫却“把家里当作玩乐的温泉旅馆,白天不做活,夜晚不休息”;当地的妇女崇尚艰苦朴素的生活——“连年轻的姑娘也要让她们满足于穿土布衣裳”,阿绫却“早打扮,晚化妆”“头发要由相生街的阿仙来梳,刮脸指定由冈源的老娘来刮,选料子的是大利的掌柜,做衣服的是马场后街的良助——真是豪华讲究到家了”;以及当地女性坚守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从来没有夫妻俩一块儿去赏过花,头一次看到老爷太太手拉着手,亲亲热热地在屋子外面走路,简直把她们吓坏了”,相比之下阿绫每天在家中睡到日上三竿,家务全交给女佣做,丈夫回家从不到门口迎接,还经常在丈夫面前随意发脾气甩脸色,甚至在贞操观念上也没有受到严厉的约束——婚后不久便和东京来的牙医发生了婚外情。
作者究竟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位东京太太的形象呢?[12]一方面从当时的散文和日记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岛崎藤村阅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思想上受到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虽然三年的小诸生活使藤村在创作上经历了由浪漫主义诗歌到自然主义散文的转变,并最终将小说确立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最合适的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作品中仍然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描写阿绫的不伦恋情时采用了大量的梦的意象,阿绫在作品中被塑造成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一辈子跟梦儿做了伴了”的女人,由于担心自己和牙医的恋情被丈夫发现,阿绫做了这样一个噩梦:
在一个好像是苹果园的地方,老爷在默默地散步,一个人好像影子似地悄悄走到他的身边,附在他的耳边说了些什么话。于是老爷大怒,张开两只手猛追太太。据说太太有两三次几乎就要被抓住了,最后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扔掉,光着身子才逃脱了。[4]205
从这个梦境来看,无论是苹果园、告密者(蛇)、还是赤裸的身躯都隐喻了圣经伊甸园的场景。岛崎藤村曾在明治21年至26年加入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中的故事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3]。例如伊甸园的意象曾被他融入到第一部诗集《嫩菜集》的《初恋》这首诗中,
你温柔地伸出白皙的手
将苹果娇羞相赠
这秋日里成熟的硕果
恰似我最初的爱情[14]
从句中可以看到藤村把恋爱的觉醒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并把恋爱的觉醒看作是人性的觉醒予以歌颂。在同册的最后一篇诗歌《逃水》中,他写道:
恋爱正是原罪
原罪也是恋爱[14]
这首诗在描写恋爱觉醒的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了罪的意识,暗示了藤村在恋爱思想上的转变。而彻底将恋爱的觉醒和原罪意识等同起来的则是在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落梅集》中,诗名就叫做《恶梦》:
不知何时
罪恶已深入骨髓
在我生命的舞台上
也会上演那样的罪吗?[15]
诗句描述了人骨子里刻着罪恶,以及生命中注定背负罪恶,这里的罪恶指的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好色、贪婪、说谎以及对金钱权力的追求等。那么在《旧东家》中,作者又希望通过阿绫的婚外恋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水田宗子在考察婚外恋题材的小说时曾指出:“当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靠自身来充实自己的时候,失落的自我便显出全貌,恋爱——通奸便成为充实自我的手段和自我审视的镜子。”[16]她指出了婚外恋的反社会性和排他性。19世纪是西欧传统婚姻观、家庭观动摇的时期,婚外恋意味着对传统的性关系、婚姻、恋爱、家庭观的批判和挑战。《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通奸小说批判了传统婚姻制度的伪善性。
水田宗子在分析男性作者创作婚外恋小说的意图时进一步指出:“婚外恋夫人是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来寻求性的满足的。换句话说,正因为婚外恋行为反制度,所以当事人认为这种行为既可以满足恋爱和性欲的需求,还可以满足自我,提供自我意识的根据”[16]85,于是作者就在婚外恋的太太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当时的日本,男性都是被社会化的,很难脱离社会体制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且婚姻制度给男性开了绿灯:即使明治民法中禁止了重婚,男子纳妾却并不违法,相反妻子若和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关系,则以通奸罪论处。因此作家只能通过刻画婚外恋的太太来体现一种超越制度道德标准的根源性道德,以及寻找到自我的存在。
太太是想到外面去散散心的,可是小诸是个勤俭朴实的小地方,茶道的先生搬到上田去了,谣曲的师傅改行到处去叫卖糖果点心,可看的可听的东西很少,仅靠家庭中有限的一点乐趣,当然一想起来就觉得腻烦。以至连绸子手绢擤过一次鼻子就扔掉;在卧室里到处乱撒香水;梳得好好的头发,只要不中意,马上就毁掉,让人重梳两次三次;自从吃惯了夜宵以来,在吃过咸糠腌的小菜加木鱼末的茶泡饭之后,还问“有什么更好吃的东西吗?”从新醉月餐厅叫来的饭菜,尝了两三口就喂狗了。女人的爱好简直是瞬息万变。太太对一切乐趣都厌倦了,整天嚷着烦死了。
“每天每天都是一个样啊!”太太靠在柱子上这么自言自语地说。轻浮的乐趣给太太的只是这么一句话。[4]186-187
从上文可以看出,阿绫的出轨是一种对小城镇单调枯燥的生活的反抗,阿绫认为自己“被人世的锁链锁住,身不由己地被人拖着走,天天过着梦一般的生活”。婚外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所以给日常生活带来一种刺激性,而阿绫只有在这种刺激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找到自我的存在。岛崎藤村通过描写这样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人的情欲本能与社会体制的对抗,这一方面体现出作者主张个人自由、赞美恋爱、肯定人性的浪漫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同样反映出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的固定观念。阿绫确实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但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任何高尚的东西——缺乏道德、贪图享乐、沉溺于官能、不能深入思考问题。作家没有赋予她思想和伦理上的高度,以便她能够超越精神和感官上的匮乏,最终只能陷入婚外恋的官能刺激中无法自拔,走向毁灭。与此相对,在《破戒》中同样受到制度迫害的男主人公丑松却通过告白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三、女佣阿定的叙述视角
作者采用一位农村出身的女佣的叙述眼光和声音来讲述主家的故事,最显而易见的效果就是凸显来自东京的太太阿绫与小诸当地女性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与戏剧冲突。例如农村出身的阿定在叙述中对节气的变化、农耕的时节和各种祭祀活动特别敏感,经常通过对季节转换的描述来刻画时间的流逝、推进情节的发展;东京出身的阿绫却“有时连日子也忘了,问我说:‘阿定,今天是几号呀?’有时看到墙上的日历,连声惊呼日子过得真快。”又如作品中描写小诸是养蚕的胜地,阿绫却“闻到蚕儿的味儿心里就恶心”,对当地女性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付之一笑”。
《旧东家》虽然以太太阿绫的出轨事件作为主线展开,但女佣阿定却不仅仅是事件的旁观者,更是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女佣身份的特殊性,作品中阿定可以相对自由地穿梭于农村与城市,主家的新宅与旧宅,家庭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对各个登场人物进行观察和描述,极大地扩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小说是以阿定的第一人称进行回顾性叙述的,但作者却没有将阿定塑造成一个客观的叙述者,而是利用她的身份立场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女佣主观的、带有阶级地域色彩的叙述声音。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能够发现,阿定的叙述立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本章将通过阿定的叙述特征和叙述立场的几次转变来分析作者的叙述策略和写作意图。
阿定初次见到太太阿绫时被其苗条的身段、姣好的容貌、精致的打扮所吸引,并且迅速从她漂亮的口音和白嫩的双手判断出她不是小诸本地的女人。阿定在太太面前对自己穷酸的打扮和娘又大又粗的手感到自卑,既羡慕阿绫年轻时髦的打扮,也羡慕老爷与太太和睦亲热的夫妻关系。随着在主家帮佣时日的增加,阿定慢慢对荒井夫妇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她注意到老爷和太太的婚姻并非表面上那么相称:太太阿绫很年轻,老爷却已经到了戴假牙和老花眼镜的年纪;太太的美貌连身为女人的阿定都感到心动魄摇,老爷却长着一副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满是皱纹的怪脸;再加上老宅的女佣人们嫉妒太太的美貌,造了许多关于太太的谣言,阿定朴素的正义感使她在情感上渐渐偏向了被本地人孤立的外乡人太太:“我一听这些关于太太的谣言,真把我气坏了”。
如果说上述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还没有超出一般女佣的身份立场和观察范围,那么阿定第一次明显的立场转变是从太太和她分享自己的秘密开始的:
“因为是对你,我才说啊。”说到这里,又吞吞吐吐不说了。
“今天晚上我跟你说的话,你要答应我跟谁也不说,就等于没听见。……不过,恐怕只有跟你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太太叮咛又叮咛,还好像有点儿说不出口的样子;一到好像要说的时候,脸蛋儿一下子红到耳根子。
太太终于放低了声音,跟我说了她的心里话。这时我才知道她跟牙科医生以前的关系。我的手被太太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我的脸不觉火辣辣地发起烧来。再没有比人家跟我坦露心里话而使我心软了。太太跟我一说她憋在心里的苦恼,我终于对她感到可怜起来。我深深地同情她的处境,给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太太一听我的话,像孩子似地啜泣起来。
我只好答应帮助她和牙科医生约会,这时我才意识到太太像火一般热的手放开了我的手。
……
有时候我也安慰安慰自己这种自我责备的心。太太的恋爱确实是不正当的,可她也确实太可怜了;她深更半夜背着人把眼泪流在床上,也没有个可以推心置腹谈心的女朋友。我一个人这么想想,也觉得宽慰起来。[4]190-191
从阿定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她对太太的同情源于一种年轻女性间的共情,为此她无视了山里人保守的风气,克服了自己背叛老爷的恐惧,与同她身份地位差距甚远的太太建立起了同性间的“姐妹情谊”。
世上的老爷们多么需要体谅跟他们一块儿生活的太太啊!——女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吧!尽管说是缘分,可是太太背井离乡,等于是出外的游人,却没有一个真正同情她的人。光凭这一点,一个女人也会活不下去的。太太真是不幸啊![4]191
但必须指出的是,促使阿定下定决心帮助太太与牙医偷情的关键因素并非仅仅出于这种女性间的“姐妹情谊”,其中还夹杂着无法忽视的经济上的原因:
他(樱井先生)是东京人,说他一看到这带格子门窗的新式房子就想起了首都。要说从东京来的医生我也见过,服装打扮都像演员似的,仪表堂堂的却不多。不过,唯有这位牙科医生我觉得还长得不错。
他来的时候总要给我带点东西,他回去之后,看门的老爷子的手中肯定要攥着一枚铜币。[4]188
……
“前些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送给你。”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往我手里塞。因为是晚上,那条紫绉绢的衬领看成好似豆沙色的。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不知道是要好还是不要好,一个劲地推辞。
“你要说不要,可叫我为难了。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为我们干活很勤快,很合我的心意。……好啦,你收起来吧。”[4]190
以及阿定在自述中意识到自己在外貌和心态上的转变:
我确实是变了。我一路上边走边想着自己,连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出来帮工以后的我和当年的我已经像换了一个人了。我在阔气的生活环境中住惯了,不知不觉地也学起太太的样儿来了。看起来我已经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了。当年我垂着发鬓儿,还有点孩子气,现在脑袋后面拖个雀尾巴,前发留得很宽,有空也对着镜子瞅瞅,偷偷地用剃刀刮脸,在澡盆里泡上很长的时间也没人说我,尽情地洗涤身子,连指甲缝里的污垢也要洗剔干净,有点儿爱美起来了。穿上太太赏我的那件漂亮的旧外褂,一定要衬上毛丝缎的领子,穿上短外褂时很注意领子上有没有脏;系好衣带去买豆腐时,如果不盖上一块小包袱皮,就会觉得丢人;醋瓶要藏在袖子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嘴里还吹响着酸浆果。当我觉得柏木的朋友有点土气时,往往就把娘也忘记了。哎呀!我对自己的变化也感到大为吃惊。出外帮工、辛劳艰苦似乎都已成为过去的事情。[4]207-208
从阿定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她的自我意识在帮佣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她在太太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习惯了舒适的生活,忘记了原本干农活时的艰辛,逐渐开始有了爱美的意识,学着太太打扮起来。她的眼光也不再是原来朴素的农村妇女的眼光了,而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与太太放到了同样的位置,将资产阶级奢侈的生活方式内化了,外出买菜时会在意路人的投向自己的眼光,不打扮一下就觉得丢人。阿定说自己“把娘忘了”,暗示着她忘记了自己的原有的身份立场,而是站在时髦的东京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乡,因此才会觉得“柏木的朋友有点土气”。
然而这种脆弱的“姐妹情谊”和虚假的“身份认同”随着太太同牙医艳闻的传开,很快就破灭了。太太对能够自由出入家庭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和老宅的女佣们沟通交流的阿定起了疑心,决心将她赶走,在老爷面前编造了许多阿定的坏话。在亲耳听到了太太对自己恶毒的污蔑,又目睹了与自己同样从柏木到小诸帮佣的阿继由于遭到主家的迫害而投水自杀之后,阿定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处境,导致其叙述立场发生又一次转变:
这件事使我太震动了。我们同样都是给人家帮佣的人,不能眼看着而没有任何同情啊!我心中的气愤、委屈都消失了,只觉得心头十分凄凉。
……
最初来帮工的时候,尽管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头一落枕头,一定习惯地想起柏木,在被子里喊着“娘!娘!”地睡去。后来我渐渐地把柏木忘了,只是偶尔才梦见娘。而这天夜里我的心又飞向了柏木。我从来没有像这天夜里这么想念过我的娘。……我的心里对东家家里的阔气的生活再也不感到羡慕了。我想的尽是柏木的事情。……我想着想着,热泪流出了眼眶,自己可怜自己地哭了起来。[4]208
此刻阿定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同太太并非处于同一立场,即使同样身为女性,她们的阶级也是对立的。无论阿定如何憧憬太太的生活,她都无法跨越主仆的身份,成为和太太平等的人。在太太眼里她不过是替自己承担家务的劳动力,以及帮助自己和牙医偷情的工具罢了。当太太需要她时会赏赐笼络她,一旦她威胁到太太的利益,则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此时阿定反复想起自己的娘的情景,暗示着她渴望回归生命的本源,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只有再次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从柏木来到小诸帮佣的贫苦的农村女性,才能帮助她找到自我,确立自己接下来行动的根据。
作者将阿绫对阿定的构陷及阿定向阿绫的复仇定义为“女人的本性”。然而结合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阶层的两位女性从互相帮助到互相攻击,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保”。作品中阿绫虽然依靠婚姻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她的原生家庭经济状况堪忧,父亲千里迢迢从东京来到小诸寻求老爷的帮助,身上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如果失去了老爷这个经济上的靠山,阿绫和她的家人可能会陷入贫困的生活。而阿定作为女佣,如果帮佣时落下不好的名声,在小诸这样风气保守的地方就很难再找到愿意接收她的东家。阿定若是失去帮佣的工作,就会像同村的阿继一样走投无路,即使回到柏木帮娘干农活也难以糊口,可能还会遭受爹的暴力。
作者通过女佣的叙述视角建构起了东京太太与农村女佣这样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实质上是将自己的创作放在“农村(传统)文化”和“城市(现代)文化”两种文化对比的价值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写作视角,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岛崎藤村出身于信州的名门望族,对农村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或复杂的乡愁,只能站在城市人的角度对农村作纯客观的描写。藤村的小说《岩石之间》曾被三好行雄评价为“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疲惫于城市生活而逃向农村的青年,然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农村体验后,青年发出了“百姓是百姓,自己是自己”的感慨,认识到即使亲自下地耕种,也不过是对农夫行为的表面模仿,根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自己只不过是个农村生活的旁观者罢了。
在《旧东家》中藤村同样是以城市(现代)文化的价值观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观照、反思和批判的。“山里人的守旧性格简直叫人可怕,见到一个跟他们稍微不一样的外乡人,就恨不得给人家迎头泼上一盆开水”,“乡下女人就是好奇,当太太花枝招展地从街上走过时,她们从土墙的窗户里看着,从格子门的洞里瞅着,挤眉弄眼地发出一阵阵邪笑”,“太太这位外乡人偏偏闯了进来,这只能叫人把她看作是带来了一片开化、奢侈的东京生活的闯祸精”,“所以外乡人太太反而比本地人老爷招来更多的憎恨”——这些乡下女人窥探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成了阿定复仇的武器,将沉溺于恋爱的太太逼入了绝境。作品中阿定的叙述立场虽然经历了几次转变,但从“这天晚上我就这么偶然起了一点邪念。——这也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常有的事吧。”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当叙述者阿定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的自己时,将自己帮助太太的行为定义为“年轻时犯的一个错误”,这明显是以农村人的道德观从批判的立场上进行叙述的。这也体现出了作者的写作策略——将农村陈旧的道德观念和保守的社会风气看作是自由恋爱的对立面,通过描写太太婚外恋的行为对其进行抨击和反抗。
四、小说结尾的双重构造
“行最敬礼!”——山岗子上会场里的叫喊声传到了屋子里。突然响起了外面的格子门被拉开的声音。
“我回来啦!”说话的是太太的老太爷的声音。
当老太爷叫第二声的时候,两个人睁大着眼睛回头一看,见到老爷默默地站在身后。太太已经来不及推开男的,伸了伸身子,脸色唰地一下变得煞白。牙科医生早已张皇失措,慌忙用左手顶着太太的下巴,右手作出象拔虫牙的姿势。
老太爷大概看谁也没有出来迎接,自己大踏步进屋来了,只听响起拉开纸拉门的声音,接着走廊上发出吱吱吱吱的声音。一阵恐怖感像闪电般从我的天灵盖一直贯通到我的脚趾尖。
这时屋外响起了一片震耳的喇叭声和大鼓声,几千人像象雷鸣般一齐高呼:
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4]213
在作品结尾处,阿定揭发太太偷情的当天正巧是冬至,红十字会北佐久总会在荒井家旁边的小学操场上举行集会活动,游行群众高唱着《君之代》的场景与屋内太太偷情的旖旎场面形成强烈对比,正当“行最敬礼”的叫喊声传入屋内时,格子门同时被拉开,千人齐呼“天皇万岁”的场景与太太偷情败露的场景在屋内外同时发生这一设定值得探讨与深究。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像的形成》[17]中指出:1891年,日本要求小学制定节庆日仪式规定,确定了“参拜天皇御照”“奉读教育敕语”“敕语相关的诲告与演说”等内容,“通过学校教育与青年团、在乡军人会等团体,天皇崇拜与国体观念逐渐深入国民意识,形成了一种共通的观念”,这意味着当时的小学是一个充斥着天皇崇拜思想的象征空间。作品中提到的《君之代》在1899年8月被日本文部省指定为学校必唱曲目,之后成为日本国歌。此外,“行最敬礼”的呼声来源于1900年文部省制定的小学校令实行规则中,有“对天皇御照行最敬礼的义务”这样的史实记载。这项校令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性、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同时将“忠君=爱国”“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植入人们脑中。
自1893年小诸义塾开办以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7年前后日本各地爆发了由大米价格波动引起的罢工运动,明治政府为了压制劳工的暴乱,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剥夺了民众的政治权力与思想自由;189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确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力,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抬头;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预示着儒家思想的复辟,以加强学校的思想教育为标志,日本迅速向专制主义国家转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岛崎藤村自1899年至1906年期间在小诸义塾担任教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所引发的小诸社会风气的剧烈变化,无疑会对创作于1902年的《旧东家》产生相应的影响。
小说结尾处阿定被屋外《君之代》的音乐所吸引,虽然看不清会场里的情况,却看到“许多农民从布幕后面往里瞅着,有的孩子跑到木栅栏上往里看”,会场的演讲内容阿定虽然不太明白,但“每句话还是听得很清楚,不觉听得入神了”。这个场景描绘了以阿定为代表的普通民众,虽然搞不清楚“近代”的实质,却仍然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冲击。作者将这个场面与偷情败露并峙的设定,揭示了作品结尾的双重结构:一是《明治宪法》中君主立宪与绝对君权并存所造成的国家体制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是近代婚姻中的矛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思想中的自由恋爱意识觉醒了,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复辟却使得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介绍婚在社会中普遍盛行。就如同荒井家那栋外观小诸风、内部结构却是东京式样的房屋一般,在彰显着天皇权力的小学操场上,却举办着象征人道主义的红十字集会,作品结尾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象征符号,隐喻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矛盾性,也暴露了日本近代化的虚伪性。
作者在描写阿绫通奸败露的场景时,将丈夫的目光、父亲的声音、以及门外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在同一时空中并列呈现的写作手法,象征着阿绫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在夫权、父权与君权三重压迫下彻底破灭。荒井夫妇婚姻关系的破裂和小家庭的崩坏,也隐喻了作者对扼杀了女性主体性的夫妻关系和婚姻制度的悲观态度。
五、小结
《旧东家》的先行研究普遍从性本能的角度解读阿定的行为动机,认为作品通过女佣的视线展现了男性的嫉妒与女性的欲望,将阿定的复仇理解为嫉妒、背叛与回归本性。但通过本论的一系列论证,可以看到阿定的意识转变是从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对美好事物和浪漫爱情的向往到逐渐被金钱诱惑、被权力意识扭曲的过程。小说的结尾实质上是两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自立能力的女性,出于对父权的恐惧而选择相互构陷、斗争的结果。阿定复仇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对太太的怨恨和报复,而是在资产阶级和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认清了自己身为底层女性无力反抗的悲惨命运,从而选择了依附父权——通过向老爷告密来保住自己的名誉与经济收入。阿定与太太乍看之下是处于两个社会阶层、互为对立面的女性,但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两个人同样是被榨取性(生育)价值与劳动(家务)价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牺牲品。
本论通过对女佣阿定的身份特征、叙述特点、以及女佣与太太二元对立的人物构造的解读,指出作品内部隐藏的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构造,揭示了在家父长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双重压迫下的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
——以《我是猫》作品中的女佣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