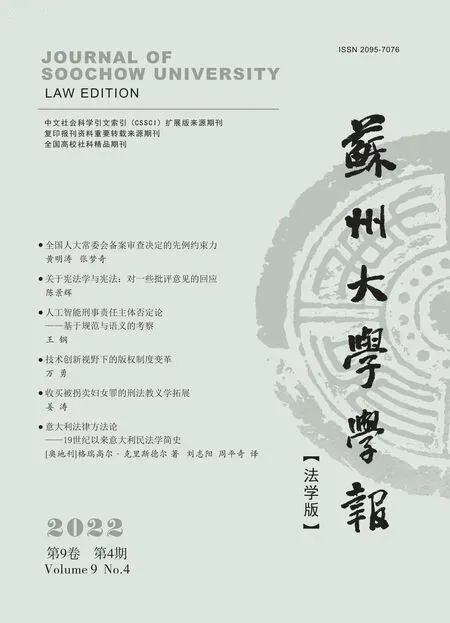中立的,还是全面的?
——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
翟小波
一、导论:问题与方法
陈景辉最近批评了“宪法是其他法的总原则”或“立法是宪法的具体化”的命题。①(1)①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5-304页。后文提到陈景辉的观点,除非指明出处,皆以此文为根据,不再标明页码。他说他在为宪法功能寻找新方向,在提出关于宪法性质的完整理论。他考察了一些关于宪法的共识性命题,强调宪法与其他法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具有被其他法具体化的逻辑可能性。陈景辉是在为传统宪法概念(姑且称之为中立宪法,下文会解释这个命名)做理论的说明和辩护。但具体化论者会反驳说:他们就是要质疑中立宪法的概念;宪法正在经历范式变迁,正在成为其他法的总原则。“总原则”或“具体化”命题依附于一种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即全面主义。通过阐释、批评和补充陈景辉的讨论,本文对宪法全面主义提出初步商榷,说明有限的法律宪法主义并为之辩护。
本文是对宪法的性质的初步讨论。该议题涉及宪法的功能、地位、必要内容、规范的结构和性质、正当性根据、效力(或存有)、形式、实现(或实施,即约束力的来源)、与其他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对宪法性质的探讨不等于对理想宪法的探讨,前者是一种说明性理论,后者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但前者对后者是有意义的。比如,理想的宪法首先必须是宪法;为了确定某个东西是宪法,首先要明确宪法是什么。因为宪法是内嵌了价值的东西,这种说明性理论不是价值无涉的。宪法是在性质上自成一类的规范体系,不具备这种独特性质的东西不是宪法。否则,会导致无心或有意的语用或概念混乱,妨碍理论、价值和制度的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宪法典不等于宪法。第一,无宪法典(如英国)不等于无宪法:核心的宪法内容不必形诸文书。第二,宪法典里常有与宪法无关的条文,比如植树造林、禁止杀牛或饮酒。第三,有宪法典不等于有宪法,宪法典有时是假的,如毛泽东曾说,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和徐世昌的宪法是“假东西”。①(2)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6页。法典化有认识论价值,宪法的法典化有助于社群认知宪法,从而有助于围绕宪法典形成关于宪法的公共舆论。但这种价值是工具性的。宪法惯例如果为众人所知晓便不必法典化。因此,本文不是在讨论特定社群里被叫作宪法的东西或实践,不是在讨论宪法典。这些受到特定时空下的考量或偏见的左右,很可能是专断的或偶然的。
探究宪法的性质不完全等于探究宪法的概念。一个社群,即使无宪法概念也会有宪法,但宪法概念的缺失反映了该社群宪法的原始性。宪法概念是对宪法性质的认知,典型的宪法是在宪法概念的指导下发展的。本文会诉诸代表性的宪法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反映了相关权威学者所认识的宪法性质。有学者会通过词源学的考察来理解宪法性质。本文拒绝这种方法,因为词语代表的概念,与它的含义或它的词源呈现的物象,并无必然关联。
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不等于学者关于宪法的主张。关于社会实践之性质的理论,是由说明该实践之典型属性的命题构成的自洽体系。关于该实践的主张,第一,未必是关于它的典型属性的;第二,时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对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关于宪法的主张必然有意无意地预设了某种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也潜含了关于宪法的主张。对本文的批评,“我没有这么主张过”不是适格的反驳,因为笔者可以回应说,“你的主张必然地预设了关于宪法性质的某个命题”。
除了“导论”外,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修正和补充陈景辉对宪法性质的共识性命题的讨论,旨在对宪法性质提供更完整的说明。第二部分简述宪法全面主义的主要命题。第三部分是对它的商榷。以这三部分的讨论为基础,本文主张,应该放弃宪法全面主义,坚持中立宪法概念和有限的法律宪法主义。②(3)②关于法律宪法主义以及与之相对的政治宪法主义,See 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Hart Publishing, 2005, pp. 10-25;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汉语学界的讨论,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田飞龙:《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二、中立的宪法
关于宪法的性质,学者们有不少分歧,他们也有共识,而且有些分歧预设了更基本的共识。这些共识,表达了宪法的最低限度的必要属性。为了与全面宪法相区别,笔者把有且只有这些共识性属性的宪法称作中立宪法。
陈景辉从三个共识出发,即概念命题[宪法是法体系的概念必然(conceptual necessity)]、实在法命题和价值命题(宪法体现社群的价值共识)。实在法命题又包括两组:第一组包括最高性命题与合宪性审查两个子命题;第二组包括稳定性、成文性和刚性三个子命题。
(一)宪法的构造性、法治与宪法的最高性
独立的政治社群必然有主权;主权的构造会涉及实在规范(如涉及主权者的内部分工或程式的安排、主权的继承等),但并不必然以实在规范为根据,而是经常以强力为根据。换句话说,从与实在规范的关系来看,主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臣民的服从为原因,其构造涉及实在规范的主权;另一种是由实在规范构造的主权。前者可称作事实主权,后者可称作规范主权。下文所说的主权,除非特别指明,皆为规范主权。
一个规范主权或一个法体系必然包含一部宪法;宪法是主权或法体系的构造性(constitutive)基础,是法体系之存在的必要条件。此即陈景辉的概念命题,它内含了“法治”命题,即主权者受宪法控制(是控制,不是限制)。否则,就无宪法,也无法体系。在本文中,“主权者”包括两类实体:第一是拥有有限主权的人民,作为间歇性主权者;第二是日常最高权的拥有者,笼统地称为最高立法者。
概念命题是二元的:宪法构造并控制主权者。第一元是构造性命题,即通过确立基础性价值、机构和程序,宪法构造了主权者和法体系。这种构造可以是自觉的、建构性的,也可以是自发的、习惯性的。这种构造的内在方面是宪法,外在方面是国际公法中涉及主权者存在的规范。一个完整的法哲学要包含关于宪法与国际公法的理论。第二元是法治命题。宪法是与专制相反的。专制没有法治,没有宪法,①(4)①Paine说,宪法“界定(defines)人民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从而控制它”。See Thomas Paine,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2),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PS Foner, The Citadel Press, 1945 , p. 990. McIlwain说,宪法“创造、界定和控制政府”“宪法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控制;它与专断统治(arbitrary rule)是对立的。”CH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21-22. Karl Loewenstein说,宪法构成对主权者的有效控制,对臣民的有效保护:它不仅是有效力的,而且被忠实地服从和遵守。See CH McIlwain, Constit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West and in the East, 30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3, 212-213 (1969). Nino说,“每个人都接受,宪法是指有限政府”;宪法最薄的意义是与法治的基本观念相联系的。SC Nino, The Constitu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See also KC Wheare, Modern Co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02; CJ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Ginn and Company, 1941, p. 131;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outledge, 1993, p. 1. 1906年,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在“奏请张君权折”中曾说,“我国固立宪之祖国也。”刘御史以“二典、三谟之记载,夏书、商誓、周礼六官之典要”为例证,认为清朝为“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109页。像刘御史这样,认为宪法就是政体(politeia或regime)或者含有某些权力制约要素的政体,中国为“立宪之祖国”,秦朝或清朝为“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第一国”,在汉语学界——尽管不是在宪法学界——有一定代表性。这种观点,通过语义的混同,使宪法成为可以与“政体”互换的概念,这实际上取缔了宪法这个概念或使这一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和价值遭到了摈弃。这种观点不是宪法学界或实务界的共识;相反,它背离了这些共识。宪法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作为它的规范对象的主权者和规范方式的法治都是历史的产物。Dieter Grimm, Constitu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 1, pp. 3-37. 宪法是近代的法制成就。并不是一切社群都有宪法,以基础性自由和民主为内核(详见下文)的法治是宪法的必要属性;一个社群有宪法的前提是这些基础性自由和民主成为这个社群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秦朝古代没有宪法,因为皇帝“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汉朝没有宪法,因为“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杜周)。英国是宪法的母国,她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或普通法宪法的典型。美国1787年宪法和法国1791年宪法是成文宪法的典型。在中国,宪法概念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传入的。也没有法体系,尽管可以有法律。②(5)②关于法治与法体系的关系,See Jeremy Waldron, 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 43 Georgia Law Review 1, p. 19-36 (2008).人性是自我优先的,不受宪法控制的主权者及其官员必然会公权私用。“宪法控制”的说法只是对表面现象的描述:宪法只有通过一套动机和力量系统才能控制主权者。这套动机和力量系统是由社群信仰、分工制约和民主责任体制等来提供。
宪法构造并控制主权者或法体系,这表明宪法是最高法或根本法,此即陈景辉的“最高权威命题”。宪法的最高性有积极和消极方面。从积极方面说,宪法是构造和控制主权(或最高权)的法,这是它与其他公法(如行政法)的差别。最高权来自宪法(即承认和改变规范)直接的授予;其他的公法主体的权力是由法律授予的;相对于后者,最高权可以说是原生性的。宪法与其他公法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别,宪法不是高级行政法。③(6)③John Gardner, Law as a Leap of Fa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8.最高权的典型是最高立法权,也包括人民的有限主权。宪法也构造和控制最高行政和审判机关,但它不干预最高行政和审判。从消极方面说,最高法是防御性概念,它防御主权者(或人民的多数)这种难以抵抗的对手。①(7)①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ol. 2), ed. by John Bowring, Edinburgh, 1838-1843, pp. 270-271.宪法处于法体系的效力链条的顶端,主权者的法律与政策亦不可以违反它。宪法作为最高法要求设立特殊的护宪机构,普通审判机关难以保护它。
以上是对陈景辉的概念命题和最高性命题的说明、补充和诠释。但是,笔者认为,陈景辉提出的概念命题过于宽泛。宪法不仅预设了通常的法治,还被普遍确信为是自由的法,它必须要确立和保护基础性自由。所以,一个规范主权或一个法体系并不必然包含一部宪法: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宪法也不是规范主权或法体系的构造性基础,它只是自由的法体系的构造性基础。
(二)宪法的内容、正当性根据、效力及宪法的后设性
宪法构造和控制主权者,但其内容高度稀薄,只有两项。其一是最高权的组织、权限及程序(下文也称为“政治过程”)。其二是基础性自由,它们构成政治过程的基础,也为它确立了不可逾越的边界。②(8)②“二战”后,制定成文的权利清单成为醒目的世界潮流,但作为宪法的内在要素,基础性自由早就贯穿于英国的普通法宪法、美国和法国的成文宪法之中。基础性自由有两类:一是消极自由;二是政治参与权。宪法的最高法、根本法地位直接地取决于它内容和功能之于法体系的基础性和优先性。这不是说世间只有宪法最重要,也不是说要把最重要的东西都放进宪法里:这将使宪法不再是“宪法”。
宪法的最高性,间接地但也更根本地取决于它的正当性。③(9)③拉兹认为,关于宪法权威的理论是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的必要部分:它“解释宪法之为正当的条件,从而确定公民有义务服从它的条件”,旨在“提供对作为宪法根基的政治道德原则的论述:宪法的强制实施要依据这些道德原则而得以证成。”Joseph Raz, On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s, in Larry Alexander ed.,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7. 对宪法的正当性的各种理论的检讨,See Andrei Marmor, Are Constitutions Legitimate?, 20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69, p. 69-94 (2007).陈端洪认为,宪法的正当性在于它表达了人民意志。④(10)④陈端洪:《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载《清华法学》2016 年第3期,第5-25页。陈景辉认为,宪法的正当性在于它表达了特定社群的价值共识(或意识形态或文化)。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宪法是超越政治过程的最高法和根本法,旨在规范或引导多数意志或共识。一个观点或意志是多数人的,这并不表明它们是有价值的;由他者强加的宪法未必不正当。正如夏勇所说,宪法的正当性应该“从关于价值原则的哲学角度来找寻”⑤(11)⑤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宪法的根据是某种道德实在主义(moral realism)。⑥(12)⑥WF Murphy, 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D Greenberg et al. ed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 See JG Murphy, Constitutionalism, Moral Skeptic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in his Retribution Reconsidered: More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w, Springer, 1992, pp. 167-179.
宪法的正当性根据不是社群的意识形态,但后者决定了社群有没有宪法。“宪法的正当性根据”和“社群有没有宪法”是两个问题。作为道德真理的宪法性价值,如果转化成了社群的意识形态,该社群就有宪法;反之,它就没有宪法:“宪法之所以是宪法,不是因为某人制定了它,而是因为它被接受了。”⑦(13)⑦Ivor Jennings,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59, p. 117.笔者把这称为“意识形态命题”。宪法的正当性根据命题回答宪法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意识形态命题回答宪法的合法性(legality)问题或效力问题,也回答宪法的实效问题。宪法的效力来自它的实效,宪法的效力与实效是统一的——这是宪法与其他法的差别之一。意识形态命题与宪法的形式及保护者紧密相关。
对作为宪法正当性根据的基础价值,一些人诉诸“个人尊严”或“自主性”,另一些诉诸“幸福最大化”,但这些不同说法背后也有共识,即个人的中心性,⑧(14)⑧See The Preamble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主要体现为基础性自由的根本性。潘恩说,“宪法之于个人自由,正如语法之于语言。”弗里德里希说,现代宪法秩序植根于“对个人之神圣性的信念”;①(15)①Thomas Paine,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vol. 1), The Citadel Press, 1945, p. 300; Carl Friedrich, Transcendent Justi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7, 19; Carl Friedrich, Limited Government, Prentice-Hall, Inc., 1974, p. 123;WF Murphy, 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D Greenberg et al. ed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 6.宪法在肯认个人之神圣性的同时,也强调人性中有阴暗或丑陋的面向。②(16)②Carl Friedrich, Limited Government, Prentice-Hall, Inc., 1974, p. 123.
基础性的宪法自由包括:做出无关或无害他人的行为的自由;良心与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和迁徙自由;免受酷刑或奴役的自由;法律的平等保护;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平等的政治参与权。③(17)③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139-140; Jeremy Waldron, Participation: The Right of Righ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98, 1998, pp. 307-337 ;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73;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35.这些基础性自由,第一,给个人保留了一片自主空间,防止最高权的侵犯;第二,使得个体可以平等参与政治。它们一起赋予了社群成员以平等的公民资格。④(18)④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00.
宪法的政治过程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主权归属的规范,即人民的有限主权;第二是关于最高权的组织和运作的规范。后者又隶属于两大原则:第一是分工制约原则,第二是民主责任原则。在这些原则的范围内,政治过程的安排(例如,何种选举制度,何种模式的分工制约,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宪法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等)呈现历史性和民族性,相关社群有不小的选择余地。
基础性自由、人民的有限主权、分工制约和民主责任等规范,一起构成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⑤(19)⑤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00, 173, 197.它们是凌驾于政治过程的高级法(higher law)。这些宪法根本是法律宪法主义的范围。除此之外,宪法把法律(非基础性权利)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等交给民主过程,这些是政治宪法主义的范围。
陈景辉把作为宪法正当性根据的基础价值称作二阶或后设价值,把宪法根本称作二阶或后设规范。一阶规范直接调整人们的行为,二阶规范直接调整一阶规范的识别和生长,间接调整人们的行为。陈景辉说,“宪法就是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二阶规则……它的改变其实就是社会成员社会实践上的改变。”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作为二阶或后设规范的宪法根本,在有宪法的社群里,被下述两类规范接纳:第一是义务性承认规范。它们是不成文的,默存于社群的政治实践中,属于基础性宪法惯例。第二是呈现为授权规范的改变规范。⑥(20)⑥Kent Greenawalt, The Rule of recogni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and Jeremy Waldron, Who Needs Rules of Recognition?, both in Matthew Adler and KE Himma eds., The Rule of Recognition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6, 327-349. 之所以说“呈现为”,是因为任何真正有意义的授权规范都要通过义务规范(命令)来落实。承认规范和改变规范的地方性并不阻碍它们对道德真理的接纳。它们是关于一阶规范的效力条件的规范,是法之法,处于法体系的效力链条的顶端。
笔者赞同陈景辉提出的“作为宪法正当性根据的基础性自由是二阶价值”的观点。但这不是说这些价值是道德无涉的或程序性的,而是说:第一,它们与关于资源分配的价值不在一个层面上;第二,它们构成了价值多元或分歧的基础或环境;第三,对价值多元或分歧,它们保持中立,此即“中立宪法”之由来;第四,它们是关于如何解决价值分歧的价值,即为价值分歧之解决方案的生成设置边界、提供程序,但不直接、积极干预这些解决方案的内容。⑦(21)⑦姜峰对“基本权利的目的”的讨论。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05-108页。与关于资源分配的价值相比,这些基础性自由,内容稀薄且简明,应该被载入宪法,获得刚性保障(entrenched)。对它们的初步(prima facie)保护适合交给由宪法专家主导的违宪审查。
对宪法的后设性的理解是渊源有自的。边沁说,宪法之外的其他法是直接作用于(immediately operative)臣民的法,而宪法是间接地、遥远地作用于(remotely operative)臣民的法,它确立最高级统治机关或人员的职权。①(22)①Jeremy Bentham, Economy as Applied to Office, in Jeremy Bentham, First Principles Preparatory to Constitutional Code, ed. by Philip Schofie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3, 37; Bentham, A General View of a Complete Code of Laws, in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3) , ed. by John Bowring, Edinburgh, 1838—1843, pp. 195-220; also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9) , ed. by John Bowring, Edinburgh, 1838—1843, p. 9; Jeremy Bentham, Lea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de, in Jeremy Bentham,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2) , ed. by John Bowring, Edinburgh, 1838—1843, pp. 270-271.宪法和臣民的关系更像是邦联关系:它通过其他法间接与臣民发生关系,不可以越俎代庖。霍姆斯说,“我们的宪法是空洞的,我们的宪法是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很不相同的人们制定的。”宪法“不是某种伦理或经济学说”。②(23)②Lochner v. New York (1905), in Max Lerner ed.,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p. 149; Otis v. Parker (1903), in RA Posner ed., 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304. 另见[奥]凯尔森:《纯粹法学说》,[德]马蒂亚斯-耶施泰特编,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45页;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Routledge, 1982 , p. 113;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39;JH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01.
因为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是道德真理,因为它们是二阶的或后设的,因为在有宪法的社群里,宪法根本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所以宪法是超级稳定的。宪法典通常会为宪法修改规定特殊程序。如果社群的宪法根本可以被轻易修改,这个社群便没有宪法。
(三)宪法的惯例性
在宪法是否必须是成文的这一问题上,陈景辉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说任何法体系都包含宪法,另一方面又认为宪法就是《宪法》,成文性是宪法的属性之一。这是值得商榷的。很多法律部门在形式上都是二元的,包含成文和不成文规范。与这个区分紧密联系的是“惯例”与“法律”的区分。法律是指可以典型地由法院来强制实施的规范。惯例是被官员或民众“共信共守”的习惯、默契或共识,它的效力不是来自它被适格权威制定的事实。就此而言,它通常是不成文的,③(24)③See Ivor Jennings,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59, p. 80.虽然法院也经常承认和适用它们,但不可以强制实施它们。不过,这不表明惯例的约束力弱于法律。
对宪法(还有国际法)来说,这种“成文和不成文”与“法律和惯例”的二元性具有特殊意义:宪法、刑法和民法是适合也应该被法典化的,但宪法惯例在范围或意义上都大于宪法法律。龚祥瑞先生甚至说,宪法惯例是“真正的宪法”。④(25)④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0页。宪法惯例的特殊意义与宪法的性质相关。⑤(26)⑤宪法惯例是优越的宪法变迁方式:通过旧瓶装新酒,它们使形式上专制的宪法在无形之中被民主化。第一,宪法是最高法,它们必然先于且超越于可以书写宪法的权威,必然首先体现为惯例或社会实践,⑥(27)⑥如Neil MacCormick所说,“某个习惯性或惯例性的基本规范是整个宪法结构的必要的规范性基础”。Neil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9; John Gardner, Law as a Leap of Fa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8-119.因为在主权者存在之前不存在书写宪法的权威,尽管宪法规范事后可以被形诸文书。这也解释了对宪法惯例的违反为什么经常导致对法律的违反,因为前者经常是后者的基础。第二,宪法根本的效力源于它们的实效:社群有没有宪法,宪法可否控制主权者,不取决于宪法有没有被书写,也不取决于作为主权者的官方建制(official establishments)的违宪审查。宪法必须被最高级官员接受,被转化成最高级官员的实践,转化成该社群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⑦(28)⑦Jennings,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59, p. 116; Neil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6.一旦宪法根本成了社群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就获得了动机力(the motive power),⑧(29)⑧Jennings,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59, p. 83 .获得了稳定性和约束力,书写也就不再必要了,违宪者将被视为异类而被放逐(social ostracism)。
三、全面的宪法
作为对宪法性质的认识,中立宪法的概念依然为学者所坚守,虽然他们未必认同笔者对相关命题的分析。一些国家的宪法实践(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典型代表)和一些学者不放弃这些命题,但不满足于它们,提出了宪法全面主义。①(30)①Mattias Kumm, Who’s Afraid of the Total Constitution, 7 German Law Journal 341, 341-369 (2006). 陈景辉用“宪法作为法体系的总原则”来概括它。其基本观点包括:
1.全面积极具体化。这是关于宪法与公权力(特别包括立法和司法)之关系的主张之一。宪法是全面的客观价值体系,它向公权力不仅提出消极不抵触的要求,还提出积极实施的要求。它要通过公权机关的行为积极地从实体上来调整和塑造其他一切法(包括私法,即间接横向效力)和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私人关系,即直接横向效力)。立法和司法机构要对宪法价值和自由做扩张性、积极性诠释,从而使宪法积极地辐射整个法体系和社会关系,在所有领域得到主动的落实。
2.母法。就宪法与立法的关系来说,宪法是母法;宪法不只是其他法之制定的权限和程序的根据,还是内容的根据。其他法的制定是宪法的规范、原则或精神的具体化。②(31)②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7-29页;王利明:《何谓根据宪法制定民法?》,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3页;韩大元:《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151页。以此为基础,张翔最近提倡“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③(32)③张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99-103页。
3.合宪性解释。这是关于宪法与司法关系的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要符合宪法。当法律规范有多种解释可能性,而某些解释使该规范违宪,另一些使该规范合宪时,解释者应选择后者(排除违宪式解释)。不仅如此,还要用宪法精神来引导法律解释,使宪法精神贯穿法律解释,推进法体系的宪法化(明确含义式解释)。合宪性解释是宪法的进一步具体化。④(33)④详见上官丕亮:《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26-28页;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9-30页。在此,可预先提出若干技术性质疑。第一,如果法律规范已是宪法的具体化,对它的违宪解释怎么可能?有必要对它做合宪解释吗?这种解释如何区别于违宪审查?它是不是已预设了立法并非对宪法的具体化,或这种具体化失败了?第二,如果司法与立法都是宪法的具体化,这两种活动还有差别吗?如果某实在规范N已是宪法规范C的具体化了,为什么要把C再具体化一次呢?
4.部门法(学)宪法(学)化。部门法要向宪法看齐,要把原本的部门法讨论转化成宪法内的讨论。⑤(34)⑤详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31-32页。
5.直接适用或宪法司/私法化。宪法不仅要在对法律开展违宪审查的过程中被直接适用,还要在公民生活中被直接适用;法院可以用宪法来直接裁判案件,包括私人纠纷。⑥(35)⑥参见蔡定剑:《宪法实施途径探索——论中国宪法的私法化之路》, 载蔡定剑:《论道宪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6-100页;王禹:《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陈景辉也在这种意义上说,“宪法不能司法化,即宪法不能成为普通诉讼的裁判根据,除非它表达的就是合宪性审查的意思。”
关于具体化的含义,有必要在此做一些分析。宪法全面主义认为,一切公权行为都应该是宪法的具体化。立法、合宪性解释、部门法宪法化和宪法司/私法化都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全面主义把宪法变成法体系内所有实在规范的唯一来源:⑦(36)⑦Stephen Gardbaum, The Place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al System, in 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as Saj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3.“整个法秩序都已被包含在宪法之中了……具体化便是它现在所要求的一切。”⑧(37)⑧EW Bockenfo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M Kunkler and T 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58.但是,什么是具体化呢?主张具体化的学者不曾对这个关键术语做出专门说明,由此可以推定,他们是在通常的词典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具体是抽象的反面;具体化是指其他法、公共政策或决定的制定、解释和适用是从宪法的实体内容出发,以之为根据,推导出在特定实践中适用的个别规范的过程;具体化是抽象的宪法规范在特定实践中的个别化。
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对“具体化”的界定太严格了。如果不应该这样界定“具体化”,它又是指什么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宪法规范要不要在实体内容上积极地形成其他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笔者的界定就是正确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会认为,其他法的实体内容取决于政治意志,宪法只是确定其他法的制定主体、程序和在实体内容上不可逾越的疆界。这样一来,关于宪法的性质,宪法全面主义者与笔者就没有实质分歧了。下一节对宪法全面主义展开具体商榷,笔者在此先要指出,具体化命题没有对不同公权力(如立法、司法和行政)在属性上的差异给予应有的关注,混同了它们。①(38)①参见EW Bockenfo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M Kunkler and T 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58-259.
四、对宪法全面主义的商榷
陈景辉和姜峰拒斥了全面主义,前者称之为宪法总则说,后者称之为宪法全能论。夏正林说的“现代公法宪法观”加上“根本法宪法观”,与这里的全面主义类似,他提醒学界要警惕之。②(39)②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108页;夏正林:《从基础性权利到宪法权利》,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8-43页;夏正林:《论两种宪法观念下宪法与部门法的三种关系》(未刊稿)。另外,夏勇、马岭、王锴和杨洪斌等(以时间为序)也对类似理念有过批评。参见夏勇:《当代中国宪法改革的理论思考》,载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90页;马岭:《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三章,第223-355页;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42-50页;王锴:《论文化宪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0-48页; 杨洪斌:《论限权宪法——从历史的角度重思宪法的概念》(未刊稿)。其中,王锴的观点有些复杂,他反对私法的宪法化,却支持部门宪法学(如文化宪法)。宪法全面主义是法律宪法主义的极端形态,在宪法概念史上,它是很新的,却是值得商榷的。
(一)部门法的自主性与法体系的“联邦”性
陈景辉认为,具体化命题导致其他法的冗余性:如果其他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只要宪法就够了,其他法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有人会反驳说,具体化并不导致其他法的冗余性:抽象的宪法条文对行为的引导,要借助于更具体的立法;法律适用的一项原则是穷尽具体规范、禁止向抽象规范逃逸;作为宪法的具体化,其他法是有使用价值的。即使这种反驳成立,它最多证明了具体化有使用价值,但否定了其他法的自主性,导致了其他法在存在根据上的冗余性,甚至沦为宪法的实施工具。这不是对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的正确认识。
其他法与宪法的关系,应该服从越权无效原则,这是共识。法律通过改变动机或理由来引导行为,它是内容无涉的功能模式(a mode of function)。根据解决的问题和用以引导行为的价值,法律获得了不同的内容,分化为多元的部门。每项法律、每个法律部门或子系统都有它要解决的问题,有它秉持的价值,有它独立的原则和知识体系,有它自主且开放的回应环境变迁的方法论。在内容上,它们既要服从普遍原则,也要因应地方情势。一些法律,如典型的民法和刑法,主要是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下的直接或变通的适用,受政治过程的影响小;另一些法律,如政策性强的社会法,虽然也涉及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但受政治过程的影响较大。
对法律的生成和发展来说,宪法的相关性在于:第一,消极地防控它们违反宪法根本;第二,界定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被采纳或变通的程序。宪法以这两种方式构成了部门法自主性的前提或环境。对其他法实体内容的确定,宪法不发挥积极的形成性作用。宪法内容的高度稀薄性和简明性,宪法的二阶性和消极防御性,共同成全了部门法的自主性。法体系的结构是联邦性的,而非单一性的。①(40)①“法体系的联邦性”这个说法是陈景辉首次提出的。中国的民法、行政法或环境法等在内容上与其他国家相应法律的相似性,远大于与中国宪法的相似性。在同一法律或部门法内时常会有规范冲突,这种冲突不必也无从诉诸宪法来解决。一些法谚也说明了类似道理,如波塔利(JEM Portalis)说,公法消逝,私法长存;托克维尔曾说,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②(41)②转引自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Routledge, 1982 , pp. 135, 178. 奥托·迈耶也有类似说法,详见陈新民:《宪法与行政法之关联》,载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287页。
其他法相对于宪法的自主性,还得到历史的支持。民法或私法学者经常诉诸历史论证,说民法不是宪法的具体化:民法的诞生先于宪法;民法的存续在时间上也经常超越宪法。同理,普通法也不是宪法的具体化。陈景辉认为,历史论证是不重要的,其局限在于它无法解释晚于某宪法而生的其他法是否具有相对于该宪法的自主性。对这一批评,可以作如下回应:如果晚于某特定宪法而生的其他法的生命,超越了该部宪法或它的重大修正案,历史论证就可以表明这个法律的自主性。所以,历史论证是重要的,它确实挑战了具体化命题。张翔对这种历史论证提供了一个同样是历史性的回应,认为即使某法律的诞生在时间上先于某宪法,在这个宪法存在之后,该法律也要宪法化、向宪法调整。这个回应如果要成功,须证明:第一,这种向宪法调整,是全面的、以积极具体化的方式展开的,而不是局部的、以消极不抵触的方式展开的;第二,这个法律的生命不超越宪法。这里的论证负担几乎是难以承受之重。比如,陈景辉就反驳说,这种调整是违宪审查式的,③(42)③《陈景辉 张翔 翟小波 李忠夏华政“互殴”实录|宪法的性质》,载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2021年4月28日。如在香港、澳门回归时原有法律向基本法所做的调整。
1.宪法与私法
在与其他法的关系中,宪法与私法的关系值得专门讨论。本小节是以私法为例对前述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展开具体说明。起草者可以在宪法典中写入私法条文,正如他可以随心所欲在其中写入任何条文。但这种做法是错误和有害的。
第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公法与私法的差异源于各自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差异。公法与私法调整的关系不一样,它们规范的主体、内容、价值与原则、性质、产生与发展、运作与实施机制也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就不应该把它们混同在一起,更不应该把私法规范放进宪法内并将它们叫作宪法规范。比如说,公权机关拥有集体性力量,这种力量应该被用来为公众谋福利;私人只拥有个体性力量,追求私人幸福无可厚非,除非伤害他人。在面对公权力时,即便跨国大公司也不堪一击。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不可以被当事人协议变更: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权机关还要负民主责任。私法调整平等主体基于自愿而产生的关系:法无禁止即自由。④(43)④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私法的基础性价值是意思自治——这为个体人格的充分发展所必需。⑤(44)⑤[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也见[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判定宪法基础性自由与私法权利的标准固然涉及权利的内容,但更在于这些权利所处的关系:关系不一样,权利的存在根据、范围、潜在受侵害的程度(如立法的侵害是普遍和持久的)和方式、被保护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与作为私法权利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就有天壤之别。今天,很多法律已很难再被纯粹地归为公法或私法;总体上是公法的制定法或部门法通常包含很多私法规范,反之亦然。⑥(45)⑥如《民法典》里有很多公法规范,如第494条关于强制缔约的规定、第153条关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等。但是,这种公私规范的混杂共处,并不表明它们性质的混同。
第二,私法原则上是“正当行为的普遍规则”,它们源于而且构造了独立于公权力的自生秩序,⑦(46)⑦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Routledge, 1982, p. 31.较少受时空或政治的影响。相反,宪法中具体的政治过程规范,有不小的政治性和民族性,易受也应该受社群具体意志的影响。这解释了为什么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程序在制宪问题上有独特重要性;对私法规范的产生和发展,民主程序则不具有同等重要性。比如说,德国和法国的民法(甚至是刑法)的共同性要远大于这两国宪法的共同性。密尔批评边沁不从制度与民族性的关系中来考察制度,但他旋即强调,边沁对制度与民族性的关系的忽视,对他的民法和刑法理论影响并不大,但对他的宪法工程影响甚巨。①(47)①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10), ed. by J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65—1991, p. 105.
第三,直接调整私人行为的规范是一阶规范,作为最高公法的宪法是二阶规范。私法先于公法而生。对于私法,公法是辅助性的:公法的目的之一是发展、保护和加固私法秩序;私法秩序之维护和发达有赖于公法。宪法的基础性自由筑造私法秩序或私法权利的环境。从私法到公法、从一阶规范到二阶规范的变迁,是从原始法规范到发达法体系的发展过程。如哈耶克所说,宪法是用来维护先在的私法秩序的上层建筑,而非所有其他法的渊源。②(48)②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vol. 1), Routledge, 1982 , p. 134.如边沁所说:“如果私法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有没有宪法这种东西,该如何对待宪法,便已根本不重要了。”③(49)③UCL图书馆收藏的边沁手稿:UC clxx. 199 (1785).宪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像是联邦关系,宪法和公民的关系像是邦联关系。全面主义把宪法与其他法及宪法和公民的关系都当成了单一制关系。
第四,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法律真理,有实际功用。如麦基文说:“罗马人对宪法最伟大的永恒贡献之一,是他们对公法和私法做了最明确的区分……该区分构成了保障个人权利反对政府侵犯之法制保障的全部历史的基础。”④(50)④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48.宪法是构造和控制最高权之法,而非治民之法。中立宪法成全、承认和尊重公私界分,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因此而豁免于统一的强行性宪法管制,即公权力以宪法之名而实施的管制。中立宪法接受私法的优先性和自主性,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独立性、私人领域的自治性、自由市场和联邦主义。⑤(51)⑤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雷磊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第75页;Stephen Gardbaum, The Place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al System, in 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as Saj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7-178.全面宪法则与此相反,它在很大范围内把宪法混同为治民之法:它要求公权主体用无限膨胀的所谓尊严、平等和言论自由等价值来干涉和取缔契约和财产自由。⑥(52)⑥参见 Ju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he MIT Press, 1996, p. 246.比如说,依照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全面主义否定侏儒有自愿被抛掷以获取报酬的权利;依照宪法平等权条款,它否定个人可以选择交易对象。⑦(53)⑦某饭馆挂出“不接待同性恋者”的牌子,税兵认为,该行为是有问题的,民法解决不了它,得诉诸宪法平等权。笔者认为,该行为是不是有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即使老板负担强制缔约义务,这个问题也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其他问题:如反垄断的问题,如果饭馆在当地具有垄断地位(《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或违反公序良俗或公平原则的问题(《民法典》第6条、第8条)等。否则,该行为就是营业自由的行使。详见朱岩的《强制缔约制度研究》(载于《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一文第77页所转述的奥地利学者比德林斯基和拉伦茨的争论。如果腾讯公司规定“同性恋者不得用微信”,它便不是在行使营业自由,它或者是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违反了基于微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而生的强制缔约义务。关于该问题的讨论,见下文。也可见朱岩《强制缔约制度研究》一文第70-71页。这些都是以宪法名义实行干预,使得尊严和平等成为侵犯个人自主性的压迫性价值的典型例证。
第五,有人会说,伴随政府与社会/市场之界分的弱化,公私界限已不再明确。很多主体或行为表面上是私人的但实际上具有强大的专制力量。这些非典型性私主体或私行为有下列特点:(1)与政府密切联系,基于授权或委托而拥有或行使公权力;(2)公有性,如国有企业;(3)公共性;(4)垄断性。⑧(54)⑧垄断性和公共性在实践中经常难以分开,公用事业通常具有垄断地位,如供水、电、气、热力的公司,公共运输承运人等。这些现象是真实的,但它们并不挑战本文对宪法性质的论述。非典型性私主体,如果根据授权或委托而行使公权力、提供公共或准公共产品或承担公共责任,则服从公法;如果行使最高公权力,则服从宪法。但如果它们(如传媒、互联网平台)只是发挥难以抵抗的社会性或经济性影响呢?这种令人们无法逃避的影响,会导致经济性或社会性专制。既然宪法是专制的反面,是不是宪法就应该规范这些主体呢?经济性和社会性专制是邪恶的;该问题的解决,可以借鉴宪法学理,但它不是典型的宪法问题。宪法可以也应该把它交给政治过程、相应的社会子系统或其他法来解决。社会或经济专制,与宪法反对的政治专制,是两类不同的问题。例如,除非有来自公权主体的授权或课责,这些专制主体(如平台或大资本家)不是公权主体。相对于政府,它们也是臣民,享有宪法中的基础性自由。不可以用反对政治专制的手段来反对经济或社会专制,后者应该由正当性根据和内在理性与宪法都不一样的安排来解决,如反垄断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2.宪法与政策性法律
本小节是以政策性法律为例对前述宪法与其他法关系的说明。政策性法律规定经济、社会政策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简称经社文权利)等,不是典型的法律。政策性法律也有普遍原则,但它们的内容较为稀薄。政策性法律要求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很易受到社会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宪法可否成为政策性法律内容上的根据,取决于宪法应不应该规定政策性内容。我们不把一阶价值、经济和社会政策或经社文权利等视作宪法根本,认为应该把它们交给政治过程。这与罗尔斯关于宪法与立法的分工是一致的,后者可以用来补充和说明前者。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正义原则是指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基本自由。第二正义原则是指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符合两个条件:(1)公私职位要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对一切人开放;(2)这些不平等要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处境最差的成员。罗尔斯认为,基本自由构成宪法根本的一部分;作为经社文权利的基础,第二正义原则是指导立法的原则,不是宪法根本。①(55)①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73-175, 199.对基础性自由,不宜参照第二正义原则做扩展解读。宪法不是政策性法律内容上的根据,在这个方面,立法机关要自主形成它的意志。参照罗尔斯的论述,这一观点的理由大致如下:②(56)②See Samuel Freeman, Rawls, Routledge, 2007, chapter 5; DA Reidy,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 in Jon Mandle and DA Reidy eds., The Cambridge Rawls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1-146.
首先,第二正义原则涉及高度争议性价值,难以凝聚共识。规定第二正义原则,会使宪法成为保姆型政策大纲,导致宪法的偏私性。第二正义原则的要求随经济社会形势而变。这些都会伤害宪法的正当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实施第二正义原则是极其昂贵的:不只取决于义务人的意志,还取决于义务人的资源。规定第二正义原则会削弱宪法和基础性自由的规范力。不在宪法中规定它,不是不解决相关问题,而是说应该把它们交给政治过程或社会来解决。
其次,宪法规定第二正义原则会为违宪审查提出难题。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如果不违反第一正义原则,便应受到尊重。基础性自由、民主政治过程的要求是什么,尽管也有疑难情形或争议,也要求宪法解释,但与典型的分配正义问题相比,它们依然较明确,争议较少,适合由宪法专家组成的法院来初步解决。什么样的政策性立法符合第二正义原则,利害相关方会有普遍而尖锐的分歧。政策性问题的解决,要求大量关于迅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的信息。这些表明,它们适合由政治或行政过程来解决。如果把第二正义原则规定在宪法中,违宪审查机构必将频繁、广泛且深入地干涉政治过程和高度争议性事宜。这会伤害民主过程。这种工作也是宪法专家所不擅长的,将会导致他们高度政治化,伤害他们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二)宪法作为客观价值秩序
与部门法自主性紧密联系的另一议题,是如何理解“宪法是客观价值秩序”这个命题。首先,宪法确立某些价值,但如前所述,它们主要是二阶的。客观价值秩序说认为,宪法还是一阶价值体系,这是把宪法等同于价值体系或道德。道德和法律是两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客观价值(或道德)与宪法及其确立的价值不可以等同,否则宪法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很多客观价值是不适合用法律手段来推行的,如友谊、爱情、夫妻忠诚,如舍生取义、先人后己等。再次,如果某些客观价值适合用法律手段来推行,把它们载入宪法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其他法可以与它们(如公平、平等、诚信、人格尊严等)直接沟通。英美宪法并没有供奉德国宪法供奉的特定价值,但这不影响前者的法律来践履这种价值。最后,一阶价值具有侵略性,客观价值秩序说不仅会(通过比例原则)弱化基础性自由的规范力,还将使主权者成为客观价值的确定者和实施者,从而导致极权主义。①(57)①EW Bockenfo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elected Writings, eds. by M Kunkler and T 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17-234. See also Maarten Streamler, The Constitution as an 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 4 Kutafin University Law Review 498, 512 (2017); DP. Kommers, German Constitutionalism: A Prolegomenon, 20 German Law Journal 534, 547-548 (2019); 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68-69页。有些宪法规定一阶价值,宪法实践也会对二阶价值做一阶解读。鉴于纳粹和大屠杀的悲剧,德国基本法把人格尊严作为宪法价值之一。全面主义在德国并未导致灾难。但在发展关于宪法性质的一般理论时,不应该把宪法预设为以德国式人格尊严为本位的宪法。另外还要考虑:如果宪法确立的一阶价值不幸是与人格尊严不同或相反时,这样的理论会有什么后果。
(三)全面宪法与民主
前文已在多处提示了宪法全面主义对民主和政治的挤压,它甚至会消灭政治。在民主制下,它会剥夺民主的空间,代之以立法者或宪法法官垄断的宪法独裁。作为全面宪法之具体化或其教义学之落实的立法或合宪性解释,与作为民主意志形成过程的立法,在性质上是背反的。针对立法的宪法教义学是自相矛盾的主张。教义学与立法是相互排斥的:要么教义学,即依照宪法文本和形式逻辑展开的法律和道德推理,同案同判;要么立法,即自主的政治意志的形成和表达,随时而变。针对立法的宪法教义学要把后者变成前者,使立法变成对宪法学教义的权威认证过程:立法不再与民主政治有关。
即使放弃“立法作为宪法具体化”的命题,假定立法是民主过程的产物,全面主义还授权宪法法官根据“全面宪法”认定立法违宪,或废止后者。当然,这之所以是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民主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政治是不民主的,如果民主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法官的宪法独裁也并不必然比政客独裁更糟,全面主义就不必然是令人遗憾的。
张翔并不主张取消政治在其他法制定中的作用,他说:“立法固然不能抵触宪法,还要将宪法对社会生活的规整予以具体化,在消极和积极的两个层面‘根据宪法’,但根据社会公意、形成政策判断的民主功能并不会因此被取消。同时,各个部门法在久远历史上形成的原则、体系乃至具体规范,只要其不抵触宪法秩序,就依然可以在其固有轨道上演进。换言之,部门法的内容,并不必然来自宪法,而是可以来自民主政治的政策判断以及部门法的固有逻辑。但是,都在宪法的规约下。”②(58)②张翔:《对陈景辉教授〈宪法的性质〉的初步回应》,载中国法学创新网2021年3月29日,http://www.fxcxw.org.cn/dyna/content.php?id=18746。张翔诉诸框架秩序说:“宪法其实为政治留下了活动空间。按照宪法作为一种框架秩序的理论,政治在宪法的框架中是有足够的运作空间的。”③(59)③《陈景辉 张翔 翟小波 李忠夏华政“互殴”实录|宪法的性质》,载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2021年4月28日。但问题在于:“宪法的规约”是消极不抵触的规约,还是积极具体化的规约?“框架秩序”是防御性疆界,还是实体性纲领?消极不抵触的规约、作为防御性疆界的框架秩序与作为民主过程的立法,是可以兼容的,但作为全面宪法积极具体化的立法、作为实体性纲领的框架秩序与后者则是难以兼容的。全面主义的规约包括积极的具体化的规约,它的框架秩序还是实体性纲领。宪法全面主义、作为实体性纲领的框架秩序和具体化命题是排斥政治的:如果其他法的制定、解释和适用是对全面宪法(作为实体性纲领)的积极具体化,而具体化是某一命题从抽象到个别的逻辑展开,政治便没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承认宪法要给政治留下足够空间,宪法全面主义、作为实体性纲领的框架秩序和具体化等命题便难以成立。
(四)全面宪法、违宪审查与宪法的保护者
陈景辉认为,具体化命题导致违宪审查的冗余性:立法和明确含义式合宪性解释,导致宪法被双重具体化。如果再加上违宪审查,在同一法律创造和适用中,合宪性控制将多次发生。既然其他法已经是宪法的具体化了,还要对它们做违宪审查吗?陈景辉把这称作多重计算难题。笔者同意张翔的回应,合宪性保障可以是多重的,多重计算并不构成难题:立法具体化(如果该命题是正确的)是守护宪法的第一关,合宪性解释是第二关,违宪审查是第三关。具体化并不会导致违宪审查的冗余性。但具体化命题为其他法抗拒违宪审查提供了理由,甚至如夏正林所说,它会导致立法至上取代宪法至上的结果。①(60)①夏正林:《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改善》,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35-241页。比如,在关于物权法是否违宪的争论发生后,立法者就在该法中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种做法的意图之一就是要阻止对物权法是否违宪的进一步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时对一些决定和立法做出合宪性确认,其意图之一是阻止其他方面对它们的合宪性质疑,所以,具体化命题的确有帮助相关立法抗拒违宪审查的效果。②(61)②程雪阳认为,各国宪法规定,只有基于公共利益才可以征收,这里的“公共利益”就属于实体性规定或“内容设定性规范”,但它的内涵或外延,宪法授权法律去进一步形成: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不可以违背宪法设定的边界控制性规范。参见程雪阳:《合宪性视角下的成片开发征收及其标准认定》,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90页。笔者的回应是: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不经公正补偿,私有财产不得被征归公用”;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鉴于财产权是不可侵犯且神圣的,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之,除非是合法确定的公共必要(la nécessité publique, légalement constatée)明显要求之,而且事先给予公正的补偿。”法律显然会确定何为“公用”或“公共必要”。但对笔者在此要捍卫的观点来说,需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宪法这里的措辞并没有为法律对公用或公共必要的确定提供任何实体指引;第二,任何法律对公用和公共必要的确定依然要服从违宪审查的控制。
笔者在前文中说,违宪审查是保护宪法的初步安排。与普通法院来保护一般法律不同,宪法通常由特殊机构来保护。这种制度安排植根于宪法的性质。历史上有过关于宪法(或国际法)是不是法律的争论:普通的刑法和民法可以由主权者来保护,但宪法要约束主权者,显然不能由主权者来保护。由特殊机构通过违宪审查来保护宪法,这是关于宪法的一项共识,也为全面主义所接受,但这只是对宪法性质的表面理解。
违宪审查机构通常比普通审判机构更有权威,但依然是主权建制的一部分。宪法是约束主权者的法。宪法根本(尤其是宪法惯例)的约束力没法通过主权建制内的安排来确保。宪法(包括宪法惯例和宪法法律)要发挥控制主权者的作用,得常规地依赖最高级官员的共信共守和围绕宪法形成的舆论,例外地依赖于民众反抗的意志和力量。即使宪法规范可以源于主权者的承诺,但它们约束主权者的力量一定是来自主权者之外,即舆论。基础性宪法价值应该成为舆论中的理由,舆论的资质又取决于表达自由:有了表达自由,宪法规范(不论成文与否,须为民众所周知)便“有能力谋得社会的尊重,确立支持它们的舆论”。③(62)③Selected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ed. by Ralph Ketcham,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6, p. 171.如果不考虑舆论和民众反抗这两个因素,便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和英国的议会大体上是服从宪法的。诚如卢梭所说: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④(63)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0页。
五、结论
宪法不应该是全面的,应该是中立的。中立宪法的概念至少有法律、道德、政治和文化四个维度。法律之维强调宪法的法律性、相对于日常政治的超越性。道德之维强调宪法正当性根据在于它对基础性自由的肯认。政治之维强调要把宪法根本之外的其他政治、法律或政策问题交给政治过程。文化之维强调宪法在特定社群的效力(或约束力)取决于对宪法根本的崇尚是否成为该社群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像宪法学界通常做的那样,不考虑宪法的道德和文化之维,只聚焦于它的法律和政治之维,可以说,我们主张有限的法律宪法主义。它的法律性在于,宪法根本是最高法,先于和高于政治过程,应该得到法律性捍卫。它的有限性在于,宪法内容有限,作用有限:它包括基础性自由和政治过程的基础性规范;它不是客观价值秩序,不积极干预其他法的生成和发展,不可以作为司法裁判的常规根据;它只是对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根据;宪法不可以消灭政治,要把基础性自由之外的价值分歧交给政治过程来解决。
宪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就之一,但也只是“之一”。宪法全面主义取缔了宪法与其他一切法律、社会系统间的边界,①(64)①Stephen Gardbaum, The Place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al System, in 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as Saj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2, 174.主张宪法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主张要把整个共同体的一切方面都宪法化。它把宪法变成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把宪法理论变成百科全书式的正义理论。这既会伤害宪法,也会伤害其他法,威胁自由和多元的社会秩序。因此,不应该依照善者无敌的思路,将宪法变成“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概念,无所不能的宪法注定是一无所能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