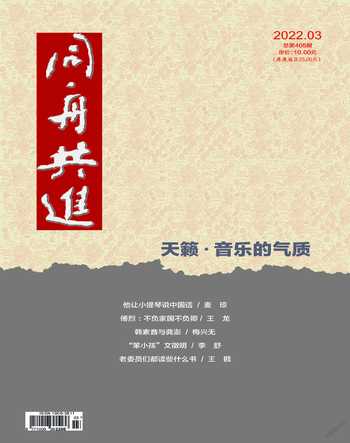《送别》:李叔同与“天涯五友”的聚散离合
李满
【影响几代人的经典】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是李叔同写于1914年的一首歌曲,是他在杭州教学时写下的大量学堂乐歌中的一首。
《送别》的曲调节奏柔缓,苍凉中略带慷慨,恰到好处地刻画了离别时刻的惆怅,其原始出处不在中国,它其实是一首地道的英文歌曲。作者是美国人约翰·庞德·奥德威,他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正式职业是一名外科医生。美国南北战争时,他是第一批志愿上前线抢救伤病的外科医生之一,曾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场服役。奥德威同时也是个作曲家、音乐创作人和政治家,他于美国南北战争前期创作了一首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没想到这首歌竟“墙里开花墙外香”,在美国传唱度并不高,却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量的音乐作品,多采用直接输入西洋唱歌集,从中选出旋律的形式。一个叫犬童球溪的作者给这首歌填写了新词《旅愁》,刊载于1907年出版的《中等教育唱歌集》。当时,犬童球溪在新泻女子高等学校任职,深深怀念着远在九州的故乡亲人。据钱仁康翻译,《旅愁》的歌词为: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
填词后的曲调进行与原曲并不完全相同,填词者根据词的需要作了相应变动。歌词改为二段词,最后八小节是原原本本地重复开头段的四句歌词,这和《梦见家和母亲》是有区别的。1907年李叔同留学日本,被《旅愁》深深吸引。李叔同回国后,所作的《送别》初见于裘梦痕和丰子恺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采用的正是《旅愁》的曲调,歌词也和《旅愁》的意境有关。
《送别》与《旅愁》情调极似,但主题意境的深浅隐显不同:前者叹知交零落,后者抒思乡思亲之情;前者是淡淡的哀愁,后者是深深的伤感。前者含蓄,后者直露。《送别》全篇,几乎每一句词都有很强的画面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充满中国古典意象的送别时的情和景,让人想起李白《菩萨蛮》中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和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长亭、古道、芳草,都是离人眼中所见,景物依旧,人在别时,看起来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描摹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经常伤怀歌咏的山峦夕阳之景,淡淡的笛声吹出了幽怨,哀而不伤;晚风拂柳蕴含了别意,缠绵真挚——“柳”字暗合“留”意,勾起了多少彼时的情怀。“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从遥渺的意境变成对现实的感叹;“一瓢浊酒尽余欢”,饮不尽离愁,反倒增添了惆怅,人生际遇,亦真亦幻。
李叔同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清词丽句与西方民谣曲调结合,达到了情趣意境出于天然而不见斧凿之痕的高度,显示了他对乐曲选择的敏锐度以及驾驭中国古典诗词文化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送别》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的影片。柔石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已经出家,柔石未能亲受其教诲。毕业时,柔石从老师夏丏尊先生那里获得过一幅李叔同的字,并装裱题字:“余乐而藏之,此非余之好奇,实余之痼性也。”为弥补缺憾,导演谢铁骊在电影中特意选择李叔同的《送别》作为插曲。影片《早春二月》主人公、小学老师萧涧秋执教的校园里,所唤起人淡淡哀愁的,正是那首低回婉转的《送别》。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在其1960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集《城南旧事》里,两次提到李叔同的《送别》。1982 年,导演吴贻弓把《城南旧事》搬上银幕,选取《送别》作主题歌。他融合了丰子恺《中文名歌五十曲》所收《送别》和林海音所记,组成两段歌词,《送别》的旋律贯穿始终,影片大获成功,享誉海内外。此后,歌曲在中国大地上流传更广,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不朽经典,至今影响着国人。
【“天涯五友”相聚上海】
李叔同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与内心情境下,创作出这部作品的呢?他送别的对象又是谁?或许,我们可以从《送别》里的“知交半零落”找到答案。所谓“知交”,既非“知己”,又非一般交往,大约相当于今天有交情的老朋友;“半零落”说明并非全部断绝,而是处于遥远相隔、似有若无的境界——这里的“知交”,乃李叔同出家后仍念念不忘的“天涯五友”之一——许幻园。
“天涯五友”分别是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和李叔同,这个五人组合在当时的上海可谓“名震一时”。据说,当时沪上之人,只要提到“天涯五友”,无不交口称赞,仿佛明星一般。
“天涯五友”第一次聚首,是在李叔同初到上海那年(1898年)。这一年,中国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失败,李叔同因为涉嫌“康梁同党”而被迫自家乡天津逃至上海。当年,满腹才学却并未大施展的李叔同年方19岁。

李叔同素来悲天悯人,他对救国救民格外上心,这点从他后来出家后仍支持抗日便可知。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李叔同之所以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牵连,乃是因为他曾公开说过“老大中华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一类的话,他甚至自刻了一方闲章,上书:“南海康君(康有为)是吾师”。
李叔同逃难为何偏偏选择上海?皆因此地在各方面都与当时他所生活的天津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李家在上海的申生裕钱庄设有柜房,到了这里,他大可衣食无忧。到上海后,李叔同租住在法租界卜邻里(今金陵东路一帶),卜邻里靠近城南,而城南是文人雅士居住的地方。早在李叔同抵达上海的前一年,后来的“天涯五友”之其余四人,即当时的“宝山文人”袁希濂、“江阴名士”张小楼、“江湾儒医”蔡小香、“华亭诗人”许幻园已建立了“城南文社”,地址是许幻园的住所——城南草堂。作为沪上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许幻园每月都会组织文人聚会,偶尔还会组织会客、出资悬赏征文。gzslib202204041223李叔同最初与许幻园等接洽上,就是因为征文。李叔同的几次投稿,得到了文社内部人的一致好评,很快,他们便正式邀他入社了。
【“平生最幸福的时候”】
1898年底,李叔同第一次到城南文社参加会课,当日他头戴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身穿花缎袍子,曲襟背心,后面扎着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脚蹬双梁头厚底鞋子。当李叔同站在许幻园等面前时,他们只觉他英气逼人,器宇轩昂,李叔同谈吐间的神色风采,更让他们欣赏不已。
李叔同第一次会课时,出题者是当时的宋儒性理学大家张蒲友,他出的题目是《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评其说》。李叔同在天津时便对性理学下过功夫,这等题目自然难不倒他。首次以文会友,李叔同便被张蒲友评为:“写作俱佳,名列第一。” 此后,李叔同尽情挥洒才情,每次写出文章必定“技惊四座”,这正是他后来在诗中所说的“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
经过几番接触后,许幻园决定将位于上海大南门青龙桥的城南草堂辟出一部分,邀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居住。许、李相识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李叔同带着家人住进了城南草堂。许幻园还特地在李叔同书房挂上了“李庐”的牌匾,李叔同后来的“李庐主人”别号,便是由此而来。
搬家后的李叔同心情格外舒畅,他曾在《清平乐·赠许幻园》里表露遇见知己后的喜悦之情:“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此后,几位文坛才俊常在一起交流学习。结拜后不久,他们还特意到照相馆摄影留念,李叔同为感念这几位好友的相遇之情,以“成蹊”之名在相片上题写“天涯五友图”的字样。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也常与五人谈诗论赋,才华不让须眉,她作为“天涯五友”的见证者,亦即兴在相片上题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尤其传神:“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与“天涯五友”结识的一二年间,李叔同在城南草堂相继撰成《李庐诗钟》、篆刻《李庐印谱》及编年诗文集《辛丑北征泪墨》等,这些作品出版后,李叔同在沪上的声名也愈发响亮。“五友”虽成长于不同背景,却又有很多共同点——同是出身名门世家,都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有良好的旧学功底,但在晚清新思潮不断涌进的大环境里,都成长为新派绅士,提倡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改革。
“天涯五友”闲来常一起举杯邀月、品茗论艺,游览名山大川。李叔同还特地写过组诗《戏赠蔡小香》给“天涯五友”之一的名医蔡小香。蔡小香出身中医世家,他专治妇科,著有《妇科述要》《女科秘笺》《验方秘录》等。因为乡里治病,每获良效,蔡小香的诊所门庭若市,妇孺皆知,李叔同见了不免偶尔拿他开玩笑,说他“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意思是蔡小香整天被女性病患围着叫“先生”,实在“艳福不浅”。
在《戏赠蔡小香》的其中一首里,李叔同还直言蔡小香“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蔡小香是否真如李叔同所言已不得而知,但李叔同与他关系极亲近,从诗中可窥一二。像这样的“唱和”,李叔同与许幻园、袁希濂、張小楼也经常有,只是因为时间太久远的缘故,这些诗词均散落各处,不见踪影了。
除了诗词唱和外,李叔同与“天涯友人”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讨论救国救民之法,谈到激动处,他们还会当场吟诗作赋。也是因着这份忧国忧民之心,李叔同等的诗词才与同时代那些单纯抒发情感的诗词截然不同。后期,随着李叔同的重心逐渐向佛教倾斜,许幻园等也受到了感染,他们甚至开始在文字上发挥补偏救弊、使人心转恶向善之功,这也为他们后来与佛结缘打下了基础。
对于这段时光,李叔同一直极为留恋,他曾言:“我自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天涯五友”各奔东西】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涯五友”也有各奔东西的一天。
1901年,张小楼应东文学堂之聘,离开上海前往扬州;不久后,李叔同入南洋公学特班就读;袁希濂进了广方言馆;许幻园纳粟出仕;蔡小香则忙于行医。就这样,“天涯五友”各自忙于事业和学业,再也无暇专注于文艺,他们所主持的“城南文社”和“海上书画公会”也难以为继,于无形中逐渐解体了。
1912年,“天涯五友”之一的蔡小香因病辞世,享年49岁。蔡小香的英年早逝,给其他人以极大的打击,李叔同听闻死讯时,竟接连几天滴米未进。
翌年,二次革命失败,使许幻园的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许家的万贯家财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许幻园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突然破产,他情绪极度消沉,为了挽救家族,许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向袁世凯讨个公道。
临走前,许幻园去跟李叔同告别。那天,上海下了很大的雪,把天地妆点成白茫茫一片。李叔同忽闻门外好像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于是他打开门,发现正是自己的好友。许幻园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话:“叔同兄,我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就转身消失在了苍茫大雪之中。
看着昔日好友渐行渐远的背影,李叔同竟无语凝噎,他独自在雪地里伫立良久,后返回屋内,伏案写下了那首我们熟悉的《送别》。
彼时的李叔同,母亲已不在人世,经历繁华极盛,又看过生命至哀,李叔同第一次对尘俗萌生了退意。他在天津的老家已破产,又曾东渡日本回国,经历失业再就业,暂在杭州安顿下来,于杭州师范学校教授图画与音乐。那时的他常与好友于湖心亭吃茶,偶尔记忆过去,总觉踌躇满志,故人已远,偶然间,夏丏尊的一句玩笑话点醒了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gzslib202204041223李叔同当下动念,先是带着棉袍棉鞋和一些简单物品去了虎跑山,实行“断食计划”。后又给徒弟刘质平写信:“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现已陆续结束一切。”

1918年,在“悲欣交集”中,李叔同决定彻底跟自己的前半生告别,他在杭州虎跑寺修心拜佛,后来正式出家,取法号“弘一”。他出家时,许幻园等并不知情。消息传到许幻园耳中时,他在诧异的同时,也想过要写信劝李叔同还俗。可思量再三,数次提笔后,他终究还是没有去信。
此后数年,“天涯五友”中,除李叔同外的三友虽都在俗尘,却都不约而同地对佛学更感兴趣了。
“五友”中年纪最大的袁希濂,曾在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学位,1911年回国后曾在天津、杭州、武昌、丹阳等地任职多年。李叔同出家次年,袁希濂由杭州调任武昌,临行前与李叔同话别,李劝他读《安士全书》。《安士全书》是清代人周安士所写,民国高僧印光法师曾大力推荐过此书,李很可能是受印光法师影响而读到了此书。袁希濂在追悼李叔同的《余与大师之关系》一文中自述:“余 52 岁时,绝对不信佛法。是年秋得《安士全书》而读之,始知佛法之圆融,佛力之宏大”。
1927年,袁希濂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法门。正如他自己所言,“余学佛之机”全为“弘一法师启迪之”。
【为抗日大业再次站到一起】
转眼到了1926年夏,出家已经八年的弘一法师途经上海,他突然想起曾经待过的城南草堂,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再度踏访旧址。原以为还可以看到昔日的景象,却发现已经物是人非。
此时的城南草堂早已不属于许幻园,它被卖给了一个五金店的老板,这位老板又将草堂送给了一群僧人。现在的城南草堂,被更名为“超尘精舍”,与青灯古佛为伴。弘一法师看到此情此景,心中五味杂陈,可转念一想,自己已不在俗世,发生这样的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四处打听后,弘一法师在草堂附近马路边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找到了分别多年的许幻园。推开门,此时的许幻园白发苍苍,耳已半聋,他靠着给别人抄些书本、上些私课,赚取维持生计的银钱。好友相见,从前的场景浮现眼前,两个人叙谈了很久,回忆着过往的一切,一切都恍如隔世。
1927年枫叶含丹之秋,弘一法师北上探亲途经上海,入住江湾弟子丰子恺的家中。闻讯后,除已过世的“天涯五友”蔡小香之外的其他三友——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等前往探访。四人见面后,感慨万分,唏嘘再三,他们重摄一影,由弘一法师题跋,以作纪念。
在那次会面后,许幻园和张小楼也皈依佛教,成了居士。
两年后,许幻园在上海大王庙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反复叮嘱第二任妻子苏琴:一定要将儿子培养成像李叔同那样做事认真的人,长大后要让他们和李叔同一样学艺。幸运的是,这两个孩子一直在“天涯五友”的其他成员照顾帮扶下成长,其中出力最大的,便是“五友”里境况最好的袁希濂。按照父亲的遗愿,两个孩子长大后,成为了中国电影界早期的演员和导演。
“天涯五友”中,最晚辞世的是张小楼。张小楼原名张柟,又名张楠,小楼乃其字,他和李叔同一样精通儒学和书画。自日本法科大学毕业回国后,他历任南京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初期开始从政,曾在北洋政府任国务院翻译官、外交部编译员,并被派驻朝鲜,任新义州领事。1926年重返上海,任上海铁路税务局局长。

1900年时,“天涯五友”曾在上海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联合发起成立“海上书画公会”,当时任会长的,就是组织、管理能力均一流的张小楼。此事被上海文化界视为盛举,上海及江浙书画名家高邕之、胡郯卿等纷纷入会,该会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宗旨,定期组织会员品茗读画,相互交流。李叔同还主持编辑《书画公会报》,每周三、日出版。一、二期随《中外日报》附送,旋即自行销售发行,前后出版40余期,揭开了中国近代书画社团的新篇章。
1930年代初,张小楼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过一段时间。然而,与许幻园一样,这位不谙为官之道的书生,不久便丢了官。长于书画的张小楼曾一度靠出卖书画或向亲友借贷度日,后輾转在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谋得教职。
张小楼一生子嗣稀薄,仅有一个女儿名叫张曼筠。1928年,张曼筠嫁给了即将赴美留学的革命者李公朴。李公朴和张小楼一样一心救国,对有这样的女婿,张小楼自然十分满意。李公朴回国后,翁婿俩还一起合作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以及《读书生活》半月刊。有了女婿的帮衬后,张小楼的生活才逐渐稳定,他专心致力于书画,并举办了一些画展。
可惜,张小楼的闲适生活终在抗战爆发后被打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拿起画笔,画了一只张着四肢的螃蟹,并在上方画了一枝鲜艳的红梅。他在画纸上写下两句话:“螃蟹腿短,看你横行到几时?我之行世,唯学红梅高洁。”借此讽刺日本侵略者在华的猖獗不会持久。张小楼晚年信佛,自号“尘定居士”。目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大业,一面做慈善救济难民,一面写文痛斥日本人的罪行。
在张小楼积极抗日的同时,他的好友弘一法师也以出家人的身份加入了抗日队伍。弘一法师冒着被日本人暗杀的危险,在炮火中开坛讲经,高喊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甚至还凛然写下了“殉教”两字横幅,以明其志。这个横幅左侧的题记这样写道:“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弘一法师甚至组织僧众创办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这支由僧人组成的救死扶伤队,将战时的救护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弘一法师的所为自然极大地鼓舞了张小楼,而另一边,身在上海的袁希濂也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自此,“天涯五友”中的三人又再次站到了一起。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数百万民众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张小楼闻讯后,立即赶往郑州,襄助全国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文六居士,赈抚受灾的同胞。不久,他又为安置河南灾民,奔赴灾民避难点陕西黄龙山,组织他们种地养猪,渡过难关。而他的妻子,却在日军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中惊悸而亡。
即时,李公朴夫妇不放心年逾花甲的老人独自在外辛劳,便将他接到了重庆。不久,张小楼又随他们转移到昆明。在昆明,张小楼又重新专注于他所酷爱的书画艺术,与书法家胡小石、摄影家杨春洲成立了“三艺社”。1942年,为支持李公朴创办“北门书屋”,张小楼、张曼筠父女和“三艺社”成员一起,联合举办书法、绘画、摄影展,作品公开拍卖,为北门书屋开办筹集到了部分资金。
就在这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享年62岁。消息传到张小楼耳边,他于悲痛中写下了不少悼亡诗句。让张小楼没想到的是,弘一法师去世不到四年,他的女婿、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好友、爱婿相继离世的打击,让他从此一蹶不振。
李公朴去世后,张小楼的生活也变得愈发艰难。回到上海后,他只能靠三联书店给烈士家属的一点抚恤金勉强维持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某日,张小楼给女婿和弘一法师上完香、报完喜后,一个人呆坐了良久,他喃喃道:“我们也该汇合了……”
清末民初之时,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革,对于一众饱读诗书的士人来说,引起的不仅仅是生活经历和身份语境的转变,更多的是在家国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挣扎徘徊。天涯五友中的四友,在各自领悟生命真谛后,均不约而同地步入佛门。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