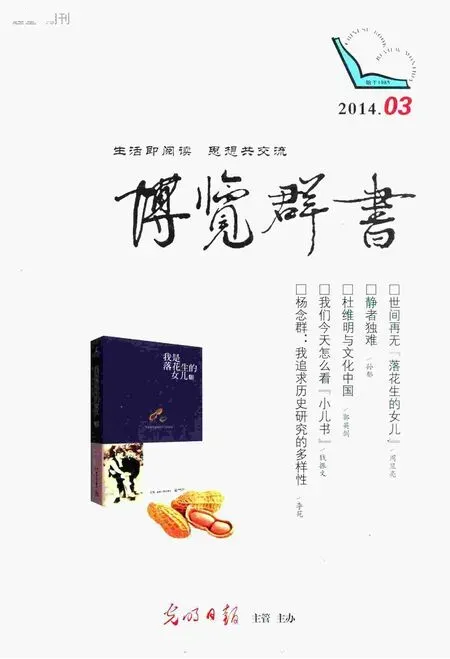长安游赏时的元白和唱
田恩铭
中国文化重视立德、立功和立言,但对于闲暇的功用,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孔子不仅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的名言,他在《论语·述而》中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张弛”之论谈的是治国,而“游于艺”的“艺”,注家一般释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以为亦可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在当时实为包罗广泛的知识技艺。朱熹《四书集注》以“玩物适情”解释“游于艺”的“游”,可谓抓住了根本。因此,“游于艺”与“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指人从俗务中抽身,在闲暇轻松的气氛中所进行的超越功利、休养身心、放松自我的活动。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这是古人重视生命、怡情悦志、自我调适身心的经验总结。
这种人生智慧,在历代文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唐人张彦远“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的名言,即是这一智慧的另一种表述。本栏目的四篇文章,分别选取了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宋代的黄庭坚、欧阳修和陆游,对他们在公务之余,通过游赏名胜、痴迷琴书、寄情诗酒、投身自然等多种方式,将这种智慧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并加以诗意表现,做了细致生动的书写。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重的当下,这些先贤的功业与著述,固然令我们无限敬仰,他们休闲“游艺”、愉悦身心的智慧,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当然也值得各级决策者思鉴。???????
——劉怀荣(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以诗歌齐名当世,两人的情谊向来为人称道。他们同在长安任职期间,公务之余重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即是结伴同游。在欣赏山水名胜,诗歌唱和中,不仅加深了友谊,也对唐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元稹和白居易的交往,“起于贞元,迄于大和,事历六朝,始终相得甚深,又皆以诗鸣,故投赠之作,积至十七卷”。(《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P54)具体来说,元白相识于贞元十八年(802)前后,两人诗章酬答三十年,写于休闲活动中的诗作尤多。其中,他们有三个阶段同在长安任职,休闲活动以游赏山水楼榭为主,在诗作中多有反映。
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三年(808)是元、白任职长安的第一个阶段。两人的仕宦生活开始不久,正在意气风发地向前奔跑。元白早期的长安休闲生活通常写在追忆性文本之中,往往是经历世事之后的回顾与思考。这一时期的游宴生活具有明显的群体性,不仅是元白二人而已。贞元二十一年(805)冬,元稹、白居易在长安一起准备制举考试。元稹、白居易、李建、李绅等人一起游览长安盛景,每到一处均有浅斟低唱。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
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
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
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
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
秋风拂琴匣,夜雪卷书帷。
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
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
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
儒风爱敦质,佛理赏玄师。
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
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
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
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
一群僚友赏月饮酒、登塔看花、吟诗研理、联句对弈,好一番高雅快活的景象。出入三省、游春曲江,又是何等惬意!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云:
情会招车胤,闲行觅戴逵。
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
胜概争先到,篇章竞出奇。
输赢论破的,点窜肯容丝。
元稹在诗中夹注中说:“予与乐天、杓直、拒非辈,多于月登阁闲游,又尝与秘省同官醵宴昆明池”,叙述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正是这段备考的时期加深了两人的友情。两人“闭户累月,揣摩时事”完成《策林》75篇。元稹《赠乐天》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诗云:
等闲相见销长日,
也有闲时更学琴。
不是眼前无外物,
不关心事不经心。
其中惬意之情见于言表。两人曾经一起去西明寺看牡丹,元稹当时有诗记之,后来元稹远贬江陵,白居易有《重题西明寺牡丹》,追忆旧游中自然会寓有无限感慨。“春到曲江池”是元白记忆中最为难忘的图景。
元和四年(809)至元和五年(910)是元、白任职长安的第二个阶段。这是元稹人生的转折阶段。他的御史官生涯为他带来了“直正”的好名声,却也遭受了仕宦、婚姻的双重打击。不过,元稹的长安生活因与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在一起仍然是相当快乐的。元、白同在长安时,常在曲江相聚,故而因地叙情。白居易去了曲江,便会追忆两人同游曲江的旧事。《曲江感秋(五年作)》:
沙草新雨地,岸柳凉风枝。
三年感秋意,并在曲江池。
早蝉已嘹唳,晚荷复离披。
前秋去秋思,一一生此时。
昔人三十二,秋兴已云悲。
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
岁月不虚设,此身随日衰。
暗老不自觉,直到鬓成丝。
曲江是白居易、元稹诗作中追忆的地方,因为此地留下两人同游的记忆,无论是白居易计算元稹从京城到江陵的里程,还是元稹叙述从京城途经各地的所思所想,曲江均是追忆的一个起点。元稹《和乐天秋题曲江》:
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
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
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共爱寥落境,相将偏此时。
绵绵红蓼水,飏飏白鹭鹚。
诗句偶未得,酒杯聊久持。
今来云雨旷,旧赏魂梦知。
况乃江枫夕,和君秋兴诗。
长安城中多胜景,惟有曲江记忆深,梅杏、芰荷皆入笔下。这组诗是一时一地之作,因曲江而叙友谊,追忆同游曲江的休闲生活。元稹不仅与李绅、庾敬休等“数人同傍曲江頭”,而且诗作中反复追忆,甚至梦中同游曲江。元和四年(809),元稹任监察御史。从长安赴东川覆狱,至梁州梦见与李建、白居易同游曲江及慈恩寺。元稹《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诗前有自注云:
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
据说,当天白行简、白居易、李建真的同游曲江,还去了慈恩寺,“遍历僧院,淹留移时。”(白行简《三梦记》)后来,到李建的住处喝酒,白居易写了一首题壁诗,推断元稹当到梁州。诗云:
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显然过去曾有的游赏生活进入梦中,刺激现实的元白,才会有如此默契的昼思夜梦。白行简特意撰有《三梦记》载录此事,唐五代笔记中也是反复录下这段故事。不过,元稹既可入夜有梦,又能追忆过往。行至嘉川驿,《江楼月》一诗题下标注说:
嘉川驿望月,忆杓直、乐天、知退、拒非、顺之数贤,居近曲江,闲夜多同步月。
因望月思步月,诗云:
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
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
诚知远近皆三五,但恐阴晴有异同。
万一帝乡还洁白,几人潜傍杏园东。
元稹于月夜中回忆在长安与白居易、李建、李复礼、白行简等人游曲江的旧事,一己之孤独中复现大家同游的乐趣。白居易有《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集中和元稹使东川的诗作,正如题下标注所说:
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
其中 《江楼月》云: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
一半是追忆曲江之旧事,一半是叙述期待再次同游之情怀。好景不长,元稹因为得罪权贵,分务东台,离开长安而赴洛阳任职。祸不单行,韦丛去世,第二年发生敷水驿事件,元稹被贬江陵,病苦相加,元、白就此天各一方,虽唱和未辍而愉悦不再。
元和十年(815)至长庆二年(822)是元白任职长安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元白仕宦生涯的波动期。元稹回到长安又再度外放,白居易因为武元衡被刺上书而得罪谏官,被贬为江州司马。一度不通音讯,以至于病中的元稹得到乐天被贬的消息为之一惊。《闻乐天谪江州司马》写下了一个黑暗的黄昏中的人生镜像: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暗淡的时光,暗淡的夜晚已然来临,暗淡的消息让“垂死病中”的元才子经受了大刺激,一句“暗风吹雨入寒窗”景语中有情语道尽无限凄凉。不过,这是元白长安生活中的插曲。元和十年(815),元稹从贬谪之地被召回长安,两人有过一段相聚的好时光。元稹与白居易、李绅等游城南,元、白马上联诵“新艳小律”,后来追忆此事,元稹作有一首题目极长的诗,题目中追忆了元和十年赛诗的场景和任职翰林的唱和往事。诗云:
春野醉吟十里程,
斋宫潜咏万人惊。
今宵不寐到明读,
风雨晓闻开锁声。
《与元九书》中也回忆此事:
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樊、李在旁,无所措口。
昭国里是白居易宅所在地。这是长安城里的一幅绝美的图画:元稹、白居易、樊宗师、李绅即景选题,在唱和穷游中比才气之短长,显然胜出的是元稹和白居易。对于这段生活,白居易有《游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归》,“老游春饮莫相违,不独花稀人亦稀。更劝残杯看日影,犹应趁得鼓声归。”算是这次“迭吟递唱”的袅袅余音。
可惜这样的诗酒唱和只是昙花一现,元稹渴望留京的愿望落空,外出为通州司马。这段没有结果的求索是元稹意料之中的事儿,却又到瘴疠之地赴任,令元稹无法接受。行前,元稹留旧文二十轴与白居易,白居易为之送行。元稹有诗《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
今朝相送自同游,
酒语诗情替别愁。
忽到沣西总回去,
一身骑马向通州。
白居易有《十年三月三十日别为之于沣上》云“沣水店头春尽日,送君马上谪通川”之句。元稹再回到长安已经是元和末期。
元稹从通州到虢州,白居易从江州到忠州,一晃四年过去了,两人从未间断唱和活动。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拜相,元稹移虢州长史,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元和十四年(819)冬,因上尊号宪宗宣布大赦天下。据《上尊号赦文》,元稹被召回长安,任膳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元和十五年(820)夏,白居易自忠州被召回,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后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白居易为撰制文;白居易转中书舍人,由元稹撰制文。两人踏上仕宦的坦途,并于长庆二年(822)达到顶峰,元稹拜同平章事,后出为同州刺史。白居易本年外放外杭州刺史,两人又一次离开长安。此后,再无在长安共同任职的经历。大和三年(829)岁末,元稹离任浙东观察史,回到长安。此时白居易为太子宾客,已分司东都。第二年,元稹又赴鄂州任职,长安月色只能在两人的诗文中不断地追忆和叙写了。三年看似很短,对于两人来说均是曾经沧海,彼此唱和的作品并不多,反而是离开长安后的追忆之作不少。白居易与元稹酬赠之作李更多的是对工作空间的描写,如白居易《待漏入阁书事奉赠元九学士阁老》:
衙排宣政仗,门启紫宸关。
彩笔停书命,花砖趁立班。
稀星点银砾,残月堕金环。
暗漏犹传水,明河渐下山。
从东分地色,向北仰天颜。
碧缕炉烟直,红垂佩尾闲。
纶闱惭并入,翰苑忝先攀。
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殷。
诗仙归洞里,酒病滞人间。
好去鸳鸾侣,冲天便不还。
该诗所写的是白居易所见元稹的翰苑生活,“詩仙归洞里,酒病滞人间。”回顾的是过往的生活。元稹有《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
未勘银台契,先排浴殿关。
沃心因特召,承旨绝常班。
飐闪才人袖,呕鸦软举环。
宫花低作帐,云从积成山。
密视枢机草,偷瞻咫尺颜。
恩垂天语近,对久漏声闲。
丹陛曾同立,金銮恨独攀。
笔无鸿业润,袍愧紫文殷。
河水通天上,瀛州接世间。
谪仙名籍在,何不重来还。
这是两人在公务之暇的酬赠之作。元白在这一时期也有游宴之作,亦写京城的四时风光,两人之间更是一直彼此理解彼此赏识,而今获得理想的工作职位,自然是各司其职,共同享受痛苦和快乐。科场案的兴起、党争场之形成,他们无法置身事外。政事一忙,共同笑看风月花草的时间自然少了。或许是遗存文本过少,我们实在难以复原这一阶段他们在长安的休闲生活图景。
此后无论元稹是在同州、浙东,还是鄂州,元白之间是以诗筒唱和,或因邻郡而时常往来,均过上相对散淡的休闲生活。如尚永亮先生所论:
元白的唱和之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前已述及的元和五年至十年,二人首次长时间分离,开始批量唱和;二是元和十年至十四年,元白分别谪居通州、江州,唱酬日盛,由此形成文学史上有名的通江唱和现象;三是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元稹出镇越州,白居易刺史杭州、苏州等地,二人借助诗筒往返酬唱,一时传为佳话。
(尚永亮《元白并称与多面元白》,《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
从文学唱和而言,长安时期的三个阶段并不是元白创作的高峰期。可是,他们寓居京都均任清职,游遍长安行乐地,每过一段贬谪或者外放的生活就会回到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安居于此,长安大道周边的一花一草、一车一马、一山一寺都留下了他们追求激情和梦想的印记。
(作者系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