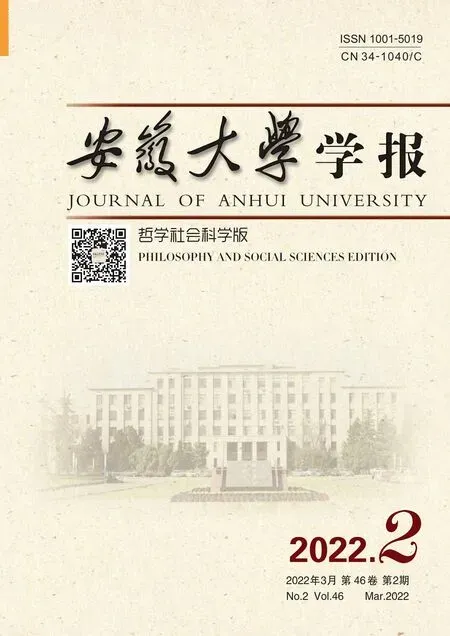宋代皮场王原型“壁镜”研究
程立中,朱正业
北宋时期,东京显仁坊建有皮场庙,又称“皮场土地祠”。原本普通的土地祠,宋徽宗不断对祠神进行加封,从建中靖国元年(1101)封灵贶侯,到崇宁四年(1105)封灵惠显通王(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引《国朝会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10页。,四年时间里皮场土地就升格为四字王,并进入国家祀典。历史上,皮场王形象演化较为复杂,有“神农”说、“席旦”说、“邳彤”说等;在神祇功能方面,涉及“疗疡”“科举”“护国”等。关于皮场王的原型,宋徽宗说“乃壁镜也”(2)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册,第988页。,但其具体形象和物种归属模糊不清。1980年代初,皮场庙和皮场王进入学者视野,但专论不多(3)相关学术史梳理,请参刘小朦《皮场庙的源流》(载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王元林和孙廷林《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而关于皮场王原型“壁镜”,学者的解释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壁镜为“毒蛇”(4)王元林、孙廷林:《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4页。,有学者主张是“昆虫”(5)刘小朦:《皮场庙的源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页。。而皮场王的形象和功能都是由最初的“原型”发展演化而来,因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壁镜”的物种归属问题。
一、缘起:皮场王与皮场庙
“皮场王”在北宋最初名为“皮场土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朝廷颁布的《皮场土地制》言:
皮场土地,人神之分异矣。传称以道莅天下,则其效至于神不伤人,尔神非特不伤人而已,疡医之所难疗者,又能愈之,以显济于一方。朕咸秩无文,肆及遐外,而况都邑之内灵贶若此者乎。爰视侯封,褒锡美号,益隆初惠,以助吾仁,可特封灵贶侯。(6)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137《礼典二十二·地示 山川 杂记·皮场土地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86页。
崇宁元年(1102),“中书省奉圣旨:皮场土地灵贶侯,以灰药救疾,所疗辄愈,尚居侯列,未称其神,可封以公爵”,制文曰:
皮场土地灵贶侯,夫神与吏,有功吾民,则褒崇之,虽幽显不同,而示天下之公一也,惟尔有神,疗民疾苦,所疗辄愈,厥功著焉,易侯而公,以称先灵,以慰民望。祗予之诚,以示朕爱民宠神之意,可特封灵贶公。(7)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137《礼典二十二·地示 山川 杂记·皮场土地封灵贶公制》,第487页。
至崇宁四年,皮场土地被封为灵惠显通王。而皮场王祭祀场所,在北宋最初“名曰皮场土地祠”(8)(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4《东都随朝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17页。,后又称“皮场土地神祠”(9)(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0页。。崇宁四年开始出现“皮场庙”之名(10)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88页。。
南宋时期,皮场王又被称为“皮场大王”,如《夷坚志》记载:“数卒挽一车,上立小黄帜云:‘皮场大王寄席相公钱三百贯。’置于地而去。”(11)(宋)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5《皮场大王》,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又载:“秀州外科张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痈疽异方》一册”(12)(宋)洪迈:《夷坚志·夷坚支乙》卷5《张小娘子》,何卓点校,第828页。,并授以手法大概,遂因医著名。相应地,皮场庙当时也称“皮场大王庙”(1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诸神庙》,第2册,第1087页。,“在临安西湖者,其威灵不减汴都”(14)(宋)洪迈:《夷坚志·夷坚三志》卷4《皮场护叶生》,何卓点校,第1493页。。也曾改称“惠应庙”,临安城中共有四处,“一吴山,一万松岭,一侍郎桥,一元真观”(15)(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0页。。但南宋时期大多仍以“皮场庙”或“皮场王庙”(16)(明)王鏊:《姑苏志》卷27《坛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482页。称之,如《燕翼诒谋录》载:“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17)(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4,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页。又如楼钥《北行日录》:“车行四十五里,道傍多陂塘……皮场庙甚饰。”(18)(宋)楼钥:《攻愧集》卷111《北行日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689页。
关于“皮场”名称之缘起,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献帝赐号”。《咸淳临安志》收录有北宋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公事周秋所写的惠应庙《记》文,文中写道:“后因河北妖人张角邪逆,攻陷邢城,向望相州。皮场镇之人,虔诚祈祷,雨雪并下,杀贼定乱,护国显灵。献帝赐号始曰‘皮场’焉。”(19)(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1页。就周秋《记》文内容而言,“它记录了现存皮场庙传说的最早版本”(20)刘小朦:《皮场庙的源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第26页。作者认为“这篇文字很可能是为纪念皇帝赐封皮场土地而作”。。由于此篇《记》文内容源自耆老之言,所言皮场庙历史缺乏翔实文献记载,故“献帝赐号”之说影响不大。
又有宋代学者提出皮场之名源自“皮剥所”,“皮场即皮剥所也”(21)(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4,诚刚点校,第36页。。北宋皮剥所“隶太仆寺”(22)(元)脱脱等:《宋史》卷189《志第一百四十二·兵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691页。当时太仆寺所辖的牧养上下监,主要掌管治疗病马及申驹之数,一旦“有耗失则送皮剥所”(《宋史》卷164《志第一百一十七·职官四》)。,开宝二年(969)置,主要职能是“掌割剥马牛驴骡诸畜之死者,给诸司工匠、亲从角抵官、五坊鹰犬之食”(2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皮剥所》,第5册,第3172页。。南宋绍兴八年(1138)九月,“复置皮剥所,以掌鬻官私倒毙牛马之事”(2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辛更儒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46页。。可见宋代皮剥所主要职能是负责死亡诸畜的割剥事务,与皮场之名关联甚少。就位置而言,北宋皮剥所“一在嘉庆坊,一在延禧坊”(25)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皮剥所》,第5册,第3172页。根据至道元年(995)张洎奉诏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可知,嘉庆坊位于东京新城内北厢,延禧坊位于东京新城内西厢。。而皮场庙所在的显仁坊,则为“新城内城东厢九坊”(26)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第15册,第9272页。之一,可见皮剥所与皮场庙所处位置差距较大,皮场之名源自“皮剥所”的可能性不大。
北宋为处理死亡诸畜皮角筋骨,除设置皮剥所外,还置有皮角场,故有皮场之名始于“皮角场”之说。如《延祐四明志》记载:“皮场庙……原在汴显仁坊皮角场,故名。”(27)(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5《祠祀考》,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53页。皮角场的主要职能是“掌收皮革、筋角,以供作坊之用”(28)(元)脱脱等:《宋史》卷165《志第一百一十八·职官五》,第3920页。。北宋时期皮角场又称“皮角场库”(29)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皮角场库》,第12册,第7174页。原为一场三库,景德三年 (1006) 并三库为一库,位于显仁坊,主要职能是“掌受天下骨、革、筋、角、脂、硝,给造军器、鞍辔、毡毯”。或“皮角四场库”(30)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物料库》,第12册,第7171页。神宗熙宁七年(1074)九月二十六日,军器监言:“作坊物料库、皮角四场库,自来诸处取索应用官物,并系本库供送。”,隶属军器监,虽称谓略有差异,实为一地。皮角场有时又称“皮场”,如“皮剥所每匹死马收炼脂油七两送皮场,充熟皮之用”(31)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皮剥所》,第5册,第3172页。。南宋皮角场归入工部(32)(元)脱脱等:《宋史》卷165《志第一百一十八·职官五》,第3921页。建炎三年(1129),朝廷下诏军器监并归工部,皮角场也随之并入工部。,绍兴八年九月三十日,高宗诏复置皮剥所,名为“行在皮剥所”(3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皮剥所》,第5册,第3173页。其主要职能为,“皮剥所收到筋皮角,令军器所取拨使用,骔尾令杂卖场出卖”。,皮角场的部分职能为皮剥所取代,尤其是嘉定以后,皮角场“事最稀简,特为储才之所”(3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7《职官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17页。。就名称和位置而论,皮场之名源于“皮角场”说更容易被世人接受。
北宋皮场王庙位于东京“显仁坊”(35)(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0页。。由北宋东京建筑空间布局可知,宫城最先营建,“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按图营建”(36)(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卷1,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随后,又营建里城,即原旧城,“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筑”(37)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4页。,后周广顺二年(952)正月,郭威下诏重修,“开封府修补京师罗城,率畿内丁夫五万五千版筑,旬日而罢”(38)(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9页。。因新外城未筑,唐至五代对宫城外旧城统称罗城。周世宗始修新城,即“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39)(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东都外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开宝戊辰(968),宋太祖初修汴京,又“大其城址”(40)(宋)岳珂:《桯史》卷1《汴京故城》,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至道元年(995),张洎奉诏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41)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第15册,第9272页。,后又经两次增筑重修。政和六年(1116),徽宗又“诏有司度国之南展筑京城”(42)(元)脱脱等:《宋史》卷85《志第三十八·地理一》,第2102页。,最终新城规模达到周五十里百六十五步。据文献记载,旧城内四厢四十六坊,新城内四厢六十七坊(4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第15册,第9272页。,其中皮场庙所在的显仁坊位于新城内东厢,该坊周围药铺众多,医药行业兴盛。如“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44)(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7册,第598页。;马行街北去,“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45)(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马行街北诸医铺》,第268页。。当时也有人定居此坊经营医药,如靳豪“北宋时居东京之显仁坊,隐居市药,每日设浆于肆,以济行者”(46)《博物汇编》卷528《医部医术名流列传五》,《古今图书集成》第46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皮场庙所在的显仁坊浓郁的医药环境,可能与皮场王医药神色彩有关。
二、封祀:壁镜的“神格化”过程
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在“三圣”封爵的准奏中,提及皮场王原型“壁镜”:
泾原路经略司言:“平夏城三圣庙,土人言有三蜥蜴见,故谓之三圣。昔西贼寇边,大云梯瞰城甚危迫,祷于神,大风折梯,遂解平夏之围。乞加封爵。”上曰:“龙蛇灵异之地,能救活人,即天录其功。如京师皮场庙神乃壁镜也,其质或白黑,有五足,疾病疕疡者造为其所,香火辄愈,盖救万民之病苦,以积功行也。”遂从其请。(47)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88页。
由此可知,宋徽宗所提及的“壁镜”类似于三圣庙神原型“蜥蜴”,也是一种动物。
目前所见关于“壁镜”记载的最早文献,为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壁镜,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杀蛇。”(4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8《支动》,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7页。按段氏所言,“壁镜”是一种具有“毒”性的动物,且毒性较强,“毒人必死”,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壁镜”的物种归属。
宋代医药文献中,对“壁镜”也有相关记载。如医家张杲在《医说》中言,治壁镜咬,醋磨大黄涂之,又言“壁镜毒人必死,用白矾治之”(49)(宋)张杲:《医说》卷7《蛇虫兽咬犬伤·壁镜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2册,第162页。。董汲的《旅舍备要方》则记载壁镜咬人立死治之方:“槟榔,不计多少。右烧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后以醋调贴之。”(50)(宋)董汲:《旅舍备要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8册,第450页。这些医书仍然没有指出“壁镜”为何种动物。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把“治壁镜咬”(51)(宋)不著撰者:《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卷17《诸虫咬蜇论》,吴康健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488页。的药方,归入“诸虫咬蜇论”。而李石的《续博物志》则记载:“桑柴灰取汁,煎白矾,治壁镜虫毒。”(52)(宋)李石撰,(清)陈逢衡疏证:《续博物志疏证》卷9,唐子恒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219页。《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把“壁镜咬、蜘蛛咬”(53)(宋)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8《治疮肿伤折》,陈庆平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并称。《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记载:“壁镜咬方……以柴灰汁三度煮沸,取白矾为膏,涂疮口即瘥。治疗毒蛇亦效。”(54)(宋)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卷14《中毒门·蛇虫伤》,郭瑞华等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综上可知,宋代医药文献大多把“壁镜”归入“虫”类,有时与“蜘蛛”并称,且与治疗“毒蛇”咬相区分。
《太平广记》把“壁镜”归入“昆虫”(5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77《昆虫五·壁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6册,第495页。类,有时壁镜又被称作“壁钱”(56)(明)张自烈、(清)廖文英编:《正字通》卷9《申集中·虫部》,董琨整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989页。该书“蛛”条注云:《本草》曰“壁钱”、曰“壁镜”,皆以窠形命名,北人呼为“壁茧”。。北宋重要本草著作《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记载:“壁钱……虫似蜘蛛……此土人呼为壁茧。”(57)(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22《虫鱼部下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457页。宋代以后,文献记载更为明确,如“壁镜,大如蜘蛛而形扁”(58)(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120《外科·损伤门·诸虫兽蜇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1册,第559页。。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载有“壁镜咬方”(59)(宋)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卷14《中毒门·蛇虫伤》,郭瑞华等点校,第346页。,该书点校者在注释中云:“壁镜,蛛形纲壁钱科动物。”可见宋代文献记载的“壁镜”,应为蜘蛛中具有较强“毒”性的一类。而这种名为“壁镜”的蜘蛛,与皮场庙神的关联,从后世皮场庙的传说中,或许可以推知:“俗呼皮场庙……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鞹。蒸溃产蝎,蜇人辄死。……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疮疡,有祷辄应。汉建武间……傍邑皆立庙。宋时,建庙于汴京显仁坊。建炎南渡……累封王爵。”(60)(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卷12《南山城内胜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54~155页。此传说中的“皮场镇”,与前述北宋周秋撰写的惠应庙《记》文中“皮场镇”相吻合,或为当时在皮角场基础上形成的皮角筋骨贸易之地。其中“萃河北皮鞹。蒸溃产蝎,蜇人辄死”,说明皮场镇处理皮鞹过程中,由于蒸溃而滋生许多毒蝎,且“蜇人辄死”,给当地民众生命带来威胁。而“祷神杀蝎”,暗含皮场镇出现一种能够克制“蝎”毒之物,可以保护当地民众生命安全。“镇民德之,遂立祠”,应为当时民众建立“皮场土地祠”(61)(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4《东都随朝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第117页。祈求护佑的初始原因。

宋代对于祠庙的赐封,“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64)(元)脱脱等:《宋史》卷105《志第五十八·礼八》,第2562页。,但徽宗初年“诸州神祠加封,多有不应条令”者(65)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90页。,故有朝臣上奏规范神祇封祀。原本普通的“皮场土地”,于建中靖国元年被封灵贶侯,“爰视侯封,褒锡美号,益隆初惠,以助吾仁”。次年三月,中书省奉旨颁布《皮场土地封灵贶公制》:“易侯而公,以称先灵,以慰民望。”可知朝廷通过封爵,意在推动“壁镜”的神格化,故于崇宁四年,壁镜成为“京师皮场庙神”(66)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88页。,“封灵惠王,七月加封灵惠显通王。十月封其配灵婉夫人,十一月改封灵淑夫人”(6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0页。。可见皮场庙神即是皮场王,而皮场王实为皮场“灵惠显通王”的简称。
元丰六年(1083),太常寺曾议定封祀规制:“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68)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90页。皮场王的封祀过程,是严格按照太常寺议定的封祀规制执行的。政和元年正月,宋廷对东京祠庙也进行规范,“诏开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区,迁其像入寺观及本庙……仍禁军民擅立大小祠庙”(69)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二○·诸祠庙·杂录》,第2册,第995页。。在此背景下,官方对皮场王再次升格,政和五年七月,“改赐额曰‘灵应’”(70)(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0页。。同年十一月,周秋为纪念皮场王赐封而作的《记》文,借耆老之言:“乃古神农皇帝。……杀贼定乱,护国显灵。献帝赐号始曰‘皮场’焉。……重建庙于古汴东京显仁坊。暨我宋列圣,褒扬累封。”(7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1页。作为官方祀典,此时刻意隐去皮场庙神壁镜,而把皮场王原型替换为“神农”,其原因可能是那次大规模的毁祠活动,“让官方对赐封的神祇越来越挑剔、越来越倾向于建构出有着重大意义的神迹故事”(72)刘小朦:《皮场庙的源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第28页。,从而使“皮场大王开始自觉抛弃毒虫壁镜的原型,积极向国家礼制教化靠拢,异化为与灵验事迹密切相关的医药神古神农”(73)王元林、孙廷林:《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8页。。虽然皮场王原型被替换,但皮场庙所奉之神,仅为皮场王与其夫人,并无其他神祇。
南宋初,有商立者,“携其像至杭”,在吴山看江亭建皮场祠,以供有疾者祈福,时人谓之“神农”。绍定四年(1231)九月,皮场祠毁,后宋理宗在故址重建皮场庙。咸淳五年(1269)十一月,“王加封显祐,灵婉加嘉德,灵淑加嘉靖”(74)(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1页。。这也成为元代《新编红白蜘蛛小说》的素材来源,“给能杀蝎治疹疾疮疡的皮场神配上蜘蛛夫人,在临安瓦舍的说话人口里就编出了皮场神和蜘蛛夫人悲欢离合的故事”(75)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76页。。实际上初封灵婉,未及改封灵淑,“止是一神,加封之际,乃误为二小君”(76)(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3《祠祀三·东京旧祠·惠应庙》,《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11页。。文献记载,南宋席益曾宣扬其父“席旦”(77)(宋)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5《皮场大王》,何卓点校,第39页。为皮场王,其原因是“南渡之后要寄寓温州的席益借皮场大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78)王元林、孙廷林:《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9页。。皮场王席旦仅为民间传说,其像并未供入皮场庙中。
总之,壁镜原本只是具有“毒”性的蜘蛛,因虫体入药可治愈蝎毒,被苦于毒蝎之害的皮场镇人奉为神灵,并为之建祠乞爵。在宋朝皇权的加持下,被屡次赐爵,进而“神格化”,成为国家认可的皮场庙神,后又被连续封王,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皮场王”。其间皮场王原型因现实需要虽发生异化,但皮场庙中所奉之神,仅有皮场王与其夫人,并无其他神祇。
三、特征:“其质或白黑,有五足”
古代文献中,以“壁镜”命名的动物,也有“壁镜蛇”(79)(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5《金翠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3册,第843页。,形体“身扁五色”(80)(清)陆凤藻:《小知录》卷12《昆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2页。,但仅见于明清极少数典籍,大量的文献则明确记载“壁镜”为一种类似“蜘蛛”的动物。探讨皮场王原型壁镜的物种归属问题,还应回到最初提出壁镜的“场景”之中。如前所述,崇宁四年宋徽宗提到,壁镜“其质或白黑,有五足”。对于“壁镜”这种具有一定地域性的物种而言,在古代方志中或有所记载,如光绪《丹徒县志》就对“壁镜”的身体颜色及其不同称谓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壁镜:一曰‘壁茧’,一曰‘壁钱’,类蜘蛛而极扁,白质而黑章,作茧壁间,其大如钱,其光如镜,封子于内而自外抱之,俗呼‘蟢子’。”(81)光绪《丹徒县志》卷18《食货十一·物产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可见丹徒县境内存在的“壁镜”,是一种类似蜘蛛的动物,身体极扁,颜色“白质而黑章”,这与宋徽宗所言京师皮场庙神壁镜相符。又光绪《黔江县志》记载:“蜘蛛:类极多,一名蟗,一名纲公,吐丝于壁,白大如钱者,俗呼为‘壁镜’。”(82)光绪《黔江县志》卷3《物产·虫豸之类》,《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22)》,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第638页。黔江县境内的蜘蛛“壁镜”,也为“白”色。蜘蛛不仅种类繁多,由于地域差异,方言发音不同,往往同一种蜘蛛,其各地的称谓也略有差异,“壁钱、壁镜、壁茧、八脚诸名,五方之方语也”(83)道光《凤凰厅志》卷18《物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7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北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记载:“虫似蜘蛛,作白幕如钱,在暗壁间,此土人呼为壁茧。”(84)(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22《虫鱼部下品》,第457页。又明代《山堂肆考》记载:“壁钱,虫似蜘蛛而身扁,作白幕如钱,著壁间,俗呼为壁茧,其抱子隔幕而伏,生子百数,坼幕而出,一名扁蟢,一名壁镜。”(85)(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228《昆虫·作幕如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8册,第502页。由此可知,壁镜作为一种“昆虫”,身形似蜘蛛,并“作白幕如钱”,无论是壁镜自身的颜色,还是其所做的“幕”,均有“白”色,这与宋徽宗所言壁镜“其质或白黑”吻合。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就记载有治“壁镜”毒人的药方,但没有涉及壁镜的物种归属和具体形状。宋代《太平广记》也有“壁镜”的记载,主要内容节录自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略有修改,其中在“巳年不宜杀蛇”一语之前,增加了“身扁,五足者是”(8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77《昆虫五·壁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6册,第495页。。这显然是对段成式所言“壁镜”形体特征进行的补充解释,可见壁镜的形体具有“五足”“身扁”等特征。张国风认为,现存最早的《太平广记》刻本,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无锡谈恺所刻,刻本前附有《太平广记表》,上表的时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太平广记》的成书时间”(87)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百余年之后宋徽宗所言壁镜“有五足”,与李昉等在《太平广记》中对壁镜形体“身扁,五足者是”的注解,或为一脉相承,可见宋徽宗所说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所依凭。也有学者依据《小知录》所载“扁蛇,一曰壁镜,身扁五色”(88)(清)陆凤藻:《小知录》卷12《昆虫》,第362页。,从而推测“五足”或为“五色”之讹(89)王元林、孙廷林:《皮场大王信仰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4页。,但难以让人信服。
在部分明代文献中,也可看到有关壁镜“五足”的记载,如黄一正所辑的《事物绀珠》:“身扁五足,毒人必死。”(90)(明)黄一正辑:《事物绀珠》卷31《昆虫部·蚑蛲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3页。这与段成式、李昉、宋徽宗等人所言壁镜特征相符,虽然也没有明确指出此物的具体形态,但作者把“壁镜”归入“昆虫部”的“蚑蛲类”(行动微虫),并没有纳入“昆虫部”的“蛇类”,显然“五足”壁镜属于虫类,而不是属蛇类。又如明代陈仁锡所辑《潜确居类书》“壁镜”条引《酉阳杂俎》,注释云“身扁五足者是”(91)(明)陈仁锡辑:《潜确居类书》卷120《飞跃部十七·虫豸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63页。。明代部分工具类书籍也有壁镜“五足”的记载,如来斯行《槎庵小乘》“壁镜方”条引《酉阳杂俎》,注解云“身扁五足者是”(92)(明)来斯行:《槎庵小乘》卷30《验方类·壁镜方》,《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75页。。成书于明清时期的《骈雅训纂》“壁镜”条:“五足,皆毒虫也。”(93)(明)朱谋玮,(清)魏茂林:《骈雅训纂》卷7《释虫鱼·壁镜》,光绪十二年后知不足斋校刊本。也有部分文献记载壁镜为类似蜘蛛,有“六足”或“八足”的动物,如清代屠粹忠所辑《三才藻异》“壁镜”条:“似蜘蛛,身扁六足,作白幕,如钱帖壁,名壁钱。”(94)(清)屠粹忠辑:《三才藻异》卷25《动物而器物名者·壁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14页。又如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壁镜”条:“大如蜘蛛而形扁,斑色,八足而长,作白幕加(如)钱,贴墙壁间。”(95)(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卷120《外科·损伤门·诸虫兽蜇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71册,第559页。清代俞樾称亲眼见过此毒虫:“壁镜,毒虫也,其状如蟢子而大,善吸人影,余前于江西见之,曾赋一诗,而不知其名。”并言新安亦有之,名曰“壁镜”。其诗云:“跂跂脉脉善缘壁,谓非守宫即蜥蜴……主人为我言,是物名‘壁镜’。不图罗钳吉网外,世更有此镜新磨。”(96)(清)俞樾:《春在堂诗编·乙巳编·诗二》,《春在堂全书》第五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0页。“跂跂脉脉善缘壁”“不图罗钳吉网外,世更有此镜新磨”等诗句,描写的均为蜘蛛的某些特征,俞樾称自己亲眼所见,应为不虚。
由此可知,具有“身扁五足”形体特征的壁镜,自唐宋至于明清,屡见于文献记载,并大都被归为“虫”类,部分文献直接标识“昆虫”类,而不归为“蛇类”。随后明清文献中又出现了“六足”“八足”的壁镜,但大都明确指出其形体与蜘蛛类似。
四、功能:“疡医之所难疗者,又能愈之”
《酉阳杂俎》中提到壁镜“毒人必死”,而含有较强毒性的动物,易于让人联想到“毒蛇”,如明代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记载:“壁镜蛇,身扁,五色,螫人必死。”(97)(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5《金翠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3册,第843页。由于《玉芝堂谈荟》援引内容常不标出处,无从稽核,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亦有错误之处,“故考证掌故,订正名物者,亦错出其间”(9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3《玉芝堂谈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3页。。《玉芝堂谈荟》中的螫人必死的“壁镜蛇”是否真的存在,无从稽核。而关于毒人必死的壁镜“蜘蛛”的记载相对较多,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壁镜……大如蜘蛛……或云其虫有毒,咬人至死。”(9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0《虫部二·壁钱》,陈贵廷等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64页。黄一正所辑《事物绀珠》:“壁镜,身扁五足,毒人必死。”(100)(明)黄一正辑:《事物绀珠》卷31《昆虫部·蚑蛲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1册,第53页。清代陈逢衡认为,《酉阳杂俎》中的“毒人必死”的壁镜,“一名壁钱”(101)(宋)李石撰,(清)陈逢衡疏证:《续博物志疏证》卷9,唐子恒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219页。。由于文献所记或口耳相传,蜘蛛壁镜具有“毒人必死”的能力,故后人对此动物较为忌惮。
作为蜘蛛的“壁镜”,除具有“毒人必死”的特点外,更重要的功能为“疗疾”,因为其虫体本身及窠巢均可入药,且为治疗某些疾病的良药。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记载:“壁钱,无毒。主鼻衄及金疮,下血不止,捺取虫汁点疮上及鼻中,亦疗外野鸡病下血。”(102)(唐)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卷6《虫鱼部·壁钱》,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壁钱是壁镜之别名,因其形如古钱,故称壁钱。《本草拾遗》作为“本草”类医药典籍,此处的“无毒”,不是指活虫咬人无毒,而是作为一种药物而言的,即虫体入药无毒。如《本草纲目》:“【释名】壁镜〔时珍曰〕皆以窠形命名也。……【气味】无毒。”(10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0《虫部二·壁钱》,陈贵廷等点校,第964页。依据陈藏器所言,壁镜虫体即可入药,可以治愈“鼻衄”“金疮”“下血不止”和“外野鸡病下血”等症,其治疗之法,“取虫汁点疮上及鼻中”。其中“鼻衄”即鼻子出血,“夫肺主气,开窍于鼻,血随气上。今血既妄行,故于鼻出而为衄也”(104)(宋)徽宗敕编,(清)程林删定:《圣济总录纂要》卷8《失血门·鼻衄》,第221页。。而“金疮”则为金属器物所伤,即“一切刀箭所伤”者(105)(金)张从正撰,徐江雁、刘文礼校注:《〈儒门事亲〉校注》卷5《金疮五十四》,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本草拾遗》所言“下血不止”中的“下血”,民国时期谢观主编的《中医大辞典》解释为“下血,便血也”(106)谢观主编:《中医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7页。。从古代医书记载来看,“下血不止”常用来描述妇女妊娠期间出现的病症现象。隋朝巢元方的《巢氏诸病源候总论》记载:“此谓卒有损动,或冷热不调和,致伤于胎,故卒痛下血不止者,堕胎也。”(107)(隋)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41《妇人妊娠疾诸候上·任(妊)娠卒下血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第847页。又如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或胎上抢心,则绝闷欲死,冷汗自出,喘满不食,或食毒物,误服草药,伤动胎气,下血不止。”(108)(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4《产科兼妇人杂病科·保产》,王育学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由此可知,唐代陈藏器所言“壁镜”入药治疗的“下血不止”,并非仅限于常说的便血不止或流血不止的“普通”病症,可能更多的是指妇女怀胎期间出现的较为危险的出血性重症。尚志钧认为《本草拾遗》中的“外野鸡病下血”中“野鸡病”,即现代所说的“痔疮”一类的疾病:“野鸡病即痔疾……外野鸡病即外痔。”(109)(唐)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卷6《虫鱼部·壁钱》,第258页。又如明代朱等编的《普济方》:“治恶疮疽痈肿疳疮野鸡病”(110)(明)朱等编:《普济方》卷275《诸疮肿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6册,第133页。,把“野鸡病”与“疮疽”“痈肿”“疳疮”并提,可见其为类似疽痈的一种“疮”疾。
除虫体可入药外,壁镜所做的窠巢也是一种药材,对治疗孕妇产后咳逆及小儿吐逆等病症,均具有较好的疗效。宋代《妇人大全良方》记载:“古壁镜窠三四个,水一小盏,煎至一半热服。”(111)(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22《产后咳噫方论第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601页。又如《本草拾遗》记载:“其虫上钱幕,主小儿呕吐逆,取二七煮汁饮之。虫似蜘蛛,作白幕如钱,在暗壁间,此土人呼为壁茧。”(112)(唐)陈藏器撰,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卷6《虫鱼部·壁钱》,第257~258页。李时珍《本草纲目》在介绍壁镜主治功能时,引用了陈藏器的论述,其中把“外野鸡病下血”写成“五野鸡病下血”。除“鼻衄”“金疮”“野鸡病”外,李时珍把“壁镜”的治疗范围进一步扩大:“治大人、小儿急疳,牙蚀腐臭,以壁虫同人中白等分烧研贴之。又主喉痹。”壁镜窠巢除治疗“小儿吐逆”和“产后咳逆”外,又增加了“窠幕〔主治〕……又止金疮、诸疮出血不止,及治疮口不敛,取茧频贴之。止虫牙痛”(11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0《虫部二·壁钱》,陈贵廷等点校,第964页。。明代“蜘蛛”壁镜治病范围的扩大,或是人们对其医药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蜘蛛”壁镜不仅自身具有毒性,甚至“毒人必死”,而其虫体本身和所做窠巢均为药材,可治疗“鼻衄”“金疮”“急疳”“喉痹”“痔疾”“虫牙疼痛”“疮口出血”和“疮口不敛”等病症,对治疗“小儿吐逆”“产后咳逆”和“下血不止”等妇幼“保生”疾病,均有良好疗效。但“毒蛇”壁镜并没有见到相关医药价值的记载。
宋徽宗所言“如京师皮场庙神乃壁镜也……疾病疕疡者造为其所,香火辄愈,盖救万民之病苦,以积功行也”,应是针对“蜘蛛”壁镜所具有的医药价值而言的,因能够救万民之病苦,故有“疾病疕疡者造为其所,香火辄愈”。又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宋徽宗封皮场土地为“灵贶侯”的制文:“尔神非特不伤人而已,疡医之所难疗者,又能愈之,以显济于一方。”正是指出“蜘蛛”壁镜虫体和窠巢入药,对于一些“疮疡”之类疑难杂症,具有良好的疗效,故言“疡医之所难疗者,又能愈之,以显济于一方”。在崇宁元年三月,宋徽宗为皮场土地封“灵贶公”时所言“以灰药救疾,所疗辄愈”,并非完全指皮场庙巫医、庙祝所为,更可能类似李时珍所言壁镜入药治病之法,“以壁虫同人中白等分烧研贴之”、“以壁钱惹矾烧存性,出火毒为末”(11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0《虫部二·壁钱》,陈贵廷等点校,第964页。之类。正是蜘蛛“壁镜”的这种“救民疾苦”“所疗辄愈”的显著功效,宋徽宗在制文中才有“有功吾民,则褒崇之”“以慰民望”的盛赞。
五、结 语
通过文献梳理,笔者认为宋徽宗所言皮场庙神“壁镜”,其原型为“蜘蛛”比“毒蛇”更为恰当。就形体特征而言,在明清方志和唐宋以来的类书、医书等文献中,名为壁镜的“蜘蛛”屡见记载,且与宋徽宗所言壁镜“其质或白黑,有五足”相一致;在功能方面,名为壁镜的“蜘蛛”,不仅能“毒人必死”,其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且对“疮疡”“下血不止”“小儿咳逆”等疑难杂症均具有良好疗效,这正是宋徽宗所言皮场王“有功吾民,则褒崇之”的主要原因。至于其形象异化方面,从“神农”到“席旦”,虽有多种演化,但大都与“医药”有关,正如学者所言:“这种演变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建构,而是原有神祇形象的挪用与转换,在皮场庙的例子当中,药物、治病等元素一直存在于传说的主题当中。”(115)刘小朦:《皮场庙的源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5卷,第28页。只有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治病的“蜘蛛”壁镜,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复杂的异化现象和拓展功能,而不具有入药治病功能的“毒蛇”壁镜则很难做到。因此,宋徽宗所言皮场王原型,是一种当时名为壁镜的“蜘蛛”,更为合理。作为皮场王原型的“壁镜”本身具有毒性,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对于某些疾病疗效显著,从而引起世人的推崇,随之其形象被人格化,而医药功能则被神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