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孟淑珍访谈录*
王丙珍
传承人简介:孟淑珍,女,鄂伦春族,1951年7月2日生,黑河市逊克县人。她醉心于文学创作,奉献于鄂伦春族“摩苏昆”的调查、传承与研究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1956年,孟淑珍随同家人搬迁至黑河市逊克县新鄂鄂伦春民族乡,她在鄂伦春族聚居地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浸染与熏陶。1979年至1986年,她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搜集并命名了鄂伦春族“摩苏昆”,并用50多盘磁带录制了几十篇“摩苏昆”作品,相关文本已陆续出版。2018年5月,孟淑珍被认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1月,《摩苏昆集成》(国际音标版)一书已公开出版发行。2017年,孟淑珍改编了鄂伦春族“摩苏昆”原生态舞台音乐剧《艾么汗与乌娜吉的亲事》,在剧本的排练及鄂伦春民歌的录制活动中,她发现并培养了24名年轻的鄂伦春族歌手,延续了鄂伦春族文化的生命。
鄂伦春族“摩苏昆”广泛地流传于鄂伦春人的聚居地。王肯于1956年8月8日-11日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和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分别采录了孟古古善、关云霞的说唱作品《金宝和银珠》与《幸福泡》,这可谓是最早的“摩苏昆”文本。2006年5月,鄂伦春族“摩苏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英雄格帕欠》《波尔卡内莫日根》《阿尔塔内莫日根》《双飞鸟的传说》《坦托鸟》《娃都堪和雅都堪》《诺努兰》《阿尔旦滚滚蝶》《罂粟花的来历》《艾赫》《库巴列》《卡拉尔和库勒尔》《薇丽彦和英沙布》《婕兰和库善》《特昂格列的故事》等。2017年4月10日-5月20日,2018年9月9日-9月23日,笔者在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新兴鄂伦春民族乡与新鄂鄂伦春民族乡开展为期55天的田野调查工作。期间,2017年4月18日,笔者在黑河市爱辉区采访了孟淑珍。她热情、生动而详尽地解答了鄂伦春族“摩苏昆”的相关问题,并在讲解的过程中即兴地表演、示范、模仿唱段,详实地阐释了鄂伦春族“摩苏昆”的本质、翻译、鄂伦春语、抢救、挖掘、萨满、传承与创新等。
一、关于“摩苏昆”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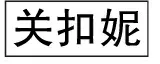
王丙珍(以下简称“王”):阿姨好!再三地打扰、麻烦您,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的著作已有两种外文译本吧?关小云与王宏刚合著的《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一书被翻译成日文版《鄂伦春族萨满》,1999年9月在东京第一书房出版社出版。如果正常的话,翻译他人的作品需要授权。今天,我一共有四个问题:一是“摩苏昆”的本质,二是您的调查研究经历,三是说唱一段“摩苏昆”,最后一个是“摩苏昆”的传承。我还想多问一些问题,赫哲族伊玛堪是世界级非遗项目,我当时对这件事挺有想法,因为“摩苏昆”和“伊玛堪”的文化价值是一样的。您讲讲“摩苏昆”,我也问过很多人。
孟(以下简称“孟”):也许有吧?那些翻译成外文版的人也不和我联系,那本书倒是给我了。据说,大连外国语大学翻译的书已出版了。你看材料就行吧?鄂伦春语“摩苏昆”的标准发音是“摩日苏昆”(morsukun),大兴安岭呼玛流域叫“达利温”(dariwen),达斡尔族有的地方叫“乌钦”,有的地方叫“乌春”。到底是“乌钦”还是“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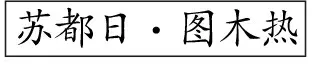
孟:我最早看过的版本是“乌钦”。我问过鄂伦春自治旗那边的人,他们说:“乌钦可能是说一段、唱一段的说唱形体的文学形式,就是口头文学形式。”马名超说是史诗?
王:你们有段时间一直都在争论“摩苏昆”是否是史诗的问题,我看过那些文献。您一直不同意“史诗说”吧?
孟:不是。我是这样的,如果完完全全地说“摩苏昆”是史诗,也不对。但是,它至少是史诗的母体。
王:您这段话说得挺好!口头文学形式就是说唱,说唱作品属于口述文学。我们能确切地把它们分开吗?口述文学与说唱文学能划等号吗?有的口头文学作品是从头唱到尾,有的则是从头说到尾,还有的是穿插式的说唱形式。口述文学、口头文学和说唱文学可以换用吗?
孟:对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来源于最早的民间的说说唱唱,包括现在所有流行的歌剧、戏剧、舞台剧。它是所有文艺的妈妈吧。所以,你说“摩苏昆”是史诗的话,也不大对。反正,它是说唱形式吧,一种口头文学形式。讲故事不就是说嘛,民歌就是唱嘛。“摩苏昆”是说一段、唱一段。说唱文学是把说和唱结合起来的一种形式。故事就是用语言去表述,民歌就是纯唱。但有时也没有很严格的界定,像《鹿的故事》那样,我也可以一开头就把它唱出来,有的人是叙述,也有的人是说一段、唱一段,它们的区别在于不能互换吧。它限定于是不是说唱文学作品,说唱文学作品一般就是说一段、唱一段。
王:口述文学内涵大还是外延大?口述文学包括说唱文学,对吧?这次,我在国家图书馆查了曲艺文献。
孟:他们现在把说唱文学归为曲艺,完全不对。因为在有了文化、文字、街头艺人以后,曲艺才形成的。而民间说唱是在那段不足的时期,不管哪个民族——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包括在内——在它的不足时期即没有文字的时候,口头文学就比较发达。在口头文学发达的时候,说唱文学的民歌、故事等这类东西就丰富多彩。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代汉语以后减少了?如果是曲艺的话,曲艺现在还存在。
王:口头文学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说的文化形式有哪些?内容有哪些?
孟:原因就是新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增多了呗。文化形式有电影、电视、戏剧、舞台剧等表演形式,内容大多反映现在的时代。比如说,随着时代的需要,那个时候的鄂伦春族民歌有这样一个曲调(表演唱la do,la do mi sol,la la do mi fa……),我们鄂伦春人在旧社会很苦,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牛、马都不会用来形容鄂伦春的生活。第一,鄂伦春人不养牛;第二,马是他们生活当中最不可缺少的、让人非常喜爱的东西。那么,鄂伦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不是与他们的生活相违背吗?所以,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时代的东西。
二、关于翻译、鄂伦春语、抢救与挖掘
////////40
王:此类做法是翻译问题吗?因为我读过的很多民间故事书里都是成语,一直以为是翻译问题。他不说“小气”,而是用“吝啬如鬼”啊。我导师问我:“你这么多年在采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是异文!”异文即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不同的人讲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地域也不一样。尤其是与书上的文字做对比,吓一跳。因为书中的成语太多了,比如东张西望、破衣喽嗖。我把那些成语划出来,一篇故事里有太多的成语了,我怀疑是二次创作。
孟:实际上,这不是翻译问题,唱来唱去,她就是这么唱的。成语是翻译问题,“东张西望”倒还可以,它比较通俗化;“破衣喽嗖”是地方方言。这也不一定,你说是二次创作,但我说,好多民间比较精华的东西用汉语翻译的话,有时还翻译不出来呢。什么叫二次创作?
王:我还以为他们自己又加工了一遍,虽然严复倡议“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民间文学只要恪守“信”与“达”就行了,民间文学本质上有别于高雅文学。我就怕文人加工它。
孟:那也不一定。为什么“摩苏昆”在那时候比较盛传?因为它精彩!精彩靠什么?除了靠好的声音表达之外,精彩的语言也要充分地展现出来。所有的汉族文学修饰成分在鄂伦春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处处存在。我说还是不一定,现在的汉族故事是最末等、最不流行的啦。它的口语化是很突出,但它不等于过去在非常发达时期的鄂伦春族传统。语言不是白开水,白开水谁愿听啊?没人愿听呀。为什么非常精彩?精彩的语言组合成的夸张的形容、形象等处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人说我融入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不是民间文学工作者,我是写小说的人,阅读与创作不融进自己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你的立足点在哪儿?你的立足点如果是汉语的话,你将现在流行的汉族口头故事硬套在少数民族的已经趋向完整化和精华化的东西上,以为就一句、一句地把它表述清楚就可以了,那完全是错误的。民间文学要是那么整的话,谁愿听啊?不精彩,淡如白水。
王:我有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感觉。过去的诸如此类的研究特别可怕,因为它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客观。
孟:是啊!而且还有一点,过去的大部分民间传承人都是萨满,或者是萨满的后代。萨满通晓一切,至少在她的场域空间,比如说越高越细密。在这场域空间往下,萨满全知道。萨满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一切都是天生的。
王:我确实佩服!我从2006年10月开始跟着萨满关扣妮调查鄂伦春族口述文学,她的记忆力太好了。她在六、七岁的时候从叔叔家门前走过,人家现在张嘴就能给你唱出来她叔叔当时唱的歌。关扣妮有一段时间得病了,身体好像要不行了。2009年,我再去找她时,她又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
孟:徐昌瀚、庞玉田认为我的翻译太文学化。现在的时代,人们说的话也赶不上过去鄂伦春人的形象化描述,如小兔子蹦蹦跳跳,鄂伦春语就这一句话:“梆梆、梆梆、梆梆……”,汉语得用很长的字才能表述完整。你怎么说它是落后的?你怎么能说它不是精华?这样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旋风旋、旋、旋、旋……它不是说旋风已过山、过水、过什么的。它就“悠呜呜呜呜呜”(手势做起伏状)的,他那么一比划人家就能看见,也能听到风翻山越岭、过河、过溪,走了很远的地方,转着到了那个地方。他也没有用词啊,没有说旋风过河、过山、过树林子,没有这些东西。但这一个动作、一个声音就能完整地表达。每一个时期创作一个经典的文化,经典的文化必须是文学化的。
“摩苏昆”的精彩在哪儿?莫宝凤连骂人都带押韵的,开玩笑都带押韵的。那她不就是李白嘛?他们说大量的押韵是我自己编进去的。我编的?我创造的?徐昌瀚在《鄂伦春族文学》中已第一个界定了“摩苏昆”到底是不是史诗。
王:我还参考了王朝阳的《鄂伦春民间故事集》一书,我没见过他。我读过你们的关于“摩苏昆”是否是史诗的那些争论,我支持马名超的观点,他认为“摩苏昆”是史诗。
孟:我是这么认为的,“摩苏昆”只不过是在还没有用文字记录的那个时期的那种程度的史诗。“摩苏昆”只能说是史诗的母体,包括所有的舞台剧。有了它以后,才有了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形式。无论哪个民族都经过那个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流传于无锡附近的吴歌,那个地方肯定比较原始,原生态的东西特别多,吴歌就传下来了。而其他地方如果先进化了,在接受的东西多了的时候,这种东西自然就减少了,或者消失了。它归属于曲艺完全是错误的,那时候应该是民间文学的说唱形式。“摩苏昆”不是曲艺!曲艺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曲艺”这个名词产生于真正的曲艺人在民间开始卖唱以后。
王:曲艺的大发展是在明末清初的那段时间。
孟:就是说,曲艺形式在那个时候才形成,它被确认了。曲艺和原始社会部族时期的“摩苏昆”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一回事!曲艺是指专职化的那种东西。
王:您说得太对了!在哈尔滨,有一个与单田芳同一时期的说书艺人王宝石,他原来在北京天桥卖艺。据他说,现在说书唱曲都不行了,因为茶馆被拆,他们没有表演的空间。而且现代人聚不了堆,建筑变得单元化,空间都被分割,再没有公共场所可以表演。我挺受启发,生存的空间改变了,山上的那种生活状态变成现在的一趟房,又由一趟房变成楼房。您如何界定“摩苏昆”是史诗还是曲艺?
孟:年轻人不愿看这些东西。他们天天在一个封闭式的空间里拿着手机、电脑,有的人长时间都不认识对门,这些都有关系。我觉得“摩苏昆”不是史诗,也不是曲艺。
王:您认为“摩苏昆”只是文学的一种说唱形式?它能被抢救过来吗?抢救会有两个结局,就像我们住院一样,抢救不一定能活过来,但至少可以多存活一段时间。“抢救”“遗产”这两个词挺可怕,因为“遗产”怎么抢救啊?一个人已经不在世了才会有遗产,民族文化的DNA需要的是民族文化“财产”。传承应该像活水那样的存活,要是仅仅停留在文字阶段,那跟汉族的曲艺是一样的了。哈尔滨早就没有茶馆了,王宝石再也没有地方弹唱了。
孟:对!“摩苏昆”就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在它的那个历史时期盛传。它盛传了,就发达了;它不盛传了、弱了,它就不行了,就衰退了,作品也少了,讲唱的人也少了,最后没了。活也活不到哪儿去!我是这么想的:“将来,它会进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你有地方弹的话,也没有人听。谁听你那玩意?他们玩手机,那里的内容多丰富啊。
王:王宝石也这样说。其实,还有时空问题。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空间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真正的传承会随着老人的去世而消失吗?民族文化传承怎么接班啊?我觉得有的东西接不了班。
孟:那当然能!她的那些东西全带走了,也没有接班人。如果仍然是那种部族的生活状态,这些人都圈在一起打猎,回来以后,喝酒唱歌什么的,这就能传下去。喜爱的人总归还是喜爱的,即使你不教我,我听一两遍就会。莫宝凤讲过,别人唱一两遍,她就记住了。
王:关扣妮会唱莫宝凤唱的“摩苏昆”作品——就是您上次培训交流的那个作品。2016年12月7日,她说:“我可以给你唱莫宝凤的‘摩苏昆’。”我服了,太厉害了!口传就是一个人的生活记忆或者民族记忆。你不得不佩服她,那种聪慧是人人能做到的吗?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不认字的话,记忆力会不会比现在好?一定好!因为你要记住一些事,所有的事都不记得的话,人生是空白的。自从人类创造了文字以后,口述就被遗忘了。现在,人们有了电脑,文字又被推到后面,我们靠影像记东西。如果没有影像的话,我们也能记很多东西。其实,口述记忆的信息量并不见得比文字少!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她的口述与记忆就没有了,真是太让人难受了。而且80年代学界对“摩苏昆”是否是史诗的争论,我还觉得挺好的。那时候集中发表的文章很多,后期都有些淡化了,这说明争论的时候还是文化繁荣的时候。伊玛堪研究做得那么好,“摩苏昆”和“伊玛堪”如果同时申报世界级非遗的话,不是一样可以吗?这要看谁来做。
孟:“摩苏昆”还有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主干线。它的主干线你知道了,剩下的可以随口去充实枝叶。有的人说我并不是完全和原唱一样,加进一些自己的东西,但基本的情节、内容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一个是谁来做,另外,“摩苏昆”的定论很重要。徐昌瀚他们的《鄂伦春族文学》一书出版以后,所有接触的人都认为这些东西是我编的,最起码占的比重和加工的成分特别大。我干嘛不大啊?本来就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当时他们搞伊玛堪,同江市宣传部带着钱去的,一部作品给200块。那个时期的200块多值钱啊!我这200块谁给呀?我一月工资35块钱,最长、最多的说唱作品,我给他5块一晚上。那是什么比例呀?
那是什么年代呀?1979年至1981年,那时纯属我的个人行为。我没有钱,我的钱袋那么紧张。如果他们真的从头到尾给你全部唱出来——包括李水花的作品,她还有肺心病,万一累着了,一下子过去了,我付得起责任啊?我说就唱这么一个曲调,剩下的部分全口述。现在,一说是口述的、没有唱的,就不承认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去解决历史问题。我也不想这事,没意思。再说,我当初也不是想靠搞民间文学怎么地。我只不过歪打正着,搞民族学调查是为了写小说,我是为了将来写剧本。
王:1979年,我还刚上小学。政府投入当然比个人力量大啦。我以为您的身体可好呢,现在,您也特别年轻,您的身体挺不错的。
孟: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期又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我在初中读了三个月就休学了,现在,我没病了,天天忙着家务,还基本上能保持这种状态呢——头发黢黑的,脸白嫩的,显得非常年轻。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现在,我老了,我的牙床也萎缩了。因为49周岁是写作的黄金年龄段,我为什么退休?干不了了。没办法,我那时病得厉害,心动过速得像火车似的,成天睡不着。
王:您在《鄂伦春》期刊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作品。如果搞创作的话,您的成果应该能够超越田野调查工作。敖长福已算很成功了,他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如果您现在写短篇小说的话,将来,您能不能写成长篇小说?因为鄂伦春族长篇小说至今还是空白,长篇小说的厚度、深度、长度都有。人的精神走得太快了,才会把身体落后面了。现在,您像电影似的要返老还童了。您不是伺候您爱人吗?
孟:文学院的那张表还在我手里掐着呢,我根本去不上。一个原因是工作关系,另外,身体状况不好。如果写的话,不管文笔还是深度,我和他们的角度肯定不一样。创作底蕴是天生的,那时候的计划挺好的,但身体不好,思维和脑层都供不上来。一个完整的身体不应该是残缺的,而我身体的主要构件不行,好比机器的马达,身体的里面有问题。我在那几年确实年轻,后来,家里有这个事、那个事的。有些事情吧,比如说,萨满研究是世界性的事,包括神学——爱因斯坦最后走向神学了,常人解释不通的事在佛学上就解释通了。比如说,人体和人的生命是咋回事?任何东西都是生命的存在形式。
三、关于萨满、传承与创新
40
王:您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人只能看见三维空间,科学无法解释清楚四维空间,它只存在于信仰之中。反正,我觉得关扣妮特别地神气,萨满就是那样。我从没见过关扣妮萨满跳神,在4月28 号的呼玛县开江节上,她跳开江祭。我一定要看看鄂伦春族萨满和大自然是怎样亲近的?她是如何祭拜神灵的?关金芳每次开会的发言都不一般,比那些教授、专家说得好多了,她讲白银纳民间艺术团的创办可不容易啊。我很佩服她,当她和我们学院派对话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她的观点有高度,因为我们是照本宣科。但她不一样,她的理论起点很高。理论从哪来?从她那样的传承人那里来。我一直跟着关扣妮采录口述文学,这次,我在关扣妮家里过年,我俩聊了一天。关扣妮的女儿孟举花去世了,她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了,他的手因喝酒的缘故而不停地抖动。
孟:任何东西都是生命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界存在的东西人体都有。人为什么会触电?你自身的电子层触了电。人体本身由分子构成,整个分子这一层的肌肤往下是看不见的。关金芳唱的歌有时候都像水似的流出来,现拼、现唱,老厉害啦,往那一坐就开始“咔咔咔……”。那个时候,关扣妮她们不应该让她的女儿传承萨满,这个东西不是指定的,怎么可能呢?好像也不是很正常吧?
过去,很多人对萨满的定论特别的反感,说她是癫狂的人、狂躁不安的人。我曾经看过词典,“萨仁”(saren)是知道、知晓。萨满就是先天知道,预先知晓,通晓一切,先知先觉。这个词本身给它下了定义,萨满就是先知先觉。逊克县展览馆介绍萨满的文字的最后落款是“愚昧的、落后的”。上次开会的时候,我跟区委、评委这么说的:“这是不对的!前面把它介绍出来好像要发扬光大,后面却一棒子打死了。”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改没改,我很长时间没去逊克县了。一般像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还有那些老师、研究者来,我首先说:“搞民俗学研究一定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否则,你搞不了这东西。”
王:民俗不是低俗,恰恰是你生活离不开它,你离开它活不了,你不起名?你不过周岁?你没有婚礼吗?从出生到死亡,人一定离不开民俗,因为你离不开日常生活。我和学生说过:“你别以为自己的专业低下,专业都是平等的。”我倒觉得中国民俗学虽然起步晚,幸亏那些先行者付出了那么多。日本特别重视民俗学,1932刊印的《满洲文学兴废考》是一本日文书。我们的很多术语都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日语从英语翻译过来以后,又翻译成汉语的。中国这么大,民俗学应该做得有声有色。我们还是说传承问题吧,有更好的或者实效性强的传承方式吗?
孟:他们整偏了,这事就这么简单。哲学也是在框架内的哲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必须和宇宙空间相沟通,你认识到那些东西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所以说,很多事情非常可笑,民族学也是一门科学。到目前为止,传承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鄂伦春语言。鄂伦春语言不会,想传承也传不了。第二是生活氛围。这种生活氛围不存在了,那么,传承要受到限制,甚至已经被淘汰掉。第三是现在公开的萨满没有了,她们都是内部的萨满。2007年,我们在黑河换班的时候,李金玲也有点仙气。她说:“淑珍啊,我明天说唱这个。”我说:“行!”我把名儿记下来了。第二天,她说:“夜里,我妈给我托梦了,我不说唱这个了,我说唱我妈妈托梦的那个。”你承不承认?
还有一次是在加格达奇,魏桂华唱美声去了,2008年呗,鄂伦春族参加这次会的大概有24人,24人里面有6个人具有这方面的功能,这个比例数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比例数大?因为越是接近原始,它被现代化的东西越少,越少就越纯,越纯的时候就越神,沟通就越直接,就这么简单。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空间,整个大脑细胞都渗透了那些东西。我没受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东西。
王: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连锁式的,完全排除影响是不可能的。现在,最可怕的事是永远不知道真相,历史比文学还可怕。您孩子学什么专业?他不学您的专业吧?
孟:人类的劣根性没有办法,一茬一茬的人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有一个孩子,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电力专业。他传承不了“摩苏昆”,首先是语言不行,没有机会和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40岁了,在上海做平面设计工作,在他们自己搞的一个小公司里。他没有精力管我的事,我们各忙各的。他现在有个女儿,我孙女我看不了。我这儿还有一个大活人呢,每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被他占去了,我还得做三顿饭、收拾屋子、洗衣服、买菜、办事。人乃命也,命该如此。
王:您这话有点像孔子的“古人云”。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诠释了仁、义、礼、智、信。过去,从商的人遵守这几个字,不像现在做买卖的人。过去的人很讲究中国传统。您教小孙女鄂伦春语吗?你们传承人到学校去讲课吗?萨满的作用是什么呢?萨满传承了那么多的东西!
孟:孔子学说的“仁义礼智信”是真理!咱不说别的,除了自然现象之外,很大程度是人心变坏了,违背自然规律和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破坏呢。现在,我教不了她,她刚三岁,指望不上。
“摩苏昆”传承人进不了课堂,第二课堂考学也不加分,人家考外语也不考鄂伦春语。谁学呀?还耽误事呢。过去的传承是什么?可以说是神学文化,以前的人大部分都和萨满有关系,莫海亭的妈妈是萨满,莫玉生的妈妈是萨满,莫宝凤的奶奶是萨满,李水花的妈妈是萨满,她的妹妹也是萨满,她们有一个算一个!
王:我觉得您的传承挺有成果的,24个人都会唱,那很好了。政府能给唱民歌的人安排工作吗?您改编的“摩苏昆”原生态音乐剧《艾么汗与乌娜吉的亲事》的唱词有什么变化吗?乐调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唱词却完全改变了?
孟:八、九个人主唱。非常奇怪的事情,现在,年轻的歌手可少了。天天卡拉OK卡拉的,嗓子都没卡拉开。嗓音怎么培养啊?17岁差不多过了变声期,嗓音条件好不好在16、17的时候就知道。逊克县的那么多毕业生哪个分配了?他们不都种地吗?他们要是认认真真地学还可以。现在咋的呢?他们不爱学。学有什么用啊?也不安排工作,考大学也不加分。种地的时候还要忙着种地,冬天能有点闲时间。
唱词没什么太大变化,基本上都是过去传过的那些话,也有这种情况,我用这个调唱别的内容,这在鄂伦春族“摩苏昆”里边属于正常。鄂伦春人是现编现唱,我用这个曲调可以唱这个,还可以唱别的内容。在这种场合,我用这个曲调这么唱,说唱就唱,有感而发呗!比如说,唱“生活好呀”,那也是歌。第一次有人唱了,就记住了,传给第二人,第二人记住了,第三个人唱了,这个歌就传下来了。同样的一首歌调,唱赛马、山花也行,唱骂人的话也行(示范唱),还可以唱猎手(示范唱),词儿可棒呢!特别形象,非常高傲。好了,我们一起听听鄂伦春族民歌(播放音乐)。
王:谢谢您,阿姨。我理解了鄂伦春族“摩苏昆”不能脱离鄂伦春语、萨满文化和狩猎生活,离开日常生活的传承等于把树干挪走,却没有把树根带上。树根留在原地也会枯死,树干亦不能独自存活。您让我茅塞顿开,在生活中教我照顾他人,在理论上教我放眼世界,在田野调查工作中教我克服困难、持之以恒。刚才,我通过欣赏鄂伦春族民歌,获得了难忘的审美体验,领略到鄂伦春族原生态文化之美。再次感谢您多次的悉心指导!恭祝身体健康!
采访后记
每一次采访的结束仿佛预示着下一次的开始,田野调查如同生命一样的周而复始。在本次的采访过程中,伴随着孟淑珍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与点评,我陶醉在鄂伦春族民歌的优美动听之中。她还将64首鄂伦春族民歌拷贝给了笔者,仿佛把传承与传播鄂伦春族“摩苏昆”的嘱托撒在心间,这是心与心、生命与生命的面对面。每一次对话都赋予笔者无限的决心和勇气,激励笔者排除杂念、努力向前。
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孟淑珍围绕传承工作将文学创作和生存、生活、生命、生态融合在一起,这与她的民族身份、艺术追求、文学素养与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孟淑珍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毕拉尔人》,散文《花果歌》《醉人的起点与飞跃》等,诗歌《无名的小河》《红箭头》《送晚饭》《杯中的喜悦》《母子情》《我们的“校徽”》等。她还创作了鄂伦春族歌曲《我是鄂伦春小猎手》《鄂伦春迎宾歌》《赞美家乡》等。孟淑珍多年如一日地为鄂伦春族“摩苏昆”无私地付出,为了鄂伦春族“摩苏昆”的抢救、保护、传承、传播与创新,她做出了非凡的贡献。笔者通过与孟淑珍面对面的访谈,期望以生命的对话、生活的体验和生态的理念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和关注鄂伦春族“摩苏昆”,让我们每个人都像爱护生命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和能力传承与传播生态文化、审美文化和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