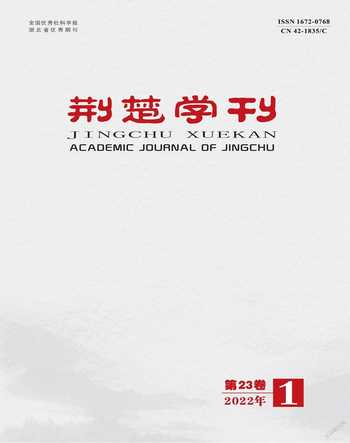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比”浅说
摘要: 过往对于秦比的研究因为材料不足多有局限。过去的观点大多认为秦“比”的本质是“例”,秦“比”包含官府“成例”和司法“判例”,并且基于汉决事“比”推测睡虎地秦简中的廷行事可能也是“比”。岳麓伍中一则令揭示出了秦“比”是秦法律形式的一种。岳麓秦令以及里耶秦简中的部分“比”包含了“比”的立法程序。分析“比”的立法程序可知,“比”并非“例”,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令,廷行事也与所见的“比”不相同。因为“比”的立法程序与令的立法程序相类,且比直接被当作令。“令”“比”的区别在于“比”形式上以“它有等比”结尾,在使用方法上不同于普通的“令”。
关键词:秦比;廷行事;令比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2)01-0085-05
“比”是秦汉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学界对于秦汉比的研究,限于秦比材料有限,多是从汉“比”出发来推测秦“比”( 1 )。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或认为其中的廷行事即与汉决事“比”一样,是秦法律体系中的“比”( 2 )。有的观点认为秦不存在作为法律形式的“比”,直到汉才出现[ 1 ]。这些观点因为材料有限或有谬误,或有不足。近年岳麓秦简肆、伍、陆的刊布,为准确地认识秦“比”提供了可能。
一、秦“比”是否存在补说
“比”,字形为两人并排状。字意由字形而来,有并列的意思。比的字义引申为与某某相类或相同。用法为A比B,即A与B相类或相同。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2 ]秩比二千石的意思是司直的秩比照二千石官,也即和二千石官相同。在出土秦簡中,亦有此种用法。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 3 ]
有的观点认为,出土秦简中出现的这种A比B的表述,就是秦“比”,称为律令之“比”[ 4 ]。应当明确的是,这种表述不是秦“比”。因为《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
简066-068/1009-1000:●制诏御史∟:吏上奏当者,具传所以当者律令、比行事066/1009,固有令,以令当,……如令。·五068/1000[ 5 ]
这条令中将“比”与律令都作为官吏“奏当”时的法律依据,说明对秦人而言,“比”是可以与律令相提并论的法律形式。再加上出土简牍中,有数条特征明显——结尾附以“它有等比”的秦“比”,可见之前认为“出土秦简中出现的A比B的表述,就是秦法律中的比”的这种观点以及压根不认可秦“比”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3 )。
对于秦“比”,欧扬认为,“它有等比”意为“其他官署遇到等同情况时需比照此事处置”,以“它有等比”结尾的比属于律令篇章之内的比。除了律令篇章之内的“比”,还有律令篇章之外的“比”,秦即廷行事,汉即决事“比”[ 6 ]。对于欧扬的观点,应认可其对于“它有等比”做出的解释以及其将“它有等比”结尾的这类秦简定性为秦“比”。但是将廷行事看作是秦“比”以及在比的形成上提出“比”是后来被编入令中的,值得商榷。略陈理由如次:
廷行事见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如:“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整理者认为廷行事是法庭成例。”[ 3 ]另有观点认为行事并不是成例,只是实际作法,廷也不是法廷,而是官府。廷行事不是法廷成例,而是官府实际作法[ 7 ]。对于廷的解释,还有观点认为廷即是廷尉,廷行事就相当于汉的“决事比”[ 6 ]。不过,虽然廷行事的廷作廷尉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廷行事定性为秦“比”的一种,值得商榷。《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 8 ]郑玄的注中提到已行故事是“比”,欧扬据此认为廷行事是廷尉已行故事,廷行事也就是秦“比”。但是岳麓秦简中明确提到“律令、比、行事”。“比”和行事被一起拿来与律令共同作为官吏的法律依据,这说明“比”和行事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或认为“比行事”不是比和行事,而是“比行事”为一个整体,是比的全称[ 6 ]。这种观点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有矛盾之处。首先在事实上,比和廷行事不同。“比”的内容较杂,廷行事涉及的是定罪量刑方面。如“比”有关于“置守”的,也有关于安置六国贵族的,亦有可能有关于定罪量刑的。而廷行事的内容主要就是定罪量刑( 4 )。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比”是“比行事”的省称,那么廷行事即是廷比行事的省称。然而现在所见的秦简中,并没有廷比行事。将“比”和行事断读,既符合事实亦符合逻辑。
因此,秦“比”是秦的法律形式之一,以“它有等比”结尾。廷行事不是秦“比”,可能是行事。
二、秦“比”的立法程序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一则比,对秦比的立法过程记录的较为完整,释文如下:
简013-018/1029-1111:●叚(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皆当完城旦,输巴县监。……有等比。018/1111[ 5 ]
这则“比”较为完整,有少数内容残缺。记载的是对故代、齐国从人的“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的处理方式。首先是廷尉正提出故赵将军乐突的弟弟和舍人袑等二十四人被判决为完城旦并且需要押送到巴郡的属县监视。其上请将这二十四人以及故代、齐从人的“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不再送往巴县,而是比照故魏荆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然后御史陈述巴郡的属县监视的人太多了,请求将袑等二十四人以及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的处理方式比照故魏荆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被判城旦舂的要押送到洞庭郡劳作,其被判处士伍、庶人的押送到苍梧郡。最后以“有等比”结尾。说明其他的六国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其子已傅嫁者”的处置方式均比照此。
该“比”的重要之处在于保留了比较完整的立法过程,值得注意。廷尉正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对罪犯的处理提出了建议。根据简文的表述,原本这些人都应该输巴县监。但是廷尉正希望比照故魏国楚国从人的处理方式,不要把这些人都送往巴县监。从这里可以推测,原本的法律规定的是输往巴县监,但是现实情况不太适合,所以廷尉正希望变通法律的规定。廷尉正将其意见上请。而后该意见应该是得到了御史的认可,御史同样进行上请。御史将详细的办法上请,并且在后面附上了“有等比”。从御史的请可以看出,御史不光是替廷尉正遇到的情况而请,而是希望变更法律。因为其请一旦被批准,因为“有等比”的存在,以后处理该类情况时,就不用再遵守原来的法律了,也不用再请了,只需要比照该规定办事即可。虽然该“比”结尾并没有“制曰:可”,但是从岳麓秦简所见的令以及该“比”最终被当成“令”来看,显然最高统治者是认可了御史的建议。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例不能够被援引比附。就本比而言,廷尉正想要比照故魏、楚从人处理的旧例来处理舍人袑及故代、齐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子傅嫁者,显然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处理从人之妻子、同产、舍人及子傅嫁者的旧例了。但是因为这个旧例并没有法律效力,只能上請,不得擅自援引比附。而经过了御史上请,最高统治者批准,在其后附上了“有等比”,例中的处事办法被确立为“比”,具有了法律效力。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即可援引该“比”处理,无需再请。这说明,“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除非经过上请成为“比”,否则不得擅自比附例来办事。“比”与“例”不同,“比”体现最高统治者的立法权。
里耶秦简中亦有一份文书,以“它有等比”结尾,释文如下:
简9-939+9-897:□子传丞相启上少府守嘉书言:北宫斡官偕为军治粟,少府属卒史不足□攻。(功)次为置守,如从军者。它有等比。□报,追。[ 9 ]
该简由两枚残片缀合而成。缀合后由两行组成,上部仍然有缺。该简结尾有“报,追”,说明这是一份传递中的官文书。而官文书会在开头记载日期。如里耶简8-152:“丗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书举事可为恒程者、洞庭上群(裙)直,书到言。今书已到,敢言之。”[ 10 ]由此推断,该份文书所缺的内容,大概是每一行十字左右。
该简记载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份官文书。从结尾的“它有等比”的字样来看,该文书所传递的是一则“比”。该“比”的内容,从残存的文字来看,应该和设置临时负责人有关。再结合置守前的攻(功)次,可以推测这里是根据功劳次第来设置临时负责人。说明第一栏的内容或许就与置守的原因有关。第一句是“□子传丞相启上少府守嘉书言。”这一句说明少府守嘉有事上书,而丞相认可少府守嘉的建议,将其上奏给了最高统治者。那么也就可以确定后文所记载的内容与少府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关。上书的第一句为“北宫斡官偕为军治粟,少府属卒史不足”。为军治粟,意为负责军队的粮食,结合后文,因为涉及到设置临时负责人的问题,所以可能是运输粮食。之后是少府遇到的情况,即“少府属卒史不足”。卒史是秦汉时皆有的属吏。在本简中,明显是少府的属吏。本简中所提到的“少府属卒史不足”,应该和后文的“功次为置守”有关。因为北宫斡官的人都为军队运送粮食,并且北宫斡官是少府的属官,北宫斡官的人全部都为军队运送粮食,需要少府派人管理。而少府的卒史出现了短缺的情况,没法为“为军治粟”的设置负责人。所以少府守嘉上书,请求根据功劳次第设置临时的负责人。最终经过丞相的上书,少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具有了法律效力。校释小组的断读为“攻(功)次,为置守如从军者。”[ 9 ]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岳麓秦令有中有“……以攻(功)劳次除以为叚(假)廷史、叚(假)卒史、叚(假)属者”,在前文捕出一个“以”字,将其断读为“以攻(功)次为置守,如从军者”似乎更为合理[ 5 ]。
以上是对该“比”的内容进行疏通。通过对该“比”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少府所提的办法应该是于法无据的,所以少府才上书请示;第二,丞相认同少府守嘉提出的解决办法,所以将少府的处理办法上书,请求将其定为成法。经由最高统治者批准,将该决定下发相关的机构。这个过程,就是“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产生了一条令。因为前文已经分析过了,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擅自比附,所以该份文书中的“它有等比”就代表经过最高统治者的许可。
以上分析的二则秦“比”都体现了秦“比”的立法程序。第一则是廷尉正夫上请而产生的“比”。第二则是丞相启认可了少府守嘉的建议后上书所形成的“比”。目前所见的“比”,大部分都或多或少保留了“比”的立法程序,大致为:官吏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遇到了需要变更法律或者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提出建议,附上“它有等比”,向上请示。请示获得批准后产生新的法律,即“比”。
三、秦“令”、“比”关系分析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比”的立法过程与令的立法过程无异。“令”的起源很早。“令”,本质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命令。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时改命为制,改令为诏[ 11 ]。在岳麓秦令中,常见“制诏”或者“制曰”。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简059-061/1125-0964:●制诏御史:闻狱多留或至数岁不决令无辠者久(系)而有辠者久留。……制曰:可。●丗六061/0964[ 5 ]
这则令包含了令的立法过程。在该令中,首先由皇帝向御史提出当前的情况,指出当前的情况亟需改善,要求就“留狱”提出具体建议。于是御史提出立法建议,即“请”。请的内容最后由皇帝批准,即“制曰:可”。令的立法过程体现命令的本质。当然到秦时,令经过了发展,已经不单单是王者之命令这么简单了。令已经是秦的一种专门的法律形式了,其立法也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从令的完善与修改上可见一斑。如《岳麓书院藏秦简(陆)》:
简005-011/1357-1523:●十四年四月己丑以来,黔首有私挟县官戟、刃没〈及〉弓、弩者,亟诣吏。……它如其令。□□□□011/1523[ 12 ]
这则令主要体现的是令的修改。该令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修改前的令,主要是规定黔首不得私自持有县官兵器。如果有私自持有县官兵器的,在令到的若干时间内(两日或者两个月)将兵器交给相关的官吏,相关官吏按照市场价回收。如果在这个期限过后还私藏县官兵器,与盗同法。第二部分是丞相启与执法对该令的修改意见,即议的内容。主要是讲该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为县官兵器和黔首兵器太过相似,而且还有人将赐给自己的县官兵器转卖。前令规定一定期限内将兵器上交给官吏的,才不犯令。但是往往有黔首在期限过了以后“过失”买到了县官兵器。而根据令的规定,即与盗同法。这样的令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经过丞相启和执法的提议,最终该令做出了变更。而该令保留下来了令的修改及修改程序,与“比”的立法程序,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经过“议”“请”或者“上书”等程序,由最高统治者批准,最后令即形成。再结合岳麓秦简中的“比”被当成是令,可以得出结论,实际上秦“比”就是秦令的一种。秦“比”应该不是在后来被汇编入令的,而是在发布的时候就作为令而存在。
虽然从立法程序和令被当作比的事实可以看出秦“比”实质上就是令,但是毕竟秦人在其令中明确将“比”和律令并列,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比”与令的不同。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比”与令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秦“比”以“它有等比”“有等比”或者“有……比”之类的术语结束。这是现在人们识别秦“比”的方式之一,也是秦吏识别秦“比”的重要方式。因为目前所见的秦“比”,在形式上几乎和所见的令没有区别。既有“令曰”起首的,也有结尾附有令名的。如果没有结尾的“它有等比”,是无法容易区分秦“比”和秦令的。
“它有等比”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术语。以《岳麓书院书院藏秦简(肆)》的一则比为例来说明“它有等比”的重要性:
简360/0319:●东郡守言:东郡多食,食贱,徒隶老、癃病毋(无)赖,县官当就食者,请止,勿遣就食。它有等比。●制曰:可。[ 13 ]
这则“比”是由东郡郡守提议而形成的。这则“比”中保留了象征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制曰:可”。表面上看“制曰:可”是整个比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象征权力的表述。然而事实上,一则“比”中最重要的不是“制曰:可”,而是“它有等比”。前文已经分析过,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官吏不能径行依照旧例办事。换句話说,官吏在处理事务时,如果想要比附,必须找到对应的“比”。以这则“比”为例,这则“比”是由东郡郡守提请,最高统治者批准而形成的。这则“比”其实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的请示,第二部分是它有等比。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批准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东郡守的请求,这个请求是一个特定的事项。然后是其他情况可以比照东郡守的处理方式来处理。结合之前的分析,可以推测“它有等比”可能是由丞相或者是御史在东郡郡守的请上附加的。实际上一则“比”一般是分为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层面的意思是就特定事项请求的批准,第二层面的意思是核心意思,是对立法建议的批准。一旦最高统治者对带有“它有等比”的请求批准,形成了相应的令。该令就会下发到相关的机构,供官吏援引。而如果缺了“它有等比”,该令就是一个普通的对请示的批复,没有赋予其他官吏援引该比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它有等比”简短的几个字,正是秦比的核心组成。没有这几个字,就没有秦“比”。
而秦“比”和秦令在深层次上的不同,是使用方式上的不同。一般令是由具体的行为和违令的后果组成的。如《岳麓书院藏秦简(陆)》:
简113/2146:●宫堂下草中有荠□,辄拔去之,弗去,赀官啬夫、吏主者各二甲。·七[ 12 ]
令具有确定性,由特定的行为规范和违令的后果组成。而“比”则不然。“比”中存在不确定性。以东郡守言这则“比”为例,如果该令下发全国的各郡,那么在“它有等比”的效力下,各地的郡守在处理相同的情况时,均可使用该“比”。又或者该“比”并没有被发往全国,而是仅仅被发给了东郡。那么东郡郡守在处理相类的情况时,则可以使用该“比”。从“传丞相启上少府守嘉书”一比来看,该“比”被制成文书传递到了洞庭郡,再结合岳麓秦简中有以“琅琊郡比”结尾的“比”,该“比”适用全国范围的可能较大。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立法时的确为适用“比”留下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应该是“比”和令深层次的不同,也是秦人将“比”和令作区分的原因。“比”在使用上已经和令产生了本质的区别,但是形式上,“比”和令仍然是一样的。不论是“比”被当作是令,还是立法程序的相同,都体现这一点。
四、结语
总之,秦法律中存在“比”。“比”是秦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的特征为结尾的“它有等比”。“比”的立法程序为官吏在遇到需要变通法律或者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时,通过上书提出建议,经过中央负责立法的官吏建议最高统治者后,将议定的内容确定为法律。在立法程序上,秦“比”与秦令无异。比也被当作令来使用,如在“比”的结尾附上令名或者以令曰起首。这说明比本质上就是令,但是因为“比”自身的独特性,“比”成为了和普通令所并列的法律形式。“比”在形式上以“它有等比”结尾,在使用方法上也不同于令。秦“比”不类汉朝的“决事比”,而秦简中的廷行事应该也不属于“比”的范畴。
注释:
(1)秦汉比的相关研究参见欧扬《岳麓秦简所见秦比行事初探》,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70-78页;马凤春《论传统中国法“比”》,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5期,第41-49页;吕丽,王侃《汉魏、晋“比”辨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0-158页;陈鸣《秦汉比考论》,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赵晓磊《秦汉时期司法审判形成的“比”——兼驳中国古代存在判例法之说》,载侯欣一主编《法律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9-68页;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第86-91页。
(2)有關廷行事是秦比的观点,参见欧扬《岳麓秦简所见秦比行事初探》,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70-78页。
(3)马凤春认为秦比还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立法,作为立法的比是在汉朝形成的。参见马凤春《论传统中国法“比”》,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5期,第41-49页。
(4)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整理者断读为“律令、比行事”,这种断读是将比和行事视为一个整体。参见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60-61页。欧扬在《岳麓秦简所见秦比行事初探》中也认为比行事是一个整体,就是秦比。但也有观点认为比和行事应当断读,如吴雪飞《岳麓简一条秦令中的“比”和“行事”》,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5.
参考文献:
[1]马凤春.论传统中国法“比”[J].政法论丛,2015(5):39-47.
[2]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725.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02-111.
[4]赵晓磊.秦汉时期司法审判形成的“比”考析——兼驳中国古代存在判例法之说[J].法律与伦理,2018(1):49-68.
[5]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伍[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59-192.
[6]欧扬.岳麓秦简所见秦比行事初探[M]//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十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70-78.
[7]刘笃才,杨一凡.秦简廷行事考辨[J].法学研究,2007(3):144-151.
[8]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六礼记正义[M]. 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2908.
[9]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221.
[10]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2.
[1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236.
[12]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49-50.
[13]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214.
收稿日期:2021-09-27
作者简介:沈子渊(1996 - ),男,山西太原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
On Qin Bi seen in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Yuelu Academy
SHEN Ziyuan
(School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00,China)
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on Qin Bi were limited due to lack of materials.Most of the previous viewpoints hold that the essence of Qin Bi was "Li" which included official"precedent"and judicial"precedent".Based on Han Jue Shi Bi,the Ting Xing Shi in Qin Bamboo Slips of Shuihudi was speculated to be"Li".One piece of Ling in YueluFive reveals that Qin Bi is one of the legal forms of Qin Dynasty.Some Ling in the Yuelu Qin Li and Li in Yeqin Bamboo Slips contain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of Bi.By analyz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of Bi,we can find that Bi is not a "Li", which essence is a kind of special Ling,and the Ting Xing Shi is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seen,because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of Bi is similar to that of Ling,and Bi is directly regarded as Ling.The difference between Bi and ordinary Ling is that Ling ends with"equal Bi form.
Key words:Qin Bi;Ting Xing Shi;Ling Bi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