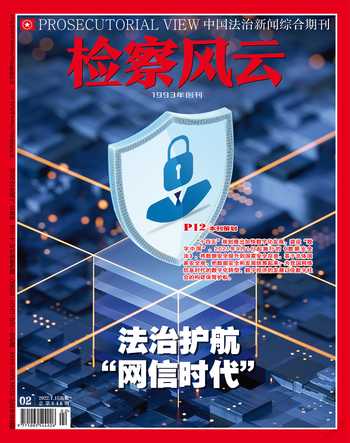抗联名将冯仲云伉俪的传奇爱情
赵进一
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之妻、抗日女杰薛雯,携两女孩,冒着敌人的炮火,突破道道封锁线,由江南北上寻夫,绕道朝鲜,转战2000余公里,历尽艰险,最终寻到的是已担任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丈夫。12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迎来幸福的大团聚,赤诚忠烈的爱情故事摄人心魄,令人感奋。

冯仲云夫妇合影(图/网络)
冯仲云与薛雯都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横林镇。他们是表兄妹,自小青梅竹马,感情厚笃。进入中学时代后,冯仲云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影响下,冯仲云浑身洋溢着革命的激情。1927年5月1日,由朱理治及崔宗培同志介绍,冯仲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8年担任了清华大学第四任党支部书记。
1930年四五月间,冯仲云因参加地下共产党组织的“五一节飞行集会”被捕。几个月以后,他与难友们趁军阀混战,监狱无人看管之际,相互砸开镣铐,冲出了牢狱……但由于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在北平待下去了,经党组织同意,冯仲云去地处哈尔滨的东北商船学校(即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担任数学教授。
从此,冯仲云与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东北战斗了大半辈子。
冯仲云挚爱着表妹薛雯,23岁时,他回到老家,与薛雯结了婚,并把她带到了东北,一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不久,薛雯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了党的地下交通员。
一晃,三年多过去了。他们有了女儿忆罗,儿子坚儿。已经成为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冯仲云,经常要到各地工作,夫妇俩有时一别就是好几个月。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薛雯常常为丈夫的安全担惊受怕。作为内部交通员的她,工作中也常常是险象环生,朝不保夕。
更为严峻的考验来临了: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宣传部长杨波、书记刘明佛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而叛变,多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明佛领着特务满城搜捕冯仲云和薛雯。他扬言:冯仲云和薛雯就是烧成灰他也能认出来。敌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画出冯的头像满城张贴通缉令,并标出了悬赏价格:人头1万元,报信3000元。情况紧急,冯仲云和薛雯已经无法在哈尔滨露面。
夫妇俩本打算把孩子安顿好后共赴东北农村参加抗日游击队,但孩子的寄养问题一直得不到落实。省委决定由薛雯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安置好以后再返回东北,与丈夫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
别离的时刻终于来临。1934年10月的一天,冯仲云挥泪离别他挚爱的妻子及一双儿女,奔赴抗日前线。这一别,就是整整12年,而且是音讯隔绝的12年!
数天后,冯仲云的妹妹冯咏莹把薛雯与两个孩子送上了南下的列车。此刻,薛雯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尽快回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立即返回东北,继续与仲云哥一起战斗。
然而,别时容易再见难。薛雯回到家乡,安顿好孩子以后,竭尽一切努力,想通过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站返回东北。但历时半年多,好不容易与交通站接上了关系,未及有所行动,地下交通站就遭到破坏,自己还受到牵连,在上海与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抓进了监狱。幸好薛雯已经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敌人没从她的身上弄到什么证据,在被关押了三个月以后,薛雯的哥哥把她从虎口里保释了出来。
薛雯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她给冯仲云写信,向他诉说自己的困苦与对他的思恋,因为不能暴露身份,用的都是暗语。她渴望得到丈夫的回复,但丈夫一直音讯杳然。
与政治上的痛苦相伴的是生活的不幸:当薛雯带着女儿忆罗从上海返回老家余巷村时,三岁的坚儿刚刚病死在床上。祸不单行,此后,薛雯的大姐接连病死了四个孩子,只剩一个比忆罗大两岁的女孩子怡文。大姐自己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受惊而死,年仅30多岁。从此以后,大姐留下的孩子怡文就一直跟随薛雯生活。
薛雯心心念念的就是与组织接上关系。1936年春,她与堂妹企仑带着孩子一同去距家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希望在那里探听点消息。因为那里是山区,可能出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那个山区小村待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却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党组织的线索,薛雯只得与堂妹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家乡。
此时此刻,冯仲云和其他抗联将领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正与敌寇进行着悲壮而激烈的战斗。他们用3万多人的兵力牵制了几十万日寇,打死打伤17万多日本鬼子。对于这些著名抗联将领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东北人民作如是评价:南杨(杨靖宇)、北赵(赵尚志)、东周(周保中)、西李(李兆麟)、中冯(冯仲云)。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历经磨难的薛雯有革命信念的支撑,在没有恢复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在乡里自发地投身地下抗日工作。她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在群众和教职员工、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不少青年人就是在她的引导下参加了新四军。13岁的女儿忆罗、15岁的侄女怡文也进了新四军卫校,成了新四军小兵。薛雯做党的工作不放过任何机会,到她家来修屋顶的3个瓦工,最后也在她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薛雯重新入党,被送进地委党校学习。一天,刚从校部回来的学习小组长喊了一声:“薛雯,东北来信了!”
思念了12年的丈夫终于有消息了!薛雯止不住簌簌地掉下眼泪。
冯仲云在给她的信中说:“雯,我在东北……身经百战,血染战袍;我曾经弹尽粮绝,在塞外零下40度的朔風中的露天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还负过重伤,艰苦卓绝奋斗,矢志忠贞祖国人民……”他还在信中说:“雯,只要你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你还是我的妻。我这样地等待了12年,我相信我对你的忠诚是能够得到(好)结果的。”
对冯仲云的这段话,薛雯完全能理解。她知道丈夫对她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但在他的心目中,信仰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爱的是与他有着共同坚定信仰的妻子。
将近1个月以后的3月26日,冯仲云再次来信,向家人告知了自己的身份(抗联三路军政委)和详细的地址,并嘱咐薛雯带着忆罗及怡文到东北找他……

1930年冯仲云清华大学毕业照(图/网络)

1946年8月,重逢后的第一张全家福(图/网络)
1946年5月,党校学习一结束,薛雯就向组织提出带忆罗与怡文一起去东北找冯仲云的要求,得到了党校及女儿、侄女所在部队党组织的全力支持。几天后,《新华日报》转载了《东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上面一排醒目的标题是“冯仲云当选松江省政府主席”。组织部马上为薛雯开具了介绍信,忆罗与怡文闻讯立马兴冲冲地赶到薛雯的身边。
1946年5月,薛雯带领两个10多岁的女孩子从江苏开始了漫漫征途。
江苏与松江省(即现在的黑龙江省)相隔近2000公里,中间横亘着好几个省。“1946”,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刚刚拟定了《双十协定》,但墨迹未干,国民党就用飞机和军舰把54万军队运送到内战最前线,将进攻的重点指向东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又进攻沈阳、四平等地。到1946年5月,又占领了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从南到北,天空中战云密布,尤其是东北,更是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
恰恰就在这样的时候,薛雯带领的“长征小分队”出发了,她们的目的地就是东北,其路途之艰险,可以想见。
薛雯已作好思想准备:没有交通工具,她们就学红军,万里长征,徒步2000公里,用铁脚板走到黑龙江!不过,她们的运气不错,出发那天,正好从延安过来的郑团长夫妇及几个小战士要去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找肖华同志(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薛雯觉得只要到了辽宁,自己再设法去黑龙江,路就近多了。于是娘仨就跟郑团长他们一起出发了。
郑团长弄到一辆敞篷汽车,确定的路线是先到山东,再由山东开往辽宁。一路颠簸,汽车卷起的尘土扑在脸上,没多时,三人都成了泥人。汽车开了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到达山东境内。这时候天已很暗了,一行人停下来稍事休息。大家在街头小摊上随便买了点吃的,就继续上路。因为要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只能步行。在当地民兵的护送下,冒着夜间国民党部队的探照灯的晃耀,一行人穿过胶济路。忆罗和怡文虽说已是新四军战士了,但毕竟还是孩子,一天劳累下来,走路也会睡觉。过胶济路通过封锁线时,要急行军四五里路才能停下来休息。她俩一边走一边睡,薛雯一手挎一个,停下来坐在土堆上,忆罗才醒:“妈妈,到哪里了?”
娘仨临行前,冯仲云曾来信嘱咐她们:到了龙口过海到大连后,找他的老战友韩光同志(曾与冯仲云同在抗联第三军做政治工作),由他安排她们坐火车去哈尔滨。但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长春,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从龙口到大连的海上交通线也被国民党军舰严密封锁,无法过去——此前,她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前面的一条民船被国民党军舰拖走了……
龙口地区党组织得知薛雯的情况后,马上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让她们跟随郑团长转道到栾家口后,再跨渤海到安东,然后乘火车去哈尔滨;第二,为避免过海时被国民党军舰发现,要求薛雯把所有证件、文书、照片,包括军装,都上缴给龙口党组织暂为保管,两个女孩子都换成便服。由于国民党舰队封锁仍很严,所以大家只能耐下心来等候过海的最佳时机。
等了三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一大早,渤海海面大雾弥漫,当地人早已摸清了国民党军舰出行的规律,知道雾气重的日子,军舰巡逻次数会减少许多。一行人上了一只小汽船,直奔辽东半岛上的庄河而去。船上坐了百多号人。由于海浪大,船颠簸得很厉害,忆罗、怡文,还有好几个战士都经受着晕船的折磨,呕吐不止。熬到下午,雾散了,船继续前行。一路上居然没有碰到国民党巡逻舰队。到庄河赶上海水退潮,大家从海滩跋涉上岸。
上岸以后,娘仨跟着郑团长没走多远,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是肖华同志派来接应郑团长他们的,于是大家一起上了车,到了安东。
安东组织部同志对她说:“现在沈阳已被国民党占领,铁路交通中断,你是个女同志,又带着两个女孩子,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建议你们还是先暂时留在安东工作,等待时机……”
薛雯一听此话急了:好不容易到了东北,距丈夫工作的地方已不是很遥远,却还是见不着面!她当然知道组织部同志是好心,为她们娘仨的安全着想,但她心里像着了火似的,一分钟也等不了啦!她的脑海里急速地思索着各种方案。她们到安东后的第三天,组织部通知她去听肖华同志的报告。薛雯心里陡然一亮。
她虽然不认识肖华同志,但报告会一结束,她就鼓足勇气走到肖华同志面前,在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就向肖华同志提出她要去哈尔滨找离别12年的丈夫冯仲云的要求。肖华同志说他知道冯仲云同志,他会派秘书长负责办理此事。
很快,徐秘书长为薛雯设计了从安东到哈尔滨的线路,虽要绕一些道,却是最佳、最安全的线路。他们先是绕道朝鲜到图们,再转车抵达牡丹江、亚布力,这样辗转到达了哈尔滨。
啊,离别了12年的刻骨思终于到了尽头!冯仲云没想到,经历了如此长久的苦难和战斗的岁月,薛雯居然还活着,女儿和侄女都长这么大了,并加入了新四军,又在战火纷飞之中,千里迢迢赶来与他团聚,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几十年后,他们的外孙女安然这样描述当时两人相见的场景——
“刹那间,一切都静了,早晨明媚的温暖的阳光洒在木地板上,在散发着松香的楼梯上下两端,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
云哥,只是身材更壮实了些,但仍是那么风度翩翩,穿着咔叽呢西装,仍戴着那厚厚的眼镜,随手拿着一叠文件;雯妹,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灰尘蒙住了她白色的肌肤,粘脏了她白色的布衫。
但兩人也有变化:他们的脸都不再充满稚气。他们两个,一个在塞北的深山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一个在兵荒马乱的江南四处找党,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所有的智慧和勇气。现在,他们都张开了手臂,迎候对方……”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