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慰藉抑或训诫之书
陈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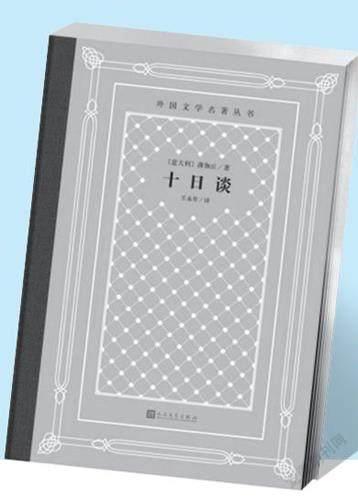
世界上鲜有书籍在序言里就指定自己的读者,薄伽丘在《十日谈》的《自序》里,开场就说自己曾经经历失恋的痛苦,知道慰藉的重要。薄伽丘曾是一个充满生命本能的青年,他在那不勒斯游历、学习经商时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他满怀热血投入一场恋爱,遭遇失败后,内心充满失望和懊恼。这些体验自然影响到他的创作。如果《十日谈》是一出戏剧,薄伽丘就是一位在开头、中间和结尾处都会出场的人物,会经历心态的变迁和态度的游移。作者对于女性的赞美和体恤,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是一位提倡“男女平等”的作家,一位关心女性生活的男性,他想通过这些故事带给女性慰藉。目前,学界也常有这样脱离时代背景的看法,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需要深入探讨。
在《十日谈》的开始,作者的对话对象就是一些陷入爱情的闺秀。作者比较公正地说明了当时禁锢在闺房的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处境。
谁能否认那些窈窕女子比男子更需要这些话?是啊,在她们柔弱羞怯的胸怀里隐藏着爱情的火焰,那些过来人或正在经历爱情的人都知道,秘密的恋情比公开的更猛烈。除此之外,这些闺秀要服从父母、兄长和丈夫的管束,要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大多数女子都深居闺中,经常百无聊赖枯坐着,很容易闷闷不乐,胡思乱想。(《十日谈·自序》)
在《十日谈》的结尾处,作者又一次重申了他写作的目的:“从我开始动笔,一直辛苦写到完稿,我始终都铭记着,我费心竭力写这本书是给那些有闲的女子解闷的。”
谄媚的背面就是诋毁。薄伽丘在四十岁之后,在作家转向学者的路途中,他在彼得拉克的教诲下,似乎彻底悔悟。作家晚年的作品《大鸦》中,他与女性断然反目,这种反目似乎也和他中年时追求女性失败相关。他在《大鸦》中数落女性的种种恶行和卑劣品行,与之前的态度判若两人。《大鸦》和《十日谈》着墨最多的故事之一—第八天第七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第八天的这个故事有一万多字,情节倒不是很复杂:是一个文士爱上一个寡妇,那女人心有所属,就哄他冬天在雪地上等了一宿。文士伺机报复,七月天让女人赤身裸体在塔楼顶上暴晒了一天,让牛虻、苍蝇叮咬。文章长篇大论对寡妇进行人身攻击和羞辱,甚至教唆她跳楼,因为这女人爱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没有接受文士的追求。文中,文士这样说道:
你要明白,只要这世道还在,我的生命,比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的女人对世界更有用……你既然很想下来,为什么不跳下来呢?要是老天有眼,你一下就能摔断脖子……(《十日谈》)
薄伽丘通过文士的长篇独白,总结了当时社会生活中贬低女性的方式。文士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千千万万个寡妇对世界更有用。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也可以随意在社会上抹黑这些女性,所以在报复的时候,他还扬言:“即使我的策划全部落空,我手里还有一支笔,可以写出你的种种行径,让你后悔生在这个世上。”(《十日谈》)
《大鸦》讲的故事也是作者狂热地爱恋一位寡妇,女人却将他拒之门外,并百般戏弄。主人公昏昏入睡,在梦中来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方,这时寡妇丈夫的鬼魂受圣母委托,前来救他。只有男性才能拯救男性,虽然这个鬼魂是自己的“情敌”。寡妇的丈夫尽其所能向他展示了女人的缺点,尤其是他妻子的丑恶。薄伽丘这时也到了摆脱情欲束缚的阶段,《大鸦》里那个亡魂苦口婆心,点明了男性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有所提升,投入到研究中去,提出婚姻和爱情对于上了年纪的文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十日谈》第四天开始,也是作者再次“现身”的时候。作者先是讲了一个佛罗伦萨版的“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强调自然的本能无法抵挡。故事里有一个叫菲利波的男人,他让儿子一直住在山中,父子俩一起苦修。儿子第一次下山,却偏偏只对衣着鲜艳的女子感兴趣。他只能骗儿子说,那些都是“坏东西”,是很难饲养的“母鹅”。故事是为了说明男性欲望的正当性,但在这个故事中,两性是彻底割裂的,女性在故事中的设定也纯粹作为欲望对象。
一三六三年薄伽丘五十岁,他应彼得拉克的邀请前往威尼斯,两人愉快地生活了几个月,与彼得拉克的交往,让薄伽丘意识到古代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这次会面也和他的精神危机密切相关,也让他逐渐转型为学者,年龄的增长让他终于摆脱了对男女情事的痴迷,他晚年在教堂里讲解《神曲》,对早年创作的《十日谈》心存懊悔。
无论如何,尽管薄伽丘静心养性,投身于哲学等古典文本学习,都无法把他提升到智慧的层面。他晚年还写出《大鸦》这样的作品,故事中的敌意和偏见,还是让情绪和本能占了上风。
面容姣好的女性在男性的争夺下必然陷入伦理困境,如何协调丈夫和追求者之间的关系,这是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女性要经常面对的问题。薄伽丘对于这一处境的处理很有时代性,他无意破坏当时的婚姻秩序、等级秩序,唯一的参照是男性的欲望强度。男性的欲望即真理,女性的意愿却是可以扭转,这在很多故事中都有体现。最典型的是第五天第八个故事:奥内斯迪家族的纳斯塔乔爱上特拉韦尔萨里家族一位小姐,为她耗尽家财,也没有得到她的青睐。他应亲友要求去基亚西散心,在树林里看到一个骑士的鬼魂追逐一个少女,杀了她喂两条狗,后来得知,那少女因为生前拒绝了骑士的追求,因此要反复遭遇“地狱之猎”的折磨。纳斯塔乔邀请亲友和那位小姐去吃晚饭,小姐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心生恐怖,怕自己也是这个下场,就同意嫁给他。
故事通过“地狱之猎”说明,一个待字闺中的女性,尽管门第高贵,如果对一个追求者冷若冰霜、置之不理,如果导致对方为情所困,丢了性命,那是要下地狱的罪行。在受到纳斯塔乔的“胁迫”之后,这位高贵的小姐终于肯嫁给他了,结局算是皆大欢喜。故事没有讲出来的是这位贵族小姐受到的困扰,和她后半生要忍受的生活。
女性面临的另一种情况是:自己已经结婚,如何面对情夫的问题。第三天第七则故事把这种情况说得很明白。泰达多和心爱的女人分手了,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多年后他乔装成朝圣者回到故乡,和那女人交谈,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救了她被控谋杀罪的丈夫—因为种种误会,泰达多的兄弟以为他杀了泰达多。泰达多让情人的丈夫和自己的兄弟和解,他也和那女人重归于好。这个女人坦白,她当年和情夫的决断,只是因为神父的恐吓:
他从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我之所以和他断绝,那是因为一个可恶神父的话。有一次,我向那神父忏悔,提到那位青年对我的爱,还有我和他的来往。神父的话到现在还在我脑子里回响,至今想起来还害怕。神父说,如果我不和情人断绝来往,那我就会落进地狱最深处,落入魔鬼嘴里,永远受到烈火的煎熬。我当时很害怕落入地狱,就决定不再和情人来往。
在薄伽丘的故事中,修士会对世俗男性构成潜在威胁,也是性资源的竞争者。《十日谈》对于教士阶层的鞭笞在作者情感上也可以找到根源:“他们痛心疾首,痛斥世人沉迷于淫欲,这样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享用那些女人。”在这个故事中,泰达多只想让情人回心转意,他无意破坏社会的婚姻秩序,他甚至出面解救了深陷牢狱的情人的丈夫,使一切秩序井然,同时也揭示了神父在这个故事中不光彩的角色。
薄伽丘故事中女性的佼佼者,如果能使用计谋完美协调丈夫和情人的关系,那似乎是很值得赞赏的行为。第七天第六个故事中,伊莎贝拉夫人正和情人莱奥内托幽会,爱慕她的兰穆贝托骑士也来探望她。这时她丈夫回家,伊莎贝拉便吩咐兰穆贝托拔剑跑出家门,让丈夫护送莱奥内托回家。丈夫和妻子的两个情人碰头,这么棘手的事都被伊莎贝拉夫人完美化解。这事虽然让人议论纷纷,但伊莎贝拉的丈夫却始终没发现妻子的计谋,也让读者惊叹这位贵妇的手段。
《十日谈》对女性人物可以说是赏罚分明,沉迷于情欲的女性并不会得到处罚。比如第二天第七个故事:巴比伦苏丹派人送女儿与加博国王成婚,一路上公主遇到了各种波折,四年之间落到九个男人手里,辗转各地,最后回到本国,作为处女还给她父亲。父亲按照之前的决定,把她嫁给加博国王为妻。这个公主因为貌美招来祸患,害死了很多争夺她的男人,她酒后乱性,沉迷于情欲,并没有得到任何命运的惩罚,反倒荣归故里。失身于人并不会受到惩罚,反倒得到了命运的奖赏。
《十日谈》中,什么样的女性会遭遇悲惨的处罚呢?那就是不听丈夫的话,违背丈夫意志的女性。第九天第九个故事,两个青年男子求所罗门王指点迷津,一个想知道如何才能受人爱戴,另一个问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妻子,所罗门对一个说“去爱”,而叫另一个去“鹅桥”。他们在“鹅桥”看到一个马夫用棍子殴打不听话的骡子,从而恍然大悟。故事通过所罗门王的智慧建议,一个青年男子进行自我赋权,把对妻子施暴当作“言正名顺”的事,在朋友的见证下,打到妻子站不起来,从而让她服服帖帖。第九天第七个故事的信息也很昭然:塔拉诺·迪莫莱塞梦见一头狼咬破他妻子的喉咙和脸蛋,就劝她小心。妻子根本不听,结果梦中的事应验了。妻子在毁容之后,幡然悔悟,痛恨之前没听丈夫的话。
另一个比较隐蔽的训诫是第十天第十个故事,也是作者花了大力气讲述的故事,放在最后,意在强调它的重要性。桑卢佐侯爵在臣子的恳求下,不得不娶妻(他对女性的鄙夷和厌弃根深蒂固)。最后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娶了个农民的女儿,婚后生下两个孩子。侯爵先是让妻子相信孩子被处死,随后又说厌倦了她,想要另娶。后来他接回了送到外面抚养的女儿,对外宣称是新娶的妻子。他妻子被驱赶,只穿着一件衬衣回到娘家,但依然耐心忍受着,最终苦尽甘来。侯爵隆重地把她迎接回来,让她与长大的儿女相认,确认她侯爵夫人的地位,也让众人敬重她。
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女性忍受丈夫的各种羞辱和虐待,并后来得到奖赏的故事,说明如果一个女性放弃自我,一切都以丈夫的意志行事,最后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相比于之前的故事,劝解女性要接受男性的追求,这个故事才是最阴险的。它强调了性别秩序、封建等级秩序,完全抹杀了一个女性的情感、需求和存在,让她的价值完全依附一个男性,让她的一切都是丈夫赋予的,她拥有的一切随时也可以失去,一切都仰仗丈夫的心情。这是《十日谈》最后一个故事,薄伽丘有意模仿《神曲》,这位忍辱负重的女性作为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被呈现出来,得到了丈夫和社會的承认和奖赏,正如《天堂篇》最后所呈现的理想境界。
目前《十日谈》的研究者或译者,因为薄伽丘说了几句体恤女性的话,动辄就说《十日谈》倡导的是“男女平等”,他笔下的女性有自己独立的意识,等等,或者只是强调他的厌女。其实薄伽丘对女性态度的变化,首先是受男性不同年龄阶段,对女性不同需求决定的,用之则鼓吹,视若珍宝;若不能称心如意,得到死心塌地、彻底放弃自我的女性,则弃之如敝屣,并进行践踏和羞辱。有意思的是,《十日谈》第八天、第九天和第十天里,部分故事开始流露出浓郁的厌女态度,揭示了薄伽丘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因为《十日谈》的写作跨度比较大,明显能看出作者男性本能的消退对于创作的影响。
《十日谈》里的女性人物居多,首先是七女三男来讲述这些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女性却是典型的“他者”,都是透过男性欲望看到的女性。薄伽丘对女性的珍视,并不是对人的珍视,而是对于喜爱之物的珍视。大可不必脱离历史阶段,努力提升作者的思想境界,凸显他的先进性,说这部作品“抨击了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赞美妇女是自然的美妙造物,主张妇女应该享有跟男人平等的地位”(《十日谈》译者序,戴冕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或者“薄伽丘在小说中对妇女表现了很大的同情和尊重,赞扬妇女的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机智,批评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十日谈》译者序,陈世丹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就连钱鸿嘉也说:“薄伽丘尊重女性,维护女权,提倡男女平等,这在《十日谈》中充分体现出来。”(《十日谈》,钱鸿嘉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理由也是薄伽丘在《自序》中的陈词。事实上,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女性在阅读这些故事之后很容易引起自我厌弃,而不是看到它提倡男女平等。
《十日谈》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薄伽丘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情有入木三分的描述,这使之能经历几百年的考验依然流传于世。这无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对人性的揭示,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
如果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在《十日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薄伽丘的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在文本中都有体现。作者的超我体现在小说的框架上,也就是由三男七女构成的理想社会,他们遵守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在瘟疫横行的时刻依然能操守行为规范,享受音乐和自然风光,具有极高的道德情操。作者的自我就是前言和后续中出现的叙事者,具有现实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写作和立场进行解释,协调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作者的本我经常出现在讲述的故事中,很多故事都遵循“快乐原则”,无论男女,都以一种恣意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欲望。
《十日谈》是人生之书,也是男女之书,智慧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极大的表彰,男性蓬勃的欲望和生命力也得到了捍卫,这对于中世纪反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但硬生生把这部名著说成是提倡“男女平等”之书,那就是脱离了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现实。年轻的薄伽丘对女性的兴趣是真实的、纯粹的,这种热爱和那位在山中隐修的懵懂少年对女性萌生的兴趣很类似,完全是出于本能。《十日谈》中对女性的训诫非常昭然,薄伽丘老年对于女性的抨击,也说明了之前的全力讨好也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致。《十日谈》是基于真实人性和真实欲望的作品,所以至今仍然散发着魅力。
文中的《十日谈》引文皆为本文作者译自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