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情感?如何认知?
邓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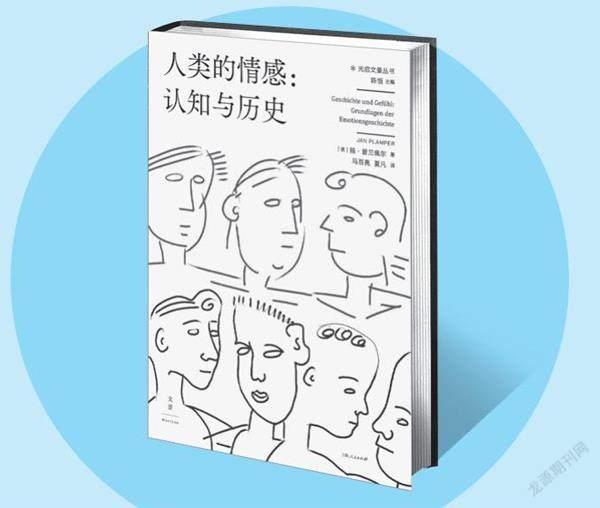
人类是情感的动物。对人类而言,情感无比重要,但人类对情感问题的认知,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德国历史学家普兰佩尔在其著作《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的“导言”中就提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情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从哲学、医学、伦理學、文学、美学到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学,人类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知识领域来思考情感问题,试图找到人类情感的本质。但是,关于人类情感的研究,并不容易找到确定答案。
在情感研究中,历来存在着普遍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普兰佩尔在这本著作的第二、第三章,分别介绍了这两种立场的情感研究。普遍主义以生命科学为主,认为人类的情感固定不变,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涵盖了所有物种,超越了时间,它既是生物学概念,也是生理学概念,它是本质主义的,与生俱来的;而建构主义以人类学为主,认为人类的情感是灵活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决定论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具有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特性。
在建构主义看来,从古至今,人类的情感是变动不居的。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曾经记录过一桩逸事,“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十七惋愤而终”,他后来还为此写了悼亡诗《哭娄江女子二首》以表哀思。汤显祖的《牡丹亭》讲述了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传奇故事。而现实生活中竟然也有闺阁女子在读了《牡丹亭》之后,心有戚戚焉而郁郁而终。这件事放在今天来看,显然是天方夜谭,但在汤显祖的时代却并不为怪。汉学家史华罗在《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中就认为,明朝后期是一个“情感至上”的时代。而如今,我们则处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其特征之一就是“情感的消逝”—“主体已经从一切情感中解放出来了”“今天一切的情感都是‘非个人的’,是飘忽忽而无所主的”。读者因为与剧中人共情而殒命,这样的事在当代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从“情感至上”到“情感的消逝”,随着社会历史变迁,人类的情感状态在发生着变化,不同时代对情感有着不同态度。大致说来,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人类经历了对情感从不重视到重视又到不重视的变化。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就认为:欧洲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之前,无论宗教还是哲学,大多否定感性(感觉/感情)的价值;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随着工商业的兴隆,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哲学开始重视情感的价值,以情感为标志的文学也随之兴盛起来。在这个“情感转向”的过程中,新型的经济伦理起着关键作用,比如亚当·斯密倡导的“同情”。斯密所说的“同情”不是宗教的怜悯、慈悲,而是设身处地代入他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个人主义,其根源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同情”是通过破坏前现代的共同体并高扬个人主义而产生的。因此,“同情”是一种全新的感情。由于高扬“同情”的价值,感情本身也开始被重新估价。
相比于文学和哲学,史学对社会情感变化的反应可以说不无滞后。强调史料的严格考订和写作中以可信的事实为据的兰克史学几乎笼罩了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学界,无怪乎美国情感史专家芭芭拉·罗森宛恩抱怨说,“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种状况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崛起后,才得以改变。实际上,普兰佩尔在其著作的第一章追溯西方情感史的历史时,就把它的开创者定为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费弗尔呼吁分析不同时期文字和图像中的情感表达。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情感的概念史,它描述了情感这一概念的意义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的变化。费弗尔是第一个勾勒出这个研究领域轮廓的人”。
可以说,西方史学领域同样经历了一场“情感转向”,而普兰佩尔自己,则一直是史学“情感转向论”的重要推手。二○一○年,他通过《历史和理论》杂志采访情感史三位先驱人物威廉·雷迪、芭芭拉·罗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时,询问他们历史研究是否已经出现了某种“情感转向”,结果大家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追溯西方史学“情感转向”的发生时,普兰佩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它是“9·11”事件推动的结果。在他看来,西方史学“情感转向”的发生既与生命科学的兴起有关,也与“9·11”事件对史学的语言学模式的冲击有关。在“9·11”之前,历史学流行的是话语分析和后结构主义,但是在“9·11”发生之后,人们开始追问,后结构主义历史学能够解释恐怖分子操纵载满乘客的飞机撞毁摩天大楼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吗?历史学的话语分析能够解释极端主义的狂热和仇恨吗?正是在这种追问下,历史学转向了对人类情感的研究。
历史学又是如何研究情感的呢?它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的情感性,即情感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情感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一是情感的历史性,即情感的历史变化以及情感在特定社会历史中的表现。与关注人类情感多样性的情感人类学、关注人类情感制度性的情感社会学不同,情感历史学(即情感史)关注人类情感的变化性。
与一般情感史理论著作不同,普兰佩尔的这本《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有一个显著优点。它虽然是站在情感史的立场上,但是对情感普遍主义持一种比较开放的借鉴态度,其用意在于建立“一种超越普遍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二分法的情感研究”。与很多情感建构主义者对情感普遍主义的漠视和敌意不同,普兰佩尔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介绍当代“生命科学”的普遍主义情感观。比如,他在书中谈到了当代的神经政治学。对这方面了解不多的读者也许很难意识到,当代社会的政治已经下沉到了情感和神经的维度。简单说,意识形态不再“晓之以理”,而是“动之以情”,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发挥作用了。这就是神经政治学为我们描绘的当代政治场景。因此,当普兰佩尔把《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也归到生命科学和情感普遍主义里来介绍时,读者大可不必惊讶。因为后者的确相信“情感是抵抗的源泉”,“我们要不断地把行动和激情之间的关系、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我们事先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心智能想什么、情感能做什么。它需要我们对这些尚不可知的力量进行探索”。
当然,普兰佩尔也意识到了,目前西方的情感史研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限制”:“情感史探讨的基本上是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在对情感史进行理论概述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非西方世界对于情感的思考”,但他本人对这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甚至没有提到史华罗对中国情感历史的研究。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情感史的视角”部分,普兰佩尔展望了未来情感史研究各種可能领域,其中尤其谈到了历史学家的情感问题。他在书中对人类学家们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极其推崇:“如果历史研究能够像人类学一样多一些研究者的反思,这将是非常有益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来自真空,他们的研究也不是‘不带任何感情’。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像人类学家写作田野调查日记那样记录自己的感受呢?”对欧美的史学家们来说,兰克史学虽然早已是过去式,但其严肃枯燥的幽灵似乎仍然在纠缠他们的史笔。在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年轻的历史学家尚能接受“共情”方法的训练,以期在历史编撰者与历史参与者之间建立“感情之桥”。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历史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客观性逐渐取代了共情观念,共情不再是历史训练的一部分。而到了二十世纪,虽然情感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但历史学家的情感问题早已无人问津了。但是,如果对中国的史学界多少有所了解的话,普兰佩尔或许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史学可以勾勒出一个情感传统来,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在历史研究中对古人应该“有了解之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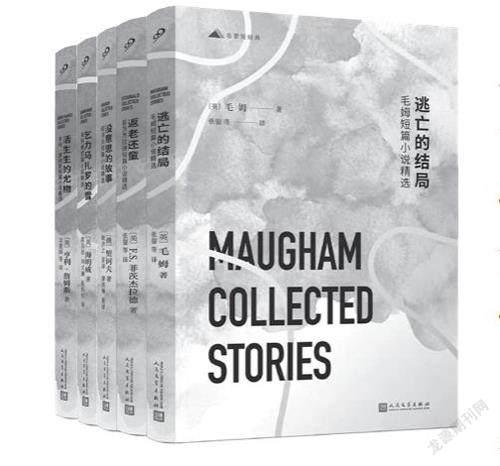
[美] 亨利·詹姆斯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短篇小说,读这五个人就够了: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开创者之一;契诃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之王;菲茨杰拉德,张爱玲最推崇的美国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被严重低估的短篇小说圣手;海明威,极简主义短篇小说之父;毛姆,以《月亮和六便士》闻名于世,也是技艺炉火纯青的短篇巨匠。
《活生生的尤物:亨利·詹姆斯短篇小说精选》《没意思的故事: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返老还童: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精选》《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逃亡的结局:毛姆短篇小说精选》……这里的每一篇都展示了这些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非凡创造力,是进入他们的文学宇宙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