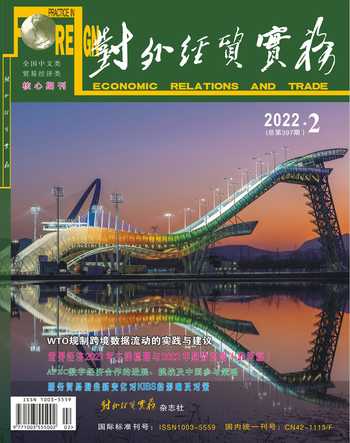“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补贴可制裁性考察
李涛 杨晓慧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企业会因从中国获得的融资支持而处于优势地位,这种融资支持引发了WTO成员方对跨境补贴实施反补贴制裁,2020年6月由欧盟委员会作出肯定性终裁的两个反补贴案件即为这一情形。本文结合WTO《反补贴协定》的规定对跨境补贴制裁的正当性进行了考察,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下向海外中国公司提供的融资支持服务于所在国的发展,不应当对其实施反补贴措施。
关键词:跨境补贴;一带一路;欧盟委员会;走出去;多边机制
2019年5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发起对原产于中国和埃及的进口玻璃纤维织物(glass fibre fabrics)的反补贴调查。根据披露的公开文件,该案申诉人声称:向欧盟出口玻璃纤维织物的埃及生产商位于埃及国内的一个经济特区内,该经济特区受中国政府支持并服务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了推动该经济特区的发展,埃及生产商通过中埃两国的协议受益于“通过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银行或其他中国国有或国家控制实体(直接或通过埃及实体)提供的财政资助”。经过调查,欧委会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肯定性终裁,决定对上述埃及生产商生产的玻璃纤维织物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另外,在欧委会于2019年6月7日发起的对玻璃纤维增强物(glass fiber reinforcements)的反补贴调查中,申诉理由与前述案件相似,但涉案产品完全来自埃及。欧委会也于2020年6月25日对该案作出征收反补贴税的肯定性終裁。
中国企业频繁被其他WTO成员方实施反补贴调查是不争的事实,但申诉调查对象通常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所受中国政府的补贴。然而,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调查对象是具有跨境因素的补贴,即中国政府(资助国)向在第三国(出口国)设立的生产商提供资助,其产品出口到其他第三国(进口国)。这就使得这些案件与既往反补贴案例有所不同。因此,这种跨境补贴能否依据WTO《反补贴协议》实施反补贴制裁措施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反补贴制度来源视角下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政府意识到补贴可能会产生潜在的贸易扭曲效应。于是,各国开始讨论在《哈瓦那宪章》(Havana Charter)和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对补贴施加某种形式的规制。然而,这两份文件并没有对补贴问题作出实质性规定,各国依旧竞相对国内出口商提供补贴,以求捍卫在全球市场的国家利益。
到1970年代,补贴的使用已成为最常用和最具争议的商业政策之一,并导致所谓的基于“竞争性补贴”而非市场力量的贸易,这促使GATT缔约国在东京回合就《补贴规则》(Subsidies Code)进行谈判。该《补贴规则》试图消除补贴的贸易扭曲效应,但其仍明确承认补贴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认为彻底禁止补贴将阻碍发展中国家培育其自身工业。
《补贴规则》没有消除补贴的贸易扭曲效应,这导致1985年乌拉圭回合筹备委员会着手进一步解决补贴问题。乌拉圭回合补贴谈判的议题集中在限制各国为发展国内产业使用补贴,以免造成国家间的补贴竞赛。正如WTO贸易融资问题专家组(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rade Financing)所言,乌拉圭回合所通过的《反补贴协定》“总体上是为了应对成员国对自身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补贴的情形而制定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补贴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具有跨境因素的补贴层见叠出。例如,出口买方保险和出口买方信贷就是出口商所在国政府向出口产品的外国购买者提供的补贴,其已在国际贸易得以广泛应用。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会涉及到跨境补贴的运用。中国国有银行一直以贷款、出口担保和出口保险的形式向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中国公司提供融资。但是,从WTO《反补贴协定》的订立历史来看,这种跨境补贴本不在规制范围之列。
二、补贴认定视角下的考察
根据《反补贴协定》的第1.1条,如果某一成员方的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并且由此而给予某种利益,则应被认定为有补贴存在。下文也将结合该条“财政资助”和“利益”的规定对跨境补贴展开考察。
(一)接收“政府或公共机构”的“财政资助”
《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对补贴的原文限定用语是,“某一成员方境内的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by a government or any public body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a Member)。国外学者Horlick指出,由于当时美国是最大的对外捐助国,为了避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诉扰,所以在起草该条时专门加上了“境内”一词作为限定条件。但是,第1.1(a)(1)条中的限定词“在成员国境内”仅指向“政府或公共机构”,而不限定“财政资助”一词,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财政资助的接收人必须位于何处。
就多边金融机构的援助而言,欧盟-大型民用航空器补贴案(EC–Large Civil Aircraft)的专家组表示,是否能将其视为“成员方境内的政府或公共机构”尚不清楚。该案专家组还指出,并非所有财政资助的案件都涉及《反补贴协议》下的可诉补贴。同样,WTO贸易融资问题专家组也解释说,多边发展机构提供的援助不受《反补贴协定》的规制,没有任何国家认为这种援助是一种补贴。
因此,尽管《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将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援助排除在规制范围之外,但它并没有排除向位于补贴成员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的接收人提供的财政资助。
(二)给予“利益”
《反补贴协定》第1.1(a)(2)的表述是“由此给予利益”(a benefit is thereby conferred),此行文表面看来没有对利益接收者的位置施加任何领土的限制。该条的规定可以说关乎整个《反补贴协定》的适用,因为只有确定了利益的接收方,才能确定补贴的接收方。正如上诉机构所言,《反补贴协定》没有规定“利益”的“接受方”的具体定义。但是,利益的接收方必须是“受反补贴调查的出口商品的生产商”,该利益的接收方可能会不同于财政资助的接收方。因此,确定谁是接收财政资助并由此获益的生产商是极其重要的,正是这个生产商确定了补贴的接收方。
例如,对于买方出口信贷,补贴不是指买方所获得的利益,而是指买方购买其产品的出口生产商所获得的利益。在巴西-飞机一案中,巴西和加拿大达成的一致认定是,出口融资付款是巴西政府向外国飞机买家的直接资金转移,但利益将根据巴西飞机制造商的情况确定。这一认定在后来的21.5条复审程序(Article 21.5 DSU–Canada II)中再次得到确认,即加拿大需要证明的是“付款使该产品的生产商受益”,而专家组所要审理的问题是出口信贷支持是否使巴西出口商受益。
因此,尽管第 1.1(b) 条不对利益接收者的所在地作出限定,但利益接收者的所在地对于确定下文所述《反补贴协定》下补贴接收者的所在地是至关重要的。
(三)对补贴接收方所在地的限定
虽然《反补贴协定》的第1.1条下的“财产资助”和“利益”不含有对接收地点的特别限定,但该协定第III、V部分规定的关于非禁止性补贴可以利用的多边和单边救济措施受到补贴接收方所在地的限制。这与该协定中关于专向性、补贴计算方法的规定有关,甚至也能从协定第25.2条关于通知的规定中发现端倪。
1.专向性。根据《反补贴协定》第1.2条的规定,若要诉诸于单边或多边救济措施,补贴必须是专向性的。该协定第2条进一步规定,除第3条所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外,补贴需要提供给“授予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行业、或企业或行业集团方可满足专向性条件。因此,除非是禁止性补贴,动用《反补贴协定》下单边或多边救济措施的条件就是补贴的潜在接收者位于补贴授予机构的管辖范围内。
根据上诉机构的说法,对“管辖范围”(jurisdiction)和“授予机构”(granting authority)的界定需要从整体上一并考察,因为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上诉机构还解释说,授予机构的管辖范围会因授予机构(“政府”、“成员领土内的公共机构”或政府委托或指示的“私人机构”)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反补贴协定》第2条使用的是“授予机构”一词,而非第1条中定义的“政府”,表明“授予机构”可能不同于补贴成员方的中央政府。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authority”是指“在特定领域拥有政治或行政权力和控制权的人或(特别是)机构、及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负责执行法律和法令、提供公共服务等的一个或多个机构”。
然而,并非所有的财政资助都来源于拥有监管权的机构。这时,就有必要审查该机构背后是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这类没有监管权的机构通常会通过特定“补贴项目”提供补贴。例如,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China))上訴审中,上述机构确认,中国国有银行的优惠贷款是根据“一些中央、省和市的法律、计划和政策发放的,如‘十一五规划(2006-2010)”。此种情况下,需要审查的是负责这些补贴项目的机构的管辖权,而与那些实际提供资金的机构无关。那么,对于向境外经济特区内的中国企业提供财政资助的情况,也应该追踪到授予机构背后的政府机构。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而言,就应该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对于“管辖范围”,在WTO判例中并没有太多讨论。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jurisdiction”是指“司法或行政权力延伸所至的区域范围”。正如在国际常设法院荷花号(SS Lotus (France v Turkey))一案中提到的那样,国家管辖权的传统理解“当然是属地的,它不能由一个国家在其领土之外行使”。尽管这种理解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当今的现实,但以此解释《反补贴协定》第2.1条中“管辖范围”应当是合适的。
《反补贴协定》的起草过程也证明了这一解释的合理性。在《反补贴协定》谈判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曾提议“要进一步表明专向性只存在于缔约方的领土内”。于是,《反补贴协定》草案第2.1条对补贴的专向性作出进一步限定,要求补贴必须向“补贴国境内”(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ubsidizing country)的企业发放。不过,在加拿大的请求之下,第2.1条与第2.2条一并得以修改,因为加拿大认为这样的规定将导致“加拿大的省级政府提供的任何补贴将被认定为是专向性的,即使是惠及全省的补贴”。这样,修改后的两个条款均修改为“授予机构管辖范围内”这一措辞。
当然,肯定会有观点认为补贴成员方的管辖范围可以延伸至其领土范围之外的出口生产商。其理由可以从中国的例子来说明,因为存在源自中国的股份,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中国公司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然而,这样的理由似乎与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Barcelona Traction)中阐明的判例不相吻合。该案中,国际法院明确驳回了一个国家可以因公司股东的国籍属于该国而对该公司行使管辖权的论点,并重申国家对公司的管辖依照公司的成立地确定。另外,一些生产商位于中国和东道国协议设定的经济特区内,这也可能被用来作为这些生产商受中国管辖的理由。但这种理由毕竟是牵强的,因为中国毕竟在这类经济特区中不具有执行中国法律的权力。
因此,《反补贴协定》第2.1条中的“管辖范围”概念仍然是“属地的”。由于在第三国设立的生产商位于中国境外,这些生产商就不属于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因此,向其提供的补贴不符合第2.1条和第2.2条所规定的专向性要求。
2.可诉补贴数额的计算。《反补贴协定》附件四第2段的脚注63确认了以下结论:就可诉补贴而言,补贴的接收者必须在补贴成员方境内。该脚注规定了根据第6.1(a)条计算从价补贴总额的准则,并载明“接受方公司是补贴成员方境内的公司”。
虽然这个脚注很少被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讨论过,但在美国-对外国销售公司税收待遇第21.5条审查程序(US–FSC (Article 21.5 DSU))中,美国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该脚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它只是重申《反补贴协定》其余部分已经叙述过的内容;另一种解释是,此脚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协定的其余部分中,并未表明接收方必须位于补贴成员方的领土内。”
无论采取何种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脚注63适用于可诉补贴之严重损害的确定。这就表明利益的接收者需要位于补贴成员方的领土内,也确证了跨境补贴不受《反补贴协定》第III部分规定的多边救济措施的约束。
3.通知。《反补贴协定》第25.2条规定,WTO成员方应当向WTO通知“在其领土内给予或维持”的专向性补贴。就其文义看来,该条没有要求成员方向WTO通知跨境补贴。
综上所述,虽然《反补贴协定》的第1.1条下的“财产资助”和“利益”不含有对接收地点的特别限定,但从协定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来看,补贴接收方应当位于提供补贴的成员方境内,因而也就不能动辄向“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补贴启用救济措施了。
三、反补贴调查程序视角下的考察
虽然可以对源自出口成员方领土的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但根据反补贴调查程序方面的规定(《反补贴协定》第V部分)来看,不能将出口成员方与补贴成员方分开看待,因此可能采取反补贴措施来解决跨国生产补贴问题。
具体而言,《反补贴协定》第13条明确规定,一旦受理反补贴申诉,调查机关就需要邀請“其产品可能会受到调查”成员方进行磋商。在上述欧委会发起的对仅原产自埃及的进口玻璃纤维产品反补贴调查案中,欧委会调查了中国公共机构提供的补贴,但在调查开始之前没有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此外,由于中国政府不是本次调查的出口国,欧委会“要求(埃及政府)提供有关中国银行业的总体法律框架以及中国金融机构的信息,因为(埃及政府)是该调查利益相关方”。
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也与《反补贴协定》第V部分给予WTO其他成员在反补贴方面的程序性权利相违背。这将导致补贴成员方可能没有公平的机会对补贴控诉作出回应,并给出口成员方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反补贴协定》第V部分仅规定了反补贴调查程序中向出口方成员提供的程序性权利,其实是因为其将补贴成员方和出口成员方视为一个主体;这样看来,跨境生产补贴就不应当受反补贴措施的约束了。
四、结语
随着“走出去”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跨境补贴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跨境补贴可以满足《反补贴协定》第1.1条下的补贴定义,但《反补贴协定》第1.2条没有将这类非禁止性的补贴纳入应受约束的范围,因为该协定第2.1条的规定要求补贴的接受者需要“在授予机构的管辖范围内”,并且这一点由第25.2条和脚注63进一步确证。《反补贴协定》也仅为反补贴调查程序中的出口国政府提供了程序权利。
尽管跨国生产补贴越来越有争议,但需要时刻铭记的是,管制贸易扭曲补贴的目标应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以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持平衡。实际上,很多“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欢迎中国作为其经济增长贡献者的参与,这一结论不应因中国崛起、西方式微的事实而肆意改变。
参考文献:
[1] 欧盟委员会贸易救济案件资料:https://trade.ec.europa.eu/tdi/index.cfm?sta=21&en=40&page =2&c_order=date&c_order_dir =Down [OL].
[2] WTO争端解决机构案件资料: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dispu_e/dispu_e.htm [OL].
[3] Gary Horlick, An Annotated Explanation of Articles 1 and 2 of the WTO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8 (9) Global Trade and Customs Journal 297, 278 (2013).
[4] 陈瑶.补贴专向性审查的争议、发展与中国对策 [J].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1(6):56-76.
[5] 胡建国, 陈禹锦.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草案)》及其WTO合规性分析[J]. 欧洲研究, 2021(5): 84-110+7.
[作者简介]李涛(1977—),男,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法。杨晓慧(1998—),女,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