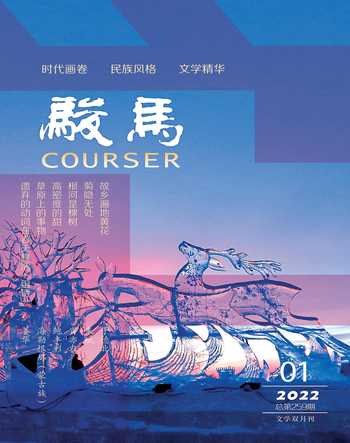菊隐无处
朱斌
一
家家户户养菊花,户户家家有埠头。说的就是菊乡,菊乡是个货真价实的水乡,紧傍着大运河。每年十月中旬,菊鄉都要办菊花节。每到菊花节,菊乡人都会广邀亲朋好友来饮酒赏菊。菊乡子弟小强曾不止一次地邀请我们到他家过菊花节,这让我拥有了一个奇特的梦,一只蜜蜂扑在一朵大大的菊花的花蕊上不停地采呀采,采得让我生出一嘴苦味来。
菊乡离开市区也就三四十里路,通水路、有游船,但我们回回都是骑车去,方便、省钱。四个人三辆自行车,小强、光光和我轮流捎着燕子。一路上燕子在三个人的车后座上飞来飞去的,真的很像是一只春燕。
我比小强大一岁,光光比我大两岁,燕子和小强同年。燕子两臂环抱着小强后腰,脸颊贴着他的脊背,一脸的半梦半醒。燕子只在小强的身后千娇百媚。小强却嫌她腻歪,捎了不多远的路,小强就说踩不动了,把她赶到了光光的车后座上。我知道光光正等着她过来呢。
在光光的车后座上,燕子坐得端端正正的,像是一枝怒放在微微秋风里的黄菊,庄重安闲。但只要燕子一坐上光光骑的自行车,这小子就霎时浑身来劲,就会脱开车把平展两臂像飞翔的大鸟一般玩车技,嘴里拖着长音吼着“啊——”。
光光带着燕子一边疯吼着,一边疯蹬着自行车,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但用不了多久,燕子就恼了。不知为什么就恼了,我们远远地看到她拿光光宽厚的脊背当鼓擂,擂得自行车扭了两扭就翻倒在路边的土沟里。我猜一定是光光又说了什么痴话。
苗条轻盈的燕子在车倒前就跳了下来,等着上了我的车,光光还在路边双腿夹着前轮,调整那辆金狮自行车的车龙头呢。
不论金狮、飞鸽、还是凤凰牌自行车,都在年轻的脚下被踏得飞快,午饭前我们准能赶到菊乡。到菊乡,穿一条花街,拐过两三条菊巷,就到了小强家。小强家也种菊花,屋前院里都是,花色撩眼、姿态各异,但我们并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这些千娇百媚的花上。我们想的是:
嘬田螺、剔蹿条、品醪糟菊圆。
小强的妈妈最懂我们的心思,早就都准备好了。
有道是入秋田螺最肥美。一大盆香辣田螺先端上桌来,光光嘬得最快,两片嘴唇一努、腮帮子一缩,“哧溜”一声,肉就进了嘴里,暗绿油亮的硬壳一个接一个从他大大的嘴巴里掉下来,落进白瓷海碗里,叮叮当当地脆响不绝于耳。燕子则不擅长嘬田螺,她得拿根牙签挑着吃。燕子擅长的是剔蹿条。蹿条是一种小鱼儿,味美但刺又多又硬,可燕子不怕,剔得最漂亮,一条完整的小鱼儿从花骨朵样的小嘴的一边角进去,很快从另一边角出来,肉全没了,只剩下个鱼头和一副白森森的鱼骨架。燕子这一手剔蹿条的绝活,让小强妈妈的一张脸笑得和外面正盛开着的菊花一样灿烂,坐在她边上一个劲地给燕子搛蹿条鱼儿。
最后上桌的是下在醪糟里的菊花汤圆,水磨糯米粉搓得珠润玉圆,红的是用红菊汁染的,黄的是用黄菊汁染的,青的是用青菊汁染的……就连白的也浸润着白菊汁,五颜六色圆滚滚地沉在清清的汤里,像一个个初生的小菊苞挤挤挨挨地欢聚一处,让人不忍下口。这样的汤圆咽进肚里,会化作菊花一朵一朵开上心头的,呼出来的气都是酒香合着菊香,透着一种雅致。
虽然,我们是来过菊花节的,但吃完午饭,我们并不上街去看菊花,还是待在小强家里,也不去他家院里赏菊。小强家的屋后有一条不宽也不窄、不深也不浅的河。等我们吃饱了,小强和光光就蹲在赭色条石铺砌的埠头上拿稻秸秆钓呆虾,呆虾也就是公虾,还叫作骚脚虾。我有两次清楚地听到燕子骂光光是只骚脚虾。
只要把秸秆垂直地插入水中,静静地等着,就有傻乎乎的骚脚虾伸出细长的脚钳来夹秸秆,缓缓提出来的时候,受惊的虾身子蜷成一团,脚钳拼命夹着秸秆兀自不肯放松。这种公虾脚长钳大,又爱夹东夹西的,所以被叫作了骚脚虾。这样子钓虾全凭耐性和运气,光光一个人定心地在一边钓了一只又一只。小强就不行,因为燕子围着小强快活得大呼小叫、拍手跺脚,扰得他一刻也不得安宁,结果是一只虾也钓不到。小强恨恨地把秸秆扯成几段撇在河里,转身离去,燕子也跟着离去。只有呆呆的光光还在那里呆呆地钓呆虾。
燕子爱小强,小强没感觉。光光追燕子,燕子不理他。我是局外人,又是知情人。
小强家的埠头边上还有一株老柳树,柳树下系着一条两头细尖细尖的小舢板儿,船肚就分三格,顶多坐得下四个人。小强告诉过我,这小舢板儿原是他父母用于摆渡到对岸去种地的,要不,得顺着河岸往下走好些路才寻得到一座很古老的石拱桥。现在这舢板儿基本上废置不用了,因为田地被征去建工厂了,小强的妈妈也去了工厂。工厂为了方便工人上下班,还特意造了一座桥,桥离小强家只有一射之地。这小舢板儿就横在那儿,落了个自生自灭的命。
我站在小强家屋后的埠头上,瞭望着对岸的苇丛、苇丛那边的细竹林、竹林上方的天空、天空中徐徐飘过的白云……
一切都让我看不够。
可是后来,化工厂的烟云飘了过来,一切就都变了。
二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是大学毕业后来这座江南小城参加工作的。单位给我安排的宿舍位于一处拆迁死角,是建在化粪池上的两间平房,还是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造的老式防震房,空斗墙,油毛毡做顶。除了北面的屋里有一个镀锌水龙头,再无其他生活设施。这一南一北两间低矮的平房背靠长途汽车站,被三四幢居民住宅楼扇形环绕着,不通风不透光,气味也不甚好。
绕过这宿舍北边的住宅楼房,就是集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金碧辉煌的常武大厦。大厦三楼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舞厅。晚上没事的时候,我就去那里跳跳舞。跳舞的时候认识了穿枪标领、喷古龙水、抽摩尔烟的小强。在去他家前,我怎么都不相信他是菊乡农家子弟。
帅气时尚的小强技校毕业,虽然比我小,但比我工作早。他原是在车间里当工人的,但他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硬笔字,还能画会刻懂美工,所以被厂里的书记看中抽上去帮着搞政工。小强在城里没住处,又不耐烦天天赶来赶去,就在朋友处打游击过宿。其实,我也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他乡害着寂寞病,便召小强来空落落冷冰冰的宿舍同住,他便欣然而至。FFBD8AE9-2850-4CAB-9371-1A560A96E423
我怕小强看不上我这宿舍,破陋且不说,还不干净。老鼠和蟑螂猖獗得很,我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别嫌弃啊,我怕一个人睡觉会被老鼠们抬走。
他倒是出乎意料地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过两天弄点药来药死它们不就得了。两间房子,门前还有这么大一块地,要是圈个院子,种上菊花,我们不也好做隐士了吗?
和他交往久了,我才知他最向往陶渊明式的生活。也许正宗的菊乡子弟都有这种情结吧。
小强来了,燕子随即而至。
燕子是大厦餐厅的服务员,专管配菜,她也爱跳舞。燕子那时已经爱上了小强,而且这姑娘有主见又主动。但小强的心不在她身上,小强看上的是大厦里的一个迎宾小姐。暗恋了好些日子,小强曾挖空心思写了一首诗:
鸳梦别晓晨光青,
寒屋娇霞微风凝。
情浓意真流温馨,
月圆夜美袭人心。
娇柔却日舞娉婷,
婀娜谢夜玉色冰。
无限相思哨哨吟,
姿容为你日日新。
我读过藏头诗,但小强写的是藏中诗,这八句诗的中间一个字依次连起来就是:晓霞真美日夜思你。这小子还真有点歪才!
挨到元宵节的时候,小强终于鼓足勇气,亲手做了一盏精美的小宫灯,拉我陪着他提着灯去向那位芳名晓霞的迎宾小姐表达心意,弄得穿着一身大红旗袍正站在门口迎来送往的小美人儿跟遭遇外星人一样,不知所措地连连避之。众目睽睽下,小强也乱了阵脚,藏在肚子里的锦言玉词一个也没能蹦得出来,只好脸红脖子粗地把可怜的小宫灯往大厦门上一挂就跑,是燕子呵呵笑着提了那盏宫灯一路追到了我宿舍……
现在想来,光光应该很久前就开始追燕子了。但燕子一直都只把他当作最要好的异性朋友。
光光不会跳舞,他是常武大厦的保安,当过兵,准确的说是在部队当过炊事员,擅长软磨硬泡。燕子追小强到了我这儿,光光追燕子也到了我这儿。那天,小强对燕子说,你身后还有保镖跟着?
没有啊。燕子满脸不解其意的神情。
小强就拉开门喊道,门外的朋友请进来坐。
等高高大大的光光终于从屋外的阴影中走到了屋里的灯光下,燕子当着我们的面拿脚踹他。那天,燕子穿着衩开到了腿根的淡粉色旗袍,白嫩的一双大腿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白得晃眼。
光光依旧笑嘻嘻地用手拍去深蓝色保安服上的小脚印,一点儿也不生气,向着我们说,她练过长拳的,懂武。
真的?我惊讶地再次打量着燕子。燕子肤色也很白,但她的白和小强不同。小强像是汉白玉削出来的,燕子则像是雪团出来的。
别看光光人长得粗,黑黑壮壮的套在深蓝色保安服里,比不上小强,一身笔挺的枪标领西服,脖子上围着马海毛大围巾,一头自来卷,嘴角叼着和他的身材一般细长的摩尔烟,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洋气。可光光有心计,有耐心,他还会搞迂回包抄,很快和我、小强都成了好兄弟。把情敌都变成了朋友,是这小子的过人之处,他反而更能接近燕子了。
第一次来我的宿舍,光光一双小眼睛在空荡荡的两间屋里四下一扫,告诉我们正好他那夜当班,要是下半夜得便的话,他会送一些东西过来的,让我们听到敲门声就开门。我和小强莫名其妙,燕子在一边撇了撇嘴,满脸都是不屑,骚脚虾做不出好事来。
到了下半夜,我们真被他的敲门声给吵醒了,他搬来了四把折叠椅,并说还有东西。我和小强要去帮他,他不让,说那样反而不好。
光光监守自盗,我和小强心知肚明,却不点破,乐得享用。有了光光,常武大厦都快变成我们的后勤仓库了,冬天的厚被子,夏天的席条子,淘汰下来却依旧可以使用的取暖器、风扇等等,他一一搬了来。我问他,光光,你这样做究竟图个啥呢?
他憨憨一笑,咱们是朋友啊,小事一桩,不足挂齿的。
我们的宿舍一天天地充实温馨起来,光光也一天比一天地受到我和小强的优待,燕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粗暴地对待他了,我们四个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很好的朋友。
燕子是大厦餐厅白案间的配菜员,也就是专管凉盘和熟菜的。所以我们也就常常有牛肉、爆鱼、三黄鸡什么的小菜吃。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就着燕子拿来的几个冷菜吃方便面。我一再地对燕子表示谢意,感谢她坚持不懈地给我们改善生活、增加营养,小强语气不屑地打断我,这有啥了不起的,有本事就弄点鱼翅什么的山珍海味来让我们品尝品尝。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别说是区区鱼翅,为了小强,燕子连天上的星星都敢去摘。过了两三天,燕子还真端来了一盆鱼翅,刚喝了几口,小强那张乌鸦嘴就又忍不住地开了口,他说像没煮透的粉丝,没啥好吃的。气得燕子的小嘴撅得老高,也不管光光和我哧溜哧溜地正喝得欢,端起大大的汤盆,把剩下的一股脑儿都倾在屋角的垃圾桶里。
我们好像是把儿时的过家家游戏玩大了。我拉小强做伴儿,结果引来了燕子、光光,有了好用的、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光光还弄了一副跳棋来。四个人下跳棋,光光的子儿还都在半路上,对家燕子的子儿就全进窝了。光光嬉皮笑脸地说,她的子儿还不是全跑我家里来了。
說得燕子又要和他动武。
夏天一过,小强就迫不及待地请我们去他家过菊花节。
去小强家过菊花节后不久,在皮革厂上班的小强妈妈就开始时不时让小强带皮鞋、靴子、小坤包等等的给燕子,说是皮革厂的样品,让燕子试穿试用。燕子喜欢得差点飞上云端。小强不咸不淡地说,又不是真正的品牌,不过是乡下厂里做的冒牌货,就你高兴要。
怎么了?我就是高兴要。
光光在一旁忍不住问,真有这么多样品?有没有皮夹克?我想来一件。
三
燕子在追小强,小强妈妈一眼就看出来了。小强的妈妈打心底里疼燕子,我和光光心里也都一清二楚。我有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光光说,你跟着混吃混喝了这么久,也算够本了吧?快识趣点自动退出吧。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FFBD8AE9-2850-4CAB-9371-1A560A96E423
这家伙只是嘿嘿一笑,眼睛骨碌碌地转上几转,厚着脸皮说,等他俩领了证,我自然就退出了。
光光骨碌碌转动的眼珠像两颗算盘珠子,让我不由地想起他的家世来。光光的父亲是乡里的主办会计,姓金,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名之金光;第二个儿子落地后,起名为金见光。金光,我们呼之为光光的,身上流淌着主办会计的血,看上去憨憨呆呆的,其实贼精贼精的,贼得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小强就是个不成熟不定心的男小佬,成天想着玩,什么新潮他就玩什么,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暗恋了那个迎宾小姐那么久,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向人家表白,被一口拒绝后,也只是难为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连再尝试一下的想法都没有。至于燕子,好像他只是把燕子当成了一个妹妹,一个烦不清的妹妹。可这反而让燕子更迷恋他。但小强的妈妈有些着急了,在她眼里,燕子和小强是玉女配金童,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姻缘。小强妈妈曾暗地里托付我想想办法快点促成他们俩的好事,她说小强听我的。我只好模棱两可地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水到才能渠成。
其实,我预感这俩人的恋爱前途很渺茫。
小强的父亲早已去世了,这么多年来,小强妈一直都是一手拉扯儿子,一手侍候婆婆,生活的艰难困苦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小强妈虽然瘦得干瘪干瘪的,却依然心灵手巧。为了讨好燕子,她偷了燕子的脚样儿,偷偷地给心目中的儿媳妇做鞋子、靴子,甚至足可以以假乱真的品牌包。几乎是市面上流行什么款式,她就让小强给她送什么样的样鞋去试穿。虽说那些鞋什么的都是冒牌货,可是伪而不劣。每换一次新鞋,燕子都要欢天喜地地到处显摆,而小强却没心没肺地提醒她,假的真不了,小心穿帮。
莫名其妙的是,每当小强说这话时,我这个局外人却有一种隐隐心痛的感觉。我知道,小强看不上那些他妈一针一线纳出来的乡货,他要的是真货。他身上穿的、戴的,每一件都出自于专卖店的知名品牌,就是内裤,也不肯将就,非三枪牌不穿。
现在想来,那一段时光真是微妙、纯洁而美好。
要想富,先修路。道路通,搞化工。可是搞起化工的菊乡人没有挣来金山银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绿水青山和原本略显清贫却也十分安适的生活。等到那个该死的化工厂的四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里冒出黄乎乎的浓烟,阴云开始笼罩我们的心头,不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化工厂正式投产后的第一年,菊乡的菊花就显得萎靡不振。我们依旧去小强家过菊花节,看到人们神情凝重,节味十分的寡淡。我心里最想的花花绿绿的菊汁汤圆变成了纯白色的普通汤圆,不带丁点儿的菊香。小强妈满脸歉意地说,今年的菊花汁苦得不能用了。
吃完饭去小强家的埠头上,河水散发出一股说不上来的怪味,一个虾影也看不到。我们也待不住,匆匆回城了。
第二年,有权有钱或有路子的人纷纷走的走、搬的搬,镇上冷清了许多。外来的鼻子可以不费力地嗅出空气中的怪味,舌头也可以轻易尝出水里的涩味。菊花开得稀稀拉拉的,还不如城市公园里的呢,节都没办得起来。
第三年,菊乡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患上各种各样的恶性肿瘤。厄运也找上了小强家,先是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得肺癌去世了,接着轮到了小强妈。
拖了近一年,小强妈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一天,我们四个围在她床边,病魔把她脸上的美丽和慈祥抹得一点儿不剩,只留下痛苦和不舍。她伸出枯瘦的青筋暴露的双手,一手攥着小强犹如汉白玉削的左手,一手拉着燕子恰似雪花团的右手。她把燕子的手放在小强手上,仿佛几根枯藤要把一团雪捆在一块汉白玉上。
燕子泪如雨下,小强两眼茫然面无血色。我不忍再看下去,拉着光光走了出去。
四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们K歌的时候,小强爱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唱完这首,燕子就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得光光心痒难耐,像只骚脚虾般的跃跃欲试,但他只会唱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他那么黑大个唱这种歌很是滑稽,逗得燕子哈哈大笑,前仰后合。现在,小强没妈妈了,光光有事没事就哼唱这首歌,哼得燕子眼睛白着他叫,讨厌,骚脚虾快别唱了。
妈妈的怀抱即便再瘦弱,也是温暖无比的。在妈妈的庇护下,小强一直是无忧无虑的。妈妈死后,生活的重担一下子残酷地压在了他的肩上。而小强是货真价实的寒门小户刻意养出来的大少爷,一双肩膀承受不住多少担子。
拖着一屁股的债,小强选择了逃避。他说他要去南方闯一闯,他把忧伤烦闷的眼光射在我和光光的脸上,心情沉重地对我们说,兄弟,你们的那笔可能要等到最后还了。
我和光光这些年的积蓄都被小强借去给妈妈治病和办丧事了。我本来挣得就不多,外加一双大漏手,所以没有多少钱借给小强,光光倒真是借了不少给他。每一笔,光光都是当着燕子的面交到小强手里的。我望着光光,这小子一双小眼睛骨碌碌转了好几圈,憋了好一阵儿,才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倒是不急等着用钱。不过……
他欲言又止地从眼角瞄瞄我,让我好生奇怪。我纳闷且不耐烦,你有話就说,有屁就放,干嘛吞吞吐吐的?
他两眼死死盯住我的脸,而话却明明白白是丢给小强的,在你走前,把燕子给我。钱还不还随你便。
他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叫,但我们都听清了。我觉得这小子好荒诞。小强从来就没表示过燕子是他的,燕子也确实不是他的。什么给不给的,怎么就这么龌龊呢?难道燕子是一株菊花,可以从他家院中挖到你家去?
我刚要开口数落光光两句,小强就吐出了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一句,你拿去好了。
啊?我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他俩就这么赤裸裸地当着我的面做这种交易,他俩把燕子当什么了?我不生光光的气,我很生小强的气,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我没有拿话去刺他,只是冷冷地反问光光,就算他同意给你,你打算咋个要法?
生米煮成熟饭。FFBD8AE9-2850-4CAB-9371-1A560A96E423
一字一顿,这小子一点都不含糊。我倒抽一口冷气。难道是我看走了眼,他难道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我真不敢相信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可让我彻底晕厥的话随之而来。
小强竟然一口应承了下来,“好,我成全你们。”
于是,我张口说出的话就成了,你们可要想周全后果啊!不要闹到吃不了兜着走的地步。
他们居然一起冷冷地望着我,光光说,这和你有啥关系呢?你只当不知道好了。
他们什么都没瞒我,又要我当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我也曾纠结着要不要去告诉燕子。事后,我很是后悔当初没有当机立断去告诉燕子。我自以为是地躲开了,甚至为他们提供了场地——我的宿舍。
他们做事的那天晚上,我在外面一场接一场地看电影。
我心乱如麻而且忐忑不安。我不停地看表。
十点了,按计划,燕子该让小强用放了安眠药的饮料放倒在我宿舍的床上了吧?
十一点了,光光该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吧?
十二点了,燕子该醒过来了吧?
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一些细节来。我觉得十分对不起燕子,她应该是被我们三个合伙出卖的。可怜的姑娘,她的美丽、她的善良、她的贞洁……
她是在哭呢?还是在寻死觅活呢?還是羞愤难当地跑向派出所了呢?我不能不想,但只要想,就有一阵一阵的寒意蹿上我心头,黑暗中,我时不时地打寒颤。
突然,一阵尖锐的警笛声切开了我混沌的思绪。血血血,银幕上大摊的血呛得我喘不上气来,我叫声不好就往宿舍跑去。
只有他们两个失魂落魄地坐在凌乱的床铺上。
她呢?我气喘吁吁地问。
跑了。光光有气无力地回答我。
我松了一口气,没做成。
做成了。小强幽幽地说道,眼睛盯在我床上。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床单上有一小摊血迹,像是揉碎的一把红梅花瓣。
做成了?然后她跑了。她不会去叫警察了吧?我的一颗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了,那对我们三个可都是灭顶之灾啊。
没人回答我,他俩忽然抱在一起开始大哭,哭得我火冒三丈地冲着他们骂起娘来。
一直挨到天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燕子没有回来,警察也没来。我们三个稍稍收拾收拾,就心怀鬼胎地各自上班去了。
到晚上,我们三个惶惶不安地再碰到一起的时候,还是没有燕子的消息。胡乱猜测了一番后,我们横七竖八地倒在那张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还在上班的时候,光光给我打电话,说燕子已经辞职走了。他说他也要辞职去找燕子,我拿着冰凉的听筒不停地“嗯嗯”着,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又过了两三天,小强也走了。
不通风、不透光的房中只剩下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光光搬来的折叠椅、玻璃桌,燕子拿来的锅碗瓢盆,小强抽空了的烟壳子,用完了的香水瓶,还有床单上的血迹都历历在目。我颓然地缩在屋角打量着这一切,好像是一个才进入现场的局外人。
五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正躺在一片黑暗中听渗进来的雨水从顶棚滴入地上搪瓷盆里的声音。
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敲我这孤零零的单身宿舍的门呢?
确切地说,我不是被敲门声惊醒的,更不是被雨滴声闹醒的,而是被一只急匆匆跑过我手臂的老鼠给踩醒的。我的宿舍屋子底下,再说准确点,我的棕帮床下面,就是对面那几排高楼大厦的化粪池。这些硕鼠会不会是从化粪池中钻上来的,每当想到这儿,我就一阵阵恶心,无法再次入睡,一边听着渗水滴落的声音,一边想着心事。
要是光光在就好了,这小子三教九流的都认识。他若在,我就不用愁求谁来修补房顶。光光还能搞来灵得很的灭鼠药,把这屋子里的鼠类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记得光光拿来毒老鼠的药叫作“三步倒”,吃了药的老鼠是再也回不到洞府里去的。我刚住进来的时候,这屋里的老鼠就很猖獗,人在桌前吃东西,它们就敢出来在墙角的畚箕里翻腾。曾经有一只彪悍的老鼠当着我们的面吃了药,踉跄着像个醉汉,燕子跟在它后面数着“一、二、三”,它就真的嘴角流血倒地呜呼哀哉了。
除了老鼠药,光光还弄来了蟑螂药,看上去像麦乳精,燕子好奇地问他,这药叫啥名儿?
叫小强死光光。
说着话他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起来。惹得一旁的小强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骚脚虾!
小强本姓章,章小强最恨别人把他和蟑螂联系起来。
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礼拜了吧。我忽然想起两句诗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原是描写春景的,可我觉得用在秋日里更好。细雨一场接一场地降下来,闲花一茬接一茬地落下去。我认为所有花中,只有菊花配得上这个“闲”字。我不禁又想到了菊乡,想到了小强家,小强家菊花盛开的小院,小院后的埠头,埠头下的清水,清水里悠闲的呆虾……
其实,现在还有点早。要等到这一轮雨水过去,才是菊的花季。可那又如何,难道还会有人邀我去赏菊,还有地方办菊花节吗?
正想到这儿,我的思绪被敲门声打断了。是谁会在午夜时分来敲我这孤零零的单身宿舍的门呢?而且这么执拗,“咚咚咚”的敲击声均匀而顽固。可是我并不想起来去开门看个究竟,我想再敲几下,那人就会离去的。管他是谁呢,总不会是小强、燕子或者光光吧。
不要小看了常武大厦里的服务员和保安,其实里面的许多人都很有脚力。若是论起家境来,燕子、光光都远远优于小强。燕子的母亲是副乡长,光光的父亲是镇里的主办会计。燕子家,我们没去过——没来得及或是没缘去。光光家,我们去过了,大得可以住进一个排的人,远看像一个古代欧洲的迷你型城堡。要说门当户对,燕子和光光更般配些。但燕子偏偏爱上了小强,小强又帮着光光……占了她。在他们身上,我还是不肯使用“强奸”这样肮脏的字眼。
“咚咚咚、咚咚咚”……
谁?怎么这么不识趣呢?FFBD8AE9-2850-4CAB-9371-1A560A96E423
我想单从破陋的外表,不知情的陌生人是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样的房子里居然还住着人的。由此推断,敲了这么久的,一定是位熟人了。可是,已经很久没有熟人来了。这样的天,这样的时段,这样的敲门法,真是活见鬼了。
那敲门的人既然不肯罢手,我不得不下床开门。
门口站着的却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人。通红的脸、贼亮的眼,湿漉漉的头发粘在额头上。我估摸着她身上敞着怀的象牙色对襟毛衣都可以拧出水来了。猛然间,我瞥见她鼓鼓囊囊的左胸上绣着一朵我非常眼熟的金菊。这件绣着金菊的毛衣是小强妈妈给他织的,怎么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身上?我不禁问道,你是谁?要干什么?
同时,我疑惑且不乏警惕的目光向她身后探去。
刚下汽车,发烧,口渴得不行,要些水喝。
要水喝?
我的双眼更加疑惑而且警惕地向她身后稍远处搜寻。果然,在这女人身后的弄堂口还立着一个男人。他一见我发现了他,便转身飞快地跑去。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小强,章小强。
我一边叫着一边追了出去。
追出弄堂,一直追到十字路口。空荡荡的大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只看到一个昏昏欲睡的治安岗亭。
等我猛然醒悟,折回來去寻那个女子时,也早没影了。
我放在桌上的桶装方便面、矿泉水统统不见了。
小强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这女子是谁?他为什么要躲着我?难道仅仅是为了那笔钱?
我正不安地蜷缩在一张椅子上百思不得其解,猛然瞥见有两三只老鼠又钻出来,在屋角的畚箕里翻腾,就顺手摸出一粒玻璃弹珠投了过去,不偏不斜地打在其中一只的大肚子上,它竟然还回过头来瞪我,黑幽幽的小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让我不禁想起了……
光光,你这个狡诈的强奸犯。
勃然大怒的我捞起一把弹珠狠狠砸了过去,砸得它们“吱吱”叫着分头逃窜。
六
一晃就是几年过去了。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常武大厦、长途汽车站……统统因为修地铁站而被拆除了。地铁站旁弄了一个小花坛,可里面没有菊花。小花坛的位置大致在我过去的宿舍门前,小强曾经想在那儿围个院子种菊花的。
虽然我常常想起菊花,想起小强、燕子、光光,但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只是我的心不能像这座城市拆除那些建筑一般将他们干干净净地彻底抹去。
每当我想念小强、燕子、光光的时候,我就会诅咒那该死的化工厂。这些年,一直有人不停地上访告它,但它后台硬,倒霉的小老百姓根本奈何不了它。它反而越做越大了。该死的化工厂的程总居然名利双收,他不仅成了全市知名的企业家,而且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花小钱,撒花露水,沽名钓誉,这些套路他们耍起来得心应手。前些日子,他又给本市的抗癌互援会捐了十万元人民币。电视、报纸又在不遗余力地大吹特吹。一看到那人那张春风得意而又俗不可耐的肥脸,就会让我想起小强的母亲,想起她临终前那张犹如枯萎的白菊的脸,疼痛就会再次掠过心头,好像我在替这城市犯着心绞痛。
假如没有网络,没有好事的网友,我或许再也不会知悉小强的任何消息了。
发达的网络传来小强的消息,这个消息却在我的心上划了又长又深的一刀。
网上疯传一个帖子,标题触目惊心:一个艾滋病人的疯狂报复。
一开始,我是怀揣着猎奇的心情点开它的,万万没想到此事的主角竟然是章小强。
说实话,此时的小强就算是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未必能认出他来。他的一头自来卷已变成了一窝秋草,脸上是一种颠覆性的古铜色,又硬又糙,颧骨高高顶起来,仿佛就要顶破皮肤了,两眼中闪烁着焦虑不安,不安的眼神中还透露着无奈和仇恨。整个人就像是烧了大半截的摩尔烟。若不是文字中载明他就是菊乡的章小强,我是真的认不出他来的。
他终于出事了。有人说他是个品行恶劣的瘾君子,为了买毒品纠集了其他几个人去敲诈那个姓程的老板。也有人说他们本是一伙无依无靠的农民工,是去讨薪的。但主角都是小强,而且众口一词地说他是艾滋病患者。
他们拦住了那个姓程的老板,也就是那个官二代富一代和所谓的明星企业家、青年慈善家的程总要钱。小强是闹得最凶的一个。杀鸡给猴看,小强被慈善家狠狠地批了两记大嘴巴子。
重重的两记耳光,打得小强满嘴都是血。
我想可能就是这两记耳光,引爆了瘦弱的小强内心的仇恨,他咆哮着,我有艾滋病,我怕谁?
他扑上去就咬,用沾着鲜血的牙在大慈善家的手臂、脸颊上胡乱地咬,咬破了好几处。
也许小强真的疯了,咬完姓程的、咬拉架的,逮一个咬一个,他要让这些人统统感染上艾滋病。
慈善家和他的手下要么被吓疯了,要么被气疯了,七八条肥壮的大汉围着小强拳打脚踢……
小强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
一开始网友们讨论的兴奋点还在慈善家等人的行为是不是正当防卫。也许他们是防卫过当致人死亡,也许他们就是谋杀,谁知道呢?此事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法律是准绳,可法律还有那么多的空白……
有人跟帖说,打死一条疯狗而已。
有人跟帖说,拍个蟑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也有人模棱两可,社会渣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网友还人肉出了小强的妻子,那个穿着胸口绣了一朵金菊的毛衣,曾经在那个雨夜敲开了我宿舍门的打工妹,一脸的麻木和茫然。难道小强还能指望她来维权?
果不然,没过多久,人们就不再关心事件的性质,他们的兴奋点又转移到程副市长的儿子程总有没有感染上艾滋病这一点上去了。
人喜隐于菊,菊难道也喜隐于人吗?我常做一个奇特的梦,一只蜜蜂扑在一朵大大的菊花上不停地采呀采,采得让我生出一嘴苦味来。我想起远在青海的故乡的人们传唱着的“花儿”中有这么一句,“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呀”。我想代死去的小强吼给燕子听,可谁知燕子在哪儿呢?
责任编辑 乌尼德FFBD8AE9-2850-4CAB-9371-1A560A96E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