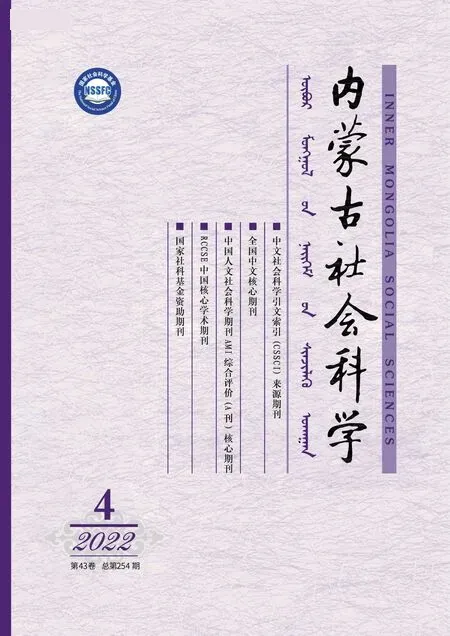自然美的疗愈价值
——由森林疗养的美学缺失谈起
王 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一、森林疗养的美学缺失与历史传统
2006年,日本正式提出“森林疗养”的概念,虽然目前学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的称谓,但涵义基本一致,即指“利用特定森林环境和林产品,在森林中开展森林休息、森林散步等活动,实现增进身心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目标的替代治疗方法”[1](P.7)。韩国每年参加森林疗养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5;美国目前人均收入的 1/8 用于森林疗养,年接待游客约 20亿人次。[2]近年来,森林疗养事业亦得到我国政府的大力推行。2019年3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2年建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300处,到2035年建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1200处[3],这预示着森林疗养的相关研究将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作为森林疗养研究的第一人,李卿博士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森林在增强抗癌免疫力、降低血压、降低压力激素水平、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提高副交感神经活动、预防抑郁症、改善精神性疲劳等方面的疗效,并创建了森林医学这一跨学科的新型学科。2018年,李卿博士的《森林浴》成为欧美地区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3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
然而,目前主流的森林疗养研究仅局限于从林学与医学的角度考察自然环境对人类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疗愈作用,忽略了疗养作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美学基础。“美学之父”鲍姆加通用来称呼美学的Aesthetic,并不是拉丁语中现成的词汇,而是从希腊语aithesis翻译过来的。拉丁语中与aithesis相近的词是sensus。为什么鲍姆加通不用sensus,而要生造一个Aesthetic呢?因为aithesis拥有sensus所不具备的涵义,即与心灵相关的内在感性。[4](PP.280~285)主流的森林疗养研究仅从科学理性的层面揭示了森林的疗愈价值,而将心灵层面的美学分析遗漏在研究视野之外。这种研究思路固然为森林疗愈提供了科学依据,是对自然疗愈价值的重要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将人的本质生物化的倾向,忽略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生物存在的灵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胡友峰所说,“生态学对于生态世界观的建构所起的作用,要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实现”[5],同样地,森林疗养若要对人产生整体性的疗愈作用,亦要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实现。主流森林疗养研究存在的以上局限逐渐被学界所认识。自2018年开始,西方学界对森林疗养的研究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关注心灵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利福德(M.Amos Clifford)《森林浴指南:体验自然的疗愈力量》一书。克利福德在书中特别提到通过静坐培养加深与动植物世界关系的意识。[6]这说明,西方的森林疗养研究已逐渐认识到,以森林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不仅能够通过负离子、植物杀菌素实现疗愈,而且能够通过心灵召唤的方式,即自然美的方式重塑人的认知与情感,产生疗愈作用。
作为自然环境中的疗愈实践,森林疗养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都喜欢在山林间游历,尤其是在遭受了仕途失意等人生挫败之后,往往会选择远游或归隐山林。他们之所以选择归隐山林,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康健,更多的是为了心灵的舒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消解内心的痛苦。谢灵运在目睹了政治黑暗和家族衰落、经历了官场失意和人生浮沉之后,内心悲郁,于是纵游山水,不得志的烦恼得以平复。李白不得重用,壮志难酬,于是离开长安,开始优游山林,大自然的辽阔使他的心胸更加开阔,重新焕发生命的激情。柳宗元因政治改革惨遭失败被贬永州司马后,又遭受母亲的病故,心情苦闷惆怅,于是他常去郊外远足,观赏秀丽山水,心中烦闷得以排遣。在中国数量庞大的山水作品中,屡屡可见大自然对文人痛苦心灵的慰藉。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感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赞叹“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李一韩《季春偕友宿宝林寺》亦唏嘘“寺僻禅心定,林深幻梦清”。孙立群指出,古代士人喜欢游历山林的缘由“或因为厌烦了都市的喧嚣和名僵利锁的束缚;或为了排遣心头的郁闷而希望走向大自然,获得一分安闲与自在,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调整,心理得到平衡,养怡性情,陶冶情操”[7](P.187),道出了自然美具有帮助人们弥补功利世界的匮乏感、获得精神补偿的功用。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隐士群体亦是自然美疗愈价值的发现者,正如萧萐父所指出的,中国的隐士们形成了与庙堂文化并立或相对峙的山林文化传统。[8](P.164)虽然隐居的缘由各有不同,“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后汉书·逸民列传》),但从本质上而言,都是源于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失望或厌倦。他们从社会生活中抽身而退,进入山林田园,乃是为了寻求更舒适的人生。
到大自然中寻求更舒适的人生,在英国的浪漫主义和美国的超验主义等西方文人群体那里亦能找到大量例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人梭罗。梭罗深感邻人们“静静过着绝望的生活”,依循一种历史的惯性,终日忙碌却对生命的意义和乐趣毫无觉知,再加上他自己接连在爱情、亲情、身体、事业以及声誉上遭受沉重打击[9](PP.38~53),于是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独居。梭罗将他的瓦尔登之旅视作一场生命实验,目的在于跟随大自然的指引,探索出一条优于现有主流生存模式的新道路。梭罗在大自然的伟力中获得了生命的启示和心灵的抚慰,两年后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命实验是对其内心深处不满社会、渴慕自然的一种生存回应,而这种回应也成为一种神秘且神圣的象征,持续召唤着后来的人们。一对美国夫妇来到加拿大的丛林中生存,并将他们写下的书命名为《家在丛林:过梭罗的生活》;现代女作家安妮·拉巴斯蒂尔在美国的黑熊湖畔独居,她将自己称为“第二个梭罗”,并将自己的生活记录结集为《林中女人》。可见,涌向自然深处寻求新生的人们络绎不绝。
无论是当下森林疗养活动的盛行,还是历史上自然美疗愈实践的悠久传统,都说明自然美治愈精神痛苦的疗效具有普遍意义。从古至今,尽管有大量在大自然中寻求慰藉的生命实践,但自然美为何能产生疗愈效果却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和充分阐发。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对自然美的疗愈价值进行揭示,以期充实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自然美对功利价值观的调整
在《瓦尔登湖》的首篇“经济篇”中,梭罗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苦难进行描述。他说,“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10](P.2),却品尝不到生命的美果。现代人仿佛总是处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与烦恼中,为虚拟的生存压力、非必需的物质享受、无止境的与他人的攀比,终日忙碌、操劳、卑微地生活着,而产生这些痛苦的根源则在于人的欲望。为欲望所困并非只是现代人的时代病。人类从自身知性的觉醒开始,就一直被欲望的痛苦所纠缠。《庄子》中有混沌开七窍而死的寓言,《圣经》中亦有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中西方早期的历史元典似乎为人类受难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共通的解释,那就是人类在有了知性以及由知性衍生的欲望之后,结束了最初与自然混融一体的“幸福”。
源于知性与欲望的觉醒和发展,人类迅速地与其他自然物种区别开来,成为最高级的物种,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缔造了叹为观止的社会文明。但与此同时,人类也饱受欲望的折磨。故而,对人类文明进程持悲观态度的思想家大有人在,老子把人类历史的展开描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世界从完善走向动乱,人心由安顺走向迷乱。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社会走的也是“下坡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青铜时代,最后到黑铁时代,人类生活得越来越痛苦,恶行越来越多。奥地利心理学教授洛伦茨写下的《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被认为“是一部公认的悲歌,它的目的是敦促人类来忏悔、改过”[11](前言P.1)。总之,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强劲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幸福的遗落史,与欢呼人类进步的主流文明观点形成鲜明反差。
在知性与欲望的支配下,人类逐渐形成一种信奉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2](P.56)。工具理性的行动模式受功利动机驱动,以达到预期目的为导向,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注重行为的结果而非行为的过程。工具理性以“有用性的物”的观念尺度把握世界,“有用”才是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因为“有用”意味着对他人期待的满足。施彭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尖锐地讽刺了人类文明的功利思维。他说:“文明本身成了一台机器,它的作为符合机器、或愿意符合机器的方式。看到瀑布时,人们无不联想电力;无论在何地,一见众多吃草的牧群,就会想到利用其供食用的肉。”[13](P.206)在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看来,人的精神性与情感性并不重要,人只是一种工具化的物,需要接受有用性的评判。有用性高,则价值高;有用性低,则价值低,于是人与人在社会中形成了高低贵贱的价值差别。当自己的有用性不被社会认可时,便会产生功利的匮乏感,引发精神的痛苦。在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自己不被社会认可,通常会产生对社会的失望与厌倦。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移情,将目光转向大自然,希望通过与大自然的交往,重新获得在社会交往中失去的价值感。
古今中外的自然疗愈实践证明,大自然中确实蕴含着完善人性、抚慰人心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大力量就是宇宙精神,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命名。道家称之为“道”、超验主义者称之为“超灵”、有神论者或泛神论者称之为“神”。自然美就是宇宙精神的显现,能够启发人类将功利人生观改造为审美人生观,从而实现对欲望之苦的超越。对于道家而言,道是宇宙的本源与终极存在,显示出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差别。《庄子·秋水》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物观之”就是以人类社会的功利性价值标准(如利益、成就、名望等)看待世界,并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功利,成为“贵”的胜利者;一旦事与愿违,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胜出,就会产生挫败感,即使因侥幸胜出而感到快乐,这种快乐也是一种无常且慌乱的快乐,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对功利之物的确定性,人总是难以逃脱因功利匮乏而导致的痛苦。大自然作为远离人类功利文明的存在,能够为饱受欲望鞭打的我们提供一种“以道观之”的视角。“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大自然并没有偏爱某一个个体,万物的存在都是自然而然、不分贵贱的,再不起眼的植物也能在自然的怀抱中灿然自若。宇宙万物在终极的本体层面都是平等的。道的境界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审美体验,而非需要不断确证我贵他贱的紧张与较量。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亦揭示了自然之道与功利思维的冲突。大自然的存在并非为人类的功利幸福而设计,人只是诸多自然物种当中的一种,大自然中存在那么多的自然灾难和足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的危险,所以大自然的法则并不遵循人类功利的法则。因此,功利的幸福是不容易实现的,更难以恒定地拥有。这启示人类不应以对功利的追求作为人生的意义,更不应因功利的不可得而烦恼。大自然作为远离人类功利文明的原初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类似庄子所说的“以道观之”的视角。对自然美的领悟,有助于人们远离对功利幸福的急切渴望和盲目追逐,从高低贵贱的功利较量中解放出来,接纳自我的功利缺失,达到疗愈的效果。
超验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向往大自然,是因为他们在大自然中体悟到了一种宇宙精神,即超灵的存在。大自然是超灵的外衣,宇宙精神充溢在自然万象之中。超验主义的创立者爱默生说:“一切自然事实都是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界的每一种外表都和一种心灵状态相呼应。”[14](P.232)在超验主义看来,自然绝不仅仅是物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的主体,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对自然之美的感受就是对宇宙精神的领悟。梭罗也坚信,对功利主义时代病的救治需要到自然中寻求答案。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与自然的原生态交往不仅是用感官感受自然的现象,更是用心灵与自然背后的超灵对话。当梭罗与自然的超灵息息相通时,他发现了宇宙更高级的秩序和规律, 那就是拒绝奢侈的简单、躲避喧嚣的安宁、净化邪欲的纯洁、远离庸俗的崇高。正是遵循了这些大自然启蔽的生存法则,让他在林中生活感受到“诸神的宠爱”,“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10](P.144),体验到在世俗功利世界中从未有过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人类是自然之子,但人类越成长,知性与欲望越膨胀,就越脱离自然母亲的怀抱。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5](P.128)诚如其言,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对自然生存的背离史。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受到与自然分离和被社会异化的痛苦。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对自然本性的异化就越深重,对自然本性的怀念也就越深切。海德格尔称这种被异化的处境为“非本真存在”,认为人的存在具有“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两种状态,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人都是处于“非本真存在”的状态。“非本真存在”即自我的异化,表现为“被他人化”和“被他物化”。“被他人化”指自我因他人而异化,即“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他身上把存在拿去了”[16](P.155)。自我为了适应“常人”居多的世界,出于安全的考虑,循规蹈矩地信从“常人”定下的日常生活方式,麻木地由作为多数人的他者决定自己的命运。“被他物化”指自我因他物而异化。自我在与他物打交道时,“一切订造看来都被引入计算性思维之中”[17](PP.1143~1144),热衷于将一切外物都纳入自己功利使用的范围,不自觉地把自己与他物混合起来,将人的价值、尊严、自由都交予它,造成自我的迷失。于是,在双重的异化中,自我遗忘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堕入沉沦、异化、庸碌的状态。诚如海德格尔所言,“非本真存在”乃是文明人的常态,自我常被他人左右、被他物役使,自我虽然能够在“常人”价值观的掩护下获得心理安全,但这样的心理安全是非常短暂且脆弱的,因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无法安顿,总在“常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自我本真渴求的撕扯中痛苦挣扎。但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人具有克服文明困境的超越性,只要世人觉醒,顺应内心本性,就能够摆脱欲望、他物、“常人”、工具理性对自我的遮蔽,回归到本真存在的状态,重觅遗失的诗意栖居的生存本质。大自然则为世人的觉醒提供了最重要的场域,因为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造物主的旨意和世界的原初样态,是本真生存的“无蔽”与“澄明”。与大自然建立审美关系,有助于人们克服被异化的痛苦,返回本真生存,获得自我与母体融为一体的归属感。
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分析了志趣高雅的文士们为何会向往大自然。他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俗世尘嚣如绳索般束缚着自我,让人心累,大自然则能让这些绳索松绑,使人自在。所以,梭罗才会选择到大自然中探求本真生存的状态,以恢复生命中的爱与活力。梭罗明确交代了来到瓦尔登的目的,“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10](P.79)。这一切都显示出梭罗寄望大自然反思非本真生存的努力,而他也在返回本真的生命实践中重觅生命乐土。
正如黑格尔所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8](P.147)对自然美的感知与体悟就是一场心灵的洗礼。“森林浴”所洗涤的并不只是疲惫的身体,还有被欲望之尘蒙蔽的心灵。自然美有助于唤醒远离初心的人们,启发人们将对世界的功利认知模式调整为审美体验模式,进入到对宇宙精神的领悟中,赢获与本真存在的切近,拯救被异化了的自身,做回“是其所应是”的自己。
三、自然美疗愈的限度与意义
自然美是宇宙精神在大自然中的显现,它有助于启发世人将功利人生观改造为审美人生观,回到本真生存的状态,实现对欲望之苦与异化之困的超越。宇宙精神是世界的终极力量,是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一种超验力量。对于“超验”,爱默生指出,“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绝对必要的形式并不来自于经验,相反,人们则是通过它们获得了经验,它们是心灵本身的直觉,康德称之为‘超验的形式’”[19](P.87)。“超验”作为哲学概念源于康德,超验超越经验、超越感官,依赖于人的直觉。这意味着,对作为超验力量的宇宙精神的认知并非源于理性的考察,而是通过直觉从心灵直接涌出。对自然美的领悟就是一个由感官过渡到心灵、由有限达致无限、由经验升华为超验的过程,这也正是自然美产生疗愈作用的过程。
杜夫海纳为我们理解这一点提供了相对深刻的解释。他著作中的“自然”存在着“Nature”和“nature”大小写的区别:“Nature”指“隐含在自然与人之下的最终生成力”,是“产生一种能够照亮自身的意识的根源,代表着那个在基础层次上将人与世界连在一起的先验的先验”;“nature”指“有机和无机现象的总体”。[20](PP.xxxix~xxxvii)换言之,后者意味着自然物,而前者意味着自然力。杜夫海纳所说的“Nature”与道家所言的“道”、超验主义所言的“超验”、有神论或泛神论的“神”所指向的是一个共同的本质,即宇宙精神,它是大自然与人的共同的根源,是自然万物的终极超验存在。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宇宙精神并不现身,却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自己,通过自然界各种现象层面的美,诸如斗转星移、水流潺潺、春华秋实、光影明灭等向我们言说。因而,与大自然拥有共同生存根基的我们也能够通过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领悟宇宙精神的启示和慰藉。
彭峰解释了为何自然的审美对象比人造的审美对象更能显示人的情感特质,“原因在于人在根本上属于自然”,而自然就是“人及其世界所共有的先验或存在”。[21](P.226)诚如其所言,在人造美的世界中,人更多地感受到的只是人类构造的意义世界,而在自然美的世界之中,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进入到内在终极本质的深度,从宇宙精神中获得莫大的情感抚慰。
故而,我们说自然美疗愈的核心意义在于超越,“超越世俗生活的种种障碍和自然深处的大精神进行交流与沟通;超越科学与理性对人精神与情感的局限,直接沉浸于自然深处的神秘与静力之中”[22](P.17)。就这一点而言,自然美与宗教有着共通之处。宗教的意义亦在于超越,超越俗世痛苦,超越科学理性,进入全善全能的神的怀抱。正因为自然美以超验为向度的超越性存在,所以大自然在美学层面的心灵治疗功效无法通过科学实验得以证明,这正如上帝、灵魂、天国等超验存在无法在现象界得以验证一样。然而,自然美却有其显著的疗愈效果,这已在古今中外的生命实践中得到证明。
虽然自然美具有强大的疗愈价值,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然性生存无法代替人的社会性生存成为现代人的主流生活方式。因此,梭罗即便如此热爱自然,也只在林中居住了两年多就选择离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其自然生存实验的结束。中国古代因仕途受挫而选择归隐山林的文人,他们在归隐后虽然能舒缓苦闷、重获逍遥,但逍遥中总有无法彻底克服的悲郁。故而,如此钟情自然的谢灵运在其《临终诗》中写下“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成为无法彻底抚平仕途失意之痛的最后叹息。这也说明,自然对痛苦的疗愈是有限度的。人类虽然是自然之子,但也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一方面,人与自然是同一的,是自在的,具有自然本性;另一方面,人又有与自然相异的一面,是自为的,具有人为性。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地用自为性改造自在性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可能将主流生活模式彻底切换到自然性生存。
其实,到大自然中旅行也好,疗养也罢,对于早已远离自然生存的现代人而言,只能是主流生活方式的补充,是一种暂时的生活选择。在美国,有一种叫作Retreat的活动特别盛行,人们通常是到大自然中放松身心,做一些在忙碌机械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做的活动,比如疗养、结识新友、改变某种生活习惯等等,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焦虑的城市生活。Retreat的意思是后退,意味着人类在一往无前的发展进程中的暂时撤退。对于现代人而言,撤退能够平衡这个远离自然的功利世界,反思欲望和社会对人身心的多重异化,回顾自身。显然,暂时撤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因为自然虽是人类的起点,但并非人类的终点。正如我们探究先验是为了经验的牵挂,探究灵魂是为了肉身的牵挂,探究自然是为了人类本身的牵挂。自然美具有疗愈价值,并非意味着大自然乃是人类的理想归宿,而是意味着大自然作为本源性的美的存在,能够召唤人类通过价值观的调整,达致更理想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