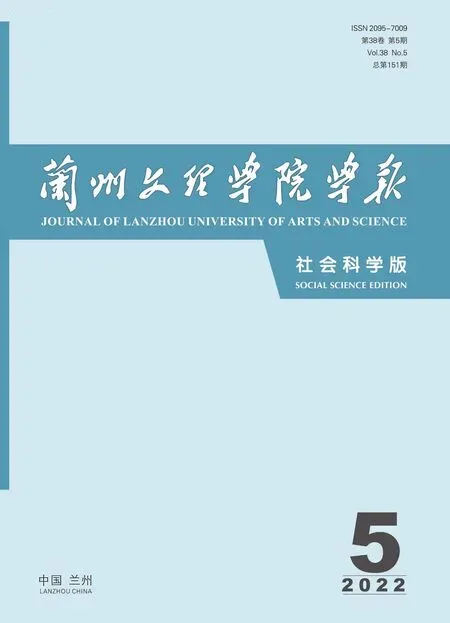由活化石到活历史
——读杨富学著《霞浦摩尼教研究》
刘拉毛卓玛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著名摩尼教研究专家杨富学先生所著《霞浦摩尼教研究》(以下简称杨著)于2020年11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继《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之后杨富学教授推出的第二部摩尼教研究专著。先前出版的《回鹘摩尼教研究》以回鹘语摩尼教写本、吐鲁番出土回鹘摩尼教壁画为基本资料,结合汉文、波斯文文献的相关记载,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摩尼教在回鹘的发展情况,内容丰富,论证周密,在回鹘学、摩尼教研究领域多有拓荒之举,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1]。与之相比,最近刊出的《霞浦摩尼教研究》一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会昌法难之后传入闽浙地区摩尼教的发展变化,是杨先生研究摩尼教入华发展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
公元3世纪源于波斯的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于唐代武则天时代东传入中国,8世纪后半叶借助回鹘的力量,盛极一时,影响及于漠北、西域以及唐朝腹心地区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及至843年会昌灭法,摩尼教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几近灭顶,余部隐遁闽地民间,以“明教”的面貌出现[2]。2008年,福建霞浦、屏南、福清等地相继发现的大批摩尼教文献、文物与古遗址表明,宋以降至清中叶,闽浙尚有摩尼教信仰的痕迹留存,成为波斯摩尼教在中国遗存的活化石。相较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文献,霞浦和屏南摩尼教文书所展现出的摩尼教面貌却大相径庭,即传入闽浙的摩尼教视时空位置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朝着民间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转变,一改历史上以依托佛教为主的态度,更多地依托道教,而民间宗教色彩亦极为浓厚,充分体现了摩尼教在闽浙地方化的特色。杨著即以霞浦、屏南出土摩尼教文书为抓手,回顾了学界十多年来关于霞浦文书的研究历程,对霞浦、晋江、屏南、福清等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尤为重要的是,将目前所知的六件特别重要的霞浦摩尼教文书全部进行校录刊布,以便于学人今后的研究,功莫大焉。用著名摩尼教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马小鹤先生的话说:“《霞浦摩尼教研究》的出版,正是霞浦(包括屏南)文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与下一阶段的开始。”[3]诚不为虚言。
一、霞浦摩尼教文书之刊布
摩尼教的盛行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宗教的关注始终不曾停息过,但作为宗教,却久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文献的发现无疑可为重新认识摩尼教教义、仪轨及发展轨迹提供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历来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和西方摩尼教资料对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及其在中亚、新疆以及中原地区的传播史做过不少发覆钩沉的工作。2008年以来发现的大批霞浦文书足以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文献相比肩。霞浦文书面世十余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仅有屈指可数的研究者有缘得识其真面目,加上这些摩尼教科仪书抄本至今还在民间继续使用,出于个人收藏与发表授权等问题所囿,其“照片不能如敦煌、吐鲁番文献那般结集图版公之于众,只能仰仗持有文献的专家学者之录文,公刊一件是一件”[4]。这样的处境导致今天的研究成果虽众,但多为对个别文献、个别问题、个别词汇的专题性研究,由于文献掌握不全,导致标点断句多有错讹之处,极易出现断章取义的问题。职是之故,一个较为完善的霞浦摩尼教文录校底本是摩尼教研究所必需的基本资料,也是重中之重。
霞浦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数量众多,有的已经为学界所知,有的尚深藏闺阁,至今搜集整理到的主要有《摩尼光佛》《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奏申牒疏科册》《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祷雨疏奏申牒状式》《高广文》《借锡杖文》《借珠文》《付锡杖偈》《吉祥道场申函牒》《吉祥道场门书》《门迎科苑》《送佛文》《摩尼施食秘法》《缴凭请秩表》《求雨秘诀》及多种《无名科文》等。鉴于《摩尼光佛》[5]《乐山堂神记》[6]与《明门初传请本师》[7]等三件文书业已刊布,杨著则选取内容比较重要的六件霞浦(屏南)摩尼教文书《祷雨疏》《冥福请佛文》《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奏申牒疏科册》和《贞明开正文科》作了录文和详细校勘、注释。看似简单的基础工作,却是筑牢摩尼教研究这座大厦的基石。
二、林瞪教主身份新辨
自2008年霞浦文书现世以来,林瞪与霞浦摩尼教之关系日益成为摩尼教学界的热门话题。陈进国和林鋆[8]、林悟殊[9]、马小鹤[10]、杨富学[11]等诸位先生曾先后撰文对林瞪之身份和地位作过专门的论述。然对于杨文《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所论证的“林瞪为霞浦摩尼教教主”一说,林悟殊颇有异议,认为“北宋明教依托道教,盖被统治者目为道门之一宗,而林瞪生前严格修持明教,死后显灵,统治者自以道门神号封之,而乡民则目为道教神仙、地方大神膜拜之,并非将林瞪奉为明教之神”。同时,林先生又批评杨文仅以《乐山堂神记》中的某些名号为据推论其教主地位,而并未举证任何可资征信的资料[9]123。针对林悟殊先生的批评,新刊杨著列出专章《再论林瞪之霞浦摩尼教教主地位》(与盖佳择合撰)予以回应,以霞浦、屏南、福清、温州苍南等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和摩尼教造像为依据,结合闽浙地区存留的活态摩尼教信仰,就林瞪之教主地位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此文或可解林悟殊先生之疑。
杨著首先根据霞浦《孙氏族谱》和《林氏族谱》等宗谱中关于林瞪的记载,对林瞪之生平及其获封缘由作了梳理,指出林瞪师承孙绵大师,孙绵大师故去后,林瞪承孙绵大师之志,重振乐山堂,广开法系,乐山堂成为上万村村民集会场所,霞浦明教经典从本堂而传至民间。其仙逝后,“果满功成”,先后被朝廷加封,获“兴福真人”“洞天都雷使”“贞明内院立正真君”等称号。然,这显然与《八世祖瞪公赞》云公“自入明教后若无所表见”[8]247,348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当亦与明教遭禁相关”:瞪公生前与明教相关的事迹乡民都讳莫如深,而特强调其为“道士”受皇封[4]139。林瞪获封入圣,其妻陈氏之身份随之被抬高,信徒通过“拉郎配”,竟称瞪妻为闾山派教主、八闽尊崇的五代闽国顺懿夫人陈靖姑,以便符合林瞪之教主身份。
霞浦、屏南、柘荣三地文书中对林瞪的称号每每涉及“灵相”“度师”等字眼,如《奏申碟疏科册》中称“本坛灵相度师、四九真人”(第258行),《乐山堂神记》称“本坛明门都统威显灵相、感应兴福雷使真君、济南法主四九真人”(第11行),《明门初传请本师》中则有一长一短两号,分别为“都统威显灵相、度师四九真人”(第19行),“本坛祖师明门统御威显灵相、洞天兴福雷使真君、济南四九真人”(第25-26行)。其中,“灵相”本为佛语,指佛之庄严妙相,如沈约《释迦文佛像铭》:“仰寻灵相,法言攸吐。”[12]玄奘《大唐西域记·憍赏弥国》亦谓:“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鄔陀衍那王之所作也。灵相间起,神光时照。”[13]摩尼教先借以指代教主摩尼,如敦煌本S. 3969《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形相仪第二》记载:“摩尼光佛顶圆十二光王胜相,体备大明,无量秘义……诸有灵相,百千胜妙,寔难备陈。”[14]及至明清时期,摩尼教科仪文书又将“灵相”之称冠于林瞪,庶几可认为此时林瞪和摩尼一样已经具有了教主身份。另,“度师”为“道教三师之一,《上清三尊谱录》:第一度师玄真明道君,即元始上皇丈人也,第二度师无上玄老,即高上九天太上真皇也,第三度师真人,即兆应现在度师,而金明七真是矣。乃先天三宝至真也”[15]。是故,“度师”则等同于道教之“真君”,为道教神祇的品位尊称。此外,在闽浙地区的一些师巫宗教中有“传度师”之称,指传法授徒之辈,作为已经鲜明民间宗教化了的摩尼教,称其初传法者至尊教主、本坛师尊为“度师”亦不为过。另案,严格来说,在道教中度师、籍师并非师承关系,故个别专家质疑孙绵并无“籍师”身份故林瞪亦不当称“度师”[16],其说也就不成立了。由是亦说明,闽浙之摩尼教实乃“一种杂糅了佛教、道教、摩尼教及闽浙当地师巫信仰为一体的综合体,《贞明开正文科》赞林瞪为‘通天三教’教主,可谓恰如其分”[14]144~145。
林瞪生前身份并不显赫,影响仅及于闽东一带,仙逝后,林瞪信仰遍及福建及浙南。关于其崇拜也不仅仅止于纸面和口耳,霞浦、屏南、福州、晋江等地更供有大量林瞪绘画与雕塑。综观林瞪形象,文武兼备而以文身形象为主流,与其“度师”身份相合,武身形象则与其“雷使真君”“威显灵相”的降魔者身份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福州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所供之“度师真人”像,经杨富学先生踏查、研究,确定为林瞪本人。该像与晋江五境宫之两种“都天灵相”形象恰相对应,由此可证,“都天灵相”与“度师真人”实为一神之二名,即同指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林瞪改造了摩尼教,借用道教斋醮科仪,以雷法或师巫之法充实了闽地摩尼教,使波斯摩尼教脱夷而华化,真正创立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深度华化的明门教派,故而被称为本坛教主或本师教主,成为科仪文书必请之神[4]157~158。
三、霞浦摩尼教之道化和民间化倾向
杨著对摩尼教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综合各类文献和田野调查结果论述摩尼教之华化问题,尤其是其道化和民间化特征。以往,学界多关注摩尼教的佛教化问题,但对摩尼教的道化和民间化问题研究相对薄弱,囿于资料所限,对摩尼教的民间化倾向更是鲜有人提及。其实,关于霞浦摩尼教的华化问题,杨先生在2016年出版的《回鹘摩尼教研究》之第十章《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及相关问题》中,即已明确指出:“会昌灭法后传入福建的摩尼教,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佛教、道教相融合,也吸收了大量民间信仰的内容,同时也展现出了一个由佛化逐渐转向道化的过程。”[2]231~246只是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进行论述,在新著中,杨先生通过比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摩尼教写本经典与霞浦文书,考释霞浦文书中出现的神祇名号、宗教术语及科仪仪轨,结合福寿宫中的摩尼教神祇,深入探讨了摩尼教在闽浙地区的发展变化特征,揭橥了霞浦摩尼教佛教化、道教化、民间化的倾向轨迹及最终形成中国本土摩尼教多元化的宗教特质。
吾人固知,摩尼教以明显融合各大宗教文化而著称于世,从波斯古国到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浙地区,在数世纪的嬗变过程中,其形态在“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个被浓缩了的基本教义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华文化精神生活土壤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沙畹、伯希和氏所云:“真正之摩尼教,质言之,大摩尼自外来传布之教,已灭于八四三年之敕,尚存者为已改之摩尼教,华化之摩尼教耳。”[17]通观霞浦文书,既包含闽地传统宗教的痕迹,也接续很多经典摩尼教的母题,将异国神明与乡土神灵、家族先人崇拜糅合,形成了一个中外兼蓄、教俗交融的法事范本,充分体现了摩尼教在闽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特征,生动展示了古代东西方宗教文化的深入交流,是摩尼教华化稀见而典型的范例。
霞浦文书所见“三清”观是霞浦摩尼教道化的典型例证。《奏申牒疏科册》《祷雨疏奏申牒状式》二文书中共有四份《奏三清》。“三清”本为道教概念,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等三位最高神明的合称,而上述二文书所奏告的对象却均为“再苏活命夷数和佛(广明上天夷数和佛)”“神通降幅电光王佛(灵明大王电光王佛)”和“太上教主摩尼光佛”(太上真天摩尼光佛)。“太上”“真天”“教主”是道教的专有名词,将其冠于摩尼教三位主神称谓首端,表明霞浦摩尼教在道教的外衣掩护下积极发展和宣传自身宗教教义,体现出明显的道化倾向。然而,霞浦摩尼教之道化只是借其外衣而已,尽管使用了道教三清观念,却冠以“佛”的称谓,指的却是摩尼光佛、电光王佛和夷数和佛,皆为摩尼教神祇;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摩尼教经典相比较而言,霞浦摩尼教道化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新增了不少神祇,且多数源自道教。如《乐山堂神记》所记神谱中,道教神祇占比远高于佛教,其中所列有北方镇天真武菩萨、九天贞明大圣、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天教主张大真人、三衙教主灵宝天尊、敕封护国太后元君、感应兴福雷使真君及贞明法院三十六员天将和七十二大吏兵等等。诸如此类关于摩尼教道化的例证在书中多有涉及,在此不一一赘述。
杨著还指出霞浦摩尼教在吸收众多的道教元素之余,民间信仰成分亦显著加深,这既是摩尼教在霞浦民间化的表现,也是摩尼教在霞浦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呈现出霞浦摩尼教的独特个性。其民间化倾向的表现如道化现象一般,首先表现在对地方民间信仰神祇的融摄。书中所列之福寿宫诸神中即有福建地区流行的地方神祇,如临水夫人、华光大帝马天君和黄、赵二大王等。作为霞浦摩尼教科仪书之一的《点灯七层科册》,也有大量的民间信仰元素,其奉请的神祇中有很多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祭祀的神仙,如飞腾玉铃使者、终户群支使者、坎母造化将军、吹涛神女、运水将军、搬柴力士等等。霞浦摩尼教科册本身便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化和世俗化特征,其内容多关乎国泰民安、稳固政权、治病除疫、祈雨求晴、生儿育女之类。如此种种,民间化倾向非常明显。
杨著利用霞浦文书对摩尼教道化及民间化的研究,说明道化和民间化倾向是摩尼教在华发展史上真实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并非偶然现象。同时,使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更直观、更具体的认识,而不仅仅停留在以往的简单概念上。
四、结语
综上,此书为一部全面研究霞浦摩尼教的力作。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18]杨富学先生在学术上素以“三新”(新资料、新问题、新观点)为秉持,通读《霞浦摩尼教研究》一书,不难看出,全书在充分运用各类文献资料的同时,结合实地调研之结果对霞浦摩尼教之发展变化进行论证,其资料新、观点新、视角新,对诸多旧说给出了新解,对诸多新问题给出了新答案,令人耳目一新。霞浦文书被称作世界摩尼教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活化石,藉由《霞浦摩尼教研究》一书,这些活化石再现了千余年来摩尼教在东方传播的历史,使长期被历史尘埃湮没的摩尼教历史活了起来,至为难能可贵。可以认为,该书是自霞浦文书现世十余年来,从宏观到微观,对霞浦摩尼教文献、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相关历史文化内容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研究著作,在世界摩尼教研究史上当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