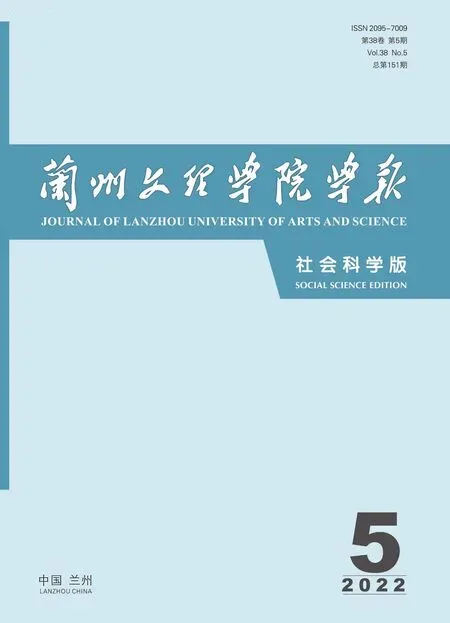触寻生命的沟壑
——评王小忠《洮河源笔记》
王 玥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洮河源笔记》是作家王小忠继《黄河源笔记》后的又一部力作,凝聚了作者在洮河岸边生存多年的真切思考,以充沛的情感和一种质朴亲切的表达方式,生成了一种极具情感穿透力的文学魅力。作为一个在甘肃甘南地区生活多年的作家,王小忠在故土中沉淀,也在现代文化与农牧文明的碰撞与发酵中奔走,书写甘南生命之源上的动人故事。当洮河流淌于这片沃土之时,它以或柔或刚的力度使得土地侵蚀或沉积,在时间的沉淀下形成了纵横的沟壑。正是沟壑起伏处,作者通过自己的目睹与耳闻,施以咀嚼与思考,记录下洮河源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生命的浮浮沉沉,或明或暗。
一、“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
阅读《洮河源笔记》,能感受到作者文笔的质朴平实、流畅简净。作者多用散句,在不夸张、不造作、不张扬的文字中,有着丝丝入扣的讲述,更有着他对于生活与生命的真挚思考。无疑,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王小忠是本雅明笔下那个“讲故事的人”。在《洮河源笔记》的8篇散文中,作者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过往的记忆以及作为教师、作为行人、亦或是作为驻村干部的所见所闻以或直接叙述或间接叙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既有身边亲近之人,亦有远行之人,更有扎根于洮河而生长于此的人们。
王小忠以他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他以“我”或听者的身份、角度来讲述故事,记录他的体察或疑虑,表达了他对生活介入的思考与深度,既达到了一种叙事的“间离”效果,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触动力。全书中多次出现一些场域,如“茶屋”“酒馆”以及“露天阳台”,甚至“蔬菜大棚”也成为作者倾听故事的有效空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故作世故与深沉,并不仰视故事的主人公,他始终拥有一种倾听的姿态。在这些故事被讲述的空间里,作者化身为一个听故事的人,把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集合起来,再成为“讲故事的人”。
《光阴下》讲述了16年前的“我”分配了工作后所发生的部分事情,记录了一个异乡人的故事。“我”曾经目睹陈兵与他女儿的故事,后来又作为离场者间接了解到陈兵的变化。陈兵与女人的纠葛,与女儿的隔阂,最后开酒吧、开洗脚店,却非法经营,试图经由“我”来解决麻烦,时隔多年“我”意识到“我”与他的感情已被耗尽。这是一个在光阴下迷失的人,读来令人感喟不已。《洮河石花鱼》是一个带有悲恸感与创伤性的故事,叙述了胡广义曾作为洮河林业局护林员,后失业回老家养石花鱼的故事,并穿插了两个儿子胡潮生、胡海生的经历。“就在那个局促而破败的茶屋里,胡海生说着他父亲胡广义的往事。我半信半疑,但还是深陷其中了。”[1]其间充满了生活的琐碎与挣扎,胡广义对孩子去“要名誉”的怒叱,和想要在当年的鱼塘之地上修房的朴素心愿却受到阻隔的叙述等更暗含着“我”对乡村的伦理遭到破坏以后的怆然。
《坡上人家》中给“我”讲述有才一家故事的“他”是有才一家人的邻居,与有才一家有着共同的引洮工程下整村搬迁的经历,并目睹了有才一家的悲剧性走向。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情感不断起伏,但仍有面对新生活的信心与坚定。这些故事展示了生活在洮河中游峡谷里的人们的困顿。“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这不仅包括自己经历的人生,还包含不少他人的经验,讲故事者道听途说都据为己有”[2]。王小忠正是以一个个故事让读者触摸了以洮河为源的个体生命的自我表达。
如果只是沉湎于一个个故事的铺陈,将会丧失文体的边界与美感。但在王小忠的叙述里,故事并不单调,富含各种质素,有着整体性的考虑与经营,将它们酝酿为具有甘南风味的故事。作者之所以能将人情物理、风俗和历史等灵活嵌入文中,还要倚赖“远行”的方式,正如本雅明所强调的“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2]106,文章中的“我”大多时间都是一个“漫游者”、一个“远行人”的形象。这种书写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游记体”散文相似,文中许多内容的记叙都发生在行移、旅途之中,并含有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大量描绘。洮河流域的自然风光、鲜美的石花鱼、洮河盛产的青稞酒、喇嘛崖老坑里那珍贵洮砚石、洮河沿岸的三海龙王的地方信仰、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所赋予其神秘与神圣的则岔石林、存留了多处文物古迹的二郎山以及拥有玉女祠的岷山等一系列元素,使故事的纹理中富有地域的光彩与自然山川的气息,散文在洮河的围裹中氤氲着光阴的水汽。
作者的行踪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推进。“远行”能够有效拉近与表现对象的距离,王小忠在移动的视角中用双脚丈量大地,体验感知所见所闻,然后诉诸笔端,予以呈现。《大棚蔬菜》是一篇极其靠近生活本质的文章,“我”走到了洮河中游的卓尼县一带,在纳浪闲逛,最后在路边一位老人的蔬菜摊前歇息下来,老人邀请“我”去现摘新鲜蔬菜,她的老伴儿安才让来到了洮河边的蔬菜大棚里,安才让老人给我讲起十几年前种庄稼的事情,“安才让给我说这些,就像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1]103。当地人如何尝试种植不同的作物、农业合作社政策等,还提起他的两个女儿的现状。当“我”想返回县城却没能遇到车时,安才让又挽留“我”,留宿一晚,才更进一步得知他们承包大棚的难处。《洮河源笔记》写“我”途径多处,抵达青海河南县寻找洮河源的故事。从出永靖县城到龙汇山看到看洮河与黄河的入汇,转至对洮河渊薮的追叙;又行至藏巴哇,与铁匠朋友叙旧,探寻九甸峡水库,从卓尼县辗转岷县,连带讲述了考察队的故事,后赶到了扎古录镇所在地——麻路村。经过碌曲县红科,到达赛尔龙乡不远处的洮河源湿地公园,一窥西倾山的雄伟全貌,最后到达洮河源头所在地——代富桑草原,在奔跑中意识到自己对于家园的疏远。洮河源头那奔流不息的河水,涤荡着作者那颗因奔波而疲惫了的心。正是作者在行走之中,丰富的内容与情感便生发出来。但与当下盛行的游记散文所不同的是,“小忠的文字早已褪去了猎奇与炫酷的成分,行文中处处可见虔敬与真诚之心”[3]。正是这样不浮躁不飘忽的“远行”下叙写的故事,才具有及物的意义。
二、“故事里有故事”
《洮河源笔记》是充盈的,更是厚重的,原因就在于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故事里有故事”[1]56,作者运用一种串珠式的故事结构方式,把层叠着的故事勾连出来。
《风过车巴河》讲“我”在麻路的故事,第一节是苏奴栋智给“我”讲的一个小裁缝尕豆草的故事;第二部分讲了一个小酒馆和捡破烂的人卖“祸首”的故事;第三节是偶遇苏奴栋智,他带“我”到台球室里去讲述台球室晚上的秘密:想要在台球室胖老板的榻榻米上过夜,必须喝够四十八瓶啤酒;第四部分主要叙述了看守水磨房的太太保和他与养母之间的关系;第五节讲“我”寻找人群,试图融入麻路的努力;第六节去扎古录镇采买物资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叫班地亚的人,“我”对电影的描述“引诱”了他,“我”却因此差点没命,落笔至麻路不为外部的“风”所撼动的固有的宁静与自足。文内故事与故事之间前后相勾连,相互衔接,环环相扣,既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小单元,亦可连为一个整体,构成组合式的故事。这种结构模式类似于东方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的结构方式,即连环穿插式的故事结构。
但王小忠讲述故事的方式与连环穿插式的故事结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刻意使用这种结构——上一个故事的结尾成为下一个故事的开端,并且故事的过渡也并非是在逻辑上极其严密的首尾相连的故事链条。在王小忠的散文中,篇内故事与故事的间距并不明显,时而有一些跳跃式的讲述,有时则刻意延宕重要的情节,例如在《洮河石花鱼》中,第三节里,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才提起胡广义想要在老家建房的困难来源于那个养石花鱼的水池的位置,以及胡潮生所做的种种努力未能见效,甚至还涉及老村支书的推诿。《三条河流》中由于大雪封锁住了车巴沟,“我”在寂寥中看到车巴河而想到三条河流,故事的主人公扎西在第一部分中被提起,第二部分故事才闪回到“我”想要去则岔石林而并不是牧村贡去乎,“我”与扎西的交集在此处安置后,进一步追问“我”对扎西研究生毕业后,不愿走出贡去乎这个牧村的原因;第四部分又回到“我”走进则岔石林,以及石林与格萨尔王的关系;最后聚焦到扎西的藏家客栈,以及藏家乐对于牧区产业结构转变的推动。故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与空白,作者有意对篇内的结构进行折叠,把一个故事单元骤停,折叠进另一个故事单元。但作者的故事并非单纯的嵌套,毫无章法的罗列,是按照故事本身所拥有的内在逻辑来展开的。有的以情感逻辑为线索,有的则以时间或地点为线索舒展开来。经由这样的结构方式,散文便拥有了独特的叙述节奏,连绵不绝却又不显得累赘、冗长,而是鱼贯而入、错落有致,内容具有纵横交错的网状形态。
不仅是在篇章之内,每篇与每篇之间也暗含着联系。此集以《洮河源笔记》为同名集,诸多故事铺陈过后,最后才是此篇,文集中的各篇散文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散-聚”式的结构模式。正如每篇故事中涉及到的河流车巴河、热乌河、则岔河以及多拉河等都是洮河的支流一样,那些河流最后终于汇入洮河,又随着洮河汇入黄河。一个个真实的坐标被点亮,那些以河流为生存源泉所发生的故事,也被以这种流动的方式组织了起来。
作者以动态的轨迹去描绘洮河岸边人民的人生百态,这些故事的展开往往又拥有一个历时的变化,从而此书便拥有了横纵式的发展脉络,例如:“我的足迹曾遍布卓尼县的几乎每一寸土地,这次又沿洮河行走,其间,相隔七八年,卓尼县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卓尼县了。”[1]97蕴涵着对于往事的回忆,对于记忆的打捞恰恰钩沉出这个空间对于个人成长的意义。集中多次出现时间的闪回,现实场景与回忆之间稍纵即逝的对比,纵深的情感就在二者的映照下表达了出来,现实情境又形成了独特的特写镜头,带来了极强的纵深感。
上述结构方式是王小忠对散文艺术的有力坚持与探索。嵌套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走向以及动态视角的使用等,使得散文的时态、节奏等方面处理得较为和谐。这种故事结构方式,使得作者没有固步自封于传统散文的写作秩序,给读者以阅读挑战,真正做到了以散文作为触碰复杂人生的中介。
三、注入矛盾性思考与深沉情感的生命叙事
集中的故事都是落地的,因为所有的故事,最终都落脚至作为故事载体的“人”,立足至每个生命前行的轨迹之上。“讲故事不像消息和报道一样着眼于传达事情的精华。它把世态人情沉浸于讲故事者的生活,以求把这些内容从他身上释放出来。”[2]103洮河岸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纹理形成了洮河地区人文风貌的实质性坐标,只有把视角聚焦到眼前之人、眼下之事时,才能凸显人的主体脉络。
王小忠深知人的一生不是扁平的、光滑的。洮河岸边的生命呈现各种样态,时而起起伏伏,时而平稳顺畅,有的人一生像是深渊,充满着跌宕起伏,而有的人一生就像小溪一样平稳流淌着,只有部分弯曲。作者以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去触碰生命的各色形态,勾勒出他们的一生中的沟沟壑壑,做到了触及生命的内部。《祥云》中对于母亲的追叙有着试图拨开母亲身上“云雾”的尝试。皈依后的母亲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我们所理解,她仿佛自愿戴上了形式的枷锁,母亲所坚持的信仰,她所坚信的“祥云”,正是她对儿子们的爱意以及试图超脱于现实生活,追求内心安宁的体现。王小忠不遗余力地挖掘生存于洮河流域的普通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境遇。《坡上人家》中在有才与哥哥有福以及老母亲的无奈处境和遭到命运的强势压迫中,写出了个体的生活里潜藏的苟且、荒谬与幻灭等一系列质素,使他的书写真正触及人的内部、暗影处,对于当地人们现实生存境况的沉溺式描写以及生存个体的的细腻刻画,构成了作者散文中最核心的精神意蕴与生命叙事。
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洮河两畔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文明变迁也被纳入。其中,作者不仅仅只是关心故事本身的引人入胜,故事发生的载体也不仅仅只有人,而是在历经多年变化之中的人与土地的动态的走向。在关于出走与返乡、游牧与农耕、乡邻与家庭等关系的状写中对乡村伦理、人物境遇等做了细腻且深沉的描画,作者以带有理智思忖的口吻,却在这种口吻的暗部饱含深切的情感,他以一个既在故土的深处生长着的人的视角,又以一个生活在故乡的远方的人的视角,传达出对于洮河流域人民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又时而不理解,甚至是完全不理解的状态。
王小忠在悼念中发出了自己的疑惑:对于母亲,对于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思考,和对这种存在于洮河中游一带的传统习惯的质疑;胡广义想要通过返回农村落叶归根的方式回归到曾经美好的岁月记忆中的艰难,这种没有彻底进城也做不到彻底遗忘农村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对于现实社会变迁的映照;作者路过以“农家乐”闻名的卓尼县木耳镇的一个自然村力赛,却并没有走进,原因在于作者看清了“农家乐”的目的性,拒绝这种伪饰的真诚和怀旧。随即作者又生发出对于乡村旅游的看法,这其实是对当地文明变迁的思考:利益的角逐虽然会带来收益,但有时就在无形中侵蚀了乡村的稳定性,使得乡村原有的种植业渐渐萎缩。政府大力扶持农民自主创业,农民集体经济经营规模也在日益壮大,看似繁荣的局面下却有着盲目性。文中对于想要不劳而获、不愿付出的年轻一代的讨论,是对老一辈人勤劳、能吃苦的品质的推崇;“我”的铁匠朋友在传统农业形态改变下失业,成为过时的匠人;洮州地域的民俗节日也渐渐失去了红火,唱花儿的人也在迪斯科风靡之时愈来愈少……“和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一边疏远,又一边不断靠近”[1]199。正是在矛盾的思考中作者终于醒悟,始终追寻河流、保持内心的坚守。
在触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时,位居散文集书写轴心的是作者真切且深潜着的情感与人文关怀,这种情感的表达是绵密却又节制的。对散文而言,“感情”更是其精神血脉,王小忠正是将真挚的情感契入文字之中,定格那些充盈着强烈情感的瞬间。《祥云》一篇内对于母亲生前事迹的追叙,带有强烈的感情驱动力,这种深沉的情感内蕴让人不禁想起李商隐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与韩愈的《寄十二郎文》,在回忆中对于母亲的深切怀念打动人心。集中多处都体现着作者对于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们的惦念与关怀,如《大棚蔬菜》中安才让老人想要小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我一边洗脸,一边在脑海中搜索亲戚朋友里的未婚青年,同时也提醒自己,这件事一定要放在心底”[1]113。《三条河流》中对于扎西父亲那一代牧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接受新理念的理解,也是一种真切的体恤。情感的积淀成为对人的最深沉的关怀,成为作品最大的魅力。
洮河是王小忠的创作之源,更是他进行文学思考的原点之一,对于这片流域下的土地与生命的触寻激活了他的文字表达与想象,关于河流、土地与人们的各种印象和记忆以丰盈的文学表达呈现出来,各种故事的联结正如洮河之水一般缠绵与滔泊。作者寓深刻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感于丰富的故事表述,避免单薄的单角度叙述,而是力求在整体性思考中整理自己在出行时的踪迹与见闻,多角度地描写出洮河流域生活的多种面貌和所经历的文明变迁,洮河流域的古老历史与文明传说、过去与当下的对比、人事与自然风物的错综便融合成为一个动态的生命整体,王小忠正是在触摸与探寻生命的轮廓中生发出对于土地的热爱与生命的追寻,在洮河的流淌中抵达生存的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