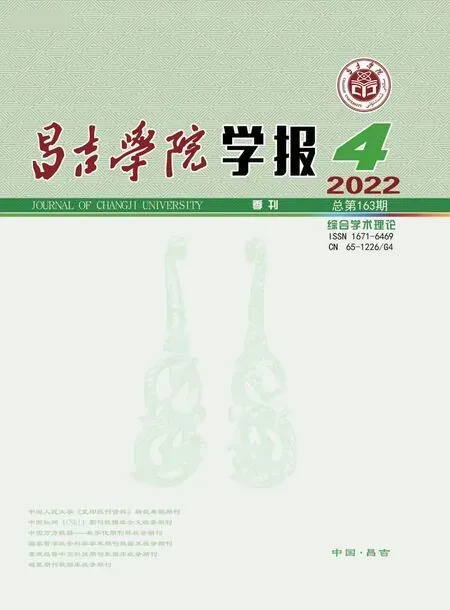典型论意义的城市勾描
——论巴尔扎克对王安忆城市写作的影响
皮 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3205)
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文学思潮,西方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追求本色创作的王安忆,从登上文坛伊始就显示出对现实主义的崇尚,在她为我们讲述的城市或乡村故事中,“真实性”成为了其演绎作品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她在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展示中所呈现出的认识论意义上客观真实的表达,与西方现实主义的科学真实观更是不谋而合。王安忆曾称自己从小是“吞书长大的”,青年时期对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阅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滋养,而其中巴尔扎克对她的影响尤为明显,他那种对都市空间手术刀一般精准的描摹及城市想象背后对其精神内核的把握,深深地影响了王安忆对上海都市的勾描。
作为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特别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呈现。于他而言,人始终是其作品表现的核心,他们不仅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更是具有时代性和概括性的典型人物。然而“在典型里,是两个极端——普遍和特殊——的有机融和底成功,”[1]所以,即便是具有普遍性的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其笔下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他们都是作家塑造的守财奴形象,也都极端的吝啬并有着无限的贪欲,但二者之间还是各有不同。高布赛克是《高利贷者》中的主人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产物,他靠原始积累来获得财富,对金钱的占有欲极强,吝啬得出奇,也贪婪得恶心。与之相较,葛朗台则不尽相同,同为守财奴的他明显带有资本主义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点,极度贪婪地占有财富的同时,他还表现出善于理财的特征。巴尔扎克不仅注重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更重视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人类作为生命个体是无法分割于环境之外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塑造形象,他在创作中对典型环境予以了细致入微的表现。
在他的作品中,承载着其重要生命体验的巴黎便是作家为我们展示得最多的典型环境。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成长在法国历史上最复杂、社会关系极为动荡的时代,在拿破仑发动的多次战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身经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的他在目睹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同时,对整个法国特别是巴黎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间喜剧》就是展示其对这个“众生趋之若鹜之地”深切感悟的作品。在这部共96篇的著作中,巴尔扎克将巴黎作为典型环境分散在“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部分内容中进行描写,这个充满邪恶、荒唐和奇迹的城市,人们还不曾“叙述过它的生活经历、道出过它的思想,解释过它的黄金或泥土的幻梦”[2],而他却细致描绘了这个满是诱惑的花花世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具有自我认知经验的都市空间。
出于对巴黎都市环境的真实再现,巴尔扎克对这座城市的景象做了全方位的展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向文明过渡的重要标志,19世纪巴黎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造就了法兰西历史的辉煌。“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3]此时的巴黎,已经由那个中世纪的都城变成了一座充满光怪陆离色彩且暗藏着奥秘、玄机的现代都市,这里有豪华的府邸、精美的沙龙;有破旧的公寓、嘈杂的剧场,对这个奢华与贫苦的交织地,巴尔扎克由外及里的对它的都市景观展开了描述。《高老头》中,在“蒙马特和蒙鲁吉这两个高地中间”,跟随着拉斯蒂涅的视线,我们看到了寒酸贫穷的小街陋巷、酸腐破败的伏盖公寓;也看到了富丽堂皇的官邸、漂亮精致的别墅,这些共同构成了巴黎这座城市的外部景象,通过对这些建筑物外观的描写,夹杂着贫穷和富贵的现实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在外部环境的映衬下,作家还对不同阶层人们所居住的内部环境展开了描写。比如伏盖公寓,作为穷人和失意者的住所,死寂的街道、干燥的石板、长草的墙根等让它看上去极为衰败萧瑟,在这个毫无生机且充斥着阴森、冷漠的建筑物里,有的只是酸腐味十足的餐厅、破烂不堪的客厅及各种腐朽、残缺的家什,这里四处弥漫着贫穷,一群落魄、卑微的底层人栖身于此。除了对这些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贫民生活环境的描写外,巴尔扎克还对贵族们生活的府邸进行了描摹,那些带着花园的公馆里,大客厅的宽敞明亮和各种器物的金碧辉煌共同成就了这里超凡脱俗、自命不凡的贵族气派,显现着奢华的光景。作家将当时巴黎的都市景象一一铺陈开来,通过对各个阶层典型生活环境由外及里的描写,再现了这座城市的全貌。
巴尔扎克这种从典型论的角度对都市图景的勾描,刷新了人们对巴黎的认知与想象,也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城市书写提供了范本。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就表现出对他的借鉴。一直以来,王安忆都在用细密的文字为我们编织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在《雨,沙沙沙》《归去来兮》《庸常之辈》《流逝》《长恨歌》《妹头》等作品中,作家对其印象中的上海做了全方位的展示,尤其是《长恨歌》,她更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俯瞰上海,以王琦瑶的人生经历来串联整个城市的风云变幻,通过对各种景象的描写及场景的再现,直接刷新了人们对上海的记忆与念想,将这座城市的“声”与“色”呈现在了大众面前。这部作品在国内外备受读者的关注和学界的青睐,特别是其勾描城市的方式,不少论者就其与巴尔扎克对巴黎的展现进行过比较。罗岗的《城市里的每个细节都蕴含意义》一文,着重对比了《长恨歌》和《高老头》两部作品,指出二者在对城市做宏观巨论式描写上是极为相似的;李欧梵、张旭东等海外评论家也对照分析了巴尔扎克与王安忆笔下巴黎和上海的异同。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有着如巴尔扎克般对典型环境的反复渲染,凭借着自己的都市经验,她一次次着力描写了“花园洋房”“弄堂”“棚户区”等上海城市景观,穿越浩瀚的历史时空,我们从中都能感受到有如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般豪华的府邸、破败的公寓、肮脏的赌馆闪现的影子。
和巴尔扎克一样,王安忆也注重对上海城市景观的描摹,在她对这一典型环境的塑造中,弄堂“作为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4]是被呈现得最多的,一条条弄堂组成了如背景般存在的石库门民居,它是上海肌体里最鲜活的存在,更是作家“个人记忆”的重要承载。在《一千零一弄》中,作家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民的居所予以了展现,这里的弄堂由形形色色的本地房子组成,中间一条石子路将其隔成两边,房号为单数的在路的北面,房号为双数的在路的南面,其中“二十七号是爿小而又小的烟纸店,没有名字;二十九号是爿微乎其微的酒店,名字倒响亮,叫个‘茂梁财’;六十八号隔壁是公共厕所,厕所隔壁是垃圾箱,垃圾箱隔壁是泔脚缸,泔脚缸隔壁是九十号。过去,再过去,一百零一号是老虎灶。”[5]这些就是弄堂里的景象,它将时代的更迭和市民日常生活裹挟在一起,再现了当时上海的都市场景。在这些弄堂里,有着各式的烟纸店、皮匠摊、裁缝铺,街上开动着的无轨电车、店铺前来来往往的顾客、趁着空闲出来交头接耳的保姆和那些叫卖桂花粥的梆子声以及夹了油烟、潜水气味的风交杂在一起,这些场景和人事便是上海最实在的景象,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早已化成各色光影渗透到了声色各异的弄堂中。在工人们的集中区与富人们的集结地弄堂各具特色,有带着深宅大院遗传着官邸脸面的石库门弄堂,有防范严密的公寓弄堂,有做出站脚的阳台的新式里弄,还有墙面透风、屋顶漏雨的棚户杂弄,王安忆有意识的按照身份差异对其进行了区分,着力展示着它们的斑驳形态。
除了从宏观的角度描写城市的外部环境外,作家还对内部生活空间进行了微观展现。《归去来兮》中的富家千金真真原来居住在淮海路的花园洋房区,这里每幢房子前都有花园,围墙上也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从外观上就透露着富贵的气息,走进它的内部空间我们发现,整幢房子都由贴墙布装饰过,里面打了蜡的地板和吊灯、真皮沙发、各式家具、冰箱、彩电等器物更把它的奢华衬托得一览无遗。《妹头》中的妹头住在淮海路的一条弄堂里,这里有着红砖的墙面、高高的台阶、石砌的圆拱门,算得上是正宗的洋房,走进妹头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西洋款式的沙发和五斗橱及各式麻织质地且流苏装饰的床罩、窗帘、桌布等,无不显露出华丽和温馨。从外到内,王安忆细致勾描着上海的都市景象,始终突显着巴尔扎克式的风情。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生活空间,更是他们的精神皈依,“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揉进城市的冰冷的石头之中,使城市成为人类欲望、文化的物质符号,城与人,构成了相辅相依的紧密关系。”[6]所以,无论城市有多么的繁华亦或处变不惊,生活于其中的人才是它的主体和都市精神的承载。对于作家而言,他们会因对城市的熟稔而将自己最感官的体验付诸于文字,但想象城市的背后更多地却是对城市精神的发掘。巴尔扎克对巴黎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799年,他出生在法国中部图尔城的一个中产者家庭,1819年来到巴黎,之后一直定居于此。作为现代化进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发散的中心,巴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雄厚的财富权利散发着巨大的魅力,来到这的巴尔扎克在感受它所带来的巨大魔力的同时,更渴望能真正融入其中,被这座城市所接纳。但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这里所展现出来的美好是非常有限的,和其他城市相比,这个国家的首都和艺术中心看上去极为繁华,并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可贫穷与富贵相对立、繁荣与糜烂共生存的社会现实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腐败的本性,金钱万能、利益至上的生存法则让生活于此的人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这个城市的外来者,巴尔扎克和它之间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面对它的“不堪”,他想要逃离,可“巴黎是一条巨大的章鱼,伸出千千万万魔爪把远远近近的一切东西抓到它的掌心。”[7]作家无法完全融入又无力断然离开,而这已注定他只能成为这座城市精神上的征服者和描绘者。
作为一个巴黎人眼中的“他者”,巴尔扎克试图接受它的改造并融入这个城市,可这种无法改变的距离感使他很难完全逾越。但庆幸的是,相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作家而言,外来者的身份反而更能让他从巴黎与外省、城市与乡村相对立的体悟中获得对这个城市的感知,站在一个“他者”的角度,透过对城市典型环境的表现来发掘其背后蕴含的都市精神反而也更深刻。巴黎是一座在资本主义迅速扩张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建立起了“金钱至上”的社会准则,在巴尔扎克描写的巴黎图景中,人们在“金钱轴心”的驱使下丑态百出。《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是法国索漠城最富有的商人,他精明能干,会敛财也会生财,但他却嗜钱如命、无比吝啬,每天的蜡烛都得亲自分发;《高老头》中的高里奥靠在大革命时代囤积面粉发了财,他很疼爱自己的两个女儿,但女儿们却在父亲有钱时对他百般示好,没钱时将其扫地出门;《高利贷者》中的高布赛克以放高利贷的方式敛财,他注视着世间的一切财富,贪婪成性,永远无法满足;《邦斯舅舅》中的邦斯是一个音乐家兼收藏家,去亲戚家讨吃时受尽侮辱,但当发现他收藏的物品价值连城时,人们又开始对他阿谀奉承。这些便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金钱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笼罩在这些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身上,他们无力挣脱,更无处遁逃,这里完全成为了一片沦陷于金钱、欲望之中的“沼泽之地”。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任何城市都有其存在的文化意义,这种意义不仅能通过外在的建筑设施得以体现,还能通过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得以反映。巴尔扎克注目于巴黎城市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着力表现了这个欲望之都人们对金钱的无限追求与热望,当理想的光环被摒弃,当文化的记忆被驱逐,唯一剩下的“金钱万能、利益至上”便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典型的精神特征,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印记。
巴尔扎克精准描摹及想象城市背后把握城市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和巴黎所经历的多次变迁相似,作为租界文化的发源地,上海也曾几度变迁,新的思想观念由此输入,新的事物从这里发轫,与其他城市相比,它更繁华、开放,也更具有现代化的气息。从最初的小渔村到后来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8],上海的发展是迅速的,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不仅后成立租界,不少外国侨民纷纷过来投资,在西方外力的推动下,它逐渐成为了集金融、商贸和航运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中西方商贸的频繁,促进了上海商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促使不少外地人移民至此。自1852年到1949年近百年间,上海人数从54万激增到545万,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地人,曾有一位人口学家说过:“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9]上海的都市化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和大多数外地来沪人员一样,王安忆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2岁左右随父母来到这里,于她而言,上海就好比是巴尔扎克的巴黎,她虽然生活在这个城市,但难免还是会产生一种作为“他者”的身份尴尬。然上海还是不同于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巴黎,这座城市相对年轻,近代以来受频繁战乱及商业发展的影响,它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外地人,没有久远的历史文化积淀能引以为豪,上海对其他的外来文化更容易接受,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无根的“上海人”也更能包容。所以,有着外来者身份的王安忆在此虽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漂泊感,但这个城市本身的人员结构特点注定了她仍然能够以城市文化构成的主体身份自居。没有巴尔扎克想要挣脱、逃离巴黎时的痛苦,也没有他碾碎自己追逐幻梦时的苍凉,有着“他者”身份的王安忆在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里能随心所欲地去畅想和表达。倚凭着自己的上海经验,她细致地描绘着这个城市的外部空间,同时注目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去发掘上海的文化精神。
当然,在这座人员结构较为复杂的现代都市,虽然对外来人员有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但在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骨子里还是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城里人与乡下人相对立的观念,通过对上海市民或外来移民的表现,王安忆实现了对上海都市精神的诠释。《富萍》中的奶奶就是其塑造的移民典型。她从外地来上海一直在淮海路做帮佣,三十年的时光流转,她在这里落了户,已然成为了上海人,对于奶奶老家的人而言,她早已不再是之前的乡下女人,而是一个有身份的上海人;对于奶奶自己而言,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她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已经不同,有一种很强烈的“城市中心居民”的成见,在她看来只有淮海路才能算真正的上海,所以她连苏州河边的老乡都不愿去结交;而对于上海人而言,奶奶最多是乡下、城里各占一半,并不能算真正的城里人。有着移民身份的奶奶其实是急切地想融入上海的,而这也是当时“那一些人”最普遍的心理,他们慢慢贴近这个城市,或许曾身处尴尬的边缘境地,亦或许曾不被理解认同,但一旦他们站稳了脚,就会迅速被上海市民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大批移民的到来为上海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他们也在接受传统市民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同时,成为了上海都市精神的捍卫者和创造者。
在新旧移民的不断交替中,上海这座城市得以不断更新,它的生命力也一次次被激活。作为城市的主体和建设者,面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于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心态随着改变,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他们变得愈发的见多识广、精明能干。《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泼辣能干,最终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野菊花、野菊花》中的年轻工人聪明灵活、善于投机,他将批发市场买回来的布娃娃进行加工倒卖;《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的小妹阿姨干活利落、精明算计,对于利害得失总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些都是王安忆塑造的上海市民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上海市民群体人格的一种体现。其实,王安忆对上海的认识是具有草根性的,她注目的不是其五光十色、声色犬马的浮华,满溢着市民气息的弄堂才是其着力描写的,她为我们呈现的上海是精致且日常的。所以,《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穿着滚边旗袍,一边吃着八珍鸭、水磨元宵,一边和年轻人聚会打发时间;《富萍》中的吕凤仙,细嚼慢咽的吃着白米饭,却还要用金边细瓷碗盛着;《妹头》中的妹头在家里随便做个菜也都精雕细琢、精致至极。可见,和巴尔扎克夹杂着爱恋和恐惧的巴黎书写相比,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流露出的是淡淡的温情,开阔多元的气质、海纳百川的气度铸就了这个城市平实、精细的市民文化精神,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极具人间烟火气息的都市图景。
无论是对城市外部景观的描写,还是对其精神内核的发掘,王安忆都受到了巴尔扎克的影响。他们对典型环境的塑造,对都市精神的表现,让我们获得了对巴黎和上海两座城市最丰富的感受。作为典型论意义上城市勾描的范本,巴尔扎克描写了金钱轴心影响下巴黎社会的风云变幻,不同于巴尔扎克对黑暗现实的暴露和揭示,王安忆更多地表现的是平常人生中的人情和人性。她对现实生活中人们极具生存韧性的人生态度的表现,对高贵、精致生活作风的描画,都是其对上海城市文明的自觉把握,所以,比起巴尔扎克深重的、尖锐的批判,即使面对这个城市的虚伪与不堪,王安忆也更愿意去表达其背后隐匿的平和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