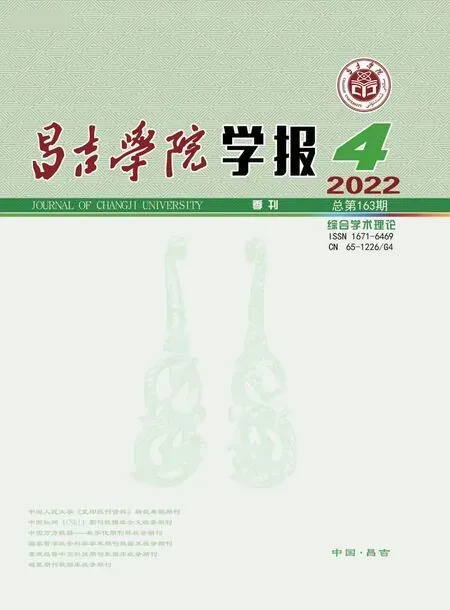当代新疆文学:民族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有机融合
陈一军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00)
一
当代新疆文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凸显不同民族人物之间的相濡以沫、和谐共生。这自然是当代新疆文学创作着意追求和展现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系列国家民族政策得到贯彻实施的结果,由此使得民族关系和谐之美成为当代新疆文学创作的中心审美品格。
当代新疆文学民族间的和谐既表现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又表现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亲善和睦,当然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友善关爱,实际构成友好的多维立体交互网络。在表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方面,有一个醒目的点就是对进疆干部的书写。王蒙《这边风景》中的尹中信是进疆干部的典型。他在新疆“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学习维吾尔语”“衷心地迷恋,执着地追求的是对于维吾尔人民的更多的了解以及赢得信任与友谊”,一心谋求“为维吾尔人民做更多的事”“为民族团结与祖国的统一添砖加瓦”。有了这样纯粹与高尚的情怀,“他的心就像海绵一样,时时吸收维吾尔人的意见、愿望、生活以至语言”,即使工作出现曲折,最终总能克服困难,赢得维吾尔族群众的信任与拥护。[1]同为《这边风景》中的人物,技术员杨辉在伊犁主动接触少数民族,热情而无私地为他们服务。阿拉提·阿斯木《生活万岁》中的中学老师陶家元与上述两位人物相似。从南方来到边疆教书育人的他,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慈父般的爱心,令少数民族学生从他眼睛深处总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光泽”,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这位“真正能称得上是老师的老师”。[2]5-6艾克拜尔·米吉提和叶尔克西的散文也记述了这样的人物,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上述小说作品人物的“原形”。1972年,艾克拜尔·米吉提刚刚从插队的生产队走上公社机关干部岗位,遇到了公社书记吴元生同志,他“人非常好……是浙江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来到伊犁,学会了维吾尔语,虽然开口说起来,他的维吾尔语颇带浙江口音,但听读方面他的维吾尔语水平几乎无可挑剔。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和维吾尔族社员进行沟通,打成一片。”[3]叶尔克西散文《北塔山的记忆》中的马尚志,在边疆“讲得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穿一身哈萨克男人的衣裤……经常和哈萨克牧人一起住在山里,与他们一起转场”。[4]205马尚志还帮助“我”父亲在北塔山牧场建立起了第一所正规的哈萨克族学校。经历种种事件,马尚志成为北塔山的一位传奇人物,深得当地哈萨克人的敬重,为此他们编了好多故事传颂他。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汉族干部进疆投身边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新疆文学自然要着力描写这类人物。文学作品中的他们,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境界高远,总是设身处地,以心换心,视边疆少数民族为亲人,展现出无私的高尚人格和宽厚的仁爱情怀。这其实体现了他们所代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先进性与人民性。这乃是当代新疆文学能够实现民族和谐书写、彰显和谐伦理精神的首要原因。
当然,进疆干部出色的工作也要有群众基础,这实际指向历史铸就的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深厚情谊。这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在草原的蒙蒙雨夜里》得到了异常动人的艺术呈现。当部队严守纪律在草原上宿营时,快活清朗的哈森老爹不干了。他对战士说:“我说孩子们,难道你们能搁着自己的温暖家室不去,非要像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蜷曲在冰冷的库房里过夜吗?”当连长向老人解释时,老人固执地摇摇头,提高嗓门说:“喂,孩子们,你们听见没有,这位同志在说些什么呀,难道这像是一家人所说出来的话吗?难道世界上还有谁家的孩子到了自家门口,却还要呆在外面挨冻的道理么?走吧,孩子们!到家里去。”还说:“哈萨克人的家里没有容纳不了的客人。”[5]370这感人肺腑的场景,实际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友善亲和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生动写照。
因此,在当代新疆文学作品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善亲和往往是相互的。叶尔克西的散文《老梁》讲述北塔山牧场职工食堂当厨师的河南人老梁及他的家人与“我们”一家人的交往。显示了在共同生活场域中具有不同地缘情感和民族习俗的两家人由矛盾对立走向互相帮助、容让、理解、接纳的过程。这分明是两家人超越各自民族界限的“共同体”建构过程。《老坟地》的故事与此有些相似。和“我们”一家同喝小水泉里的水的邻居皮匠老唐,在“我们”的帮助和照应下,和“我们”一样在充满死亡气息的坟地面前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由此“我”对老唐建立了深切的同情,“我们”一家和他的家庭也成为没有隔阂的真正好邻居,从而成就了心连心的“我们”。这里还包括“长眠在老坟地里的人,无论他们是被时光老死的,还是为了一口水死于战火,他们和我们一样也生活过,爱过,恨过”。[4]87这是汉族和新疆少数民族在共享区域生活中达成的彼此深切的认同,时间在这里成为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纽带。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著名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则典型体现了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融通与交好。具体来讲,这篇小说展示了维吾尔人对哈萨克青年的亲爱友善,也在显示一位哈萨克青年作家对维吾尔兄弟民族“真挚的同情和爱心”[6]。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新疆文学作品中,由于有党和国家制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又基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发展、巩固了伟大祖国的历史,共同开发建设了美丽边疆,艺术地表现充满了和谐精神的边疆美好生活世界便焕然可观了。
二
当代新疆文学创作不仅突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还突出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这显示了当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与自然的深度交融,这种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新疆当代民族间的和谐相融。当代新疆文学创作中这种突出的天人合一表达与深刻影响了新疆众多民族的自然崇拜文化有关。
作为远古的自然崇拜的高级形式,萨满教遵循万物有灵论,而万物有灵论属于人类远古时期的普遍认知。它将人是有灵魂的观念推向一切事物,认为植物、动物、棍棒、石头、武器、船、食物、服装、装饰品以及河流、山峰、大地等等事物都具有特殊的灵魂,都有“个性和生命”。[7]389-390萨满教曾经长期兴盛于新疆及北方草原多个民族,在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几乎独占了它们的古老祭坛。具体来讲,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撒拉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民族都曾信仰萨满教。[8]后来,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兴起并成为这些民族的主流信仰,萨满教作为宗教形式便日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萨满文化生命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不仅在北方中国广大国土上刻下了遗痕,更重要的是“深潜在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头脑中”[9]3,还“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文化之中……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7]349。这就是说,万物有灵观念不仅仍然存留在现在新疆众多民族的心中,还构成他们现实文化的重要基础,正是这种文化让当代新疆文学创作表现出天人合一的独特景观。
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的《女巫吉孜特尔娜克》一文讲述了陪伴作者童年生活的女巫吉孜特尔娜克的故事。女巫吉孜特尔娜克当是哈萨克族古老萨满信仰的组成部分,她“住在森林中、旷野中、荒漠上,任何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像一阵风一样在这些地方穿梭自如”,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滴露珠、每一缕晨光,懂得野兽的语言和鸟的歌声。她的丈夫是一个像一棵树一样又瘦又高的高个子男人。吉孜特尔娜克不贪图钱财、不爱慕虚荣、没有权力欲,也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法……[4]182可见,女巫吉孜特尔娜克和大自然息息相通,完全属于自然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艾克拜尔·米吉提笔下的“风”所呈现的特性:当清晨的冷风闯进人的怀里,又顽皮地旋即从人的怀里挣脱出来,“得意地打着唿哨,追赶那个走向苍凉古老的草原深处的人去了”。[5]442显然,“风”在这里同样被赋予灵性,与人的亲昵关系便彰显出来。
叶尔克西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这种灵性书写在当代新疆文学创作中实际具有普遍性。例如,王蒙的《杂色》这样讲:“草是有生命的,山是有生命的,大地是有生命的……”因此世界便有了“不可阻挡的”生命力量[10];而《在伊犁》系列小说中,人与畜生在打麦场上由于共享劳动成果实现了生命的贯通。显然,在新疆长期生活工作的王蒙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疆自然崇拜文化的影响。寓居新疆十年的红柯则同样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一切都因为灵魂的存在而活泼灵动起来,与人类的声息处处沟通。于是,《美丽奴羊》《跃马天山》《大河》等作品中的羊、马、熊等动物便和人类建立了神圣的人兽亲族关系[9]78,彼此精神相往来。至于视万物有灵论为自己创作原则的刘亮程,在小说《凿空》中深情款款关照像人一样有感情、懂进退、知冷暖、会思考、有情谊、能担当的驴子形象,彰显人与驴之间的生命与共。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生活万岁》《好姑娘》等作品则以迷人的诗意方式有效实现了人与阳光、绿叶和树木果实之间的深情爱抚与友好交流。
当代新疆文学的这种泛灵书写不仅表现出人对动物、植物以及其他无生命自然物的深切同情和关爱,还让它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存地位。于是在作品中,人类主体便“怀着尊重与敬畏去感受、体悟与倾听大自然”,与自然之间更多呈现出一种“在保持彼此独立性基础上的‘对话’关系”,自然因此“不再被主体随意拉扯、比附类推,恢复了自身的独立性、自足性”。[11]254结果,动植物等自然物本来拥有的生活习惯和天性便得到有力维护。正因为如此,刘亮程才明确讲:“在我们的文字中,自然也应该是自然本身”。他所著的《一个人的村庄》就在“努力使这些自然之物还原本真”,让“这些自然之物从我们的隐喻系统、象征体系中解救出来,让草木还原到草木中,还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为我们的情感去做隐喻体,做象征体。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欢喜,有自己的风姿,有自己的生命过程”。[12]420显然,这是万物有灵观念的真正贯彻,因为“‘万物有灵’首先意味着主体借助与自然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心灵真实,并把自然作为一个有力的对象来确立”。[11]255
无疑,当代新疆文学这样做的时候,便在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因为它确立了自然的正义,维护了和谐的生态关系,从而有力批判和矫正了现代性的片面性。现代性突出张扬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性,结果招致人类自我的无限膨胀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流行,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这便是刘亮程在《凿空》中借裴教授之口表达的现实:“机械时代的到来,使人和其他动物维系了千万年的依存关系被彻底打破,动物从人的伙伴、帮手、相依为命的朋友,变成单一的人的肉食。机械把前者都替代了,只有后者它无法替代,机器不能吃,驴最终对于人只有肉体意义”。[12]305这样做的结果是地球上自然物种的大量灭绝,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破裂以及深重的生态危机的到来。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当代新疆文学以万物有灵的书写方式批判现代性片面性的同时向人们昭示了“道法自然”的大智慧、大命题,形象生动真切地告诉人们:人与自然是“有血缘上的属性”的[13]。“全人类是兄弟,动物也是我们人类的兄弟。”[14]这即是说,“人类与母性的自然应该和睦相处,对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应平等对待”。[15]既然如此,人与自然之间就不是人对自然单方面的控制、奴役与征服关系,而是破除人之唯我独尊,尊重和敬畏自然,心存善念,与众生灵平等相处,对自然生命葆有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在生态整体主义基础上与之建立平等友爱的交互主体间性关系,通过理解、同情、对话与交流的方式解决两者共同面对的生态问题,一面恢复自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面消除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长久的和谐共存。[16]
三
当代新疆文学中的民族和谐和天人合一总是有机交融在一起的,这种交融使得文学创作本身具有了大爱情怀,一面使人与自然充满了富于情感的对话与欣赏关系,一面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美好温馨之感,从而构筑了一片诗意氤氲的“栖居”之地。
我们还是结合具体创作来论述这一问题。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在当代新疆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一部内涵丰富、风格朴素自然的作品。它在表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伊犁地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状态的时候,为我们呈现了由诗词、歌舞、美丽的大自然以及葆有天性充满爱的人生状态组成的美好世界。其中即使乱中寻乐、苦中作乐的生活样态,也在凸显人性的坚韧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因而伴随的苦涩反而使生活更有诗意,更显生机与活力。其中《虚掩的土屋小院》展示亲爱的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在那个“濯脚渠边听水声,饮茶瓜下爱凉棚,牍牛无赖哞哞里,乳燕多情款款中”[17]的“虚掩的土屋小院”度过的相敬相爱的纯朴生活,那种出门不上锁的古风犹存浸泽着人类美好生活的遗风;漂浮的奶茶和清茶的香味与浓浓的人间温情一起弥漫在阿依穆罕大娘“彻日饮”的悠然闲散的生活姿态中,其中沉淀的凄恻动人的生活质地格外让人动容。这里承载着朴实厚重的美好人情人性人格的内容充实的诗意,和大自然怀抱中虽然艰辛却依然淙淙流淌不止的溪水一样绵长。在这样的表达中,“我”对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深厚的爱便汇聚成潭了。这显然是民族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有机交融的境界,让人充分体味多民族在美好自然烘托中共同生活所呈现出的敞亮的生命真谛。《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鹰谷》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虽以悲剧结尾,但是其中表现的“我”与阿依夏木汗大妈一家亲人般的关系,以及“我”与拥有金色年华的美丽的哈丽黛之间的美好爱情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而当温情的大自然爱抚心爱的人时,那种熨帖便让人无比陶醉了:
“四周静悄悄的,唯有泉眼里的水,在带着大地心底的羡叹汩汩喷涌。层层涟漪却在悄无声息地用它柔软洁净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哈丽黛那被渐渐暗淡下去的晚霞倒映在水面上的模糊身影……”[5]239
这是“我”去挑水时在哈丽黛对面的(水塘边)草坪上坐下时感受到的情形。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因为“我”把情感和灵性给予了泉水、倒影等等物象,的确让一些本无感觉的事物成为真的具有生命实质的事物,以哈萨克民族文化汁液浸泽其中的方式,让“万物有灵”的妩媚在具有“诗和歌的民族”美誉的哈萨克民族作家的笔端舞蹈,并且造成了写实性与象征隐喻的和谐统一而导致的诗化倾向。[18]人所向往的美好生存境界便在一瞬间定格。
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创作与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作品异曲同工。小说《生活万岁》生动描写学生们和他们尊敬的陶老师一起吃饭的动人场面:“我们有说有笑地吃着。果园里的鸟唱着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民歌,热风亲吻着我们的脸庞,美丽的蝴蝶落在女同学的头上,跳着古老的双人舞。几个性情文静的同学沉默地躺在柔软的草坪上,透过桑树叶的空隙望着灿烂的天空。”[2]5这里,充满了灵性的鸟、风、蝴蝶等为“少长咸集”的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快乐融洽歌唱、亲吻和舞蹈,真的就是人间乐园的感觉。弥漫同样的诗意生命感也是中篇小说《好姑娘》突出的特点,在此向往美好纯粹境界的好姑娘和周围高高的白杨树、垂吊着“互相挤在一起亲嘴啃脸”的黑葡萄的葡萄藤、悬着明亮的星星的含苞待放的玫瑰以及“那些虔诚歌唱的候鸟,飞舞的蜻蜓和蝴蝶……”一起构成了扑朔迷离的诗意飞扬的灵性世界,这又因为好姑娘与王古丽兄妹之间凝结的跨越民族界限的美好感情而成为“潜藏着人类精神无止境的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审美冲动”的诗性冲动的显现。[19]
对于红柯的新疆书写来讲,恰如李敬泽所说:“人在大地上诗意地安居……是红柯最深的梦想”,也是他小说“反复弹唱的主题”[20]。的确,在其小说《奔马》《美丽奴羊》《鹰影》《金色的阿尔泰》《库兰》《喀纳斯湖》《乌尔禾》《生命树》等作品中,红柯都在人与自然高度吻合的诗情意境中展示新疆的生命景象,以诗性哲思观照着“人类赖以生息的精神家园”。[21]而沈苇的诗文创作在作者随意游走,亲身感受、理解、拥抱新疆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着意礼赞“各民族各色人种汇而为一”[22]的无比斑斓的和合“生命”场景。
总之,由于着意表现民族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新疆文学深刻揭示了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与大自然之间深厚的关联与情缘,从而将自己的焦点凝聚在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23],达成了诗性圆融的书写,成为新疆多民族历史与现实本质存在的言说。这意味着当代新疆文学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召唤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牢固确立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全面的和谐,永葆新疆的和合之美。显然,这样浸透着人类深厚情感、融注了多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视域宽广的带有浪漫特质的理想书写,对于提升新疆社会文明程度、促进新疆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