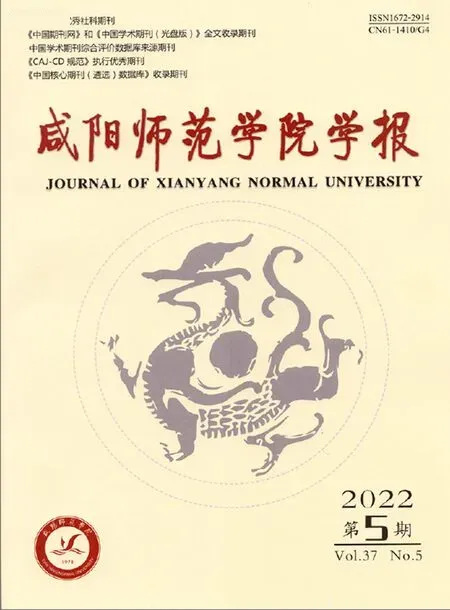论唐代的“行”与城市商业组织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
刘啸虎,陈 淅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多年来,中国行会史研究成果显著,但中外学者对行会产生的时间尚无定论。学界普遍认为,唐代的“行”与后世的行会存在某种关联。研究唐代的“行”,对于探索中国商业组织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唐代的“行”,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唐宋同业商人组织似乎胚胎于同业商店的街区,而作为商人同业组织的“行”是会馆公所之先驱,已经具有行会的一些特征[1]337-355。清水盛光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行会至少始于唐宋时期”[2]。全汉升更是认为“周末至汉代”工商业行会已有存在,其在隋朝凸显并且有了“行”之称[3]21-23。刘永成、赫治清认为“唐宋是行会的形成时期”[4]120-121。彭泽益也明确指出:“至迟在八世纪末(公元780—793年),唐代已有行会组织的雏形存在。”[5]张沛则将唐代诸“行”的性质具体分为行业店铺与同业组织两种,并分析了作为行会的“行”出现的原因与特征[6]。冯兵、黄俊棚进一步指出唐代“行”的肇兴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并研究了唐代“行”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7]。有关唐代的“行”,除了围绕行会的产生问题进行探讨,尚须进一步厘清其具体所指和含义变化,明确其在唐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所以,唐代的“行”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 “行”在“市”下
目前所见有关唐代诸“行”史料,“行”主要应指“市”下的同业店铺集聚区。众所周知,唐代的“市”是商品交易的专门场所,《唐律疏议·名例律》载:“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8]92王仲荦先生指出,在唐代,“邸”相当后世的货栈和批发店;“店”相当后世的商店,经营零售;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称作“肆”[9]382。唐初贾公彦《周礼注疏》释“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以“置其叙”为“谓胥师贾师等所居”,将“正其肆”释作“谓诸行列肆之等”[10]248。在唐人眼中,“市”下不仅存在像“邸”“店”“肆”“行”这样作用不同、规模各异的单位,恐怕还存在“市—行—肆”的金字塔形状等级关系。
具体而言,隋唐时期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是市下的重要单位。隋人杜宝《大业杂记》言洛阳事,“桥南二里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11]6。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亦记洛阳南市,“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12]160。唐代洛阳南市即隋时丰都市,从这两则史料看,“行”作为重要单位,应在“市”之下、“肆”之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条言:“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物烧尽。”[13]172同样说明“行”在“市”之下。《唐会要》更载:“(唐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州县职员令,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查。州县市各令准此。”[14]1583王永兴先生认为这里的“师”即敦煌文书中的“市壁师”,职司在“市”内分“行”检查,而“行”就是对沿着“市”的四“壁”、按行业整齐排列的各“店”“肆”总称[15]。这些都表明,彼时的“行”乃“市”之下、由众多“肆”组成的集聚区。
从唐人韦述《两京新记》中,亦可辨析“行”与“市”“店”“肆”之关系:“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门市齐正,高低如一,环货充积,人物甚盛。时诸行铺竞崇侈麓,至卖菜者亦以龙席借之。……(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识。”[16]9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引“市署前有大衣行”句,下有按语云:“市署前有大衣行,当即此大衣肆也。”[12]118不知何据。韦述言“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所谓“店”“肆”者,已见前文。细究文意,“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此处之“行”应作“同业集聚区”解。又《两京新记》此段行文,“店”“肆”“行”三者俱在。韦述谙熟唐都掌故,不会不知此三者之异同,其在此处用“大衣行”应足为今人所采信。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乾馔子》之“窦乂”条,言唐德宗建中年间长安巨富窦乂事:“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汙之地……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棚子。……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17]1877由行文的层次与逻辑观之,“行”自是与“店”“铺”相区分。这里的“秤行”当指集聚众多相关店铺的街区。再如《太平广记》卷一五七引《逸史》之“李君”条,记李君得仙人三书相赠之事。李君启第一封书有富贵,后“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17]1130。去处为“鞦辔行头”,而此同业店铺集聚区“行”之“头”乃是一家酒楼。《玄怪录》卷三“吴全素”条,记吴全素被地府判官错判后回到阳间前在地府一游事,其中便描绘了鬼吏及其登门捉人投胎的情景:“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诵经,香烟满户。”[18]400此与前揭“李君”条同理,都说明了唐代的“行”主要指同业店铺集聚区,是“市”下之重要单位。
或因彼时名称尚未固定,唐代史料中“肆”与“市”实际也可泛指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如唐传奇名篇《李娃传》中郑生流落之“凶肆”:“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馀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17]3987-3988这里的“肆”显然非前揭王仲荦先生言“市里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铺子”。所谓“凶肆”,其实是唐代长安丧葬业店铺集聚之“凶行”。沦为乞儿的郑生与李娃重逢之后,“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17]3987-3988。所谓“坟典之肆”,所指当然是长安市内售卖书籍的同业店铺集聚之“书行”,今人则多称其为“书市”。与《李娃传》同出自白行简手笔的《记梦》言:“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得名。”[19]7102如果“帛肆”仅为一家店铺,姓张之人显然无以“贩粥求利”。“帛肆”所指当为“帛行”,即售帛店铺的集聚区。
又《柳宗元集》卷一七《宋清传》云:“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20]471-472依唐制,文中“长安西部”应是“长安西市”。从“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看,采药之人优先将“善药”卖给宋清,此“药市”应是具有开放性的同业市场,即“西市”之下药店同业集聚的“药肆”。“市人以其异,皆笑之”,便是同业之人对宋清的排挤。作为泛指的“市”“行”和“肆”有时混用,当加以留意。
二 “行头”与“肆长”
如上文所述,唐代市下的“行”,指同业店铺的集聚区,是严格的市制下人为规划而成的单位。而作为同业组织的“行”,一般认为系唐中期以后由其衍生而出。傅筑夫先生言:“行既是工商各业的总称,而工商业者的组织不论是临时的还是常设的,事实上又只能按照共同行业来形成,所以行又很自然地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名称。”[21]402唐代,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和作为同业组织的“行”,都是在同业的基础上形成,同业之首“行头”(又称“行首”)受官府管控。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的“行”,是唐代官府为方便市场管理而设;作为同业组织的“行”,则是同业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关于唐代同业店铺集聚区“行”如何衍生出同业组织“行”,加藤繁先生认为:
同业商店集聚在同一个地方,结果,自然就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大约先发生共同祭祀神佛的事情,更进一步的,为营业的方便多少互利共协。而等到市的制度崩溃,同业商人的业务独占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同业商人就团结起来,要维护他们的特权,于是,行就成为了有力的组织,代替了市的制度,而成为维护特权的屏障。[1]358
加藤繁先生之论高屋建瓴,其将唐宋的“行”谓为“同业组织”的处理方式尤为精辟。唐前期坊市制度已有松动迹象,《唐会要》载:“景龙元年十一月敕……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14]158发布此等敕令,意味着在诸行内已有人挑战原本严格的市场规划。中唐以后,突破坊市制度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22]。这种背景下,唐代作为同业组织又具有行会特征的“行”开始出现。究其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则可将“行头”作为观察的切入点。
唐初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六“肆长”条记:“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按照唐人的理解:“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10]540又《唐六典》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23]543唐代前期设有市令、丞等官吏专门管理市场,彼时“行头”仅是市下各“行”的小头目。与前文所论“行”和“肆”有时混用一样,“行头”与“肆长”在唐代语境之下同样如此。前揭唐传奇《李娃传》中,东西二“凶肆”各有“肆长”,实际应为“凶行”之“行头”。二肆长“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于是“邀立符契,署以保证”之后,“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17]3987-3988。所谓“天门街”,所指当为长安城中轴线之朱雀门大街。经过东西二市之“肆长”商议,便可借用“天门街”场地举办竞赛性的大型商业展示活动。即便这仅为彼时小说家言,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唐代坊市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此事决于两名“肆长”之议,再由里胥经贼曹一路上报至京兆尹。掌管长安地方事务的京兆尹只是被动批准,事先并无所闻,更未参与相关工作。有学者就此指出,市场是唐代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机构之一部分,因此设有管理市场的官吏;虽受到中央集权的支配,市场还是有市人自主的活动空间,行政机构也承认市场的部分独立性[24]。在这场东西两市“凶肆”(或曰“凶行”)的较量之中,市场的部分独立性正是由两名“肆长”(或曰“行头”)来承担,其作为同业组织首领的色彩已颇为鲜明。
同样有学者注意到,唐代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北市丝行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南市香行社”,造像时间均在七世纪末的唐前期[25]。唐代佛教大兴,造像风气盛极一时。而平民百姓受财力所限,无法独立完成造像,众人合作“共舍身资”,便成为广大佛教信徒普遍采取的方式[26]。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有诸“行”,说明市人已经以“行”为单位集体进行此类宗教造像活动。但题记中所见主持造像活动者,仍是“社官”“邑正”之类基层社会组织首领,尚不见同业之“行头”“肆长”出面。尽管如此,这样的宗教造像活动应对同业组织“行”的成型与发展有所推动。正如陈宝良先生所指出的,商业社团与民间的宗教社团关系非浅[27]215-216。
《太平广记》卷二八〇引《纂异记》之“刘景复”条:“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绢画美人捧胡琴以从。”[17]2235-2236这则史料展现了中晚唐江南社会的面貌。“行首”即“行头”,彼时苏州吴泰伯庙祈福这样的宗教活动由“金银行首纠合其徒”共同参与。唐前期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主持本“行”造像活动者尚为“社老”“社官”,而中晚唐的江南,“市肆皆率其党”祈福于苏州吴泰伯庙,扮演本“行”组织者角色的已是“行首”“行头”。从中清晰可见,作为同业店铺集聚区乃至同业组织的“行”,其力量正逐渐增强。
三 作为同业组织的“行”
“行”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旧唐书·食货志》载:“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当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行人。”[28]2124-2125姜伯勤先生认为,唐宋时期“行人”是属于城市中一定行业的工商人户,并且逐渐成为加入一定同业组织“行会”的工商人户之名称[29]。此处“行人”应为专卖米粮的工商人户,甚至是同业组织“米麦行”的成员。同业集聚区“行”虽已衍生出同业组织“行”,但同业组织“行”的力量尚有限,“行头”角色地位尚不甚重要。中唐时官府对市场仍可采取直接管理,“每石量付两市行人”,并不经过“行头”。
“行头”在官府对市场的调控管理中虽不甚重要,但地位显然在不断上升。《旧唐书·食货志》载:“(元和)四年闰三月……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28]2102此时“行头”已是同业店铺集聚区乃至同业商人的代表或负责人,向官府承担义务。从“行头”的身份地位观之,中晚唐作为同业组织的“行”已发展至一定程度,初具后世行会的雏形,尽管依旧处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
及至宋代,《梦粱录》卷十六“米铺”条记杭州人烟稠密,遍地米商,“且言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30]149。与唐代中期官府直接管理市场、平抑米价大相径庭,宋代已是由一行之首的“行头”统一掌握本“行”(即本同业组织)的经营活动,负责为本行接洽生意、决定价格。又《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条云:“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31]338由唐至宋,“行头”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强化。从“行头”地位和作用的强化中,能较为清晰地看到“行”的发展。再就具有行会特征的同业组织“行”本身而言,《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卢氏杂说》之“织锦人”条: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綵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17]2005
出身织锦人家者,因“如今花样,与前不同”而遭“本行”拒绝接纳。王仲荦先生认为这里的“行”为组织之行,“行家”犹今言“内行”[9]424。事实上,无论此则史料中“本行”是“行业”还是作为同业组织的“行”,两者并不矛盾。李姓人前属“织宫锦巧儿”,其“伎俩”“花样”无疑优秀。“本行”却皆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他,表明彼时应已存在一个团结众多同业店铺、对本行业产品实施统一章程的“行”。该“行”排斥外来竞争,保护同业利益,显然具有同业组织的特质。“行”中掌握一定话语权的“行家”,正是李姓人诗中嘲讽的对象。前揭嘲笑宋清之“药市”,应亦属此类。姜伯勤先生以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押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为例,通过考证该文献中“画行”的上下尊卑关系,证明了沙洲行会制度的存在[29]。实际上,这种尊卑关系更表明同业组织“行”彼时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此种发展并非曹氏归义军对应的五代时期可以一蹴而就的,从侧面印证了同业组织“行”在唐代的出现与发展。
四 结语
唐代的“行”作为同业店铺聚集区,在唐代语境中虽亦用于泛指,但基本可以明确为“市”之下、“肆”以上的单位。自唐代史料可知,“行”乃是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结构中承上启下的一环,不可或缺。唐代前期,“行”仍是官府划定的商业聚集形态。及至中晚唐,作为一行之首的“行头”地位上升,并得到官府认可,同时,“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同业组织方向发展的趋势。王仲荦先生认为:
行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唐代的手工业商业确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生产发展不充分,如海外贸易受到限制,国内市场比较狭小等等,因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激烈。他们不得不利用行之一组织来保护自己,防止同行的竞争,并排斥外来的竞争。……另一方面,在当时封建制度还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势力还极其微弱,封建统治者往往利用行这一组织,来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勒索和压榨。……这就点明了行是封建统治者剥削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一种工具。[9]381
王仲荦先生识见弘深。无论是同业店铺集聚区“行”,还是同业组织“行”,都具有双重性:一是工商业发展之产物,一是封建制度之附庸。不过,同业组织“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体现出彼时市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官府划定的同业店铺集聚区“行”并不相同。“行”在唐代的发展相对缓慢,且始终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但“行”经过在唐代的缓慢发展,摆脱了部分束缚,建构起了同业组织的内涵,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此意义之下,可以将唐代“行”的变化发展放置在历史转型的宏观语境中考察,这同样为研究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