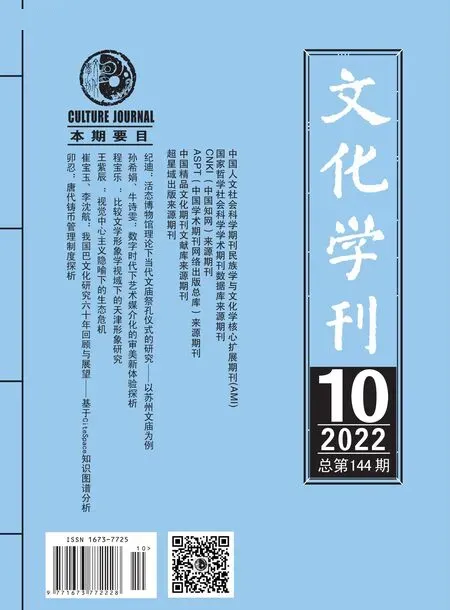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向 娇
约翰·贝尔德·克里考特(John Baird Callicott)(1941)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多年来,克里考特一直致力于环境伦理领域的研究,出版了诸多环境伦理学著作,并担任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会长。其研究成果一直处于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前沿,他于197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独立的环境伦理课程,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有史可查的最早的环境伦理学课程。克里考特的重要学术成就是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提供较为严格的哲学论证,并据此拓展出一种关于“地球伦理”的独特理论。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的提炼及研究,试图激发学界对克里考特本人及其思想的关注,进而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素材,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拓宽视野。
一、国外学者对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
针对国外环境哲学界关于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核心理论的讨论,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大地伦理的思想基础、自然的内在价值、形而上学和元伦理学。
关于大地伦理的思想基础,克里考特从一种全新的伦理学视角出发,运用生物进化论、生态学以及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理论为环境伦理提供哲学论证。有学者认为克里考特对道德情感理论的论述有失偏颇。欧内斯特·帕特里奇[1](Ernest Partridge)分析了休谟对道德情感的论述,认为休谟的道德情感源于人际关系,是一种对人的态度,并不能成为环境伦理的基础。相反,他认为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会强化人类中心主义,不能论证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学家罗伯特·麦金托什(Robert McIntosh)将焦点转移到了大地伦理在现代生态科学中的基础上。麦金托什声称:“如果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不明确,那么它作为环境伦理基础的论据就不明确[2]。”
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研究,克里考特把自然内在价值作为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认为它是完整的环境哲学所必需的。他明确表示,将自然的“工具价值”提升为“内在价值”是合理的环境伦理的必要条件[3]。克里考特的论述引起了其他思想家的批判。温迪·唐纳[4](Wendy Donner)批评了克里考特的现代主义内在价值理论,认为该理论无法“得出生态系统和物种具有内在价值的结论”。他将有意识的价值评价者作为内在价值的主要评估者。同时代的霍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同意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他分析了克里考特对内在价值的论述,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来自有意识的评价主体。罗尔斯顿对内在价值的解释是比较客观的: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独立于评价主体而存在。在克莱尔·帕尔默(Clare Palmer)看来,克里考特只是选择了一个最符合他自己道德观的自然价值理论,这使他的观点更具意识形态性而非哲学性。
在克里考特的著作中,形而上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认为大地伦理需要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而科学能够塑造并影响人们世界观的建立。科学具有形而上学的含义,即通过将科学观点阐述为一种范式不仅可以理解自然界,还可以理解人类社会的关系,从而渗透到人类文化中,将这种范式转变为世界观。因此,克里考特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一种从古典机械论物理学发展而来的世界观。凯瑟琳·拉雷尔[5](Catherine Larrère)考察了克里考特从科学中衍生出的形而上学和伦理概念,并将其思想与法国新兴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具体而言,拉雷尔指出了克里考特所说的“生态学的形而上学含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科学“蕴含”本体论;第二,“自然哲学能够囊括道德哲学”。在第一点中,她同意克里考特的观点,认为他的方法比一些后结构主义者的方法更有建设性。但她反驳了克里考特的道德哲学从属于自然哲学的观点,声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模式,即我们可以赋予道德哲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于是尤金·哈格洛夫(Eugene Hargrove)提出了折中的观点。他反对环境伦理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认为环境哲学家应该坚持“描述的”形而上学(描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避免“修正的”形而上学(试图发展一种更好的思考世界的方式)。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环境伦理确认了对几种实体的道德义务——个人、物种、生态系统、生物群落。许多环境哲学家认为我们需要多种道德原则来解释和确定我们的道德义务,即道德多元主义。克里考特反对道德多元主义。早期,他将利奥波德的原则解释为凌驾一切的道德准则。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我们不得不牺牲生命来保护环境。在后来的著作中,克里考特倡导将几种原则或美德统一在一种道德哲学中。他坚决反对道德多元主义,即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诉诸一种道德原则,在另一个问题上诉诸另一种道德原则。这种多元主义将导致“人际关系的矛盾和自我矛盾”[6]。彼得·温兹[7](Peter Wenz)对克里考特反对“极端”多元主义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任何不能为每个道德问题提供单一公式化解决方案的理论都是“最低限度的多元化”,但他不同意克里考特摒弃这种多元化的观点,原因在于,没有任何道德理论(包括克里考特的理论)能为我们所有的道德困境提供单一、明确的答案。折中的多元主义依然存在。温茨既为其辩护,又声称克里考特的理论也是类似的多元主义,因为克里考特在一个单一的理论中支持了多种原则,可见这两位思想家仍然存在分歧。
克里考特所阐释与发展的大地伦理对理解人类与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他的思想显示出一定的争议性,其争议点在于道德情感理论以及道德一元主义的论述。但克里考特对环境伦理学所做的贡献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他的研究在许多环境哲学论述中也被明确地引用。虽然国外的学者对克里考特思想的研究取得一些成就,但在环境伦理的实践指向以及与当代社会现状的结合、深度和广度研究等方面仍然有很大不足,且就其环境伦理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仍然较为缺乏。
二、国内学者关于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
纵观国内学者对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大地伦理的生态学基础、大地伦理的整体主义理论、大地伦理中的“事实—价值”问题、大地伦理的美学内涵、自然的内在价值等。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生态学事实向伦理价值的转变;二是整体主义的伦理意蕴。哲学上把这两个问题分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和“生态整体的本质”。因此,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学给予了新的哲学阐释。鉴于大地伦理的广泛影响,克里考特与各种文化实践相联系,对大地伦理进行了深入探讨。而思想家们也从一个广泛的理论角度出发,对克里考特的环境理论做出了种种探究。目前存在的主要观点是:克里考特修正了自然主义谬误,填平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逻辑鸿沟[8]。他的解释模型,即休谟—达尔文—利奥波德表述模式。同时,他还从大地伦理的科学基础出发,进一步对整体主义进行了阐释。另外,有学者从克里考特与大地伦理学的理论渊源着手,概述了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学的捍卫与发展及其伦理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9],并探讨了大地伦理的生态学基础、大地伦理论证中的休谟问题,以及大地伦理的生态学论证及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辩护等问题,有力地阐明了克里考特对解释与发展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所做的努力[10]。余怀龙详细阐释了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的论证过程。在借助 “大地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概念为环境伦理奠定根基后,克里考特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自然内在价值论,阐释了一个与生态学、新物理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相适应的环境伦理。这样,生态学为环境伦理提供了“生态共同体”概念,而新物理学为环境伦理提供了超越主客二分的内在价值。
克里考特把伦理整体主义视作完全合理的生态理论引起了学界的质疑。在面对整体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诘难时,王国聘《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一文中写道:“关于大地伦理学整体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克里考特一方面论证了整体主义,另一方面回答了对它的诘难。”有学者对克里考特的类型学与二阶原则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大地伦理与仁慈的道德主义、伦理的人道主义三者之间关系,通过二阶原则补充了整体主义的一阶原则,有力地捍卫了大地伦理,揭示了大地伦理不是环境法西斯主义,使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获得合理性辩护。应该说,伦理整体主义改变了人类的环境理念。整体主义的伦理观把地球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类不过是地球这个生态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其中心或主宰。因此,人类必须善待地球,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和平共处。伦理整体主义彻底改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大地伦理可应用于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其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环境时,尽可能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多样性、完整性、稳定性。
关于自然内在价值,克里考特把它的概念视作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表示以自然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生态自然主义对于环境哲学的完整性是不可少的。由此,国内学者详细分析并论述了克里考特从对自然主义内在价值论的整体批评出发,以“价值人类生成论”和量子物理学对主客二分的消弭这两种理论为基础,所提出的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立的自然内在价值学说。同时澄清克里考特和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学说仅存在具体理论发展路径上的差异,不存在根本的理论动机和目标上的差异,因此不能视之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学者指出,罗尔斯顿和克里考特对美国的荒野观和荒野保护路线有不同的看法。罗尔斯顿捍卫美国既存的“无人”荒野观,主张荒野保存;克里考特批判美国既存的“无人”荒野观,主张建立生物多样性保留区。实际上,克里考特的生物多样性保留区虽解决了对印第安人的环境正义问题,但易导致对环境的影响与破坏。而罗尔斯顿揭示了环境正义的根源,即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只要在荒野保存中坚持生存原则,尊重文化差异和环境权利原则、公正原则(含补偿正义原则),就能在保护荒野的同时实现环境正义。针对罗尔斯顿与克里考特自然内在价值的比较,我们认识到,“荒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自然维度意义上,同时也突出在生态伦理层面上的重新评估,遵循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更是目前人类应倡导的道德义务。”对二者的荒野论争进行反思,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环境正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克里考特的环境伦理思想具备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关于针对当前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局面,在伦理层面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解决。研究克里考特的环境伦理思想可能会为我们提供路径或启发。
三、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研究的总结性分析
克里考特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他的研究工作在许多环境哲学论述中被明确地引用,但他的思想也显示出一定的争议性。以怀疑态度对待克里考特环境哲学思想的学者不胜枚举,争议点在于道德情感理论以及道德一元主义的论述。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中国目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也面临一些和西方国家类似的自然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不分国家和种族,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因此,研究克里考特环境伦理思想对环境哲学的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均具有重要意义。